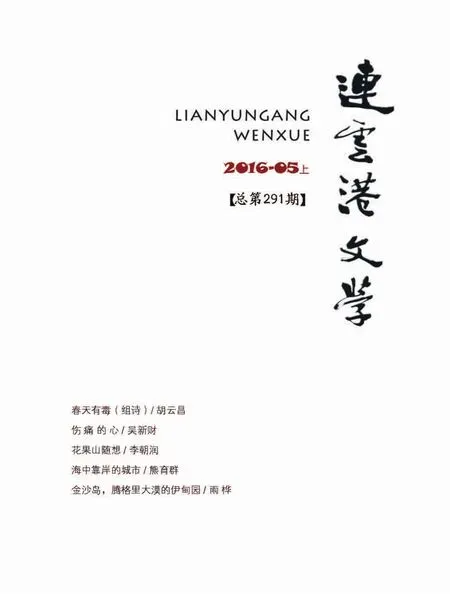疼
殷俊/江蘇
?
疼
殷俊/江蘇
(一)
疼,是我們的糖。
當我們春風得意趾高氣揚之時,唯有它讓我們對這個世界俯首稱臣。
安寧與幸福被長久擁有之時,經常會發現這安逸的日子太需要什么來刺痛一下。如同一個人在長久的孤獨里會有一種靈魂脫殼的感覺,你搞不清自己是活著還是死去。活著,是孤獨的存在;死去,使一個人的塵世陷入永遠的寂靜。人間遼闊,卻偏向暗處尋得幽香與疼。
比如如今的歲月里,我遭遇的一切剛好可以用“安寧”來形容,樓下的植被綠得正好,太陽從我的窗口舒緩地升起。我的前面左右充滿親人的溫暖,且我們之間的距離恰到好處。但我仍然時不時想要將這“剛剛好”的狀態做不合時宜的調整,讓自己處在一種稍不自在的狀態中。
于是,疼應運而生。
(二)
萬物沉默的夜晚,窗外的夜燈在蒼茫夜色中恍惚著。十點多的房間,恰是安靜。隔了一層玻璃的塵世體現出萬物共生的和諧。若不是頸部的疼隱隱約約傳來,我幾乎快相信了這生活賜予的美意。
此刻,它就這樣以柔軟而堅持的決心向我提醒它的存在,提醒著今日的禍端完全得益于以往的濫用和疏忽。雖然這樣的疼絕不會要了我的命,卻以足夠的促狹將我的注意力集中到這該死的痛感上。在這持之以恒的惡作劇般的疼痛中,我不得不對以往的怠慢產生愧疚之心。
每當痛感襲來,總抓心撓肺地表示一定“聽話”,然而痛感一過,死性不改。當我在滿樹的泡桐花下站立,以充沛的激情仰望那些紫白的夢想;當斑駁的樹影和花影相得益彰,塵世向我袒露出最初的美好,我從不覺得我需要約束些什么。沒有一朵花釋放出的不是最初的誠意,我的幸福感也是。
令我恥辱的痛感,也是。
“夠加大,才會道歉;但只有更強大,才會原諒。”顯然,這頸椎病是個心胸狹隘的家伙。
(三)
小時候,經常磕著碰著,流血受傷是家常便飯。似乎童年有多長,疼痛便有多長。
比如說,將訂書釘訂進食指、腳心戳上鐵釘、膝蓋磕傷一月未愈、將腳塞進正在行駛中的車輪、唯一的一次打架經歷卻被倆姐弟抓得滿臉血痕……哇,實在是太多了。
但,真正是好了傷疤忘了疼,我從不把這些教訓銘記得有多深刻。來自于身體上的疼痛似乎很少真正警醒過我。相反那些一茬接一茬的熱愛,如園子里生生不息的韭菜苗,刺激著我為之付出更多的傷痛,并在所不惜。
在家人和鄉鄰的印象中,我實在是個很乖很懂事的孩子。只有我知道:我的骨子里其實有多么任性與叛逆。
但我把這一切,藏得很深,如同藏著那唯一一次令我刻骨銘心的疼。
十歲那年的暑假,雨后初晴,小路被車壓出高低不平的車轍,剛學會騎車的我心花怒放狂飆車技。一輛拖拉機從對面開過來沖正在路心的我狂按喇叭。一時心急,連人帶車摔倒在地,車壓在左胳膊肘上,一陣劇烈的痛感瞬間令我大汗淋漓不能自持。
在此之前與之后,我就是一個很能哭的孩子,常常要為一點點的小事哭到斷氣;但是這一次明明已經疼到要死,我卻只是將淚含著——也許是覺得哭也沒人聽吧。我彎曲左臂,獨用一條右手將那輛極高極大的自行車從地上推起回到了家。
一路上,一些人從我身邊經過,小孩子的笑聲響得要蓋過麥子成熟的歡呼,中午的太陽熱火朝天地曬著,不時有相識的人從我身邊經過并奇怪地看著我的表情。
此刻,我正以一種別人不能覺察的痛苦無聲亦無淚地哭著,用一種極其難看的表情哭——如果我能看到的話。在我十年的有限經歷中從未遭受過比碗口更大的疼痛。那是一種什么樣的疼啊,就如把天空挖個洞,讓那些原來很舒緩的藍色的血液滴落下來,而周圍的藍也跟著一點點地塌陷;或者說似乎向我交出疼痛的部分已經不存在了,我無法判斷要咬緊牙關挺著還是直接躺在路邊死掉,我無力判斷哪種選擇會令自己稍微好過一些。
一直到晚上,我才在覺察出異樣的媽媽再三的追問中,道出了實情。
第二天去醫院,診斷結果為肘部骨折。
多少次我為無關緊要的人和事疼著,唯獨這一次,我把刻進骨頭刻進記憶的疼,獻給了自己。
(四)
我是極其怕血的。
那紅色的液體,哪怕只是沁出來一滴,也令我感到四肢發麻并伴隨隱約的眩暈感。這樣的后果,來自于一次特殊的經歷。
同樣是十歲那年,曾和弟弟一起把我的臉抓傷的海燕的爸爸,在一場禍事中雙腿被齊齊碾斷。
且說當時的我被人群推著擠著,時而向前時而被擠到邊緣。自虐般的好奇心和恐懼感使我獲得一種變態的欲望,想一探傷者究竟。小個子的我總算擠到了前面,我捂著眼睛、卻又忍不住讓目光透過指縫,就在那一瞬間,我看到垂死的男人、被截斷的大腿、血流成河的慘狀。我的一顆心劇烈地跳著,身體內的每一個細胞都在急速的痙攣中重生并破滅。一種巨大的惡心與眩暈感襲擊了我,使我全身癱軟搖搖欲墜。
并且,我是真的癱倒在地。當我發現血色河流正在我倒下的地方蔓延,如見鬼般的嚎哭起來……
至此,那條紅色的河流,正式成為我的夢魘。
直到現在,我依然不明白:那些血是如何從鮮活的肉體中汩汩流出、并退為一具蒼白沒有痛感的存在。他靜靜地躺著,卻把這種痛感完完全全地轉交給了他的妻子和一雙兒女、一對年邁父母,以及圍觀的人們——那一天,他的家人無數次在劇痛中昏死過去。
最疼的時候,并不一定來自于肉身,而在有感知的靈魂,然而它們在現實生活中并不一定歸于一體。
是愛,讓人們深刻地疼著。
(五)
生活的歷程有多長,疼痛便會陪伴多長。有可能它會在某一時段暫時抽離,但永遠不會徹底消失。
在我看來,沒有疼痛的人生,比沒有幸福更殘缺。且戀愛時光,疼總比幸福感更勝一籌。
常常在無邊的黑夜中,校園的紫藤還在轟轟烈烈地開著,那些前一秒緊緊擁抱的戀人、已在下一秒道了再見。彼時,我正經歷著人生的初戀,且不能判斷是否能修成正果。我是如此愛他,卻總是拿不準對方的感受,于是疼便如影隨形。敏感的內心往往如白蟻噬心,醞釀豐滿的情緒如飽滿的水滴紛紛墜落。這一刻肉體是完整的,然而痛感卻明明白白地傳輸到了每一根神經,每一個細胞都獲得了最大限度的飽和。
我無限地害怕黑夜。童年時的黑夜給我的是恐懼和不安全感,戀愛時的黑夜同樣如此,它讓我絲毫不能忍受黑暗星空下的任何一點痛楚。要么相擁,要么結束,唯有它們方能將疼痛暫時拋棄。
然而天亮后,我再次從疼痛中活了過來。窗外,天正空著,白云不知去向,我愛著的男人如陽光一樣走來。
(六)
昨晚,給媽媽洗澡。
第一次在這么狹小的空間里赤裸相對,彼此很有些不適應。
想起年幼的時光里,夜夜抱著她的脖子入睡,那時的我們如此坦然。如今的她已真正老去,身體上的病痛日漸嚴重,必須借助我的力量,她才能完成一次徹底的清洗。
那么愛干凈的老人!在所有的記憶中,我從沒有聞到她的身上有任何的難聞氣息。每個傍晚,她一身汗地回到家中,總要用水一遍遍將自己洗好。
留在記憶中的香皂味道,也成了她的一部分。
此刻,水從她的頭頂淋下,我輕輕搓著她綿軟而稀疏的頭發。在我的手下,是一塊塊沉睡了六十多年的傷疤。我的手指從其上輕輕摸過,如同摸著一個個陳舊的夢魘。彼時兩三歲的她尚記不起滿頭害瘡流膿帶來的刻骨疼痛,是來自于我的大姨——她的大姐多次的描述使她重新擁有這段往事。然而她每一次的轉述,卻似乎走進的是別人的故事,只不過把傷留在自己的身體里。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她已完全不記得那段疼過的日子,那種痛感早已被她留給了六十多年前那個可憐的孩子。
但是作為反復傾聽這段往事的我,卻反復被這樣的疼痛硌著,坐立不安——從七八歲的我、十幾歲的我、開始在婚姻中行走的我、有了孩子的我,直至現在。當溫暖的水一遍遍從無知無覺的傷疤淋過,我感覺它們將早已被主人遺忘的疼、連接到了我的心臟。
是的,我穿越六十多年的歲月,把她疼過的、又認真地疼了一遍。
她顯然通過我反復的撫摸與目光覺察到了我的心境,她說:
只要害不死,就算撿回了一條命。
(七)
對于這個世界,我們從來記不清它給過我們多少好處,卻深深記得那些曾被深深淺淺跋涉過的疼。
因為它的存在,我們開始相信——這低過塵埃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