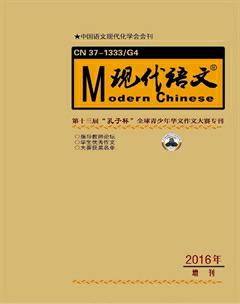京胡老人
王佳寧
老李每次下班回家都會在街邊碰見那拉京胡的大爺。
過時的深藍色中山裝,洗得有些發白卻一塵不染,花白的頭發梳得整齊,拿只小凳,端端正正地坐著。
那把京胡也有些年歲了,白膠帶纏了一圈又一圈,活像具木乃伊,又被塑料袋裹得嚴實,好像生怕被別人搶了去。
老李并不知道大爺什么時候開始出現在街邊的。也許是一月前,也許他一直都在只是老李沒有注意過。實際上,老李哪有心情注意這個啊,在單位里被領導訓,回家還得挨媳婦罵,心里有苦說不出。
這天趕上媳婦過生日,老李提著大包小包著急忙慌往家走。路過街邊,沒有聽到熟悉的“咿咿呀呀”聲,反而是一陣吵嚷。老李湊上前去看,哎呀不得了了,這大爺和一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吵起來了。只見那外國人無奈站在一旁,大爺面紅耳赤地扯著嗓子喊:“你把我當什么人了?別以為你們外國佬有錢就到處送,我拉京胡我高興,我兒子每月給我的錢我都花不了,你這小兔崽子還……”老李這才注意到大爺鞋底下還踩了兩張紅票子。罵完了,大爺還不解氣,又往錢上踹了兩腳。
那外國人不會說中文,忙著打手勢和周圍人解釋。也有人看明白了這回事,小聲地和旁人議論著該如何處理。一邊是外國友人,一邊是花甲老人,得罪誰都不是件道德事兒。還沒等他們商量完呢,人群里鉆出來一愣頭青。
“老頭兒,我告訴你,人家給你錢是給你面子。我在這聽了好幾天差點沒聽吐了。”
“胡說什么,這是京劇,是國粹!”大爺更生氣了,胡子跟著身子一起顫。
“什么國粹,現在誰還聽這老掉牙,小心我去告你擾民,你還得賠我精神損失費呢!”愣頭青倒是一臉笑嘻嘻。
大爺突然呆住了,緩緩地坐下,低下頭不再說話,手里不住地撫摸著那把歷經滄桑的京胡。眾人也沒了看戲的勁頭,作鳥獸散。愣頭青撿起地上的錢揚長而去。那傻站的外國人臉上的表情從無奈變成了驚愕。
老李嘆了一口氣,想去安慰下大爺,又怕回家晚了挨罵,只好拍拍那外國友人的肩膀,示意他離開。留下大爺一人像個犯錯的孩子。
第二天,大爺沒有出現。第三天、第四天,老李都沒看到大爺。直到半個月后。
那天老李剛漲了工資,心里樂呵呵的。轉過路口便看到了大爺。衣服沒變,位置沒變,但好像背駝了許多。拿出京胡,大爺試了一遍又一遍弦,卻并不準備彈奏。
“哎,大爺,老長時間沒見您了啊!”老李朝大爺打了個招呼。
“病嘍!也不知怎的,就生病了,爬層樓還得喘三喘,真是一把老骨頭了!”大爺抬起頭看了看老李,又低頭把京胡裝進袋子里,欲起身離開。
“大爺,怎么不拉上一曲,這么長時間沒聽見這聲音還挺想念呢!”
大爺猛抬起頭,連說話聲里都帶著驚訝:“真的?我可以嗎?你們不嫌難聽,不嫌吵?”
原來,大爺還在意那件事!
老李連連擺手,“不會不會,別理那毛小子說的話。”說到這兒,老李頓了頓,聲音突然降了八度:“那天,我也在場。”
“那好,我就給你來一曲!”大爺立刻恢復了往日的神采。
一曲作罷,老李發現那胡柄上有不少裂紋,音色也不夠響亮了,忍不住去摸了摸。
大爺明了老李的疑惑,開口說道:“它啊,跟我50多年了。年輕的時候我是縣話劇團的,也算學了一門手藝,誰料碰上文革,憑這個不能養家糊口。后來成家有了兒子,便想法賺錢,就把它撂在一旁了。前幾年收拾東西又翻了出來,看見它啊,就忘不了過去了!”
老李聽著聽著,仿佛看到小時候的自己在麥場上放風箏,又仿佛聽到母親喊自己乳名。
“后來兒子有出息了,把我接到城里,要給我換把新京胡。我說:‘不行啊,時間一久都有感情了,舍不得再換!再后來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孫子。我知道兒子和媳婦吵架是因為我在家拉京胡太吵,兒媳婦不樂意聽,還怕我嚇著孫子。我也不想為難我兒子,這不就出來了嘛!唉,現在這些小年青怎么就討厭京劇呢?”大爺低頭沉思著,半晌,又說了一句話:“老伴走得早,能陪我的只有它了。”
一滴渾濁的老淚悄悄地流到地下。
老李張了張嘴,想要說些什么,卻發覺自己的安慰也是蒼白無力。
幾年后,老李升了職,舉家遷往外地。
期間,老李打聽過大爺的生活狀況。最后一次是聽說大爺已經去世了。京胡和大爺一起進了火葬廠。
(指導教師:蔣玲玲 評委:賈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