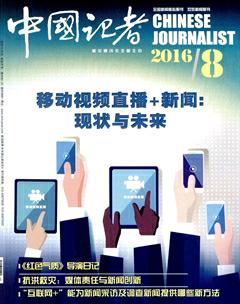攝影記者如何開拓思維,出新、出奇?
邵全海
內容提要 任何個體都很難定義為這個時代最優秀的攝影記者,但他們對新聞攝影的熱愛始終如一。正是這份愛,給他們帶來可觀的成績。紙媒下滑時,當我們在浮躁功利地談論跳槽、逃離的日寸候,他們身上有一種繼續向前、不斷創新的執著。這是本文作者的親歷感悟。
關鍵詞 攝影創新 攝影記者的職業觀
2016年6月初,2015年度“趙超構新聞獎”(攝影類)評選結果揭曉。我憑借攝影作品《錢江大潮中:最后一個撤離的特勤》獲得攝影類一等獎。
獲獎后,回望這幾年,在日常新聞、突發新聞方面,“海量”的“公民記者”屢屢搶奪紙媒攝影記者的陣地,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也是對傳統攝影記者的考驗。但我認為,有創新精神的攝影記者無法被淘汰,震撼人心的好照片不會被淹沒。
拒絕跟風:發掘老題材中的新主題
年年歲歲潮相近,歲歲年年人不同。每年,錢江大潮都如期而至,但大部分照片集中表現大潮中人仰馬翻的主題。老題材如何出新?我一直在思考、觀察、等待。
2015年9月28日,我像往年一樣來杭州九溪觀潮點拍攝。那一天,我捕捉到了潮水沖上堤壩,觀潮人群瘋狂跑動的情景,但這個“不錯的畫面”仍然人云亦云。如何避免跟風?我不斷地盤算如何取景:用長焦壓縮景深,照片場面小,背景模糊;用魚眼鏡頭拍攝,照片雖然場面大,但又“雜”;抬高拍攝視角,例如用航拍器從空中鳥瞰,畫面中潮水和人太小,效果不理想……
經反復比較,我認為用中焦鏡頭接近潮水和人群,拉近拍攝距離,才能較好地強調視覺震撼力。但僅提高鏡頭表現力,依然無法跳出“潮水來到人沖倒”的老思路。這時,我下決心更換拍攝主題:尋找有個性、別人沒有拍攝過的畫面,擺脫攝影創新只停留在更換攝影技術的層面。我從宏觀入手,精心挑選適合現場且能出奇制勝的主題。絞盡腦汁的過程中,我忽然靈光一閃:潮水即將沖上堤壩時,特勤人員冒著危險勸說觀潮客離開危險區域,這就是我想要的主題!至此,我心中有了底,獲獎照片也因此產生。照片發表后,獲得讀者和專家的好評,媒體傳播也收效頗佳。騰訊網、路透社、視覺中國等媒體紛紛轉載。
我認為,一個老題材若要在前人基礎上出新,不僅要在鏡頭的表現力上做選擇,更要動腦筋做宏觀思考,只有這樣,才能常拍常新,與眾不同。獨特的視覺沖擊力要服務作品的新聞性和主題,做到主題和畫面形成合力,震撼人心。
靠近,靠近,再靠近!
數碼相機的普及為廣大攝影人群提供極大的方便,但新聞攝影絕不是唯器材、唯技術的競爭,我認為,記者到“新聞最近點”去拍攝的理念依然值得堅守。
2015年9月29目,在臺風影響下,攜風雨而來的錢江大潮呼嘯而至,翻過堤壩,數米高的浪潮沖過多道防潮設施,橫掃之江路雙向車道,快速拍擊對面約60米遠的山邊,令游客猝不及防,許多行人被沖翻在地。
我的拍攝點扎在大潮的“最前線”。潮水即將沖上來時,特勤們正在一遍遍地勸導在危險區域內不愿離開的觀潮人群。頃刻間,最后一位特勤還沒翻過第二道防線撤離時,兇猛沖上岸的回頭潮鋪天蓋地而來。我同樣來不及撤離,心想“完了”!雨聲、潮聲、嘶喊聲交織在一起。我一咬牙,背身護住相機,盤在欄桿上不逃跑。事后證明,沒跳下欄桿逃跑是明智的選擇。如果跳到一片汪洋“大海”中,人將被一浪連一浪的回頭大潮沖倒,面對地面上的鐵欄桿,相當危險。
當第一個回頭潮過去時,我抬起頭,正好看見前方幾米處的欄桿上,那位無法撤離的特勤也緊緊地抱住欄桿。這時,另一個回頭潮又迅猛地沖過來。我不顧危險,左手緊緊地抓住欄桿,右手端起用塑料袋包好的相機,露出鏡頭,對著這名彎腰死死抓住欄桿的特勤,連續按下快門,記錄下這位因保游客安全而無法撤離的敬業特勤。驚心動魄的畫面烘托了最美特勤的主題。事后,《今日早報》以這幅圖片為線索,展開《觀潮守護者,你在哪里?》的連續報道,最終找到了這位好特勤。
攝影記者要有精品意識和使命感
如果說“大事”是優秀新聞作品的產生基礎,那么“精品”就是評判記者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準。
2012年4月1日,國內第一家專門從事入殮服務工作的機構——天泉佳境禮體服務中心開業。服務中心有職業入殮師9人,3男6女,全是90后。我立即聚焦“嘉興來了中國大陸首批90后入殮師”。
面對入殮師這一與眾不同的新職業,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看法。做這組報道,如何解讀這一新職業?如何避免落入“獵奇”的巢窟?這是個“棘手”的題材。最終,尊重家屬、逝者,敬畏生命,秉承真實,成為這組紀實專題的拍攝原則。或許這樣做會導致畫面構圖、光影不完美,但作為紀實專題,我認為現場的真實、感人最重要。這一年,我前后11次晝夜進殯儀館追蹤拍攝,經歷了最初的恐懼和后來的從容。最終,作品《90后入殮師》獲得2012年度中國新聞攝影年賽日常生活類組照金獎。
拍攝前,我做了很多準備,查資料,看圖片和視頻,以期增加對職業的熟悉,感受和思考要呈現的畫面。盡管做了很多準備,但當你真正走入那個環境,體會到死亡所特有的壓迫感時,才會真切理解直面生死的“五味雜陳”和想“逃離”的心境。
拍攝初期,我的心理壓力很大,一走進殯儀館,心慌腿軟。起初,妻子見我常去拍攝這個題材,直皺眉頭,勸我放棄,甚至連吃飯也躲著我。為拍到入殮服務,我克服種種障礙,融入年輕的入殮師群體,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情感困惑。從殯儀館乘坐入殮師們的“電摩”到宿舍,與他們一起同吃、同住。關系融洽后,我和他們溝通順暢,配合默契。
但入殮工作的突發性使我無法提前得到消息來安排拍攝。一次深夜采訪溝通無果后,我失望地陷入矛盾之中:要不要等入殮師新聞圖片見報后就此放棄,轉而騰出時間掙工分?還是繼續下去直至拍攝出一組有深度的精品?我十分彷徨。經過一段時間的內心掙扎,我下定決心,要么不做,既然做了就要做出全國一流的精品。
拍攝過程很艱辛。由于初次在嘉興開辦入殮服務,當地多數人不接受,我常常是白等一晝夜。一次次去嘉興,一次次在入殮師身旁等待,一次次被家屬拒絕……最后,終于有家屬同意我隨同拍攝,我甚為感激。在對逝者尊重的前提下,我進行了全程拍攝。
作為一組講求深度的專題,我全程追蹤入殮師去太平間睡覺等逝者、去醫院推銷業務被罵等工作過程,并聚焦入殮師的日常生活,找尋真實自然且反映本質的畫面。
這組專題拍到“最前線”的影像,但對我而言,收獲最多的還是關于“人生與生死”的感悟:讓自己對社會、他人更有價值,同時樂觀從容,敬畏生命。
勿忘初心,方得始終
近幾年,傳統媒體有不少攝影記者紛紛離職、改行。我經常問自己,要不要離開?真離得開攝影嗎?
回歸初心。
從1985年第一次在《空軍報》上發表“小豆腐塊”開始,還在部隊的我就想:將來要做特約通訊員、特約記者、記者、名記者。這個新聞理想一直伴隨我。
在部隊時,我省吃儉用從津貼中擠出一筆錢,買了一臺當時還不錯的美能達X-700。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我利用休假,狂拍不已。在過年的大雪天里,買站票擠上人滿為患的老式火車,站20多個小時去拍攝雪中的張家界;為提高暗房技術,在暗房洗片通宵達旦,等同事來上班,才發覺天已大亮,接著就去辦公室打水上班……
1999年,我毫不猶豫地放棄轉業當公務員的機會,拿著一本厚厚的見報本,毛遂自薦地走進了《浙江日報》。當時的我面臨著人生中一個最重要的選擇:做文字記者還是做攝影記者?盡管我當時攝影水平一般,領導也直言指明我與高水平的省報攝影記者有差距,但依然走上攝影的道路。近二十年來,我癡心不改。有差距,就笨鳥先飛,不斷地經歷失敗,總結,失敗,總結的循環。向書本學,向經典照片學,向競爭對手學,向大獎得主學……我一邊學,一邊揣摩別人為何這樣選材和拍攝?遇到相同的題材和場景,我會怎樣想,怎樣拍?找出差距,確立短期、長期目標,不斷地嘗試把照片拍出新意。
與攝影結緣30多年,一路走來,我對新聞攝影的愛始終如一,不理會外界的浮華、躁動,一心追求永恒的經典瞬間。只有這樣,才不會在眼前的沖擊、誘惑中迷失自我。每每想起費盡心血拍攝的一個個獨家瞬間,是那么震撼,這帶給我的成就感是任何金錢無法代替的。(作者單位: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圖片新聞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