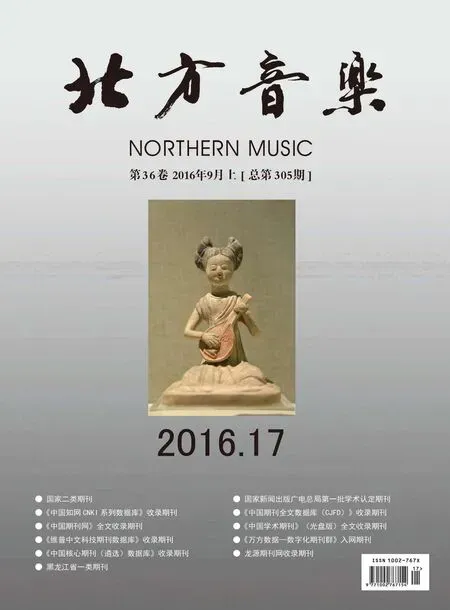“靈魂”深處聽驚雷
——阿爾班·貝爾格歌劇《沃采克》的創作給我們的啟示
傅薪穎
(北京交通大學海濱學院,北京 100000)
“靈魂”深處聽驚雷
——阿爾班·貝爾格歌劇《沃采克》的創作給我們的啟示
傅薪穎
(北京交通大學海濱學院,北京 100000)
阿爾班·貝爾格所創作的《沃采克》是一部表現主義的代表作,也是整個西方音樂史中極為罕見的偉大作品。為了探討作品創作的奧秘,筆者從作者創作的歷史背景、過程、目的、方法、風格等方面進行了分析研究,從而揭示了貝爾格為了忠實地反映內心的所思所想,勇敢地沖破各種障礙,大膽地在技法上進行創新,真實地再現了歌劇中各種人物的內心世界,充分地反映了作者靈魂深處驚雷般的吶喊。他的創作為我們留下了眾多的啟示,對指導今天的音樂創作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阿爾班·貝爾格;歌劇;《沃采克》
阿爾班·貝爾格(Alban Berg,1885-1935)是公認的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特別是他創作的《沃采克》,不僅是西方歌劇史上的杰出之作,亦是整個西方音樂史中一部極為罕見的偉大作品。作曲家選擇了最深刻、最具戲劇性的優秀歌劇腳本,將所有前人想要用歌劇這一理想音樂體裁所表達的東西展現地淋漓盡致……《沃采克》早已超越了音樂藝術的界限,進入到了人類思考自身生存命運的廣闊空間中去,成了“永恒”和“無限”的代名詞。
本文運用歷史的觀點分析研究歌劇《沃采克》歷史和現實的價值。并試圖通過這種分析去揭示音樂作品的內涵,揭示音樂作品中各種小人物和他(她)們所處的時代之間的深層關系,最終深化我們對音樂作品的認識。通過研究和分析歌劇《沃采克》創作方法,從中尋找出對我們現代人有益的啟示,指導我們現今的音樂創作,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1]
一、阿爾班·貝爾格不畏“招災之險”,以驚人的毅力創作了歌劇《沃采克》
(一)表現主義思潮的形成給創作歌劇《沃采克》創造了良好的機遇
進入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墮落、社會的畸型,人的孤獨感劇增,藝術家們對人類的未來充滿了危機感和種種憂慮。尤其是在一戰前后,德奧君主國從沒落的邊緣逐漸走向崩潰,使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當時的社會給藝術家們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繼續閉著眼睛說瞎話,繼續創作那些所謂英雄大人物的花前月下的虛偽的浪漫主義生活來粉飾當時的腐朽社會呢?還是把社會的真面目、真實的丑惡和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搬上舞臺來警示世人,真實地反映靈魂深處的所思所想,對腐朽的社會發出吶喊和反抗?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產生了藝術界的表現主義創作思潮。表現主義者們以一種近乎空想的熱情,用自己的藝術向社會發出了強烈的抗議。
貝爾格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極度動蕩的時代。與當時許多文藝界人士一樣,貝爾格最初也認為戰爭是解決當下社會危機與矛盾的一條出路。因此,當參軍的機會來臨時,盡管他的健康情況不佳,但貝爾格還是應征入伍,并為能夠參與這個“偉大的事業”而感到興奮不已。然而三年多的軍旅生活,使貝爾格受盡了折磨、痛苦與屈辱,把他對戰爭的狂熱慢慢耗盡。在這場人類的災難中貝爾豐深深地體會到了孤獨與絕望,甚至是信念的破碎,使他從戰前的一個主戰者徹底轉變成為了一個“反軍國主義者”。
1914年5月,阿爾班·貝爾格在維也納的室內劇院觀看了19世紀上半葉德國現代戲劇家畢希納(Georg Buchner)的戲劇作品《沃依采克》的首演。《沃依采克》是畢希納根據1821年發生在德國的一起真實謀殺事件為藍本創作而成的。畢希納是西方戲劇史上第一個把“卑賤者”作為悲劇主人公的劇作家,并把主人公生活的社會說成是犯罪發生的真正原因。畢希納在戲劇中著重突出了沃依采克作為一個掙扎于底層的窮人、作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是如何被富人侮辱嘲笑、如何被社會邊緣化;作為一個弱小而木訥但卻又憑靠自己辛勤勞動賺錢養家的男人,是如何被迫失去自由和意志,最終被異化成了一名殘忍的殺人犯的過程。[2]
阿爾班·貝爾格在看過《沃依采克》后,被這部戲劇徹底地征服了。他立刻寫信給韋伯恩,在信中他這么寫道:“不只是這個被整個世界剝削和折磨的窮人的命運,而且還有一些個別場景中聞所未聞的緊張情緒如此深深的打動了我”。[3]
此時阿爾班·貝爾格認為將戲劇《沃依采克》移植為歌劇的時機已經成熟。作為歐洲戲劇史上第一部以反英雄人物為主人公的現代悲劇,《沃依采克》在十九世紀未能確立自己的地位是不奇怪的。它在深刻地追逐人的內在本質的過程中預示了一些20世紀現代戲劇中才會出現的東西。因此,它默默地等待了幾十年,直到20世紀初,人們才能真正地認識到畢希納與《沃依采克》的深刻意義,這顆被人們遺忘于黃土之中的珍珠才重新大放異彩。
(二)阿爾班·貝爾格為創作歌劇《沃采克》遭到來自各方面的反對
阿爾班·貝爾格下定決心創作歌劇《沃采克》時,卻遇到了重重困難和來自各方面的反對。
1.創作歌劇《沃采克》遭到恩師勛伯格的反對
20世紀初,雖說人們對上世紀畢希納的戲劇有了一定的認識,但這種現實主義題材作品中的強烈的戲劇沖突和矛盾在當時人們眼中是“反音樂”的,壓根不適合用音樂方式來表達。然而,貝爾格卻要將畢希納的《沃依采克》以歌劇的形式搬上舞臺、呈現在觀眾面前,這在大多數人眼里無異于“癡人說夢”。就連平時一貫支持他在歌劇方面有所建樹的恩師勛伯格也提出了反對的聲音,甚至是在歌劇完成后,還一再潑冷水[4]。然而阿爾班·貝爾格這一次卻沒有因老師的反對而改變自己的信念。這個生性靦腆卻性格堅強的青年,并沒有考慮他的作品是否會成功,只是忠實地跟隨自己的內心,按照自己的真實想法去做。他深知藝術的創作必須遵循作者真實的內心想法,而這正是他的老師勛伯格一貫提倡的。
2.創作歌劇《沃采克》遭到了傳統創作文化的反對
以勛伯格為代表的表現主義音樂自從誕生以來,受到了整個社會不同方面的抵制,處于極端的孤立狀態。歌劇《沃采克》也不例外,既有贊賞的,但更多的則是批判。有的公開認為貝爾格是個音樂騙子,是一個對公眾有危害的音樂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復雜的。一是表現主義音樂從一開始就站在傳統音樂語言的商業化墮落的對立面。這種音樂強調“自律”于社會的需求,并非供人享樂。在勛伯格等人看來,非享樂性的藝術作品才具有真正的藝術價值。為了這樣的藝術真實,作曲家們背離了某些傳統的作曲技法和美學思想,利用與傳統審美習慣有所沖突新的新形式來表達真實,不被觀眾欣賞和認可。二是當時傳統的音樂“充滿美的遮掩與秩序的幻覺的自我欺騙”。[5]尤其是其中所體現出的唯美主義傾向,是必須加以反叛的,反對那種完全沉迷于安逸、舒適、幻想飄渺以及不思進取的藝術。只有直面現實,正視人性自身的弱點,才能真正告慰亡靈并反省自我。貝爾格既需要聽眾的支持,又不愿為此放棄對新音樂語言的追求,因此陷入了創作困境。
3.創作歌劇《沃采克》遭到政府當局的反對
隨著希特勒政權上臺,《沃采克》在德國遭到政府當局的禁演。在他們的眼里,這部作品是一部違背道德倫理的作品。在信奉共產主義的蘇聯,把它當成是頹廢的資產階級藝術而備受指責。在如捷克等一些反德國家,則把它看成是他們的反德情緒的發泄點。而在其他一些國家和城市,對這部歌劇也往往是毀譽參半。
他的老師勛伯格說:“我大大震驚于這位溫柔、怯懦的青年竟有勇氣冒這種招災之險創作了《沃采克》,一部好像不能入樂的奇特的悲劇性歌劇。”[6]
(三)阿爾班·貝爾格第一次在歌劇中把“卑賤者”作為主人公推向前臺
1914年,阿爾班·貝爾格決定創作《沃采克》。由于服兵役,貝爾格被迫中斷歌劇《沃采克》的創作。直到1918年11月戰爭結束后,貝爾格才重新開始了《沃采克》的寫作。到1921年8月貝爾格終于完成了這部歌劇的縮譜。次年5月配器部分也全部完成。1925年12月14日,阿爾班·貝爾格的第一部歌劇《沃采克》由埃利希·克萊伯(Alichi Klerbo)指揮在德國柏林歌劇院首演,并取得了成功。[7]
歌劇《沃采克》中的人物形象一反傳統歌劇中“英雄”色彩,轉而突出最不起眼的社會低層小人物,使他們走向了表演的前臺,使歌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宮貴族和那些英雄化、理想化和神化了的顯赫人物,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貝爾格歌劇《沃采克》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現實生活中的失敗者:作為一名下層的士兵,他終日忍受著上尉的百般羞辱;為了養活情人和私生子,他甘愿成為醫生做精神病實驗的犧牲品以獲取廉價收入;而情人的不忠與背叛,最終讓沃采克在極度痛苦、屈辱、神志不清的情況下將情人殺害,而后自己溺水身亡。然而貝爾格在這里想要表達的不僅僅是對兩條故去生命的痛惜,更重要的是對所有生活在社會底層、深受現實碾壓的民眾的悲慘命運的痛心。
《沃采克》這部歌劇充滿了沉重、壓抑、痛苦、怪誕甚至病態,將隱藏在人物內心的孤獨、恐懼、悲痛和絕望等感情夸張、放大,充分展現在觀眾面前,最終以宿命論式的做法凄慘落幕,與傳統歌劇的大圓滿結局形成鮮明對比。
貝爾格的老師勛伯格曾這樣評價這部歌劇:“它以完全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通過音樂語言的豐富與從容,敘述上的有力與自信,以及寫作上的仔細和值得注意的獨創性而使我感到驚訝。”[8]
二、阿爾班·貝爾格堅持為戲劇服務的原則,在技法上進行大膽突破
在創作之初貝爾格就明確了自己的創作思想,要以創作好的音樂為己任,要用音樂來表達出畢希納劇作中的深刻內涵,要用音樂來表達劇中戲劇性的矛盾與沖突,完美地用歌劇來再現畢希納的不朽之作。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創作一部歌劇的根本目的就是“還戲劇以戲劇”。[9]
(一)為了深化主題內涵,選擇象征性技法
在這部歌劇結構中,大量運用了具有象征意義的主導動機,同時這些主導動機貫穿全曲又使得歌劇整體具有緊密聯系。聲樂演唱與器樂間奏的結合,又將不同的象征和暗示意義包含于其中,使得劇情體現出現實與象征虛實結合的特點。在歌劇中“刀子”的主導動機曾多次出現,是沃采克殺害情人瑪麗的象征。[10]在第二幕第三場,第一次出現了“刀子”這個動機。

沃采克因憤怒而舉手打了背叛他的情人瑪麗,而瑪麗卻回應“我寧愿讓刀刺進我的胸膛,也不愿讓你的手碰我!”,這里對最后沃采克用刀子結束瑪麗生命埋下了伏筆。
除了“刀子”這一主導動機外,“我們窮人”[11]主導動機也在劇中反復出現,象征著沃采克這個窮人逐漸深化的悲劇性命運。

“我們窮人”不僅僅是一句無奈的磋嘆,更是對沃采克這個主人公的象征。他是現實社會的犧牲品,飽受生活的摧殘,被情人拋棄,神志不清,最后被逼得走上兇殺和自殺的結局。[12]
歌劇《沃采克》象征技法的運用,利用多個縱貫作品始終的主導動機,深度刻畫了沃采克的悲劇命運,無情地揭露了社會的陰暗與病態,深化了作品的內涵。
(二)為了刻畫人物,在唱腔上選擇了“念唱”音樂技法
所謂的“念唱”就是指歌唱家不必唱出準確的音高,而只是用“念”或“說”的方式念出與該音高差不多的音。這種由勛伯格所創的“念唱”式的歌劇演唱方法,實際上就是根據作曲家的記譜,把譜上所標記的節拍、音值、近似音高及音量變化等,用說話或近似說話的聲音“念”出來。
為了突出劇中沖突性的故事情節和矛盾性的人物性格,《沃采克》采用了這種半念半唱式的演唱方式。這種類似“吶喊式”的表達,讓演員在表演時不受具體音高的約束,強調是對角色性格的演繹。貝爾格認為唯有這種“吶喊”式的獨白,才能真正刻畫出角色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才能引起觀眾的共鳴,才能讓觀眾切身體會劇中人物的那種糾結、掙扎與癲狂的性格特征。
貝爾格曾經親口說到:“這種戲劇性強的人聲手法做為一種由旋律、力度、節奏綜合支配的念白方法,它不僅能在最好的程度上確保劇詞能清楚地聽明白,更能為歌劇增添一種有價值的、肇始于音樂最本真一面的表演方式。它不啻是對普通演唱法的有益補充,更為其提供了一種很有趣的對比。”[13]
(三)為了渲染氣氛,在音樂色彩上選擇濃淡有致的色彩搭配
貝爾格認為音樂必須服務于戲劇。在歌劇中,除了人聲外,樂隊的編配也要同樣符合戲劇表現的真實需要。小到一個音樂動機的出現與發展,大到幕與幕之間的銜接過渡,器樂的編配、樂隊的色彩性使用都是為了更好地渲染氣氛、烘托劇情以及對人物形象、心理等方面進行深入刻畫。就仿佛是在用五彩斑斕的樂器來一同講述故事劇情。只有音樂的色彩性使用與劇情發展達到了緊密結合,才能使整部歌劇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才能使戲劇的沖突性達到完美的釋放。歌劇《沃采克》為了逼真地刻畫一個備受壓迫、經常處于緊張恐懼心理狀態下的一個社會底層人物形象,舍棄了傳統的和聲、和弦安排,拋棄了傳統的配器技法,用一些嘈雜、刺耳的新式演奏方式去表達人物內心的苦悶與病態。這種奇怪而又豐富、撕心裂肺而又極具音響效果的器樂表達方式大大增強了戲劇的真實性,使沃采克這樣一個飽受生活摧殘、內心充滿恐慌、時刻瀕臨癲狂的小人物形象躍然于觀眾面前。貝爾格在音樂作品中涌動著經久不衰的激情,體現著非理性、混亂、零散化的文化特征和夸張、變形、怪誕、抽象的藝術理念。作曲家希望用音樂來創造一次奇跡,使得喪失靈魂的、墮落的、被埋葬的人類重新復活。[14]這種音樂風格的形成,絕不僅僅是貝爾格主觀想法的引導,更多的是其生活的歷史時代與社會環境給予他的選擇。斯圖肯斯米特曾這樣評價這部作品:“《沃采克》的音樂使腳本中僅僅是潛在的某些特質,做了充分的展開,揭示了人物最隱秘的心理細節,同時也表明了貝爾格作為當代最杰出的歌劇作曲家的獨創性”[15]。
三、阿爾班·貝爾格歌劇《沃采克》的創作給我們的啟示:
通過對歌劇《沃采克》創作上的分析研究,給我們很多的啟示。主要的啟示有以下幾點:
(一)音樂創作要為劇情服務
一切為劇情服務,這是創作歌劇的指導思想。貝爾格一切創作方法都是為了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塑造。無論是不規則、無調性和十二音創作方法,傳統性的創作方法和現實主義、表現主義等方法的運用,都是為了刻畫劇中主人公內心世界。體現了藝術為內容服務的思想。
(二)親身體驗是創作的動力源泉
阿爾班·貝爾格一生的苦難經歷和重重的磨難,給他的音樂創作帶來了無盡的音樂創作源泉。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經常會發現貝爾格把自身的經歷和內心的感受帶入到了創作中。劇中主人公的遭遇往往就是貝爾格自己的一個縮影,或是某一方面性格的放大化。
(三)在靈感的感召下進行創作
貝爾格音樂創作不搞無病呻吟,在有靈感的基礎上進行創作。創作過程比較緩慢,但每一個作品的寫出都是精品,都是傳世之作,都是他內心的吶喊和呼喚,都是他心靈的感應。而當他的靈感到來的時候,他將會放棄一切完全投入到創作之中,不顧一切地拼命創作。
(四)為了表現內心的所思所想,不畏“招災之險”,大膽進行創新
貝爾格為了創作《沃采克》,戰勝了重重困難。其中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是在創作時,貝爾格沒有考慮成功與否,只為了忠實的反映自己“內心的要求”,不考慮強權的報復,不考慮世俗的反對,不考慮權威的干涉,不考慮經濟的得失,不畏“招災之險”,敢為天下先。不虛偽、不掩飾、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靈魂深處真實的感受。把自己的愛和恨真實地反映在歌劇上,引起社會的共鳴,以達到反抗之目的。
而西方藝術家最讓人欣賞的是,他們常常有著干預現實,譴責現實不管個人前途、名譽,懷著極大的熱情創造新藝術的勇氣。僅憑這一點,便值得我們贊嘆。
藝術家們常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去挖掘往往被人們忽略的小人物形象。用他們獨特的方式去再現這些社會下層人的悲慘生活以此來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貝爾格歌劇《沃采克》也正是如此,其在音樂技法以及社會學方面所蘊涵的獨有價值,將永遠在歌劇史中綻放其獨特的光芒[16]。
[1]余志剛.阿爾班·貝爾格的生活與創作道路[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3:137.
[2]王璐.歌劇《沃采克》最后間奏曲的音樂學分析[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13,(12).
[3]自余志剛.阿爾班·貝爾格的生活與創作道路[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3:70.
[4]余志剛.論阿爾班·貝爾格的歌劇《沃采克》[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8,(04):50.
[5]自余志剛.阿爾班·貝爾格的生活與創作道路[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3:5.
[6]《勛伯格論作曲家》,譯自《風格與思想》:94.
[7]金鑫海.從《沃采克》到《露露》[D].天津:天津音樂學院,2010:8.
[8]自孟雁翎.貝爾格早期作品《弦樂四重奏》的三重風格元素——繼承性、探索性、貫穿性[J].人民音樂,2013,(2):85.
[9]Jarman Douglas,Alban Berg: Wozze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52.
[10]刀子出現在(II/3m.395,398;II/4m.599-602;II/5m.752;III/2 m.77,100;III/4m.222一5;270一4).這種幕和場次的簡略寫法采用了余志剛教授的寫法。在《論阿爾班·貝爾格的歌劇<沃采克>》一文中,余志剛教授指出:I、II、III代表幕次;m代表場次;數字代指小節數。其余類推。
[11]“我們窮人!”(1/1;I1/1 m.114; I1/5 m.776, 796; I/1-2 m.191, 198——200: III//4-5 m.361)。在《論阿爾班·貝爾格的歌劇<沃采克>》一文中,余志剛教授指出:I、II、III代表幕次;m代表場次;數字代指小節數。其余類推.
[12]徐艷.西方表現主義音樂的審美現代性[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7.
[13]賈偉亞.悲劇命運的必然——卡門和瑪麗[J].作家,2012,(8):181-182.
[14]徐艷.西方表現主義音樂的審美現代性[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7:2.
[15]自姜蕾.乘著表現主義的筏子 感悟貝爾格的歌劇《沃采克》[J].音樂愛好者,2006,(9):47.
[16]孫嘉藝.貝爾格歌劇《沃采克》中的拯救意識——以第二幕第一場為例[J].歌劇,2013,(11).
[17]余志剛.阿爾班·貝爾格的生活與創作道路[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3.
[18]余志剛.論阿爾班·貝爾格的歌劇《沃采克》[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8,(04).
[19]金鑫海.從《沃采克》到《露露》[D].天津:天津音樂學院,2010.
[20]孟雁翎.貝爾格早期作品《弦樂四重奏》的三重風格元素——繼承性、探索性、貫穿性[J].人民音樂,2013,(2).
[21]Jarman Douglas.Alban Berg: Wozzeck[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2]古斯塔夫·科貝[美],張洪島編譯.西洋歌劇故事全集[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
[23]賈偉亞.悲劇命運的必然——卡門和瑪麗[J].作家,2012,8.
[24]徐艷.西方表現主義音樂的審美現代性[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7.
傅薪穎(1989—),女,漢,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畢業,現為北京交通大學海濱學院藝術系音樂學專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