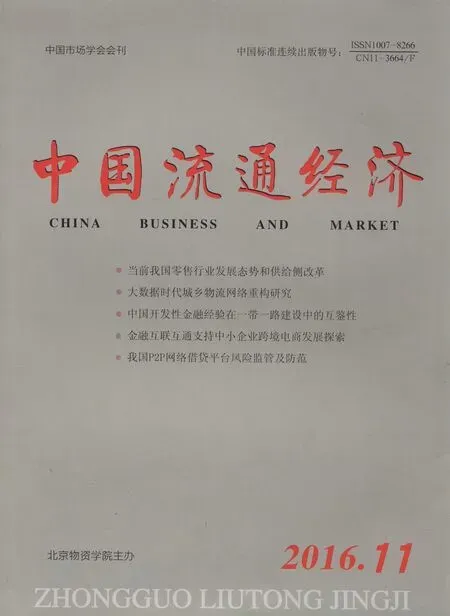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與環境質量
黃娟,汪明進,孫坤鑫
(1.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市300071;2.紹興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浙江紹興312000)
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與環境質量
黃娟1,汪明進2,孫坤鑫1
(1.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市300071;2.紹興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浙江紹興312000)
本文從“胡煥庸線”這一地理學的概念出發,以基于沿“胡煥庸線”垂直遞減假說而量化的生態承載力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選取中國大陸30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未含拉薩市)2003—2013年間的面板數據,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分別實證了經濟集聚與環境質量的關系,用固定效應向量分解模型分別實證了生態承載力與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與環境質量的關系。結果表明,城市環境質量是生態承載力和與之相關的經濟集聚共同作用的結果,較高的生態承載力會提高地區的經濟集聚能力。
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環境質量;固定效應向量分解模型
一、引言
在提倡綠色、協調發展理念與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不同區域的生態環境質量既取決于自然系統所決定的生態承載力,也取決于該區域經濟社會活動的生態負載。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既能讓經濟集聚發揮拉動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作用,又能改善生態環境,進而促進城市經濟、社會、自然的協調發展,將顯得尤為重要。從考慮城市的生態承載力出發,通過對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與環境質量的理論演繹和實證檢驗,探索合理、可持續的經濟集聚模式,對于進一步促進城市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協調城市經濟集聚發展與環境改善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迫切。
關于生態承載力的計算,從環境科學來看十分復雜,本文參考鐘茂初[1]關于我國生態承載力沿“胡煥庸線”垂直方向梯度遞減的假說,引用孫坤鑫[2]計算各城市距“胡煥庸線”的垂直距離,以此表征其生態承載力,分析生態承載力和經濟集聚對城市環境質量的影響,論證在生態承載力約束下,經濟發展水平、集聚程度如何對環境質量的改善施以影響;闡述生態承載力、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科技創新等如何對經濟集聚產生綜合影響。本文嘗試在各地區生態承載力基礎上,探索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集聚模式和運行機制,這對于生態城市建設理論的完善以及對于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都將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生態承載力理論的演化與發展
1.生態承載力的內涵
1921年帕克和帕吉斯(Park&Burgess)在有關人類生態學雜志上提出承載能力的概念,并將其應用于生態領域,稱為生態承載力,指一個小區域良性生態系統對某一物種可承載的最大量。[3]這一定義奠定了此后學術界使用“極值”或“容量”來衡量承載力的基礎,特別是隨著“承載力”在生態學中的廣泛應用,“生態承載力”便逐漸成為衡量生態容量或環境容量的有效工具。歸納現有文獻可以發現,生態承載力研究經歷了從單要素到多要素、從靜態到動態、從單獨的生態系統到加入人文系統的綜合研究過程。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單要素的資源承載力方面,如土地資源承載力、水資源承載力、森林資源承載力等。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能源危機、人口膨脹、環境污染等危機的影響,生態承載力研究逐漸轉化為多要素和相對要素承載力研究,主要包括環境承載力、相對資源承載力、土地人口承載力等。近年來,生態承載力理論在預測區域合理的經濟規模和人口密度、確保城市水資源安全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2.生態承載力的量化方法
伴隨著相關環境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生態承載力的量化方法在數據收集、指標選取、過程論證等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發展。里斯(Rees)[4]提出的生態足跡方法,將生態承載力折算成某一區域所能維育的最大人口數量及其所需要的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由于該方法指標分類清晰、研究結果直觀明晰,目前得到了廣泛推廣與應用。美國生態學家奧德姆(Odum H T)[5]將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能量轉換成同一單位的太陽能值,根據該太陽能值的大小量化區域生態承載力的大小。該方法引入國內以后得到學者們的重視,在實際使用過程中也得到了較大改進。如陸宏芳等[6]構建了評價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能值指標(EISD),認為生態承載力越大,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也越強。無論是生態足跡法,還是能值轉換法,其所需要的等價因子、生產力系數以及能值轉換率均無法直接觀察或收集得到,需要復雜的測算與轉換才能確定最終的參數。因此,二者在推廣過程中受到一定限制。目前,生態承載力量化方法出現了一種新趨勢,即將新技術手段運用到區域生態承載力的定量研究上,如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的空間生態承載力方法,使得生態承載力研究從平面上升到空間立體的高度,彌補了僅使用統計數據來描述生態供給量的缺陷,更克服了傳統統計方法不能表達生態承載力空間分布格局方面的不足。
分析現有文獻可以發現,生態是一個包含經濟、環境、資源、人口及其他生物的綜合系統,因此生態承載力在指標選取時遇到的巨大挑戰是“能量壁壘”問題,如何將生態系統中環境、資源、經濟以及人口等不同性質的要素單位統一為可直接比較的單位,將是重點研究的內容。本文基于“胡煥庸線”生態承載力涵義的視角,將生態承載力表征為某一地區到“胡煥庸線”的垂直距離,由于“胡煥庸線”揭示了中國人口區域分布特征,由此可以引申出中國生態承載力沿著“胡煥庸線”垂直方向梯度遞減的規律。將生態承載力以距離表征,一是可以精確測算出某一城市或地區到“胡煥庸線”的垂直距離,數據可靠且易得;二是以垂直距離表征的生態承載力,彌補了傳統評價方法中各指標的量綱得不到統一的缺陷。
(二)經濟集聚與環境質量的關系研究
1.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質量
學術界論述經濟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經典理論主要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EKC假說由格羅斯曼和克魯格(Grossman&Krueger)[7]首先提出。該假說指出,在經濟增長初期,環境污染會伴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從中長期來看,在經濟活動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以及政府環境規制的共同作用下,環境污染會跨過拐點進而逐漸下降[8]。倒“U”型的EKC曲線得到諸多學者的驗證。一些學者將環境質量視為生產要素,認為環境污染的下降是由技術或人力資本對環境質量要素的替代所引起的[9-10];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環境污染是生產的負外部性體現,當技術力量、政府環境規制能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強之后,這種負外部性將逐漸減弱,環境污染隨之下降[11]。瓊和佩切諾(John&Pecchenino)[12]構建的世代交替模型顯示,經濟增長與環境消費之間存在著多重均衡,主要包括低經濟增長—低環境消費的“雙低”穩態、高經濟增長—高環境消費的“雙高”穩態以及高經濟增長—低環境消費的“高低”穩態。這種多重均衡狀態便于解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所對應的環境質量狀況,對于分析截面數據很有說服力,但是缺乏對環境污染隨時間序列變化的分析[13]。
2.經濟集聚與環境質量
在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關系的研究中,維爾塔嫩(Virtanen)[14]、任等(Ren Wenwei et al)[15]認為產業集聚加劇了環境污染,曾等(Dao-Zhi Zeng et al)[16]、李筱樂[17]、陸銘和馮浩[18]、豆建民和張可[19]、楊仁發[20]、黃娟和汪明進[21]認為產業集聚可以改善環境質量;還有一類觀點認為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不能確定[22],特別是在長期內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之間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23-24]。
在經濟集聚與空氣質量關系方面,杜雯翠和馮科[25]認為,城市化中產業集聚帶來的“生產效應”大于人口集聚帶來的“生活效應”,城市化并不必然帶來空氣質量的惡化。王興杰等[26]認為,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助推人口密度不斷提高,使得大氣污染物遠超城市大氣環境容量,造成城市環境質量明顯下降。馬素琳等[27]認為,較高的技術水平和產業集聚度會改善空氣質量,可以從不斷提高科技水平和產業集聚度入手,通過各種方法減少能源消費需求、降低工業化水平,來達到改善空氣質量的目的,應在不斷提高產業集聚度與人口集中度的同時追求綠色GDP,注重人口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質,從而提升公眾的環保意識,以抵消隨人口集中度提高帶來的環境壓力。
(三)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與環境質量
城市環境質量是生態承載力和與之相關的經濟集聚共同作用的結果,必須分析經濟集聚對生態負載的影響及其環境質量效應,即生態負載與生態承載力之差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可持續發展理論與脫鉤理論均描述了生態承載力、經濟集聚與環境質量的相互關聯。其中,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受生態環境約束,存在著增長的極限,正如達理(Daly)[28]超越增長理論所指出的經濟規模并不是無限增長的,當物質資本或人造資本相當富裕以后,相對稀缺的自然資本(或自然要素)便成為制約經濟規模的核心要素。諸大建等[29]認為,當前某些地區的環境負載已經超過了其生態承載力,導致生態自然環境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我國經濟發展必須遵守C模式,即在保證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前提下,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消耗,以期走出一條相對的減物質化發展道路。當然,可持續發展理論僅僅為我們描述了作為一種環境負載的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產生的深刻影響,一旦環境負載超過生態承載力,那么經濟增長將會破壞生態環境質量。而真正將可持續發展理論用于數理推導以測算其大小的是脫鉤理論,它描述的是在生態承載力約束下,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是否同步變化,其中,脫鉤指數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0]首次構建,其數值等于末期的資源環境效益與GDP之比除以基期的資源環境效益與GDP之比。塔皮奧(Tapio)等[31]使用彈性系數方法對此進行了改進,并將脫鉤狀態細分為8大類,后來學者稱之為塔皮奧脫鉤彈性系數,該系數由資源環境質量變化率除以經濟增長率得到。由于脫鉤理論綜合考慮了經濟效益與資源環境效益,彌補了傳統經濟理論單獨研究經濟增長或僅探究資源環境的缺陷,因此,脫鉤理論很快成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模式與可持續性的工具[32]。
(四)文獻評述
綜上可知,將生態承載力、經濟集聚與環境質量結合在一起考慮的文獻相對較少,而大多集中于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直接研究。這主要是由于生態系統是一個關于經濟、資源、環境、人口等的集合,因此,在指標選取上存在量綱不統一的缺陷。由于生態承載力很難準確測算,導致既有研究往往繞過生態承載力這一約束條件,單獨研究經濟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同時,EKC假說以人均GDP和環境污染的截面數據為考察對象,探究經濟與環境之間在某一絕對量(或存量)上的非線性關系;而脫鉤理論描述的是經濟與環境是否同步變化的關聯,主要以彈性系數分析法為研究框架,側重分析經濟與資源環境的時間序列數據,這就決定了脫鉤彈性指標僅限于描述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變化速度,卻忽視了二者的絕對變化量。同時,EKC假說和脫鉤理論均只能解釋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非線性關聯,二者沒有解釋經濟增長影響環境污染的作用機制。在關于經濟集聚影響環境質量的研究方面,既有研究只是重點突出了產業集聚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經濟集聚所包含的人口集聚及其他方面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研究則相對不足。其中,由于研究樣本與研究方法的不同,學術界對于經濟集聚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既有人認為經濟集聚存在減少環境污染的正向促進作用,也有人認為產業集聚不利于改善環境質量的觀點,還有人認為二者的關系不明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觀點為:第一,基于“胡煥庸線”的視角,將生態承載力表征為到“胡煥庸線”的垂直距離,既避免了傳統生態承載力測算時量綱不統一的缺陷,也使得生態承載力更加符合我國經濟和人口梯度遞減分布的現狀;第二,環境質量與生態承載力和經濟負載息息相關,環境質量既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也受到生態承載力的制約,且在一般情況下,在生態承載力相同的地區,經濟負載越高其環境質量越低,反之,則越高;同理,在經濟負載相同的地區,生態承載力越高其環境質量也相對越高,反之亦然。
三、計量模型、變量及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為了考察經濟集聚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同時為了檢驗經典EKC曲線,本文在模型(1)中引入人均GDP的二次項和三次項,模型(2)引入其他相關的控制變量。為了考察生態承載力對空氣質量的影響,本文建立模型(3)。為了考查生態承載力對經濟集聚的影響,本文建立模型(4)。

其中,下標i表示地區,下標t表示當期時間,Airit表示環境質量,agglit表示經濟集聚,pgdpit表示經濟發展水平,Ei表示生態承載力,innovit表示科技創新,populit表示人口規模,fdiit表示外商直接投資,α0、β0、γ0為常數項,α1-α7、β1-β8、γ1-γ3為各變量系數,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說明
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中國大陸30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未含拉薩市)2003—2013年間的面板數據。除生態承載力以外,其他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等。為了提高估計的準確性,本文用人均GDP指數對相應的貨幣量進行平減指數計算后,調整成基期為2003年的數值。為了減少異方差和統計偏誤,本文對有關變量進行了自然對數處理。
(1)環境質量(Airit)。本文參考池建宇等[33]、楊肅昌和馬素琳[34]的研究方法,用空氣質量達到及好于二級的天數來表示,其值越大代表空氣質量越好。
(2)經濟集聚(agglit)。參考西科恩(Ciccone)等[35]的做法,用經濟密度即單位土地面積(平方公里)上的GDP(億元)來表示。
(3)經濟發展水平(pgdpit)。與現有多數基于EKC框架的實證研究[36]相同,用各城市人均GDP來表示。
(4)生態承載力(Ei)。從“胡煥庸線”的角度出發,以各城市的中心距“胡煥庸線”的垂直距離表征其生態承載力。“胡煥庸線”指自黑龍江省黑河市至云南省騰沖市的一條劃分西北—東南的直線,其東南區域多為平原、丘陵,具有良好的降水等氣候條件,以36%的土地面積集聚了94%的人口;而其西北地區多為沙漠、高原,氣候條件相對較差,盡管擁有64%的土地面積,其人口卻只占全國的6%。本文從“胡煥庸線”出發,在分析“胡煥庸線”東南、西北生態條件的基礎上,引用鐘茂初[1]關于我國生態承載力沿“胡煥庸線”的垂直方向(自東南向西北)梯度遞減的假說,并參照鐘茂初[1]、孫坤鑫[2]測算的各城市生態承載力比值表示生態承載力(參見表1)。
(5)科技創新(innovit)。普拉卡什和博多斯基(Prakash&Potoski)[37]、王和金(Wang&Jin)[38]認為,科學技術投入可以提高清潔環保技術的水平,從而降低污染程度。張可和汪東芳[39]認為更環保、高效的生產和環保技術能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本文借鑒袁鵬和程施[40]等人的經驗做法,以當地財政中科學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反映科技創新水平。

表1 各城市生態承載力比較
(6)人口規模(populit)。為了分析人口擁入大城市是否會產生“城市病”、惡化城市環境,同時考察人口集聚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本文采用年末總人口數來表征人口規模。
(7)外商直接投資(fdiit)。以往文獻研究對外商直接投資能否改善環境質量存在爭議,存在“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環”兩種對立觀點。本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額占GDP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水平,根據各年匯率調整為人民幣后進行計算(參見表2)。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分析
四實證分析
本文分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向量分解(Fixed Effects Vector Decomposition,FEVD)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其中固定效應向量分解模型是普拉珀和特勒格爾(Plumper&Troeger)[41]提出的。
一般從表面上來理解,經濟集聚可能會加重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負荷,造成更多污染物的排放,從而降低環境質量。但表3的回歸結果表明,經濟集聚與空氣質量正相關,集聚水平的提高會帶來空氣質量的改善。因為經濟集聚促進了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污染減排效率,從而改善環境質量。本文的4個模型均實證檢驗了經濟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空氣質量的改善。
模型(1)至模型(4)顯示,人均GDP與空氣質量的關系呈倒“U”型,經濟水平較低時,空氣質量較差,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會改善空氣質量,這也驗證了人們起初對大自然的無限索取、經濟粗放式發展再到自覺保護環境這樣一個螺旋式發展軌跡。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受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質得到大幅提升,而人們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也相應提升,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和認知得到大幅提高,進而共同推動環境質量的提升。
模型(4)顯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經濟集聚水平的提高。在模型(1)至模型(4)中,科技創新對空氣質量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而對經濟集聚是顯著為正的影響。人口規模對空氣質量的影響為負,但在不考慮生態承載力的情況下,影響并不顯著。考慮到生態承載力的影響,人口規模顯著惡化了空氣質量,表明在既定生態承載力約束下,人口集聚帶來的城市生態負載過高,進而惡化了環境質量。
模型(3)顯示,生態承載力對空氣質量的影響顯著為正,生態承載力高的地區環境質量會更好。在模型(4)中,對應生態承載力和經濟集聚的關系,考慮對經濟集聚程度的影響,可以看出生態承載力高的地區更能充分利用經濟集聚的積極效應,環境質量趨向更好。生態承載力是自然決定的,不同區域空間的自然條件、要素稟賦不同,其資源環境集聚人口和經濟的能力存在著差異性。一方面,良好的氣候、土壤、水源等生態條件是吸引人群聚集的基礎;另一方面,許多經濟活動與某一地區特定的地理條件有關,這種生態承載力決定的自然稟賦為企業的經濟活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較低的運輸成本、良好的氣候等地理條件,建立了企業的自然成本優勢。因此,生態承載力和經濟集聚密切相關。生態承載力強的地區(如我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由于其良好的自然條件,再結合其他歷史和經濟因素,能夠吸引更多的人口,進而加強了經濟集聚;反之,在“胡煥庸線”西北部,惡劣的生態條件先天性地決定了其經濟集聚能力的缺乏。

表3 回歸估計結果
表3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為負,在固定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向量分解模型中都很顯著,表明我國在吸收國際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存在著污染嚴重的產業在中國布局的現象,間接證明了“污染天堂”假說。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主要結論
本文通過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描述,利用2003—2013年中國大陸30個省會城市(不含拉薩)和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對經濟集聚、生態承載力與空氣質量進行實證分析,結論如下:
各城市距“胡煥庸線”垂直距離越遠,則其生態承載力越強,環境質量也越好。生態承載力對環境質量呈現線性影響。生態承載力是環境質量的基礎,在生態承載力一定的情況下,生態負載越重,環境質量越差,一旦這種負載突破了生態承載力的紅線,則環境質量就會顯著惡化,近年來京津冀地區空氣質量指數(AQI)不斷“爆表”就是生態負載突破承載力的表現。
人均GDP與空氣質量的關系呈倒“U”型,經濟水平較低時,空氣質量較低,但經濟發展提高到一定程度會改善空氣質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經濟集聚水平的提高,生態承載力和經濟集聚密切相關,生態承載力高的地區環境質量趨向更好。
城市環境質量是生態承載力和與之相關的經濟集聚共同作用的結果,生態承載力越高,表明其抵御污染和自凈化的能力越強,城市環境質量越好,而較高的生態承載力會增強地區的集聚能力,經濟集聚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改善空氣質量,總之,生態承載力高的地區可充分發揮經濟集聚的積極效應,其環境質量會更好。
(二)政策啟示
各地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考慮到自身環境的生態承載力,因地制宜發展適合自己的優勢產業。由于經濟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空氣質量的改善,各級政府應該有針對性地建立產業集聚區,對污染企業進行集中治理。而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應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改進污染治理技術。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農村勞動力不斷融入城市生活圈,導致人口集聚,相應地會帶來區域環境污染的擴張和凸顯。因此區域政府應不失時機地提高人們的受教育程度,綜合提高人口素質,提升大眾的環保意識和認知水平。在實施新型城鎮化建設時,還應充分考慮到生態承載力以及經濟發展水平,不盲目求大求全,積極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升企業科技創新水平,發展集約型創新企業和附加值高的生產服務性企業,從源頭上減少污染排放。
[1]鐘茂初.如何表征區域生態承載力與生態環境質量?——兼論以胡煥庸線生態承載力涵義重新劃分東中西部[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1-9.
[2]孫坤鑫.城市生態承載力的測度——從胡煥庸線出發[C].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學術論壇,2016:166-177.
[3]轉引自朱永華,任立良,夏軍,等.缺水流域生態承載力研究進展[J].干旱區研究,2011(6):990-997.
[4]WILLIAM E Rees.The ecolo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The ecologist,1990(1):18-23.
[5]ODUM H T.Environmental accounting: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M].New York:John Wilely,1996:320-370.
[6]陸宏芳,藍盛芳,李雷.評價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能值指標[J].中國環境科學,2002(4):380-384.
[7]GROSSMAN G M,KRUEGER A 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NBER woking paper,1991,W3914.
[8]GROSSMAN G M,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2):353-377.
[9]LOPEZ R.The environment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163-184.
[10]DINDA S.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a survey[J].Ecological economics,2004(4):431-455.
[11]SELDEN T,SONG D.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147-162.
[12]JOHN A,PECCHENINO R.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of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 journal,1994(427):1399-1410.
[13]陸旸,郭路.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和環境支出的S型曲線:一個新古典增長框架下的理論解釋[J].世界經濟,2008(12):82-92.
[14]Juhani Virtanen.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metal deposition in the bay of T??l?nlahti,Southern Finland[J].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1998(9):729-738.
[15]REN W,ZHONG Y,MELIGRANA J,ANDERSON B,WATT W E,CHEN J,LEUNG H L.Urbanization,land use,and water quality in Shanghai:1947—1996[J].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2003(5):649-659.
[16]ZENG D Z,ZHAO L X.Pollution have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9(2):141-153.
[17]李筱樂.市場化、工業集聚和環境污染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14(8):39-45.
[18]陸銘,馮皓.集聚與減排:城市規模差距影響工業污染強度的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2014(7):86-114.
[19]豆建民,張可.空間依賴性、經濟集聚與城市環境污染[J].經濟管理,2015(10):12-21.
[20]楊仁發.產業集聚能否改善中國環境污染[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23-29.
[21]黃娟,汪明進.科技創新、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6(4):50-61.
[22]李偉娜,楊永福,王珍珍.制造業集聚、大氣污染與節能減排[J].經濟管理,2010(9):36-44.
[23]閆逢柱,蘇李,喬娟.產業集聚發展與環境污染關系的考察——來自中國制造業的證據[J].科學學研究,2011(1):79-83.
[24]譚嘉殷,張耀輝.產業集聚紅利還是“污染避難所”再現?—基于廣東省的證據[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6):82-89.
[25]杜雯翠,馮科.城市化會惡化空氣質量嗎?——來自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經驗證據[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5):91-99.
[26]王興杰,謝高地,岳書平.經濟增長和人口集聚對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的影響及區域分異——以第一階段實施新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為例[J].經濟地理,2015(2):71-76,91.
[27]馬素琳,韓君,楊肅昌.城市規模、集聚與空氣質量[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5):12-21.
[28]DALY H E.Economics in a full world[J].Scientific american,2005(3):100-107.
[29]諸大建,臧漫丹,朱遠.C模式: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戰略選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6):8-12.
[30]OECD.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Paris:OECD,2002.
[31]TAPIO P,BANISTER D,LUUKKANEN J,et al.Energy and transport in comparison:immaterialisation,dematerialisation and decarbonisation in the eu15 between 1970 and 2000[J].Energy policy,2007(1):433-451.
[32]孫耀華,李忠民.中國各省區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關系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5):87-92.
[33]池建宇,張洋,晏思雨.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空氣質量嗎——基于中國31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經驗驗證[J].經濟與管理,2014(5):26-31.
[34]楊肅昌,馬素琳.城市經濟增長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基于省會城市面板數據的分析[J].城市問題,2015(12):4-11.
[35]CICCONE A,HALL R E.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1):54-70.
[36]GROSSMAN G M,KRUEGER A 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NBER Working Papers,1991.W3914.
[37]PRAKASH A,POTOSKI M.Racing to the bottom?trade environment and governance,and ISO14001[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6(4):350-364.
[38]WANG H,JIN Y.Industrial ownership and environment:evidence from china[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7(3):255-273.
[39]張可,汪東芳.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交互影響及空間溢出[J].中國工業經濟,2014(6):70-82.
[40]袁鵬,程施.中國工業環境效率的庫茲涅茨曲線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1(2):79-88.
[41]PLUMPER T,TROEGER V E.Efficient estimation of timeinvariant and rarely changing variables in finite sample panel analyses with unit fixed effects[J].Political analysis,2007(2):124-139.
責任編輯:方程
Economic Agglomeration,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HUANG Juan1,WANG Ming-jin2and SUN Kun-xin1
(1.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China;2.Shaoxing Reg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Shaoxing,Zhejiang312000,China)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Hu line,the authors take the quantifie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s the key explanatory variable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descends vertically along the Hu Line.On account of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30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during 2003-201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by the fixed effect and random effect model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economic agglomeration,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empirically tested with the FEVD model.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related economic agglomeration.The higher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region is,the stronger the ability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will be.
economic agglomeration;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environmental quality;FEVD model
F124.5
A
1007-8266(2016)11-0058-08
2016-09-07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城市生態文明建設機制、評價方法與政策工具研究”(13&ZD158)
黃娟(1981—),女,河南省商城縣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經濟學、創新經濟學;汪明進(1978—),男,安徽省樅陽縣人,紹興區域經濟研究中心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效率、技術創新;孫坤鑫(1990—),女,河北省邯鄲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