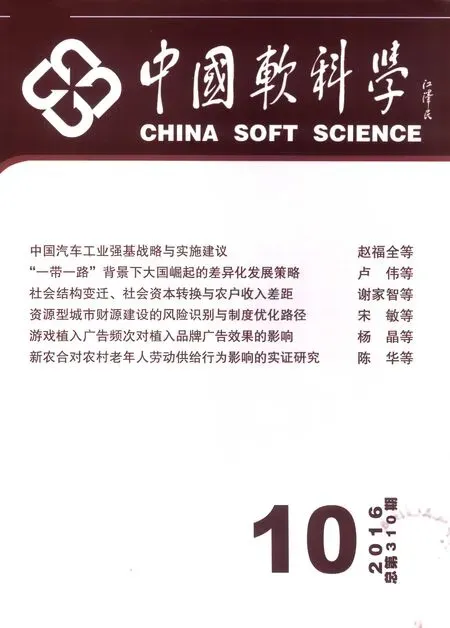社會結構變遷、社會資本轉換與農戶收入差距
謝家智,王文濤
(1.西南大學 農村金融與農業現代化研究中心,重慶 北碚 400715;2. 西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重慶 北碚 400715)
?
科技與社會
社會結構變遷、社會資本轉換與農戶收入差距
謝家智1,王文濤2
(1.西南大學農村金融與農業現代化研究中心,重慶北碚400715;2. 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重慶北碚400715)
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強化了農民的跨地域性流動,使農戶社會資本具有越來越明顯的脫域性特征,但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形成及對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沒有引起關注。基于此,本文將農戶社會資本分解為地域型社會資本和脫域型社會資本,構建了社會資本影響農戶收入差距的理論分析框架。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采用再中心化影響函數(RIF)等回歸方法,多維度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研究發現,傳統的地域型社會資本并未明顯影響農戶收入差距,而脫域型社會資本更有利于農戶收入增加,進而刺激了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論文拓展了農村社會資本理論研究范疇,并為解釋社會變遷背景下的農戶收入差距找到了新的理論和經驗證據。
社會結構變遷;脫域型社會資本;收入差距;再中心化影響函數回歸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現有研究更多關注城鄉收入差距。然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時間和空間維度都呈現出明顯上升趨勢,突出表現為農村基尼系數的擴大以及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的滯后(如圖1所示)*圖1顯示,衡量收入差距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2407上升到了2012年的0.3867,日益逼近國際警戒線0.4;同時,2000-2013年間,按五等份分組的高收入農戶(前20%)的人均純收入增長了近3.1倍,而低收入農戶(后20%)的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2.2倍。。沿襲經典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已有研究多關注正式制度安排下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等對農民經濟產出的影響,而忽視了農戶收入差距形成與擴大的社會性誘因。Granovetter曾明確指出,任何個體的經濟行為總是嵌入于其生活的社會網絡之中,也必然會受到諸如社會關系、規范、信任等社會資本潛移默化的影響[1]。因此,忽略了嵌入于市場的社會資本特征,僅僅依靠市場機制來解決農民收入分配問題是存在理論不足的。
事實上,中國農村是一個典型的“關系型”社會[2]。對于受經濟和體制限制的農村居民而言,社會資本不再僅僅是維持社會運轉與利益協調的一種非正式契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日益成為信息分享與資源配置的一種替代機制。尤其在信息相對閉塞、流動性較弱的貧困地區,利用社會資本將各種資源進行有效配置以實現其福利改善顯得尤為重要。大量實證研究也肯定了社會資本在促進交易完成、增加農民收入、降低農村貧困發生率、緩解農村家庭脆弱性等方面的積極功能[3-5]。
然而,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學術界尚且存在較大爭議。Grootaert最早提出“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這一論斷,強調社會資本對窮人或貧困地區更加有利[6]。在隨后的研究中,Ram等對此提供了經驗證據[7]。但是,一方面,Cleaver發現社會資本對窮人產生了結構性的排斥效應,導致窮人無法依靠社會資本機制脫貧[8];另一方面,社會資本更為豐富的“精英”家庭往往憑借其“關系”優勢扭曲市場規則,從而為自己謀得更多的機會和報酬[9]。因此,社會資本更有可能是“富人的資本”,甚至成為惡化農戶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0]。對此,周曄馨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多維概念,應當構建出涵蓋多層次的綜合度量指標[11]。然而,這種做法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綜合指數構建方式的不同將限制研究結論的可比性與推廣度。Grootaert通過相乘的方法構造社會資本的綜合衡量指標[6];而周曄馨則采用的是因子分析法賦權的加權平均[11]。此外,由于社會資本的概念與內涵往往是變動著的,因此,過于籠統地使用一個異質性指數來反映動態性概念本身就是值得詬病的[12]。所以,更多的學者認為,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分布的影響具有明顯差異[13-14]。因此,在研究社會資本對收入差距的作用機理時不能忽視社會資本的異質性,應重視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細致分解,將社會資本的不同類型和層次納入模型進行綜合考量。

圖1 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時間趨勢圖資料來源:《中國住戶調查年鑒》和《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各期。
此外,值得高度重視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面深化的社會改革導致農村的社會結構和農民的社會網絡特征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5]。首先,社會交往的方式與范圍日趨脫域化。所謂的“脫域”(disembedding),指的是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16]。也就是說,受信息化、網絡化的影響,以及伴隨社會流動性的增強,農民的社會交往逐漸擺脫地域的壁壘,交往的方式和空間得到大幅延展。其次,社會資本的類型與結構日益多元化。社會關系的脫域屬性使得農村傳統的“差序格局”①狀態出現松動,深刻改變了農戶的社會資本形態。隨著現代社會脫域機制的日臻完善,脫域型社會資本逐漸成為農民社會資本的主要形式[17]。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農戶社會資本的收入效應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其一,現有文獻多從整體視角管窺社會資本的經濟效應,而缺乏對社會資本異質性的考究,尤其是在農村社會變遷過程中農戶社會資本的新特征與新趨勢,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相關的理論研究與經驗證據都比較匱乏。農村社會變遷將引起農戶社會資本形態發生什么樣的變化?社會資本的不同形式對農戶收入差距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事關社會資本理論在中國農村變遷情境中的拓展與應用,更關乎中國緩解收入差距矛盾政策的制定與評價。其二,基于田野調查數據,從微觀層面探討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形成機理的文獻相對較少,而涵蓋中國大部分省域農戶數據的研究更是十分鮮見。本文采用一項全國性調查數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基于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背景,研究脫域型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差距的作用機理及渠道。
① “差序格局”是費孝通先生對中國鄉土生活中的社會關系格局的總結。與西方農村社會的“團體格局”不同,中國的鄉村社會是以“倫理本位”和“人情關系”為導向的“熟人社會”,個人的社會關系是以“己”為中心的、親疏有別的“波紋”,恰如一顆投在水面上的石子。
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1)將農戶社會資本分解為脫域型社會資本和地域型社會資本,不僅拓展了農村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范疇,而且更為準確地把握社會結構變遷背景下的農戶社會資本的屬性與特征。(2)發現了脫域型社會資本和地域型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差距的不同影響,為解釋社會變遷背景下的農戶收入差距找到了新的理論和經驗證據。(3)采用多種手段處理社會資本的內生性偏誤等問題。一方面,在社會資本度量指標的選擇上避免產生與收入或收入差距的聯立性;另一方面,采用新近發展起來的再中心化影響函數回歸方法(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簡稱RIF回歸)以弱化由遺漏變量等引起內生性問題的可能性,從而得到更加穩健、可靠的估計結果。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一)社會結構變遷與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形成
伴隨農村地區社會結構變遷,農村居民的社會關系特征呈現出分化和異質性的傾向,由此導致農村社會資本出現新的特征和趨勢。根據美國學者Nelson提出的“三力作用模型”,人地關系的改變、信息科技的發展與農村人口的流動是農村社會變遷的內在作用機制[18]。而這三種“力”的合力又會強化社會關系網絡的脫域機制,從而深刻改變農民之間的交往方式,影響到農戶社會資本的形態。因此,在農村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中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形成機理可以繪制為如圖2所示。

圖2 農村社會結構變遷與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形成機理
1.人地關系改變驅動的農民社會關系質量的提升與范圍的擴大為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形成奠定基礎與條件
傳統農村地區人們的社會交往大多被拘囿在相對封閉的狹小社區,農民的社會關系具有非常明顯的“同質性”(homophily)特征;戶籍制度更是割裂了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的交往空間,限制了農村居民分享社會網絡外部性收益的能力[19]。社會交往的“同質性”與戶籍制度的壁壘導致農民的社會資本不僅存量欠缺而且質量偏低。因此,在中國典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條件下,如果農民能夠通過社會網絡動員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資源,將是其社會資本質的跳躍[20]。究其原因,社會網絡的異質性更能體現社會資本的質量,并能夠為農戶帶來更多的經濟回報。所以,當人地關系的改變使得農民能夠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時,理性的農民會選擇脫離原有的封閉性、同質性的社會網絡,而積極擴展自己的開放性、異質性的網絡關系,從而提升社會資本的數量與質量。
2.以信息化為主要特征的科技發展客觀上更新了可供農村居民社會交往的工具選擇
在鄉土文化中,農村居民的人際交往主要以“面對面”(face-to-face)的直接交流為主,這樣的人際傳播方式是低效、單一、封閉的。然而,在信息化的社會背景下,隨著手機、網絡、媒體等傳播媒介的普及,農民之間的交往與互動模式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面對面”形式,而是更多依賴于信息網絡技術的間接交流方式。信息科技的發展不斷豐富著農民之間的交往工具。交往工具的多樣化不僅降低了農村勞動力獲取外界信息的交易成本,而且為農民突破空間距離的限制、重構新的人際關系網絡提供便利,從而加快了農民的脫域進程與融入速度。
3.由農村人口的跨區域流動導致的農民社會網絡在廣度與深度上的延展加速了脫域型社會資本的積累
伴隨農村社會結構變遷進程的推進,中國正經歷著人類和平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農村勞動力遷移。農村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是近年來中國農村地區社會結構變革最顯著的特征[21]。社會流動性的增強不僅擴大了農村居民的社會交往半徑,并從中獲取更多的異質性網絡資源,從而加寬農民社會資本的廣度;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本質上是職業流動的過程[22],流動經歷的增加有助于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和社會網絡資源,提高農村勞動力與工作的匹配度,并產生基于業緣的新型社會資本形態[13],從而加深農民社會資本的深度。農戶社會網絡廣度和深度的延伸又會深刻改變農村的社會關系結構,使得農村社會從基于“倫理”與“人情”的“熟人社會”向基于“信任”與“契約”的“市場社會”轉變,從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向人際關系的“理性傾向”邁進。
因此,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變遷促進了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形成。與農村原有的基于血緣與地緣關系形成的地域型社會資本相比,脫域型社會資本是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以業緣和更廣闊的就業空間為基礎、以間接交流為主要手段而積累的異質性網絡資源,具有質量高、融合性強、邊界開放等特征。因此,脫域型社會資本涵蓋了“空間流動”、“職業轉換”、“業緣關系”三個維度。其中,農民空間上的流動打破了社會網絡的地域限制,拓展了農民社會網絡的廣度;農民由傳統的農業勞動者向非農就業者的職業轉換,客觀上加速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市場規范向傳統農業社會的倫理規范的滲透;與基于血緣的“差序格局”相比,基于業緣關系的社會信任具有更為明顯的理性化傾向。
(二)脫域型社會資本與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
脫域型社會資本通過信息獲取、知識分享、教育機會、金融參與等渠道的差異性而影響收入差距(如圖3所示)。
1.信息獲取
農村勞動力的務工收入已成為農戶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本質上是職業流動的過程[22],能否獲取到有關非農工作的人際關系網絡和有效信息是農民是否能夠謀求到職業以及獲得的務工收入多寡的一個重要因素*使用社會關系作為謀職手段的勞動者比重由20世紀70年代的20%一路飆升到2009年的80%,近幾年這種趨勢表現地依然明顯[23]。。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外出遷移,農民的社會網絡在地域外得到拓展,可供其操控的資源運作空間與創收空間也更為寬廣,從而增加外出農民找到合適工作的機會;另一方面,擁有脫域型社會資本的農民通過與來自不同網絡的人進行交流,不僅節省職業搜尋成本,而且能夠增加可獲得的信息量,從而促使其找到收入相對更高的工作;此外,異質性社會資本本身也是傳遞個體能力信息的一種有效工具,并能夠影響到個體對信息的甄別能力與處理過程[24],因此,即使面對相同的信息,擁有脫域型社會資本的農民能夠做出更快捷、更精確的反應。
2.知識分享
知識和技能是影響職位獲得與職業流動的關鍵性要素[25]。社會資本通過促使群體內、群體間的相互學習,共同分享知識與技能信息,有利于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升[26]。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農村居民在城市的學習與再社會化過程,一方面,這部分農民得以擴展其“弱關系”(weak ties)網絡,從而獲得更多的就業渠道與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在同效率更高的人進行知識與技能交流時,他們也能提升自己的知識與技術含量[27],從而增強與高收入回報工作的契合度。因此,脫域型社會資本的開放性、異質性特征能夠為其運作者帶來與傳統的地域型社會網絡相異的知識與技能信息,使得他們的收入水平傾向于向上流動。
3.教育機會
區域間不平等的教育機會是導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28]。在教育機會的獲取過程中,家庭的社會資本狀況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29]。不同階層的家庭占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與質量都存在較大差異,相應地在能夠獲得的教育機會上也會存在明顯差距。尤其對于擁有脫域型社會資本的農民而言,一方面,跨地區的社會流動為其選擇更優質的教育資源提供了渠道與空間;另一方面,在與城市當地居民的交流過程中能夠接觸到更先進、更科學的教育理念,增加其對高質量教育的需求,從而促使其增加教育投入。教育數量與質量的不同又會通過生產率差異[30]、創新能力差異[31]等渠道拉大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4.金融參與
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持有者在金融參與能力方面更具競爭優勢。其原因在于:其一,脫域型社會資本的高質量屬性為分散投資風險、改變風險偏好、降低風險損失等提供條件,顯著弱化農戶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變數;其二,社會網絡半徑的擴大不僅能夠帶來更多的非正規金融支持[32],同時也提高了居民參與股市等金融市場的可能性[33],增加了農民的資產性收入;其三,交往工具的多樣化降低了獲取金融信息的成本,加速了居民的金融知識儲備,而金融知識不僅是參與正規金融交易的鑰匙,更是促進家庭主動創業的重要變量[34]。

圖3 脫域型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差距的作用機理
因此,脫域型社會資本通過信息優勢、知識(技能)含量、教育質量、金融手段等渠道對農村收入差距產生影響。與限制在農村狹小地域的農民相比,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擁有者在收入向上流動中更具比較優勢。據此,本文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
假設1:與地域型社會資本相比,脫域型社會資本更有利于農戶收入增加,進而刺激了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
Wetterberg指出,個體運用社會資源的能力不僅受到可獲得的社會資本的種類及數量的影響,更取決于在既定環境中這些既有社會資本種類之間的關系[35]。因此,為了明晰社會資本作用于農戶收入差距形成與擴大的機制,有必要探討農民傳統的地域型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與脫域型社會資本不同,地域型社會資本主要建立在血緣、地緣的基礎上,關系網絡也局限于親朋、鄰里,是一種具有交往頻繁、互惠性強、情感深厚、相對封閉等特征的強關系網絡。雖然這種同質性社會資本具有“共渡患難”的功能。但是,與脫域型社會資本相比,其資源重復且含金量偏低,甚至還可能限制農民的自由發展空間。此外,中國的市場化是一種社會資本嵌入式的發展過程[36],市場化進程也會改變原有的地域型社會資本的作用空間。在市場化進程中,伴隨農村居民的大規模遷移,曾經聯系緊密的家族與宗族型農村社區開始出現“空心化”趨勢,留守成員之間相互觀察、模仿的學習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從而限制了農村社區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收入增長空間;同時,遷移農民的“候鳥式”生活方式導致農村原有的基于血緣與地緣的地域型社會資本結構只能“間歇式”地存在于春節這么一個簡短的時間段內[37],難以形成常態化。因此,在由市場化誘導的農村社會變遷進程中,農民的地域型社會資本對窮人收入的保障作用將會被弱化。陸銘等的研究表明,在市場化進程中,中國農村地區運用社會資本來抵御自然災害與社會風險的功能被減弱了[38]。所以,對于缺乏脫域型社會資本的農村居民來講,由于其掌握的社會資源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并且其社會網絡在市場機制深化過程中被某種“社會共識”(tacit knowledge)所取代,從而弱化了地域型社會資本化解農戶收入差距矛盾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假設2:傳統的地域型社會資本并未明顯影響農戶收入差距。
三、理論模型
為從數理上推導脫域型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本文構建如下的兩期“社會資本投資模型”:第一階段,農民在從事工資性勞動和進行地域型社會資本投資之間進行時間分配;在第二階段,農民決定是否投資于脫域型社會資本,并將總時間在勞動和脫域型社會資本(或地域型社會資本)積累之間重新分配。個體從實物消費和社會交往中獲得效用,即農民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U=u(C1,S1)+βu(C2,S2)
(1)
其中,Ct為第t期的消費量,S1和S2分別代表農民的地域型社會資本存量與脫域型社會資本存量,β為貼現系數。為后文分析方便,本文沿襲現有文獻的做法,假設農民的效用函數可分[39],即式(1)可簡化為:
U=aC1+v(S1)+β·(aC2+v(S2))
(2)
其中,a>0,v′(·)>0,v″(·)<0。進一步,將函數v(·)以C-D形式表示,即有:
(3)
其中,b>0,ξ>0,下標t=1,2分別代表的是地域型社會資本與脫域型社會資本。將式(3)代入式(2),得到農民效用函數的簡化形式為:
(4)
下文將主要以式(4)所示的簡化效用函數形式為基礎進行分析。在第一階段,農民將總時間L分配為工作時間(Lw1)和培育地域型社會資本時間(Ls1)兩部分。工資率用w表示。假設第一階段開始時農民的地域型社會資本稟賦S1是給定的,第二階段的脫域型社會資本存量S2在地域型社會資本的基礎上拓展而成,定義為原始社會資本與后天培育的社會資本之和,即得到:
S2=(1+δ)S1
(5)
假設社會資本存量與農民投入到社會資本積累中的時間成正比,簡單起見,定義社會資本的積累方程如下:
St=Lst
(6)
根據已有文獻的通常做法,本文建立C-D形式的家庭生產函數,即:
Y=AKmHn
(7)
其中,m,n∈(0,1),K和H分別代表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的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借鑒李清政等的設定,假設社會資本通過倍化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參與生產活動[40],即有:
K=SθK0
(8)
H=SηH0
(9)
其中,θ,η>1,K0和H0分別為農民的物質資本稟賦與人力資本稟賦。將式(8)和式(9)代入式(7),得到:
Y=A(SθK0)m(SηH0)n
(10)

(11)
其中,α度量的是社會資本的收入倍增效應,且α≥1。
在此基礎上,如果農民i在第二階段考慮進行脫域型社會資本投資,其面臨的決策問題如下:
s.t.S2=(1+δ)S1
(12)
在式(12)的基礎上構建的拉格朗日函數為:
(S2-(1+δ)S1)
(13)
其一階條件為:
(14)

(15)
那么,進行脫域型社會資本投資的農民i在兩個階段中獲得的總收入為:
(16)
其中滿足下式成立:
(17)
(18)
同理,假設農民在第一階段的時間分配是最優的,那么,不進行脫域型社會資本投資的農民j在第二階段將維持第一階段的投資策略,則農民j的總收入可以表示為:
(19)
由式(16)和式(19)可以得到,農民i(進行脫域型社會資本投資)與農民j(不進行脫域型社會資本投資)的收入差距為:
(20)
參照已有文獻的研究成果,并結合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踐,對主要參數進行賦值*B的賦值參照了周京奎、黃征學的研究成果[41];α的賦值參照了李清政等的設定方法[40];其余參數的賦值參照了Mogues and Carter[39]、Mogues[42]等文獻的做法。:
w=0.6,L=2,β=0.95,ξ=0.25,S1=Sw1=1,B=1,α=1
(21)
在式(21)的賦值條件下,得到農民i與農民j的收入差距Δy為:
Δy=0.0911>0
(22)
式(22)表明,與只具有地域型社會資本的農民相比,進行脫域型社會資本投資的農民獲得了更高的收入回報,即脫域型社會資本刺激了農民群體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這與本文的理論研究假設是一致的。
事實上,通過α的不同取值而得到的收入差距Δy的數值模擬結果顯示(見圖4),伴隨社會資本的收入倍增效應的強化,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收入回報逐漸增加,農民群體間的收入分化趨勢愈加明顯。

圖4 不同α取值下的收入差距數值模擬結果
四、實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篩選
本文所使用的實證數據來源于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發起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年的數據。為了剔除無效值、缺省值等對結果的影響,本文根據實證研究的需要對樣本進行篩選:(1)保留樣本類型為“農村(村委會)”的樣本;(2)剔除農戶家庭收入、社會資本等變量存在缺失的樣本;(3)剔除年齡大于65或小于18周歲的樣本;(4)剔除數據存在明顯紕漏的樣本,如外出勞動力人數占家庭總勞動力規模的比例大于1等。經過上述處理過程,最終得到的有效樣本量為3447個,覆蓋全國25個省份。
(二)內生性處理與實證模型設計
現有研究社會資本的收入效應的文獻大多忽略了由內生性問題所誘導的估計偏差[11]。本文在回歸模型的設計中通過以下兩種手段來處理社會資本的內生性偏誤問題:
(1)社會資本度量指標的選擇上盡量避免與收入或收入差距的聯立性。一方面,使用綜合指數以弱化社會資本潛在的內生性影響。本文根據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概念界定,基于“空間流動”、“職業轉換”、“業緣關系”三個維度構建脫域型社會資本的評價體系,采用因子分析與熵權法相結合的賦權方法加權得到脫域型社會資本綜合指數*賦權方法的具體操作手段請參照謝家智等[43]。,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會資本內生性問題。另一方面,本文從“老鄉信任”與“鄰里關系”視角構造地域型社會資本的度量指標。這是因為,信任與關系融洽程度能夠減輕社會資本的聯立內生性問題[36]。相關變量的含義及賦值方法見表1。
(2)采用再中心化影響函數回歸方法(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簡稱RIF回歸)以降低產生內生性問題的可能性。與傳統的OLS回歸相比,由Firpo et al提出的RIF回歸的估計結果更加穩健,能夠有效弱化由遺漏變量等引起的內生性問題[44]。而且,RIF回歸方法能夠反映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各種分布統計量(均值、方差、基尼系數等)的邊際影響*以分位數為統計量的RIF回歸又稱為“無條件分位數回歸”(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簡稱UQR)。詳細的處理過程請參照Firpo et al[45]。,在對群體收入分布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具有其它方法無法比擬的優勢。其中,基尼系數是度量收入不平等的常用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
νGini(FY)=1-2μ-1R(FY)
滿足:
(23)
p(y)=FY(y)
定義基尼系數的影響函數(influence function)為:
IF(y;νGini)=A2(FY)+B2(FY)y+C2(y;FY)
滿足:
A2(FY)=2μ-1R(FY)
B2(FY)=2μ-2R(FY)
(24)
C2(y;FY)=-2μ-1[y[1-p(y)]+GL(p(y);FY)]
在式(23)和式(24)的基礎上可以得到基尼系數的再中心化影響函數(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如下:
RIF(y;νGini)=1+B2(FY)y+C2(y;FY)
(25)
Firpo et al[44]對上式的估計過程給出了詳細的討論,在此不再贅述。將農村家庭收入對數的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以社會資本、家庭與戶主的社會人口學特征為解釋變量進行RIF回歸,可以找出影響農戶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在RIF回歸方法的框架下,本文構建的農戶收入差距模型的形式如下:
Gini(Income)=α+β1DSC+β2ESC1+β3ESC2+βX+μ
(26)
上式中,Gini(Income)為農戶收入對數的基尼系數,DSC為脫域型社會資本,ESC1和ESC2分別代表地域型社會資本的兩個度量指標,X為控制變量。變量的具體含義與賦值方法見表1。
(三)變量設定與描述性統計
參照已有研究成果的經驗[46-47],本文在實證過程中進一步控制了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人力資本、政治資本、外出勞動力比例等變量。指標含義及賦值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變量的設定與賦值方法
表2匯總了采用多種度量指標計算出的農村家庭收入差距。以最常用的基尼系數為例闡述:全部樣本的農戶總收入基尼系數為0.4698,大于國家統計局的結果0.3783,但小于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估算結果0.61*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的數據估算,2010年農村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61。數據見于該中心于2013年發布的《中國家庭收入差距報告》。,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過比較各項收入來源的不平等程度發現,農村家庭的財產性收入差距最大,其次為轉移性收入差距、工資性收入差距,最小的為經營性收入差距,表明非農收入差距是導致農戶收入分布不均的主要誘因。

表2 農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注:為了使得本文的收入差距計算結果與現有研究具有可比性,本表采用家庭收入的絕對量得到相關結果。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農戶總收入差距模型的估計結果
本文采用Firpo et al[44]提出的再中心化影響函數回歸方法(RIF),實證檢驗脫域型社會資本、地域型社會資本等變量對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表3是以基尼系數作為不平等衡量指標的農戶總收入差距模型的RIF估計結果。從表3的結果可以發現,脫域型社會資本(DSC)的估計系數為正,并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脫域型社會資本刺激了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即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1。地域型社會資本(ESC1與ESC2)的估計系數均為負,但只有以鄰里關系度量的地域型社會資本(ESC2)的估計結果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一旦控制了在農村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中形成的脫域型社會資本,原有的地域型社會資本緩解農戶收入差距矛盾的作用將會被弱化,從而本文的研究假設2也得到佐證。事實上,這一實證結果與林南的社會資本回報理論并不沖突[15]:脫域型社會對農民的影響更多體現的是社會資本的“工具”屬性,即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額外的經濟回報;而地域型社會資本則更偏向于社會資本的“情感”屬性,其目標在于鞏固和維護現有的社會網絡資源,帶來的回報更多表現為身心健康、生活滿意等主觀幸福感層面[48]。
控制變量中,以年齡(Age)衡量的“經驗”是擴大農戶收入差距的變量,顯示出農村勞動力以經驗優勢彌補學歷劣勢現象的存在[49]。受教育程度(Edu)、身體健康狀況(Health)、相對經濟狀況(Status)、婚姻狀況(Marr)、外出勞動力比例(Labor)等是緩解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這與現有研究的結論基本一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沒有發現參與合作社(Coop)能夠縮小農戶收入差距的證據,這其中的機制可能是由于存在合作社對小規模農戶的入社限制,從而弱化了參與合作社、互助組等行為對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50]。

表3 農戶總收入差距模型的估計結果
注:1.小括號內為相應變量的t統計量
2.***、**、*分別代表在1%、5%、10%水平上顯著。
(二)分區域的估計結果
“區域異質性”是討論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時必須加以考慮的因素之一。表4報告的是分區域的農戶總收入差距模型的RIF估計結果。表4的結果顯示,脫域型社會資本(DSC)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在中西部的結果中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脫域型社會資本加劇了農戶收入分布不均的矛盾,并且這種拉大效應對于來自中西部的農戶而言更為顯著。地域型社會資本(ESC1與ESC2)的估計系數依然均為負值,且僅有模型(12)中的鄰里關系指標(ESC2)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與前文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即農村居民積累的傳統社會資本在改善農民群體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已經被弱化了,尤其對于東部地區市場化參與程度更高的農村居民而言,地域型社會資本并未顯著影響農戶的收入差距。

表4 農戶總收入差距模型的分區域估計結果
注:1.小括號內為相應變量的t統計量
2.***、**、*分別代表在1%、5%、10%水平上顯著。
(三)分收入來源結構的估計結果
上文分析了社會資本對農戶總收入差距的整體影響及區域差異,而基于農戶收入來源結構差距的進一步討論,有助于理解社會資本等因素影響農戶收入差距的機理及渠道。根據農村居民收入來源的結構,農戶收入差距可以分解為經營性收入差距、工資性收入差距、財產性收入差距與轉移性收入差距四部分。表5匯總的是各個農戶收入來源差距模型的RIF估計結果。從表5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脫域型社會資本(DSC)在經營性收入差距模型和轉移性收入差距模型中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而在財產性收入差距模型中為顯著的負值,顯示出脫域型社會資本主要通過拉大農村居民群體間的經營性收入差距與轉移性收入差距來刺激農戶總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脫域型社會資本具有緩解農戶間財產性收入差距矛盾的作用。地域型社會資本(ESC1與ESC2)的估計結果與表3的結果基本一致。

表5 農戶收入來源結構差距模型的估計結果
注:1.小括號內為相應變量的t統計量
2.***、**、*分別代表在1%、5%、10%水平上顯著。
(四)穩健性檢驗及進一步分析
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通過以下三個途徑進行穩健性檢驗:
(1)借鑒Grootaert等文獻的做法[6],將“老鄉信任”(ESC1)與“鄰里關系”(ESC2)合并為一個綜合指數來反映地域型社會資本(ESC)。
(2)在實證性的文獻中,方差也是反映經濟不平等的常用指標。因此,本文采用方差作為農戶收入差距的度量指標。
(3)為了控制各個地區信息化發展程度差異對于農戶脫域型社會資本積累與收入差距的內生性影響,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局統計科研所信息化統計評價研究組提出的“信息化發展指數”(IDI)作為區域分組的依據[51]。以信息化發展指數的中位數為臨界值,高于該臨界點的省域劃歸為信息化程度高的區域;反之則是信息化程度低的區域。
穩健性檢驗的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表6的結果與前文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即脫域型社會資本(DSC)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而地域型社會資本(ESC1、ESC2或ESC)在大多數模型中的估計系數為不顯著的負值。說明將農戶社會資本分解為脫域型社會資本與地域型社會資本后,傳統的地域型社會資本并未明顯影響農戶收入差距,相比之下,脫域型社會資本更有助于農戶收入增加,從而刺激了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因此,穩健性檢驗的結果進一步印證了本文研究假設的成立。

表6 穩健性檢驗
注:1.小括號內為相應變量的t統計量
2.***、**、*分別代表在1%、5%、10%水平上顯著。
進一步,Lin基于資本視角指出,社會資本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過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資本欠缺(capital deficit);二是回報欠缺(return deficit)[15]。其中,資本欠缺指的是由投資和機會的不平等導致了不同個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與質量不同,進而形成了群體內的收入差距;回報欠缺指的是一定數量的社會資本在不同的個體間產生了不同的收入回報,其形成的原因在于不同個體在動員策略、行動努力或制度性反應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為了分析脫域型社會資本影響農戶收入差距的過程,本文進一步考察了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擁有量與回報率在不同收入群體中的分布狀況。一方面,針對脫域型社會資本擁有量的分布問題,本文將收入劃分為10個分位區間,然后計算各個分位區間的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平均值,相關結果匯總為圖5(a)。另一方面,針對脫域型社會資本回報率的分布問題,本文遵循周曄馨的做法[11],以農戶收入的對數值(Income)為被解釋變量、以社會資本以及相關控制變量為解釋變量,通過在0.01-0.99分位點上進行99次無條件分位數回歸,得到不同收入分位點上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收入回報率的變化規律,從而比較窮人和富人脫域型社會資本的經濟回報率的特征及差異,相關結果匯總為圖5(b)和(c)。圖5(a)顯示,脫域型社會資本與收入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富人擁有更多的脫域型社會資本。圖5(b)和(c)的回歸結果表明,脫域型社會資本的估計系數呈現出伴隨收入分位點增加而逐漸上升的趨勢,而且,估計系數在大部分分位點上均是顯著的,即富人從脫域型社會資本中獲得了更高的收入回報率。綜上所述,低收入農戶脫域型社會資本的擁有量與回報率均顯著低于高收入農戶。因此,脫域型社會資本刺激了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圖5 不同收入分位點上脫域型社會資本擁有量與回報率差異注:1.上面三個圖中的橫軸代表的是收入的分位點2.圖(a)中,散點標注的是各個收入分位點上脫域型社會資本擁有量的平均值,曲線代表的是這些散點的二次擬合曲線;圖(b)中,散點標注的是99個分位點上脫域型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曲線代表的是這些散點的二次擬合曲線;圖(c)中,散點標注的是99個分位點上脫域型社會資本回歸系數所對應的P值。估計技術采用的是Firpo et al提出的無條件分位數回歸[45],抽樣方法采用的是200次Bootstrap。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大量的理論研究表明,市場中個體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1],社會關系顯著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與行為結果。因此,農戶的社會關系網絡對農戶收入差距形成及擴大具有內在影響。特別是,中國正在持續經歷的社會結構變遷背景下,聚焦于社會資本作用于農戶收入差距機理的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與大多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重點關注社會資本異質性的特征和事實,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地域型社會資本和脫域型社會資本,構建社會資本影響農戶收入差距的理論分析框架,并提出“與地域型社會資本相比,脫域型社會資本更有利于農戶收入增加,進而刺激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與“傳統的地域型社會資本并未明顯影響農戶收入差距”兩個研究假設。基于兩階段社會資本投資模型的理論推導結果證實了研究假設的成立。另外,本文采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農村樣本數據,運用再中心化影響函數(RIF)等回歸方法,從整體影響、區域差異、來源結構等多維度實證檢驗本文的兩個研究假設。最后,通過構建綜合指數、采用方差指標、控制信息化程度等角度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到與前文相一致的估計結果,進一步佐證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與地域型社會資本相比,由社會結構變遷而形成的脫域型社會資本更有利于農戶收入的增加,從而加劇了農戶收入差距的擴大。因此,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脫域型社會資本逐漸成為農民社會資本的主要形態,農村傳統的基于地緣、血緣形成的地域型社會資本的經濟功能將遭遇到發展的“瓶頸”,甚至可能會出現一些負面的影響,如對“外人”的排斥效應、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擠占效應等。如果不加以引導,農村地區的貧困“自我復制”問題將會凸顯。論文的研究發現了農戶收入差距擴大新的理論機理和渠道。因此,農民收入差距的調控,特別是農村精準扶貧的政策研究,更應該關注農村社會結構變遷中社會關系管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決策層應重視通過改革與創新戶籍制度、農村土地流轉制度、農民的教育與培訓制度、農民工市民化制度,以及加強農村地區的通訊、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順暢農民社會交往的渠道,擴大交流機會,降低交流成本,在市場化進程中,加速農民的社會化質量和效率,縮小農戶間的社會化差距。
[1]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2]梁漱溟. 中國文化要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ZHANG Jian, GILES J, ROZELLE S. Does it pay to be a cadre—estimating the returns to being a local official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3): 337-356.
[4]MACCHIAVELLO R, MORJARIA A. The value of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a supply shock to Kenyan rose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9): 2911-2945.
[5]楊文,孫蚌珠,王學龍. 中國農村家庭脆弱性的測量與分解[J]. 經濟研究,2012(4): 40-51.
[6]GROOTAERT C.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n integrated questionnaire[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4.
[7]RAM R. Social capital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2013, 41(1): 89-91.
[8]CLEAVER F. The ine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hronic poverty[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6): 893-906.
[9]李樹,陳剛. “關系”能否帶來幸福?——來自中國農村的經驗證據[J]. 中國農村經濟,2012(8): 66-78.
[10]趙劍治,陸銘. 關系對農村收入差距的貢獻及其地區差異——一項基于回歸的分解分析[J]. 經濟學(季刊),2010,9(1): 363-390.
[11]周曄馨. 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嗎?——基于中國農戶收入的經驗證據[J]. 管理世界,2012(7): 83-95.
[12]SABATINI F. Social capital as social networks: a new framework for measurement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t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9, 38(3): 429-442.
[13]葉靜怡,周曄馨. 社會資本轉換與農民工收入——來自北京農民工調查的證據[J]. 管理世界,2010(10): 34-46.
[14]王春超,周先波. 社會資本能影響農民工收入嗎?——基于有序響應收入模型的估計和檢驗[J]. 管理世界,2013(9): 55-68.
[15]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吉登斯. 現代性的后果[M]. 田禾,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17]蘭亞春. 居民關系網絡脫域對城市社區結構的制約[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4): 122-128.
[18]NELSON P 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4): 395-407.
[19]DIMAGGIO P, GARIP F. How network externalities can exacerbate intergroup inequal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116(6): 1887-1933.
[20]邊燕杰,王文彬,張磊,等. 跨體制社會資本及其收入回報[J]. 中國社會科學,2012(2): 110-126.
[21]蔡昉. 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 經濟研究,2010(4): 4-13.
[22]GERBER T P, MAYOROVA O. Getting personal: networks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Russian labor market, 1985-2001[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116(3): 855-908.
[23]程誠,邊燕杰. 社會資本與不平等的再生產:以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的收入差距為例[J]. 社會,2014(4): 67-90.
[24]JIN Dawei, WANG Haizhi, WANG Peng, et al. Social trust and foreign ownership: evidence from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6, 23(C): 1-14.
[25]吳愈曉. 社會關系、初職獲得方式與職業流動[J]. 社會學研究,2011(5): 128-152.
[26]HASAN S, BAGDE S. The mechanics of social capital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an Indian colle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 78(6): 1009-1032.
[27]LUCAS R E Jr.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5): 85-88.
[28]吳曉剛,張卓妮. 戶口、職業隔離與中國城鎮的收入不平等[J]. 中國社會科學,2014(6): 118-140.
[29]趙延東,洪巖璧. 社會資本與教育獲得——網絡資源與社會閉合的視角[J]. 社會學研究,2012(5): 47-68.
[30]SERRA T, POLI E. Shadow prices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India,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5, 240(3): 892-903.
[31]AK?OMAK I S, WEEL B T. Social capital, innovat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Europ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9, 53(5): 544-567.
[32]馬光榮,楊恩艷. 社會網絡、非正規金融與創業[J]. 經濟研究,2011(3): 83-94.
[33]王聰,柴時軍,田存志,等. 家庭社會網絡與股市參與[J]. 世界經濟,2015(5): 105-124.
[34]尹志超,宋全云,吳雨,等. 金融知識、創業決策和創業動機[J]. 管理世界,2015(1): 87-98.
[35]WETTERBERG A. Crisis, connections, and class: how social ties affect household welfare[J]. World Development, 2007, 35(4): 585-606.
[36]王晶. 農村市場化、社會資本與農民家庭收入機制[J]. 社會學研究,2013(3): 119-144.
[37]陳波. 二十年來中國農村文化變遷:表征、影響與思考——來自全國25省(市、區)118村的調查[J]. 中國軟科學,2015(8): 45-57.
[38]陸銘,張爽,佐藤宏. 市場化進程中社會資本還能夠充當保險機制嗎?——中國農村家庭災后消費的經驗研究[J]. 世界經濟文匯,2010(1): 16-38.
[39]MOGUES T, CARTER M R.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polarized societie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5, 3(3): 193-219.
[40]李清政,劉天倫,陳子夏. 社會資本視角下家庭增收效應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 宏觀經濟研究,2014(1): 126-134.
[41]周京奎,黃征學. 住房制度改革、流動性約束與“下海”創業選擇[J]. 經濟研究,2014(3): 158-170.
[42]MOGUES T. A two-dimensional measure of polarization[R]. Washington, DC: IFPRI, 2008.
[43]謝家智,王文濤,車四方. 巨災風險經濟抗逆力評價及分布特征分析[J].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 85-93.
[44]FIRPO S, FORTIN N M, LEMIEUX T. Decomposing wage distributions using recentered in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s[EB/OL]. http://www.economics.uci.edu/files/docs/micro/f07/lemieux.pdf, 2007-06-23.
[45]FIRPO S, FORTIN N M,LEMIEUX T. 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s[J]. Econometrica, 2009, 77(3): 953-973.
[46]KEMP-BENEDICT E. Inequality and trust: testing a mediating relationship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J]. Sustainability, 2013, 5(2): 779-788.
[47]AGHION P, AKCIGIT U, BERGEAUD A, et al.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R]. London: CEPR, 2015.
[48]SARRACINO F. 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high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do happiness equations differ across countries?[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13, 42(3): 51-66.
[49]JEONG H, KIM Y, MANOVSKII I. The price of experi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2): 784-815.
[50]ITO J, BAO Zongshun, SU Qun.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China: exclusion of smallholders and potential gains on participation[J]. Food Policy, 2012, 37(6): 700-709.
[51]國家統計局統計科研所信息化統計評價研究組. 信息化發展指數優化研究報告[J]. 管理世界,2011(12): 1-11.
(本文責編:王延芳)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Social Capital Transition,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XIE Jia-zhi1, WANG Wen-tao2
(1.Research Center of Rural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has strengthened the flow of farmers across regions. As a result,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rural household has more and mor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disembedding. However,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embedding social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has not yet caused concern. Based on this, the social capital is divided into embedding social capital and disembedding social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is also built. Based on data of CGSS, and method of 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 hypotheses are carefully test from multi dimen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embedding social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however, the disembedding social capital is more favorable to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income, which will stimulate the expansion of the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farmers. The research scope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has been extended, and a ne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hange has been found.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disembedding social capital; income inequality; 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
2016-01-19
2016-05-27
本文受教育部規劃項目(12YJA790149)、西南大學決策咨詢項目(2016SWUJCZX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SWU1609239)和重慶市重點文科基地項目(16SKB041)資助。
謝家智(1967-),男,四川西充人,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研究方向:國民收入分配、農村金融與財政。
F124.7
A
1002-9753(2016)10-0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