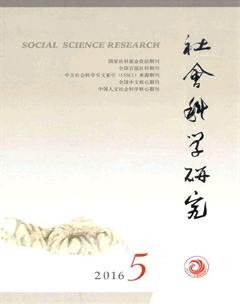大文學(xué)視野下的近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
李怡
〔主持人語〕1918年,謝無量出版了《中國(guó)大文學(xué)史》,這是中國(guó)學(xué)者在文學(xué)史著作中對(duì)“大文學(xué)”概念的最早使用。他已經(jīng)意識(shí)到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流傳的、外來的“文學(xué)”一語無法涵蓋中國(guó)文學(xué)自身的諸多現(xiàn)象,需要用“大”字來打破其“純粹”的逼仄,讓“文學(xué)”聯(lián)通古代的“文”或者“文章”,讓“純”對(duì)話于“雜”。謝無量的用詞證實(shí)著現(xiàn)代初期“文學(xué)”理念的沖突與尷尬。將近一個(gè)世紀(jì)之后,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的發(fā)展業(yè)已成熟的當(dāng)下,又有學(xué)者在盤點(diǎn)、檢視我們的學(xué)術(shù)家底之時(shí),再一次感受到了作為“藝術(shù)”的文學(xué)的種種局促,于是在2013年,楊義先生提出“以大文學(xué)觀重開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寫作的新局”,重新構(gòu)想能夠容納“通俗小說、文言詩詞、傳統(tǒng)戲曲、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大文學(xué)”格局(《以大文學(xué)觀重開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寫作的新局》)。經(jīng)過一百年的文學(xué)歸納,我們依然能夠體察到對(duì)象的豐富遠(yuǎn)非單純的概念所能夠涵蓋。
大文學(xué)之為“大”,除了前述的描述對(duì)象“增容”而外,其實(shí)還有著一個(gè)更加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對(duì)近現(xiàn)代以來作家寫作態(tài)度以及文學(xué)現(xiàn)象之時(shí)代意義的重新衡定。在今天,隨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文學(xué)諸多歷史事實(shí)的逐步澄清,我們已經(jīng)越來越清晰地意識(shí)到,近現(xiàn)代中國(guó)作家的歷史使命與近現(xiàn)代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一樣,等待他們關(guān)懷和解決的“問題”決不只是作為“藝術(shù)”的文學(xué)。在更多的時(shí)候,文學(xué)的問題、藝術(shù)的問題不得不納入更大的也更為復(fù)雜的社會(huì)歷史的總體發(fā)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說,在20世紀(jì),既然文學(xué)本來就不能獨(dú)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這一基本的歷史事實(shí),將文學(xué)的闡釋之旅融通于尋找歷史真相之旅,這里有近現(xiàn)代中國(guó)政治理想的真相、經(jīng)濟(jì)生態(tài)的真相,也有社會(huì)文化整體發(fā)展的深刻烙印。與歷史對(duì)話,將賦予文學(xué)以深度;與政治對(duì)話,將賦予文學(xué)以熱度;與經(jīng)濟(jì)對(duì)話,將賦予文學(xué)以堅(jiān)韌的現(xiàn)實(shí)生存品格。也就是說,跨出純粹的文學(xué)門檻,我們是在一個(gè)更廣闊的社會(huì)文化相互聯(lián)系的空間中勘定和闡釋近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的價(jià)值。這樣的闡釋,將使得我們過去熟悉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煥發(fā)新的價(jià)值,同時(shí),也讓一些場(chǎng)景被忽略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散發(fā)其耐人尋味的意義,或者,讓我們能夠透過一位寫作者獨(dú)特的智慧,發(fā)掘他介入歷史,與時(shí)代對(duì)話的良苦用心。這樣的話題,在過去的研究中很可能還來不及充分展開,在今天,在“大文學(xué)”的視野中,卻可以理直氣壯地成為最重要的學(xué)術(shù)命題。
本期“大文學(xué)視野下的近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專欄,圍繞這一理念展示了數(shù)篇具有大文學(xué)視野的論文:李哲從近代史研究路徑入手,通過對(duì)長(zhǎng)期以來為人們忽視的“木瓜之役”本事的考辨、分析,揭示其中的思想史意涵,管窺清末公共輿論中的權(quán)力運(yùn)作機(jī)制;康鑫從經(jīng)營(yíng)管理的角度考察民國(guó)時(shí)期民營(yíng)出版社的生產(chǎn)機(jī)制,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如何產(chǎn)生提出了新的解釋;門紅麗透過對(duì)解放區(qū)“有獎(jiǎng)?wù)魑摹爆F(xiàn)象的剖析來研討特殊的文學(xué)活動(dòng)如何參與文學(xué)的建構(gòu)。這些研究都沒有就文本談文本,就文字論文字,而是將文學(xué)的文字意義與文字背后的社會(huì)歷史的諸多背景緊緊相連,在彼此的關(guān)聯(lián)中發(fā)現(xiàn)介入精神現(xiàn)象的新的途徑。希望這樣的方法能夠?qū)τ谖覀兘裉斓闹袊?guó)文學(xué)學(xué)術(shù)有所推進(jìn),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