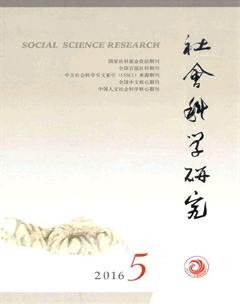“詩性倫理”導論
〔摘要〕儒家哲學建立在由詩歌表現(xiàn)出來的本真情感上。在詩情本源之上,可以依據(jù)詩的修辭建構起絕對和相對的主體性,給出倫理主體和社會規(guī)范。因此,儒學是“詩情儒學”,而儒家倫理則是“詩性倫理”。詩性倫理由“興于詩,立于禮”構成,并分別以“克己復禮”與“禮有損益”作為其規(guī)范性和時間性的維度。
〔關鍵詞〕儒學;詩情儒學;詩性倫理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6)05-0143-10
一、情感儒學
蒙培元先生曾指出:“儒家的情感哲學如果能夠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仁。儒學就是仁學。”而“為仁之本”在于如孝悌這樣的真實原始的情感。〔4〕儒學是奠基在本真的情感之上的,一切主體性或本體論的建構,都不能離開生活情感的本源。唯在此本真的領會中,人才得以成人,“真”與“善”才得以可能。
“善”的來源是哲學與倫理學追問的目標,性善論向來是儒家的主流解答。而自思孟后學以來,傳統(tǒng)的“性善論”總是建立在“性-情”的架構上,即從形而上的“性善”發(fā)出了形而下的“情”;但在孔孟儒學那里,“性”卻是以本源的“情”中確立起來的,這就有了更為先在的“情-性”架構。“性”的確立是個言說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這個絕對的主體性會將自我擴充為形而下的主體個人,并通過個人情感敘事構建起倫理話語的體系,由此才有了“性-情”的架構。
(一)儒家“博愛”論
儒家的情感通常包括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其中“欲”的出現(xiàn)最為頻繁,在《論語》中有44次,《孟子》有96次,《荀子》里有244次之多。相比之下,“樂”在《論語》中作為歡樂的情感使用,大約出現(xiàn)了十幾次,“愛”出現(xiàn)了9次,“喜”僅有5次。
《論語》中“喜”往往有直接的對象,也正因此,這種物欲化的情緒并不為孔子所提倡,如“哀矜而勿喜”,“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克制自己對物欲的喜好,甚至成為境界高低的判準;“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孔子仍然不稱其為“仁”。(《子張》《里仁》《公冶長》)既然對欲望如此貶低,為何“欲”的出現(xiàn)又極多?先秦儒家對欲既保持著極大的關注警覺,也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層次;一部分是形而下的欲求,而另一種欲則是絕對的主體性意志。比如: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
欲仁而得仁,又何怨?(《堯曰》)
通過“欲”“我”和“仁”的距離消失,主體匯入了仁。而仁往往與另一種“樂”的情感相關。從“貧而樂”“不改其樂”來看,“樂”不會因個人在俗世中的處境而改變,因而是先于主體和客體的關系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又喻示著這是與天地共在、與萬物一體的本源情感。而從“樂而不淫”可見,樂又不是無所關注的沉浸,而是有著確切的指向,對形而下的規(guī)范話語有清晰的把握。(《學而》《八佾》《雍也》)或許恰恰因為“樂”包容了在場和缺席的存在者全體,消除了主客的對立和人際的界限,才能使存在者的界限敞顯出來,并在回歸樂的情感中保持其澄明和充盈。因此,樂是動態(tài)的,蘊藏和發(fā)動著去“愛人”的主體之“欲”,而主體同時在此欲求帶來的愉悅中而返歸“樂”本身。換言之,樂就是愛人之樂,正如仁是愛人之仁;樂與仁可以互換,都是韓愈《原道》中的“博愛”(“universal love”普遍之愛)這種前主體性的情感。從仁而樂到“愛人”,是由主體性的意志——“欲”來體現(xiàn)的;欲包含了對所有人的愛,主體因這種愛欲而起,又在此愛欲中重新融入了無對待的本源之仁。仁因欲而彰顯,主體性正是以欲的方式由本源的仁所給出。
從仁樂之情開顯為“我欲”的主體性,欲的目標依然指向愛人之仁,就在主體的愛欲——“我欲”發(fā)生的瞬間,仁-欲-仁形成了一個輪回。立足于主體向前、向后觀照,其終點都是空無一物的仁;因其既無物我的對待,也無時空的始終,仁也是永恒的本源。當把這種愛欲向前觀照,就映現(xiàn)出自我對他者的愛,通過“立人”并“立己”的方式言說出來,人、我的對待就在這種愛欲的話語中產(chǎn)生了。“我欲仁”“己欲立”是在行仁的驅(qū)策中實現(xiàn)的,行仁是欲的目的,也是欲的應然性之所在,只有以行仁為目標的欲求才是善的。“我欲仁”就是把博愛落實到與人交往的行為中,使自己的愛推及所有人,讓每個人得其所宜,也即韓愈的“行而宜之之謂義”。這種普遍的適宜,也就是“欲”的價值——善的普遍性所在。
居仁由義就是這樣的主體化過程:從仁愛的情感中,通過“我欲”,分化出人、我的對待。仁-欲的轉換,在《中庸》里用“不誠無物”來表達;假如沒有誠懇的情感,就沒有任何存在者的存在。誠既是成己,也是成物,他人與自我共同出現(xiàn)在“欲仁”的情感轉化中,也就是從“博愛之仁”到“行宜之義”的過渡。主體由此具有了終極的價值性,這是情-性架構的前提。
(二)儒家“情性”論
隨著仁愛之情感轉為主體之欲,普遍的善就成為了絕對的主體性——性善論。這個絕對的人性是倫理善惡的依據(jù)。主體性的愛欲會落實到形而下的相對主體上,形成人們相互的謙讓、尊重以及角色規(guī)范;然而君子不器,相對主體又會從自我中綻出,回到“仁-欲”的主體性重建。在這個往復中,普遍之愛得以推行下去,那么這樣的相對主體可以在持續(xù)綻出中保持善的人格。如果相對主體滯迷物欲,偏離了綻出于器用的君子人格,就形成了倫理的惡。傳統(tǒng)的“性-情”架構講的是人性的善下貫為倫理的善,然而情善的根據(jù)并非什么純善的天理心性,因為性理本體的善也是在“博愛”-“欲仁”-“行義”的流轉中獲致的,這個流轉的實現(xiàn)就在于不斷回歸本源的仁愛。
①“詩”在早期常與“辭”通用,似乎專指詩歌的語言文辭,而并非后世所指詩歌的全稱。如《詩經(jīng)·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卷阿》:“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詩作為一個整體,最初被稱為謳、歌,或誦;而“詩”僅指其辭句,后逐漸衍為詩的全稱。詩發(fā)乎質(zhì)樸的語言,旨在表達誠懇的情感,如《六藝論·論詩》:“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zhì),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六藝論疏證》,〔漢〕鄭玄撰,〔清〕皮錫瑞疏,《續(xù)修四庫全書·經(jīng)部·群經(jīng)總義類》(影印本),第17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0頁。
②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言志”;《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等。多以“詩言志”出自堯舜之時,也有觀點認為,出自《虞書》的這句話是戰(zhàn)國時期的擬作,參見陳良運《中國詩學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34-40頁。
③正義曰:“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fā)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fā)見於言,乃名為詩。”《毛詩正義》,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十三經(jīng)注疏》(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頁。
④陸機:“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文賦》,〔梁〕蕭統(tǒng)編:《文選》(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240頁。
⑤上博簡《孔子詩論》,一說為子夏所著,見李學勤《詩論的體裁和作者》,《上博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54頁。另一說為子思后學的作品,見陳桐生《〈論語〉與〈孔子詩論〉的學術聯(lián)系與區(qū)別》,《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李存山《〈孔叢子〉中的‘孔子詩論》,《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無論出于哪種孔門后學,可以承認的是,《孔子詩論》是對孔子《詩》學思想的繼承和闡發(fā)。
⑥《孟子·萬章上》:“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朱熹注:“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宋〕朱熹集注:“孟子集注”,《四書集注》,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340-341頁。因此,“性-情”架構源于“情-性”,如果把這兩部分合而言之,就是本源之情—形上之性—形下之情的結構。第一個情是本源的仁愛情感,從中確立起絕對的主體性,即性善的本體論;再將主體的性善充實為人倫日用中的善的情感,從而建立起了倫理的善惡規(guī)范。
這個“情-性-情”的架構如下圖所示:
二、詩情儒學
在本源情感中確立形上的主體性和形下的主體性,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興于詩”。因為在孔子看來,詩只是本真情感的顯現(xiàn),所謂“詩情”(poetic emotion)也只是由詩歌所表現(xiàn)的本真情感。而這正是儒學的基本特征:本真的情感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而此情感由詩來表現(xiàn)。《易·乾》“文言傳”中的“修辭立其誠”①,講述的正是以語言的形式,將誠摯的情感抒發(fā)于筆端,并建構起主-客對待的人倫體系。
《尚書·堯典》中有“詩言志”,這句話同樣流傳于諸多先秦文獻中。②《詩大序》對此進行了闡發(fā):“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③陸機《文賦》也指出:“詩緣情。”④無論言志還是緣情,詩都是本真情感的顯現(xiàn),表達著主體的情感志意;從“情動于中”到“在心為志”“而形于言”,主體心性是在情-志的轉化中,通過訴諸詩的語言而確立的。而孔子的“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孔子詩論》)⑤,則指出了做詩不能遮掩本真的情感、偏離主體的意志,而務必保證主體性的言說充分而暢達。因此,孔子從《詩經(jīng)》刪去了對主體性有所蔽塞的修辭表達,確立起“興觀群怨”的詩學理念,作為儒學的主體性話語的表率。
主體性是從詩的言說中興起的,由此才能在主體的觀照中構建群體的世界,并產(chǎn)生個人的訴求、感懷,甚至怨嘆。做詩是這樣一個由情入理、創(chuàng)造意義的過程,而評詩則從詩的文字返歸作者的情感,并在詩句的分解與重構中體會作者的主體性如何建立。孟子認為,評《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⑥,作者之志與評者之意,只能通過與文本間的交談“逆”向返歸兩者交融的本源情境,從中把握主體性的植根所在,以此托付詩的旨趣所向。在孔子的詩論中對原文的“吾信之”“吾善之”,其實就是以“逆”向的交談托付主體的“志”意,也是主體性的重新確立和價值的再次判斷。例子集中體現(xiàn)在《孔子詩論》中,如: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簡21)又如:《兔置》,其用人,則吾取。(簡23)換言之,在對原詩的文本的重構中,主體“吾”與客體“之”通過交談得到了相互的確立,以主體對客體的肯定判斷為終點;這個判斷既是主體性的匯通,也是對詩旨的重新認可。《孔叢子》中的“于……見”句法中有很多例子;如“于《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yǎng)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有學者認為,這與《孔子詩論》的“以……得”相似,表達的也是對詩旨的解讀。〔5〕而這種解讀也就是通過文辭的解析,還原到共通的本源情境,將詩旨托付在一致的主體性上,從而達到主體對詩旨的肯定。這種肯定是讀者主體在重詮中的判斷,而其所認可的詩旨也就是歷史的、延宕的重塑。
無論做詩還是評詩,都以文本為門徑,這與詩的“修辭以立其誠”的特點有關。其中的“立”與“立己”“立人”是同一個過程,即主體性的確立。在詩的表現(xiàn)手法中,“立”是借助“興”來表達的。孔子說詩,經(jīng)常提到興的手法。《論語·八佾》中,子夏從“繪事后素”的情境中引發(fā)出“禮后乎”的問題,孔子贊他為“起予者”;這里的“起”即有起興的意思,也是啟發(fā)意欲、立己立人的開端。主體意欲是從“繪事”的本源情境中興起的,在詩的文辭中被具象化,并延拓為理性的思考。《毛詩正義》解“詩有六義”,孔穎達引鄭玄注:“興者,托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fā)己心,詩文詩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朱熹也有類似解釋:“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詩集傳·周南·關雎》)然而這種解讀卻偏離了興的本義,即從本源中興起主體性。參見王坤兒(王堃)《比興:詩學與儒學之本源觀念——朱熹〈詩集傳〉再檢討》,《儒教文化研究》國際版(第十五輯)韓國成均館大學,2011年。興同樣可以用在做詩和談詩中:當用于做詩,興是在詩的情境中用語言構筑起主體的心性,并展開相對的情感和意義空間;而當用于論詩,興是在交談中建立起共同的主體性,再以此主體的目光和言行展開人我對待的世界。
儒家詩學中另一種重要修辭方法是“比”,與“興”合稱為“比興”。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描述是:“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他認為相較于興,比更切近實事,在事理的類比中講求精確。朱熹對“比”的定義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詩集傳·周南·螽斯》)比連綴起事物彼此之間的關系,成為了概念范疇的依托。然而,比還有一種前主體性的意義,即本源的“相與”、親密之情。許慎《說文解字》:“比,密也”;“‘比從二‘匕”;“匕,相與比敘也”。《周易·比象傳》說:“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正是在“比”的本源詩情中“興”起了主體性,由此產(chǎn)生當下的價值判斷——詩旨,并構建起概念的邏輯關系。例如《孔子詩論》22簡:“鳲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也。吾信之。”在與鳲鳩面對面的詩情中,確立起一個穩(wěn)固的主體性,并自我充實為儀表專一、內(nèi)心“固結”君子;這既是君子之“興”,也是與“鳲鳩”之“比”。讀者則重構比-興,從比于詩境的詩情中建立起“誠”“信”的絕對主體性,以此托付對原詩旨趣的歷史性肯認。就像程子所說的“主一之謂敬”,評詩是在誠敬的情感中逆向解構原詩的修辭,還原到詩的原始情境;同時在解構中建構,即“先立乎其大者”,重構唯一的主體性,并對原詩旨進行判斷。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這是對“曲禮”中“毋不敬”的解釋,參見《禮記·曲禮上第一》,〔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頁。“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取自《孟子·告子上》。
比既是返溯詩情,也包含從情感的本源中主體的重興,以及重新審視修辭的構成。修辭以確立誠、敬的絕對主體性為旨歸,否則就是壞的修辭。《論語·八佾》贊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就是好的修辭典范。“淫”或“傷”的個人感受,不應摻雜進本源的詩情,也不宜置換入主體性的確立中,這是詩之“比”的修辭應遵守的原則。只有持守著仁而樂的本源情感,才能興發(fā)對所有他者的愛欲,以此托付著立己立人、切象比義的目標。在詩的特定情境下,表征著絕對主體性向相對個人德性下貫的詩旨就成為了這個目標。《孔子詩論》10簡中的“關雎之媐、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報、綠衣之思、燕燕之情”,都用一個字概括了詩中相對主體的意義世界;而這個字之所以成為詩旨,因其蘊含并擴展了絕對的主體性的意涵,凝聚在“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的修辭中,以充盈著相對的人倫空間。在理學家看來,詩的興觀群怨不過表達著符合形上心性的“中節(jié)”情感,殊不知絕對的主體心性恰恰是由詩給出的。詩情藉由詩句的修辭,感發(fā)起絕對和相對的主體,從而建構了情理交匯的世界。
①時間性(Temporality)被海德格爾定義為此在的性質(zhì),它體現(xiàn)于此在的情感喚起對未來的籌劃之中。這里援引了時間性,也在表達儒家情-欲結構的未來指向,時間性就體現(xiàn)在欲對將來目的的籌劃中。下詳。
②一般認為,中國詩歌的萌芽產(chǎn)生于甲骨上的卜辭,《易經(jīng)》中的卦辭也包含這種古歌的形式。參見黃玉順《易經(jīng)古歌考釋》(修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做詩與說詩是在詩情中建立主體性的過程,主體的愛欲和由此生發(fā)的個人情感和理性,都不能離開詩情的本源。情-性-情的架構在詩的語言中往復生滅,源于詩情又歸于詩情。在這個意義上,儒學即是詩學,詩學即是儒學,故可統(tǒng)稱為詩情儒學。
三、詩性倫理
倫理學往往是關于社會規(guī)范(social norms)的表述,也就是“規(guī)范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但傳統(tǒng)的規(guī)范倫理學往往是由某種“形而上者”直接給出一套規(guī)范;而在這種“形而上者”遭遇危機的今天,倫理規(guī)范也在另尋建構的蹊徑。既然儒學可以看作詩學,那么在詩性的建構中,儒家的社會規(guī)范——禮,也可以得到重新的闡釋,從而發(fā)展出一套“詩性倫理”的敘述。
(一)“詩性倫理”的觀念
以理性主義為背景的德性倫理,和以家族紐帶為核心的血親倫理,一直充當著儒家倫理的主流,然而二者在當今各自面臨著質(zhì)疑。血親倫理以父系血緣關系為倫理的起點,但這種關系只是在一種特殊歷史境域下的建構結果。德性倫理預設了人的心性中都具有契合天理的能力,以陸九淵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為例;人都有心的事實,并不能推出“心皆具是理”的事實,這兩句不是類比的關系,那么后者只能作為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天理作為形而上的價值,被擺放在不可質(zhì)疑的地位。而回到孔子的“我欲仁”,主體心性只有在“欲仁”的意志中才能確立;也唯有在詩情-愛欲中起立的絕對主體性中才有了善的普遍性,是詩情給出了人性、天理,而非性理反過來塑造了情感。反觀血親倫理所注重的親情,倒是詩情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呈現(xiàn),只不過隨著生活樣式的改變,詩情的表現(xiàn)也就不再局限于孝慈了。總之,倫理價值以詩情為本源,而非依據(jù)某個形而上者或形而下者。
詩情是境域化的,“入則孝、出則悌”就是詩情在不同情境中呈現(xiàn)的各種樣態(tài),從中可以樹立起誠而敬、“謹而信”的絕對主體性;絕對主體以“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為欲求目的,希望把愛欲推及所有,讓每個人各得其宜。在孔子看來,孝悌的情感是本源的,而在不同場合踐行孝、悌的則是各個相對的存在者,“欲仁”則是絕對主體從相對主體中的綻出。在相對主體看來,“仁”的目標似乎是瞻之在前又不可觸及;而“欲仁”把相對性消融在“仁至”“親仁”的詩情本源,并重新開顯出絕對的主體性。絕對主體與仁的親近,就在“欲”的綻出拉力中,那么絕對的主體性就是拉動所體現(xiàn)的時間性。①以“去實施普遍的愛”為目的,在“欲仁”的時間性籌劃中,絕對主體觀照出“萬物皆備于我”的時空維度,由此把愛欲向前推向每個相對的存在者,這正是善的普遍性之所在。換言之,善是由絕對主體意欲的時間性決定的。
亞里士多德也曾說過,詩總是表達著普遍的事物;而普遍性在于即將發(fā)生的可能中,那么詩所關乎的是未來的可能。〔6〕而未來的可能性與其說在修辭(rhetoric)的推理中得到,不如說與辭句背后的情感和想象更為切近,這在亞氏詩學有關或然性、隱喻等諸多研究中表現(xiàn)得很明顯。相比古希臘的修辭學,中國的早期詩歌以易經(jīng)古歌的形式出現(xiàn),而后才繼以《詩經(jīng)》。②與其說卦辭與卜筮方法有關,不如說是以詩的語言表達著守仁行義、居仁由義的德義,即以推行仁愛為目標、以道義立足于世的主體意欲。在最早的詩中,無論詩經(jīng)還是易經(jīng),都是通過表述這種意欲來喻示普遍的價值追求的。
詩所要揭示的是普遍的善,這個目標在主體對未來無限可能的意欲中,而這個捉摸不定的欲求目的是通過詩的語言來表達的。從格律化的詩句中探尋這個難以把握的普遍性,就注定了詩的困境。①而如果回到孔子詩學的“思無邪”,(《論語·為政》)則有助于超越這個困境。詩思之所以“無邪”,因為在詩思中沒有主體與客體的距離,“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②隨著距離感的消失,形而下的相對主體不復存在,融入了詩情的本源;同樣在詩思中,絕對主體重新切合著無邪的詩情而誕生。思而不遠,如同欲仁而仁至,同樣表述著從相對主體的綻出,和絕對主體意欲的時間性發(fā)端。將詩思形于言辭就成了詩,詩以音律的抑揚揭示著主體性的隱現(xiàn)。詩的語言就是朱熹《詩經(jīng)集傳序》里講到的“咨嗟詠嘆”:
①關于詩的這個困境,最經(jīng)典的表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67-68頁。
②《莊子·齊物論》:“吾喪我。”《論語·子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③海德格爾:“胡塞爾與黑格爾如出一轍,都按同一傳統(tǒng)而來,這個事情就是意識的主體性”;“從黑格爾和胡塞爾的觀點來看,哲學之事情就是主體性。”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65頁。
④Parmenides: “What there is to be said and thought must needs be: for it is there for being, but nothing is not.” Kirk, G. S. et al.,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i History with a Sélection of Texts, 2d é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 247.
⑤“being as being”不應譯為“存在之為存在”,而應譯為“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意指作為眾多相對存在者背后的終極根據(jù)的那個絕對存在者,亦即所謂“本體”(noumenon)(希臘語onta)——“形而上者”。參見黃玉順《形而上學的黎明——生活儒學視域下的“變易本體論”建構》,《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2卷第4期。
⑥《論語·先進》:“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fā)于咨嗟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jié)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7〕
從“有欲”“有思”到“有言”,主體性的意欲通過詩的“音響節(jié)族”興起、呈現(xiàn);同時也在這些節(jié)奏中,絕對主體借助詩的意象將自己相對化,以“比”的格式形成詩的主旨。當詩的情境借助詩句而具象出來,普遍的善就凝聚為一詩的主旨。如果倫理學是關于善的討論,那么詩學既是儒學的話語樣式,同樣也是儒家倫理學的闡述方式。因此,儒家倫理可稱為詩性倫理。
(二)詩性倫理的構成
若如海德格爾所說,哲學的事情就是主體性的事情③;同樣,倫理學的問題首先就是主體性的問題。只不過相比較哲學意義上的“絕對主體”,倫理主體是具體而形下的,講述著規(guī)范的建立和持守。也正因如此,倫理主體需要哲學上的絕對主體的支撐,而絕對主體又依賴詩情的奠基。根據(jù)詩情儒學的情-性-情的架構,在詩情的本源之上,依次建構絕對主體和相對主體,從而可以為儒家倫理提供一套詩性的詮釋體系。
1.興于詩:絕對主體性的確立
帕爾米尼底斯(Parmenides)曾說:“被說和被思者必須存在:存在者如是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④不論是“真”還是“善”,絕對形而上者就是被說出的存在者,只能在詩的語言中得以存在。帕爾米尼底斯的詩所創(chuàng)造的存在者是當下的、無時態(tài)的(tenseless),這一絕對的形而上者是諸多形而下者的終極依據(jù)。⑤而從儒家的“思無邪”可見,詩情同樣是超越了時空的。在詩的吟詠中,詩思不斷從其所描繪的意象中綻出,在新打開的時空維度中再度描畫。詩思就是主體的愛欲,在其不斷趨前的時間性中,超越有限時空的普遍的善成為主體的目標,而此主體也具有了先于時空的絕對終極性。
絕對主體不同于無時間(timelessness)的絕對空間存在物,它并不是一塊寂靜不移的石頭,其超越性恰在其具有內(nèi)在的生長性。這個生長性就是超時間的時間性(Temporality)。新舊時空切換的節(jié)律是由主體愛欲的時間性給出的,當這種節(jié)律以詩的格律凝固,主體就依格律的詠嘆感興和籌劃著人倫化成的樣式;“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記·孔子閑居》)孔子與曾點的默契就在這種“詠而歸”中達成。⑥在儒家的詩論中,詩的格律映現(xiàn)出主體性的朗現(xiàn),給出了價值的層級和人倫的次第。由于主體的時間性是超越而絕對的,故成為倫理價值的根據(jù)。
絕對主體性恰如王夫之的“日生日成”,在流俗的時間里似乎是屢遷的;但主體性不隨流俗而沉淪,而從中綻出并重生。因而對流俗之物而言,絕對的主體性如僧肇所說的不遷之物。荀子常引《詩》證之: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荀子·勸學》)
《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子·不茍》)
在詩書禮易的誦讀修習中,君子使心志凝結于“一”,即獨立不遷的主體性。而主體性在于“唯其時”而“當之”,依時間性而將愛欲推及世間萬物,使其恰如其分、左右皆宜。俞樾認為,毛傳以陰陽之道解釋“左右”失于狹隘,而稱荀子“以柔而立說”,以柔的方式“自立”,從而“不為物傾”;因而,《詩》中的“左之”“右之”不過是富有柔和節(jié)律的話語樣式,表達著一種分寸感的把握,而此分寸感正是時間性的所在,即絕對主體性的基礎——“維德之基”。〔8〕
朱熹在《詩集傳序》中的“自然之音響節(jié)族”〔9〕,就是主體時間性的體現(xiàn),荀子稱之為“中聲之所止”,而《大序》將此描述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荀子·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毛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劉師培認為,《大序》“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與荀子“中聲”句同,且列出荀子與《大序》多處關聯(lián),似于《毛詩》與荀子的師承之說有所印證。參見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不過在朱熹的解釋里,情、欲是形而下的“人情”并從屬于性,那么“自然”也就淪為一物。其實荀子的“性之質(zhì)”是本源的詩情,由情-欲轉化中樹立的主體心性,是通過“直而溫,寬而栗”的“自然”節(jié)奏抒發(fā)出來的,這個節(jié)律就是“中聲”。詩的節(jié)律中,蘊含著絕對主體的超越性和價值的普遍性;只有在詩的言說中,才足以移風俗、厚人倫,詩既是絕對主體的給出者,也是形而下的倫理主體的終極奠基。
2.立于禮:倫理主體的建成
當詩的語言連綴成完整的意象,絕對主體在意境中現(xiàn)身,充實為相對的主體,與其面對面的世界也顯現(xiàn)出來。相對主體與客體世界一旦照面,就在相互交往之中;而交往需要遵循著“行而宜之”的“義”,以及依據(jù)“義”而因事制裁的“禮”。禮規(guī)定著個人的行為儀則,只有立足于禮,才能使人性普遍的善落實為倫理價值和個人道德。
孔子的詩論其實就是關于各種倫理價值的界定,一首詩的旨趣就是一個相對的價值。《關雎》的詩旨是“改”,這意味著這首詩的現(xiàn)實指向是,從“聞關雎”的本源情境中樹立起“君子”思改的倫理主體,并建構出一個禮法的世界。而《樛木》所突出的相對主體性是“時”,《甘棠》所給出的是“報”,這些詩都在表達著與詩的特定情境相關的倫理價值。從絕對主體的興起到相對詩旨的凝固,也是藉由修辭格律而完成的。例如,關雎與男女之別、君子之改的隱喻,就是“比”的修辭格律的體現(xiàn);而“比”本身蘊含著主體性挺立的整個過程,即“相與”比敘的詩情-絕對主體的起興-相對主體的價值。因此,個人化的德性與禮義可以通過修辭的方式闡述出來。
在特定的意境中,由絕對主體所充實的倫理主體是形而下的。比如《孔子詩論》由《甘棠》講到“敬”“報”的德性時,也留意到“民性固然”,敬愛一個人,必尊敬其身份、喜愛其行為。《孔子詩論》第二十四簡:“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為,惡其人者亦然。”民性中既含有普遍而形上的善,也有著勢所必然的情性,因而,民性代表著形而下的相對主體,在群體中有著世俗的交往,呈現(xiàn)為有限時空中的性格特征,如“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又如“幣帛之不可去也”。《孔子詩論》第十六、二十簡。民性需要禮尚往來的交際來構筑,而詩的對仗、反復等修辭格正是這種構筑的模式。
絕對主體先于有限的時空維度,獨立于其所籌劃和構建的對象,不會在流俗時間中逐物而遷;而相對主體是物理時空里的存在者,因而是隨時間空間的遷轉而流變的。比如,《關雎》之“改”的德性,對應的是和樂恭敬、謹守容儀的倫理主體〔10〕;而這個相對主體未必固定在文王一人,而應舉一反三,推及所有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行為。荀子常引《詩經(jīng)》里的“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毛詩》也有“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zhí)義當如一也。”①從心結于一到執(zhí)儀如一,德性與儀則并具于倫理主體一身,《論語·學而》的“三省吾身”就是依據(jù)德性自我檢查。但這并非根據(jù)一定規(guī)則進行封閉的自查,而是在顧及周圍的他者中,對親近者“狎而敬之”,對位尊者“畏而愛之”,直到行為使自己心安為止,這就獲得了“遷”“改”的德性。(《禮記·曲禮上》)因此,合禮的行為在細微枝節(jié)上是可以有所出入的,而并不違反總體的德性與儀軌。②簡言之,符合相對的倫理價值的禮儀,是在交往行為中求得心安的過程,比如從“慍于群小”的憂心、臨深履薄的審慎中,才得到了“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的倫理準則。③而這個由危而安的遷改過程,也是思安而得安、欲仁而仁至的絕對主體性的確立;換言之,絕對主體性就是在相對主體言行的綻出中得以確立的,這個確立也是絕對主體充實為倫理主體的過程。
①荀子與《毛詩》的文本,都引自《曹風·鳲鳩》中的“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參見李學勤《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476頁。
②子夏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論語·子張》)
③《詩經(jīng)·柏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荀子·臣道》:“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
④《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⑤〔明〕王畿:“‘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為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義。”《格物問答原旨》,《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六,明萬歷43年刻本。
⑥〔明〕羅汝芳:“‘能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即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近溪子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30,280頁。
⑦《論語·憲問》:“(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絕對主體的言說是溫順的詩性,左右宜之、節(jié)律柔和;而相對主體的話語則需要“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荀子·性惡》),因而對應的是嚴謹?shù)脑娦浴0乩瓐D的修辭術以辯證法為依托,而儒家詩學則以嚴密切實的賦象比義來應對德義的要求。但嚴謹?shù)倪壿嬓砸廊坏旎跍厝岫睾竦脑娗橹希皇且再x辭的外表連綴起比-興的節(jié)奏。孔子所謂“立于禮”,就是在禮義的言行中樹立起溫恭而審慎的倫理主體,作為“興于詩”的絕對主體性的下貫。從詩情本源中樹立的絕對主體性,在倫理主體的話語中得到了擴充;而倫理話語也只是以一種縝密的修辭技術,保守著君子人格的詩情奠基。
(三)詩性“正名”:詩性倫理的兩個維度
儒家倫理可以用詩的修辭來闡述,而修辭本身也是“正名”。詩性的正名體現(xiàn)為“克己復禮”與“禮有損益”兩條線索,前者是倫理體系的規(guī)范性維度,后者是其時間性維度。規(guī)范性維度是一根橫軸,關乎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在既定時空中的展開;時間性維度則是根縱軸,圍繞著它,主體性隨詩情流轉徑自呈顯與隱沒。這兩條軸線是相互交匯、互為支撐的。
1.克己復禮:詩性倫理的規(guī)范性維度
孔子有關倫理的學說,以克復之道為核心,克己復禮是“為仁由己”的方法。④復禮的目的是為了“天下歸仁”,把普遍的愛輻射到世界中去,這是通過“克己”實現(xiàn)的。在程朱理學的解釋中,克己就是克制私欲,但這個觀點遭遇了陽明后學的反對。王龍溪指出,“克”有修治的意思,克己就是由己、修身。⑤羅近溪則認為,“克己”就是“能己”⑥,就是在遵循禮的言行中,敞開自己的全部可能,挺立自己的主體性。當今儒者杜維明也認同,克己就是修身。〔11〕其實,這兩種說法各有道理。首先,“己”是有私欲的,并且情欲有逐利趨惡之勢,即《詩論》中的“民性固然”,這是需要克制的。然而“己”的另一面是主體性,在禮的言行中完成自我充實,以此節(jié)制前一個自己。“欲雖不可去,求可節(jié)也。”(《荀子·正名》)如果把“克”解為克制,也并非孔子所反對的“克伐”⑦,而是節(jié)制與運化。節(jié)欲是通過視聽言動完成的,在與人交往中時刻省察,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從而塑造出端愨溫恭的君子人格。復禮就是制定名約,使自己和他人都手足有措,這是孔子與荀子“正名”的初衷;而名約本身也是在日常的言行中約定俗成的,并且行為也可以化約為語言。奧斯汀認為,一切言語最終都是行為。芬格萊特引用了他的觀點來解釋孔子的“正名”思想,指出語言是禮儀的本質(zhì),并以“仁”為“在‘禮中塑造自我”。赫伯特·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國翔、張華譯,南京: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2010年,11,42頁。那么,約定俗成就是以話語建構主體性的過程,既是克己也是復禮。
在絕對主體性的確立中,一切行為、意象、包括音樂和畫面的上手印象,都可訴諸超越的詩性敘事。而當上手態(tài)充實為在手態(tài),行為被界定為儀式,節(jié)奏感形成了詩句的修辭格,所有的意象與主體性本身一道被對象化為有限存在者,絕對主體的詩性話語就相對化了。當語言從上手的意象轉為在手的摹狀,一個有形態(tài)、有方所的個人存在者也隨之出現(xiàn);其所居處的空間形態(tài)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這決定了它的行為延展的方向。《荀子·正名》:“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shù)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方所固定,性狀隨時間改變者為一個實體或個體,這是“正名”元語言中的一條。不過,行為的方向雖是多樣的,但并不偏離“執(zhí)義如一”的君子風范,只是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詩性和聲。如《荀子·不茍》所描述的:“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這是對其所引《詩經(jīng)》中的“溫溫恭人,維德之基”的君子人格的充實,也是對孔子“溫柔敦厚”的詩教理念的充實。從形而上的心性人格,到形而下的行為規(guī)范,約定俗成就在不斷返歸本源的詩性敘述中重建主體。因此,外在的話語規(guī)范、修辭格律,都以溫柔的詩情為本,以詩性的克復為道。
孔子與荀子的詩教,都常引用詩來討論政治倫理的建設。例如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學詩的目的是為了現(xiàn)實的政事需要,而非僅止于陶冶性情,這喻示了絕對主體向相對主體充實的必要性。荀子也批評“《詩》《書》故而不切”,而只有踐行禮義的師法操持中,才能落實詩書的教義。否則,“不道禮憲,以 《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喪之矣。”(《荀子·勸學·禮論》)這再次申明了,復禮、正名都是以詩為奠基的,而詩的言說必須和禮義的行為相結合,始于誦詩,進而“道禮憲”,倫理主體才能得到充實。從“詩無隱志,樂無隱情”到“文無隱言”,也就是由“默語”到“辯言”,由“道言”到“人言”的轉化。《中庸》:“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行之有出處,言之有默語,依時而定。”《荀子·非十二子》:“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智也。故知默,猶知言也。”中國哲學中,形而上學常被稱作對道的言說,或“道言”,形而下學則為“人言”;人言不能越界入于道言,而道言可以充實下貫為人言。因此,“克己”就是“成己”“能己”,同時也就是“復禮”。簡言之,克己復禮就是從詩性語言中建立絕對主體,并在禮義論辯中將其充實為倫理主體的話語建構。
2.禮有損益:詩性倫理的時間性維度
絕對主體向相對主體的下貫是通過詩性語言的對象化實現(xiàn)的:先從詩性的道說中成就了“大人”,這個大人又會在自己的話語中,自我充實為身心并具的個人,也就是形而下的“小人”。《孟子·告子上》:“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如果把絕對主體的“道言”作為元語言,那么由元語言給出的對象語言就是相對主體的倫理話語——“人言”,孔子和荀子的“正名”所要給出就是這樣的語言層次。〔12〕如上文所述“克己復禮”,正名同樣既是正人之名,也是正禮之名;換句話說,正名就是在道言向人言的轉化中,不斷重建著禮的規(guī)范,從而推進禮的沿革,這就是《論語·為政》中的“禮有損益”。《論語·為政》:“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雖自稱“述而不作”《論語·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其實他不但刪訂六經(jīng),自己也有創(chuàng)作。他注重從文本的沿革中把握意義的損益,而對這種損益的判斷不以某種靜態(tài)的形而上學結構為中心而展開,而是將意義在文本延續(xù)中的彰顯當作一種詩性的歷史書寫。從文本延續(xù)的差異中,他不是要去還原一個最初的本源在場者,而恰恰是在現(xiàn)下的文本中把握本源存在。“子曰:‘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從“郁郁乎文”的詩性意象洋溢中,倫理主體得到了充分的展現(xiàn);“郁郁”的這種充實是立足于“監(jiān)于二代”的絕對過去之上的,同時又作為孔子當下的本源體驗,并在新主體的充實中再度成為絕對過去。當下“郁郁乎文”存在者在回歸詩情和主體重建中隱藏為絕對的過去,主體才能立于全部歷史蹤跡之上,作出未來的籌劃并進行自我的充實,這就是“述而不作”中的“作”。
“吾從周”是基于文本痕跡的闡釋,這種闡釋既是“述”也是“作”,意義在述與作中完成了創(chuàng)造中的延續(xù)。述作除了是與歷史文本的交談,也可以是當下與人面對面的言談和行為。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鄉(xiāng)黨》:“入太廟,每事問。”,并非因為孔子不懂得禮,而是他認為,禮就是在問答的交談和行為中被構建起來的。主體性在對談中失而又得的逆向重構,是詩之所以“起予”的時間性體現(xiàn),倫理主體因此得到充實,禮也因此而得以損益。
孔子論詩的時間性,在荀子的文本中表現(xiàn)為從法先王向法后王的過渡。先王之道與后王之道的一以貫之是通過“徑易不拂”來表述的,而徑易不拂正是從言談上對約定俗成的歷史性展開。從約定到俗成,儒家詩性倫理跟隨詩性的節(jié)奏,沿著“徑易不拂”的軌跡,趨于“稽實定數(shù)”的規(guī)范制定。約定俗成、徑易不拂、稽實定數(shù)是《荀子·正名》中列舉的三條制名之樞要,也是“正名”元語言的主體。參見王堃《自然語言層次的倫理政治效應——以荀子“正名”倫理思想為中心》,山東大學2014年博士論文。這三條制名之樞要構成了儒家詩性的元語言,以此成為每個新的歷史情境中倫理話語沿革的根據(jù)。無論“克己復禮”還是“禮有損益”,都是從不同側面描述主體性的充實和規(guī)范的成立,而這是在詩性的修辭中構建出來的。儒家倫理就在這個詩性的話語系統(tǒng)中得以成立,故可稱為詩性倫理。
〔參考文獻〕
〔1〕王堃.德性倫理還是詩性倫理〔J〕.湖北社會科學,2012(2).
〔2〕王堃.詩情的奠基——論孔子倫理思想研究現(xiàn)狀〔J〕.美與時代(下),2012(4).
〔3〕王堃.詩情儒學——蘇軾儒家思想與文藝創(chuàng)作之關系〔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
〔4〕蒙培元.情感與理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310-313.
〔5〕李存山.《孔叢子》中的“孔子詩論” 〔J〕.孔子研究,2003(3).
〔6〕Aristotle. A Hypoth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Poetics II〔M〕//Poetics 1, with the Tractatus Cioslinianus.trans. ty Richard Janko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51.
〔7〕〔9〕〔10〕〔宋〕朱熹.詩集傳序〔M〕//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0,350,402.
〔8〕〔清〕俞樾.荀子詩說〔M〕//曲園雜纂:卷六.春在堂叢書(四).光緒九年重定本:5.
〔11〕杜維明.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從克己復禮為仁的現(xiàn)代解讀出發(fā)〔J〕.探索與爭鳴,2014(2).
〔12〕王堃.自然語言層次的倫理政治效應——以荀子“正名”倫理思想為中心〔D〕.山東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