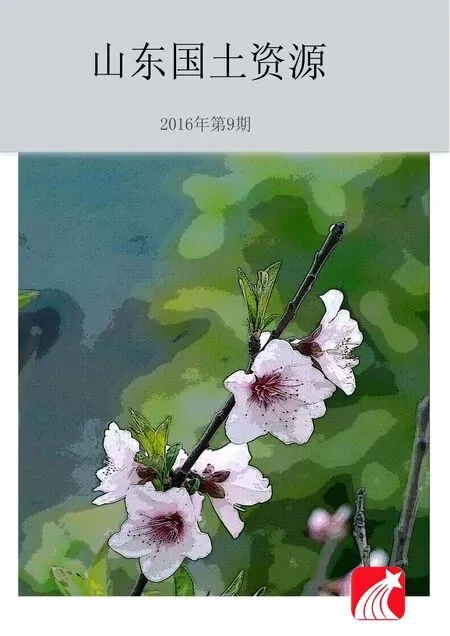百脈泉泉群流量動態(tài)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
崔愛萍,于翠翠
(1.山東科技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山東 青島 266590;2.山東省地礦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山東 濟南 250014)
?
環(huán)境地質(zhì)
百脈泉泉群流量動態(tài)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
崔愛萍1,于翠翠2
(1.山東科技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山東 青島 266590;2.山東省地礦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山東 濟南 250014)
對1971年以來百脈泉泉群流量動態(tài)特征進行了系統(tǒng)分析。根據(jù)研究區(qū)巖溶地下水的補徑排條件,開展巖溶地下水動態(tài)、泉群噴涌與大氣降水、地下水開采、土地利用(植被覆蓋)等因素之間的定量相關(guān)性分析,為有針對性的做好泉水保護奠定了基礎。
百脈泉泉群;流量;動態(tài)特征;影響因素;相關(guān)性分析
明水泉域東起禹王山斷裂,西至文祖斷裂;南以泰山巖群古老變質(zhì)巖為界,北到奧陶紀灰?guī)r頂板埋深600m分界線。地理位置位于魯中山地和山前傾斜平原過度地帶,地勢總的趨勢是南高北低,東高西低,海拔由南部山區(qū)800余米向北逐漸降低,至明水市區(qū)附近為50~60m,向北又逐漸高起。南部主要是古生代寒武、奧陶紀灰?guī)r組成的低山丘陵地形,標高400~800余米。而百脈泉泉群主要位于章丘市區(qū)北部,分別位于東麻灣和西麻灣附近(圖1)。
1 百脈泉泉群成因
泉群形成一般需要良好的儲水構(gòu)造、相對隔水巖層的阻擋、條件適宜的地形、地貌以及斷裂構(gòu)造的控制作用[1]。禹王山斷裂和文祖斷裂為東西兩側(cè)隔水邊界,南部以變質(zhì)巖系為界,向北古生代寒武、奧陶紀地層依次排列,構(gòu)成單斜斷快蓄水構(gòu)造;含水層為寒武、奧陶紀灰?guī)r,裸露面積404.3km2,厚度約1220m,裂隙巖溶發(fā)育,極有利于大氣降水的入滲,接受大氣降水補給,地下水由南向北徑流,受煤系地層阻擋后,在章丘市城區(qū)附近匯集;東麻灣和西麻灣等地勢最低洼處,沿斷裂構(gòu)造沖破薄弱隔水層上涌成泉(圖2)[2-6]。
2 百脈泉泉群流量動態(tài)特征
以1971—2013年來的百脈泉泉群出流量長期觀測資料為基礎,探究泉群流量的動態(tài)特征,發(fā)現(xiàn)百脈泉群泉流量變化過程主要可分為以下4個階段(圖3)。
(1)高水位大流量階段(1970—1981年):該階段降雨量較大,多年平均降雨量達642mm,最大年降雨量為988.8mm(1973年);該階段泉域內(nèi)煤礦排水量少,泉域內(nèi)巖溶水開采以分散式開采為主;泉水水位較高,一般在60m以上;期間泉水持續(xù)噴涌,泉流量25萬~39萬m3/d,最大年流量14079萬m3(1976年)。
(2)水位下降斷續(xù)出流階段(1982—1998年):該階段降雨量較大,多年平均降雨量達603mm,最大年降雨量為894.1mm(1990年),最小年降雨量為309.63mm(1989年);該階段泉域內(nèi)煤礦排水量較大,由于社會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泉域內(nèi)巖溶水分散式開采井不斷增加,城鎮(zhèn)集中供水水源地相繼建成,巖溶地下水開采量大大增加;泉水水位標高一般在56~65m;期間泉水1983年4月、1984年4月及1987年5月出現(xiàn)過短暫的停噴,1989年4月—1990年6月期間,由于降水量少、煤礦排水等原因,泉水停噴達15個月之久。之后復噴至1993年4月又停噴了3個月。期間泉流量3萬~31萬m3/d,最大年流量11308萬m3(1996年),最小年流量1134萬m3(1989年)。

圖1 百脈泉泉群水文地質(zhì)圖

圖2 泉水成因水文地質(zhì)剖面圖

圖3 1970—2013年泉群自流量變化圖
(3)極低水位持續(xù)停噴階段(1999—2003年):該階段降雨量相對較少,多年平均降雨量556mm,最大年降雨量為849.9mm(2003年),最小年降雨量為412mm(2002年);該階段泉域內(nèi)煤礦抽排巖溶水量大,達7.94萬m3/d;巖溶水人工開采量也增大至14.56萬m3/d;泉水水位標高在29.98~63.05m,平均水位標高為43.29m;期間泉水自1999年7月停噴,至2000年10月復噴[7],2001年4月停噴,至2003年9月16日重新噴涌,2次停噴時間分別達16個月和29個月。最大年流量3922萬m3(2003年),2002年泉水自流量為零。
(4)人工調(diào)控階段(2004—2013年):該階段內(nèi)多年平均降雨量達684.3mm,最大年降雨量為870.7mm(2004年),最小年降雨量為394.8mm(2006年);該階段泉域內(nèi)煤礦抽排巖溶水量減少為1.5萬m3/d;人工開采量減少為9萬~14萬m3/d;自2003年9月泉水復噴至2014年9月,泉水水位標高在53.7~65.7m,平均水位標高60.3m;2004—2013年之間,泉水僅在2007年4—7月及2010年4—7月斷流。期間最大年流量14571萬m3(2005年),2007年泉水自流量最小為4335萬m3。
3 影響百脈泉泉群出流量因素分析
影響泉群噴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大氣降水、人工開采、煤礦排水及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情況等[8-10]。其中大氣降水的多少是影響泉群補給量變化的根本原因,而泉域內(nèi)人工開采地下水及煤礦排水是影響巖溶地下水排泄途徑的主要原因,此外,土地利用變化則通過改變大氣降水入滲情況等對泉群的補給量造成影響。
3.1 降雨年際變化的影響
大氣降水是水循環(huán)系統(tǒng)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對一個巖溶地下水系統(tǒng)而言,其可以獲得的補給量的大小最終取決于大氣降水的多少及其分配情況。通過已往資料分析得知,無論是泉域內(nèi)大氣降水的年際變化、年內(nèi)變化還是某一次大氣降水過程,都對泉群噴涌情況及巖溶地下水動態(tài)有著明顯的影響。
3.1.1 大氣降水年際變化動態(tài)
泉域內(nèi)多年降水量如圖4所示,選用1970—2013年泉域內(nèi)雨量觀測站平均降水量數(shù)據(jù)作為泉域的平均降水量。采用如下經(jīng)驗公式對大氣降水進行豐枯規(guī)律的分析:




式中:Si為第i年的降水量(mm);S為多年平均降水量(mm);σ為標準差(mm);n為統(tǒng)計年數(shù)。據(jù)計算結(jié)果,并結(jié)合泉域大氣降水情況,可以看出明水泉域在1970—2013年的44年間里,共出現(xiàn)了16個豐水年,15個平水年,13個枯水年(圖5)。

圖4 多年降水量柱狀圖及累計均值離差圖

圖5 1970—2013年明水泉域大氣降水年際變化圖
3.1.2 大氣降水年際變化對泉水噴涌的影響
通過對比分析泉水流量、泉水水位標高與降水量變化趨勢線(圖6、圖7),泉水流量及水位的變化與大氣降水變化除了在時間上存在一定的滯后外,三者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但其各自的變化梯度卻并不相同,泉流量及水位的衰減梯度較大氣降水更陡,這是因為明水泉域泉水噴涌同樣受到人工開采地下水、煤礦排水及土地覆被等影響因素變化的影響。

圖6 1970-2013年泉流量與降水量變化趨勢線
3.1.3 大氣降水年內(nèi)變化對泉水噴涌的影響
根據(jù)降雨資料分析,隨著大氣降水的季節(jié)變化,泉水流量及泉水水位也相應地表現(xiàn)出明顯的季節(jié)性變化。一般在豐水年及平水年,泉流量、水位高峰值在時間上較降水的高峰值略有推遲,推遲約1~3個月,如明水泉域大氣降水主要集中在6~10月份,月降水量峰值多出現(xiàn)在七八月份。

圖7 1970—2013年泉水水位標高與降水量變化趨勢線
在降水偏枯時期,泉水流量及水位動態(tài)與豐水期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不同:枯水期流量不低、水位不低,豐水期流量不高、水位不高,泉流量及水位高峰值往往出現(xiàn)在年底或年初。
3.1.4 次降水對泉水水位動態(tài)變化的影響
某次大的降水過程對泉水水位的影響是極為顯著的,且水位最大升幅一般僅在大的降水過程之后1~2天,顯示出大氣降水對巖溶地下水的補給較迅速。
3.2 地下水開采的影響
人工開采巖溶水,一是在泉口附近大量抽排巖溶水,直接降低了泉口水位;二是在泉域內(nèi)其他區(qū)域大量抽取巖溶水,襲奪了巖溶水向下游的補給量,從而減少了巖溶水從泉口的排泄量,因此人工開采地下水是影響泉群出流的重要因素。20世紀70年代泉群未曾干涸過,至八、九十年代,泉水斷流的次數(shù)明顯增多,每次斷流時間也越來越長,與人工開采量的增加有著一定程度的聯(lián)系。
3.3 煤礦排水
煤礦排水對泉群噴涌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2個方面:一是在煤礦正常開采過程中礦山抽排巖溶水,消耗了部分泉群的補給量,從而減少了泉水流量。二是在泉口附近的煤礦突水,直接襲奪了泉水排泄量,降低了泉水水位,其對泉群噴涌的影響顯著但時間較短,當煤礦老空井巷充滿水后,泉水水位即恢復原平穩(wěn)變化趨勢[11]。另外,采礦活動用地特別是南部山區(qū)露天采礦用地的增加,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大氣降水的入滲,增加了地表徑流量。
3.4 土地利用類型對徑流的影響
由于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城鎮(zhèn)化迅速擴張,人類活動改變了水循環(huán)系統(tǒng)原本的空間格局與時間過程,加劇了水資源變化的復雜性,導致水循環(huán)系統(tǒng)中徑流、蒸發(fā)及入滲等各種自然過程發(fā)生變化,從而影響了地下水的入滲補給量。由于工作區(qū)內(nèi)暫無全面的、長系列連續(xù)的地表水文監(jiān)測資料,借用濟南城區(qū)規(guī)模擴展對地表徑流的影響進行對比分析[12]。據(jù)資料,1960—1965年間濟南城區(qū)附近最大降雨徑流系數(shù)僅為0.41,隨著城市建成區(qū)規(guī)模不斷擴張,到1990—1992年間,城區(qū)徑流系數(shù)達到了0.366~0.588,最大降雨徑流系數(shù)達0.82。地表徑流系數(shù)的增大直接造成了降水入滲補給系數(shù)的減少,泉群流量也相應的。
3.5 影響泉流量因素的相關(guān)性分析
當觀測井水位標高超出57.80m時泉水自流,而泉水自流量的大小主要取決于泉域地下水補給量、排泄量的相互轉(zhuǎn)換關(guān)系:地下水人工開采量和煤礦排水增加,則地下水天然排泄量即泉水流量減少;反之,地下水人工開采量和煤礦排水減少,則地下水天然排泄量即泉水流量增加。基于泉水流量、降水量、地下水開采量、煤礦排水量的長期動態(tài)監(jiān)測(表1),繪制了1991—2013年泉水流量與當年降水量、前一年降水量、煤礦開采、地下水開采量之間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綜合反映了泉水流量與各補排量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
3.5.1 單因素相關(guān)性分析
對1991—2013年的泉水流量與當年降水量、前一年降水量、煤礦開采及地下水開采量各因素,采用皮爾遜相關(guān)系數(shù)法進行了單因素相關(guān)性統(tǒng)計分析(表2)。通過分析,前一年降水量對泉水流量的補給影響大,為強相關(guān)關(guān)系,當年降水量影響略小;地下水開采與泉水流量呈負相關(guān),對地下水的排泄貢獻較大,為強相關(guān)關(guān)系,煤礦采水影響稍小。
3.5.2 多因素綜合分析
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定性和定量相結(jié)合的多目標分析方法,從分析影響泉群流量因素及其構(gòu)成關(guān)系入手,對影響泉群流量的因素進行優(yōu)選,提出泉群流量影響因素的層次結(jié)構(gòu)評價模式。通過建立指標權(quán)重體系,進行權(quán)重的測算、排名,得出對泉群流量影響較大的因素,通過對這些影響因素的控制,從而加強對泉群流量目的性的保護與控制。

表1 泉水流量與各相關(guān)因子監(jiān)測數(shù)據(jù)
注:泉流量Q實;當年降水量Pn;前一年降水量Pn-1;煤礦Q煤開;地下水開采Q超采。

表2 百脈泉泉水年流量及水位與大氣降水量相關(guān)性統(tǒng)計分析
注:相關(guān)系數(shù)絕對值越大,相關(guān)性越強;y為泉群流量;x1,x2,x3,x4為各影響因素。
根據(jù)影響因素的分析,結(jié)合單因素分析結(jié)果,運用層次分析法AHP[13]對影響泉流量的各因素包括當年降水量、前一年降水量、地下水開采、煤礦開采及地面徑流系數(shù)進行綜合分析,分析結(jié)果如表3。
可以看出,前一年降水的影響最大,權(quán)重高達0.3783,當年降水的影響相對略小,權(quán)重為0.1892,兩者權(quán)重和為0.5675,顯示降水量對泉水出流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該結(jié)果與線性相關(guān)分析基本一致;而地下水開采和煤礦排開采權(quán)重和為0.3574,說明兩者對泉流量影響程度較大;地面徑流系數(shù)權(quán)重0.0751,表明土地結(jié)構(gòu)變化影響泉流量程度較小。

表3 影響泉自流量的各影響因素權(quán)重
4 結(jié)論和建議
(1)明水泉域東邊界為禹王山斷裂,西邊界為文祖斷裂,南以變質(zhì)巖及早寒武世朱砂洞組底板為界,北則以奧陶紀灰?guī)r頂板埋深600m線為界,總面積660km2。
(2)百脈泉群泉流量變化過程主要可分為以下4個階段:高水位大流量階段(1969—1981年),水位下降斷續(xù)出流階段(1982—1998年),低水位持續(xù)停噴階段(1999—2003年)以及人工調(diào)控階段(2004—2014年)。
(3)影響泉群噴涌的因素主要有大氣降水、人工開采、煤礦排水及土地利用情況等,其中,降水量的大小(特別是當年及前一年降水)對泉水出流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遇枯水年地下水開采及煤礦排水是加速泉水斷流及延長泉水斷流時間的主要因素。
[1] 胡丙忠.明水泉群成因機理及泉域巖溶地下水數(shù)值模擬[D].山東科技大學,2012.
[2] 祁曉凡,楊麗芝,韓曄,等.濟南泉域地下水位動態(tài)及其對降水響應的交叉小波分析[J].地球科學進展,2012,27(9):969-978.
[3] 高贊東,劉術(shù)明,邢立亭,等.濟南巖溶泉域區(qū)域水文地質(zhì)信息系統(tǒng)構(gòu)[J].山東國土資源,2012,28(3):25-27.
[4] 商廣宇,王建軍,李森.開發(fā)濟西停采東部確保名泉常年噴涌:關(guān)于恢復名泉正常噴涌若干措施的建議[J].地下水,2002,24(3):143-150.
[5] 商廣宇,王建軍.有的放矢科學保泉:濟南泉域邊界條件論證[J].地下水,2002,24(4):191-194.
[6] 孫斌,彭玉明.濟南泉域邊界條件、水循環(huán)特征及水環(huán)境問題[J].中國巖溶,2014,33(3):272-279.
[7] 李媛媛,孟憲紅,李雅靜.百脈泉群斷流及明水泉群水資源保護的探討[J].山東環(huán)境,2001,(3):44.
[8] 袁傳芳,劉偉,劉永紅,等.影響百脈泉噴涌因素淺析[J].山東水利,2006,(9):23-24.
[9] 張茂國.影響濟南市區(qū)泉群流量的因素分析[J].山東水利,2005,(2):43-44.
[10] 曹潤珍.神頭泉流量動態(tài)及影響因素分析[J].山西水利,2008,24(3):22-23.
[11] 袁傳芳,張運區(qū),逯志強.煤礦開采對明水泉的影響淺析[J].山東國土資源,2003,19(6):48-51.
[12] 劉莉莉,宋蘇林,崔春梅.濟南泉水的成因及保泉對策研究[J].山東水利,2013,18(5):17-18.
[2] 鄧雪,李家銘,曾浩健,等.層次分析法權(quán)重計算方法分析及其應用研究[J].數(shù)學的實踐與認識,2012,42(7):93-100.
Analysis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charge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Baimai Spring Group
CUI Aiping1, YU Cuicui2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Qingdao 266590,China)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charge in Baimai spring group since 1971 have been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According to runoff discharge conditions of karst groundwater in the studying area, quantitativ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karst groundwate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springs flowing and precipitation,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land-use (vegetational cover) has been carried out. It will provide the basis for protecting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is area.
Baimai spring group; discharge; flow;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factors; correlation analysis
2016-03-24;
2016-05-17;編輯:陶衛(wèi)衛(wèi)
崔愛萍(1990—),女,山東濰坊人,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水文地質(zhì)方面的研究;E-mail:2682566619@qq.com
P641.6
B
崔愛萍,于翠翠.百脈泉泉群流量動態(tài)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J].山東國土資源,2016,32(9):30-35.CUI Aiping, YU Cuicui.Analysis o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charge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Baimai Spring Group[J].Shandong Land and Resources, 2016,32(9):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