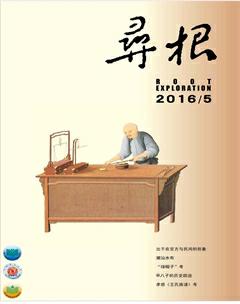山西地區龍天廟考論
李薈 王金平
中國境內廟宇眾多,諸神共奉,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其中,祠廟建筑內容豐富,數量龐大,是民間祭祀和信仰活動的主要場所。龍天廟是祠廟建筑的代表之一,主要分布在山西境內。龍天廟究竟為何廟,所祀何者?有人直接將其當作“龍王廟”;也有人將“龍天”一詞作“真龍天子”解,認為該廟是祭祀漢文帝劉恒或后漢皇帝劉知遠的;還有人認為該廟供奉的是佛教的龍天護法,即天龍八部。本文旨在對龍天廟史料、碑刻及縣志等文獻加以分析和論證,并找出該廟的祭祀對象。
龍天廟概況
龍天廟集中分布在山西中部地區,即晉中和晉西地區。明清時為太原、汾州兩府,以及平定、霍、沁直隸州所轄地,即今太原、呂梁、晉中、陽泉四市以及長治沁源所轄地。
根據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資料可知,山西境內現存龍天廟共計133處,其中孝義市30處,汾陽市18處,介休市、靈石縣各11處,其他地區均不超過10處。其中,孝義市所存龍天廟數量最豐。
現存龍天廟年代最早的是孝義市的南姚龍天廟,為金代建筑;元代龍天廟建筑共計5座,分別是孝義市的舊尉屯龍天廟、東董屯龍天廟和汾陽市的柏草坡龍天土地廟、石家莊龍天廟、東石龍天廟;其余均為明清建筑,共計127座。
汾陽府龍天廟
關于龍天廟,乾隆《介休縣志·壇廟》載:“龍天廟,祀晉邑賈公渾,在當樂村墓前。各村亦多建廟,謂其能致雨澤。競不知其忠節,惟北里村碑文詳述其事。”在同書“藝文”下收錄有乾隆十六年(1751年)該廟碑文:
新北里村龍天廟記王彥柱
侯,名渾,魏昌賈氏。來令我邑。與眾聚,勿施民歌,孔邇良有司也。時晉永興元年,劉元海遣將喬唏寇西河,攻破介休。侯與夫人宗氏俱不屈,死。邑人既懷其德,復憫其中,立廟祀之。歲時,暴嘗弗替,而水旱疾疫禱之,必應,祈雨猶靈。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二者侯具有焉。宜乎俎豆千秋,遍邑中皆尸祝也。顧廟號龍天,祀典未之載,古碑亦剝落不可考,不知始于何代。間當思之,龍能興云致雨,澤及萬物,侯之歲被陰膏,其靈昭昭而民無不戴之,如天義或取諸此乎!我里之廟創于元至正間,數百年來屢經整茸,今復將圮焉,爰告于眾日。侯令我邑時,愛民若子,既而死衛社稷,無非心衛我民。至千百載后,調雨嚦介,黍稷靈爽,在天愛民如一日,則千百載后猶我父母也。既為我之父母,而忍其露寢乎?眾欣然相與維新之工,既竣,勒碑以記其事。時乾隆辛未十月三日也。
由新北里龍天廟碑文可知,該廟為祭祀西晉八王之亂中守節而死的介休令賈渾。同時,乾隆《介休縣志》《冢墓》篇有“賈侯墓在常樂村,離城三里,賈侯渾夫婦死節,邑人收葬于此”的記載,《藝文》里有《晉邑令賈公墓碑記》的碑文,對照龍天廟碑文可知,賈渾墓與廟相對而建。《禮記·祭法》載:“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肆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賈渾守節而死,符合祭法“以死勤事”,死后立廟,“水旱疾疫禱之必應,祈雨猶靈”,符合祭法“能御大災”,祭法五種符合有二,當是祭之。另《晉書·列傳》的《忠義》篇有對賈渾的記敘: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唏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日:“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茍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唏怒,執將殺之,唏將尹崧日:“將軍舍之,以勸事君。”唏不聽,遂害之。
由是可佐,介休一地龍天廟當為祭祀賈渾夫婦的。
嘉慶《介休縣志·壇廟》中也對龍天廟做了介紹:“賈侯廟,俗呼龍天廟。祀晉邑令賈公渾,在常樂村墓前。縣境及孝義、永寧、寧鄉各境亦多立廟,謂其能致雨澤……”可見孝義、永寧(離石)、寧鄉(中陽)所祀龍天廟也應當是祭祀賈渾的。《晉汾古建筑調查紀略》一文對汾陽縣峪道河旁的龍天廟做了詳細的記述,其中正殿廊下的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重增修龍天廟碑記》也有載:“龍天者,介休令賈侯也。公諱渾,晉惠帝永興元年,劉元海……攻陷介休,公……死而守節,不愧青天。后人……故建廟崇祀,……像神立祠,蓋自此始矣。”介休、孝義、永寧、寧鄉明清時屬汾州府,除該四地,汾州府還轄汾陽、平遙、臨縣及石樓,這些地區與上述四地相互穿插。《汾陽縣宣柴堡村志》所載《重修龍天廟觀音堂記》中有述“余村西北隅有龍天廟一所,其神靈地吉,前人之說備矣。自修建以來雖屢經補葺……大清光緒十七年”,并未說明龍天廟由來,卻說前輩人關于這方面的記載敘述已經很多,遍查縣志,卻并未有對汾陽縣龍天廟的記載。康熙《永寧州志·寺廟》也沒有對龍天廟由來有所記述,平遙、臨縣等地也未尋到。
人們對神靈的崇奉具有地域性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地域的祭祀圈和信仰圈,一般來說,同一地域的祭祀對象是相同的。可以推斷,汾州府境域內汾陽、平遙、臨縣等地的龍天廟也應當是祭祀賈渾夫婦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上,賈渾廟先后兩次列入國家明確承認的民間祭祀,一次在宋代,一次在明代。
《宋史》“諸祠廟”載:“熙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州縣岳瀆、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諸小祠,皆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多,不能盡錄云。”賈渾本為介休縣令,其“功及生民”“能興云雨”,應是在“熙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增入祀典。《晉書》中將賈渾列入“忠義”,而宋時加封爵為“賈侯”。
《大明會典·有司祀典上》有載:“舊典、雜列各處山川土神、古今圣賢、忠臣烈士、能御大災、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或奉特敕建廟賜額,或沿前代。降敕護持者、皆著祀典、秩在有司、不可勝列。”而賈渾為“忠臣烈士”,其“有功于國家”“惠愛在民”,在此時又一次列入國家正祀之中。調查中,筆者發現龍天廟多為明代以來所建(計127處),應為統治者提倡故。
太原府及平定、霍、沁直隸州龍天廟
乾隆《太原府志》及道光《太原縣志》的“祀典”篇載:“龍天廟在南關,七月七日祭。”《太原縣龍天廟祭龍民俗考略》一文說,南關龍天廟(晉源區南街村)是祭祀漢文帝劉恒的,而《龍天與圣母:晉水流域民間信仰的在場與城鄉關系》一文又說南關龍天廟是祭祀北漢劉知遠(筆者在此糾正,應為后漢劉知遠),那么,南關龍天廟所祀究竟何人?
據道光《太原縣志·帝王》載:“漢文帝,諱恒。高祖中子,太后薄氏出。初立為代王,都晉陽。高祖崩,諸呂為亂。大臣共誅之,乃相與謀立代王。奉天子璽迎之,在位二十年。當幸太原,賞賜故舊群臣。賜里民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飲十余日,晉人立廟祀之。”該文記載漢文帝巡幸太原,賞賜舊臣,宴請太原百姓,百姓感念文帝恩德,所以建廟來奉祀。由此,漢文帝廟是肯定存在的。《大明一統志》中記載“漢文帝廟在陽曲縣東北。文帝當幸太原,故立廟于此。”乾隆《太原府志》也有載“漢文帝廟在府城東北”。明清時期的太原府城便在陽曲縣城,所以說府城陽曲東北的漢文帝廟是真正祭祀漢文帝劉恒的。而乾隆《太原府志》《祀典》篇同時記載“龍天廟在南關”和“漢文帝廟在陽曲縣東北”,可以肯定南關龍天廟并非祭祀漢文帝,祭祀漢文帝的廟在陽曲縣,南關龍天廟主人另有其人。但在臨縣張家溝2010年的一處重修碣(《重修龍天廟碑記》)中又有這樣的記述:“……龍天廟,唯三晉獨有。相傳,公元前一九六年,漢高祖封劉恒為代王,統轄晉陽,恒攜生母在晉十七年,以德化民,仁孝聞于天下。登基后,勿忘故地,在位二十三年,曾四次重游,情深義重,足見一斑。百姓沐浴,知恩,謝恩,油然敬仰。公元前四十年,朝廷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官府奉旨毀廟,民間卻很難忘劉恒賢良。于是,唯在三晉出現了‘龍天廟,以祀之……”文中“朝廷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之郡國廟是西漢特有的產物,從漢高帝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開始,惠帝又“令諸侯王立高廟”,此后陸續增加,到元帝時,形成龐大的“廟群”。這是漢初通過制度神圣化出身寒微的統治家族之計劃的一環,漢帝國從文、景以后,劉家的神圣地位已經被充分承認,立郡國廟神圣化皇家權威的用意已經喪失。由于讓同姓諸侯分享宗法上的特權,朝廷面臨神圣權力被分享的窘境,亦即諸侯國由于立有先帝的宗廟,等于有了“禮制”給予的入承大統的正當性,所以朝廷要罷郡國廟。郡國廟是皇帝宗廟,非劉氏皇族之人不得祭,而供奉漢文帝的廟是晉陽人自發而立的,并非郡國廟,因此說“朝廷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官府奉旨毀廟,民間卻很難忘劉恒賢良。于是,唯在三晉出現了‘龍天廟以祀之”的說法不可信。在太原南關祭龍民俗活動跪拜上供時嘴里說的“代王,代王,我來也!”或是“代王到!代王到!啊哈彌而拉茂!”的這類話也并不足信,因為民間所說的“代王”多是“大王”的音意,憑此類民間語句并不能說明是漢文帝劉恒。況劉恒巡幸太原時已稱帝,民間不可能還稱其為“代王”,反而“代王”一詞容易讓有心人誤認為是未稱帝時的劉恒。
南關龍天廟又說是祭祀后漢皇帝劉知遠的,這一說法在當地百姓中間口耳相傳。《舊五代史·漢書·高祖紀》載:“高祖睿文圣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禺,本名知遠,及即位改今諱。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史臣曰: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并、汾,遄臨汴、洛,乘虛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圖,雖日人謀,諒由天啟。然帝昔蒞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來蘇之望。良以急于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蓋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睹為君之德也。”可見后漢高祖劉知遠并未有恩于民,反而戰禍連年,民生凋敝。他并不符合前述祭法所列的入祀條件,其德行也非需人民祭祀信仰。因此,南關龍天廟是祭祀后漢皇帝劉知遠一說也待考。《龍天與圣母:晉水流域民間信仰的在場與城鄉關系》一文將后漢皇帝劉知遠寫作“北漢皇帝劉知遠”,且在文中說“劉知遠曾經篡位為王的歷史……”“北漢是晉陽古城輝煌時期的最后一個割據政權,龍天廟的最初產生也許是地方官扶持的,甚至極有可能有著皇家背景……”筆者認為該文作者將劉禺(劉知遠)誤作劉崇。因為在《舊五代史》中,劉知遠所建的后漢王朝是作為正統政權來寫的,而將劉崇所建的北漢政權列在“僭偽”篇。若說龍天廟的祭祀對象是劉崇,則更是不對;若說是劉知遠,則也存疑。
太原府其他地區及直隸州龍天廟所祀對象也無考,僅在縣志中對其所在地點有零星記載。
龍天廟分布范圍廣泛,區域內又呈集中分布,且廟宇規模較大,其建造應不僅僅是靠民間鄉紳籌資,其中也應當有官方力量的介入。在各地史籍中,唯西晉介休縣令賈渾列入官方記錄,在《晉書》《山西通志》《介休縣志》以及碑文、墓志銘等均可尋到,脈絡清晰。早期龍天廟建筑也多分布在介、孝、汾等地,山西中部的龍天廟應當都是祭祀賈渾的,其信仰應是從一地向多地擴散的結果,即龍天信仰在空間方面實現其自身的擴張。在擴張的過程中,伴隨著迎神祭賽活動的盛行,如清人劉大鵬所著《晉祠志》中便描述了“圣母出行”途中經過龍天廟時,鄉人祭祀龍天的場景。
龍天廟中有爭議的是上述的太原南關龍天廟,一說是漢文帝劉恒,一說是后漢高祖劉知遠。上文已證實并非漢文帝廟,而劉知遠也實非圣君,稱帝時戰火不斷,在位不足一年,并未于民恩澤,像這樣大范圍的祭祀是不可能的,因此說也不應當是祭祀劉知遠的廟宇。最有可能的還應是賈渾,宋代和明代兩次列入正祀之后,經由官方勢力的介入,使得龍天廟信仰廣泛傳播,其廟宇也遍布山西中部地區。在這一過程中,對賈渾個人的推崇漸無,取而代之的是對其副功能(祈雨、消災解難)的崇敬。以至于僅介休、汾陽等地個別廟宇碑文有對龍天廟由來的記述,其他地區均不見記載。龍天廟最初是祭祀個人的,屬先賢祠廟。因其“水旱疾疫禱之必應”“祈雨猶靈”,漸被人們當作神靈來信奉,并與民間俗神融合,逐漸演化為神祠或神廟。這些神有土地、龍王、觀音(或娘娘)、圣母(或娘娘)等,大多數龍天廟內部供奉數個神靈,主殿是龍天廟,前殿或配殿供奉土地、龍王、觀音、圣母等。有些龍天廟是直接和神靈一塊命名的,如龍天土地廟、龍天圣母廟、觀音龍天廟等。
結語
龍天廟是地域性的民間祠廟,集中分布在山西中部地區,以介(介休)、孝(孝義)、汾(汾陽)為多,今存建筑多為明清所建。介休應是龍天廟的起源地,最初為祭祀西晉介休縣令賈渾及其夫人的,通過經年累月的民間傳播,加之統治者的提倡,使龍天廟迅速擴散,其廟宇也占據了幾乎整個山西中部地區。
在龍天廟擴張的過程中,因其能“致雨澤”、消“水旱疾疫”,人們便逐漸淡忘了其原來建廟的初衷,久而久之,龍天廟漸漸披上了神的面紗,民間俗神進駐廟宇,被人們當作神靈廟宇來祭祀。該廟宇能興云致雨、消災解難,人們將龍天廟當作龍王廟也就不難理解了。將“龍天”作“真龍天子”解的,文中也已闡明,并非供奉漢文帝或是劉知遠。認為是“佛教的龍天護法”的,并沒有任何依據,所有龍天廟建筑內并未供奉任何佛教神像(觀音菩薩雖為佛教人物,但已被世俗化,其神靈角色更類于民間俗神)。
龍天廟是先賢祠廟轉化為地方神廟的代表,是中國古代社會民俗信仰變化的縮影,對于區域性廟宇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作者單位:太原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