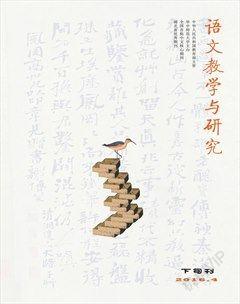唐詩的花與果
劉醒龍
一個(gè)人怎么會(huì)在心靈中如此迷戀一件鄉(xiāng)村之物?
這種感覺的來源并非是人在鄉(xiāng)村時(shí),相反,心生天問的那一刻,恰恰是在身披時(shí)尚外裝,趴在現(xiàn)代輪子上的廣州城際。那天,獨(dú)自在天河機(jī)場(chǎng)候機(jī)時(shí),有極短的一刻,被我用來等待面前那杯滾燙的咖啡稍變涼一些,幾天來的勞碌趁機(jī)化為倦意,當(dāng)我從仿佛失去知覺的時(shí)間片段中驚醒,隔著熱氣騰騰的咖啡,所看到的仍舊是掛在對(duì)面小商店最顯眼處那串鮮艷的荔枝。正是這一刻里,我想到了那個(gè)人,并且以近乎無事生非的心態(tài),用各種角度,從深邃中思索,往廣闊處尋覓。
那個(gè)人叫石達(dá)開。這一次到南方來,從增城當(dāng)?shù)厝四抢锏弥?xí)慣上將這位太平天國(guó)的著名將領(lǐng)說成是廣西貴縣人,其實(shí)是在當(dāng)?shù)赝辽灵L(zhǎng),只是后來家庭變故,才于十二歲時(shí)過繼給別人。十二歲的男孩,已經(jīng)是半個(gè)男人了,走得再遠(yuǎn),也還記得自己的歷史之根。傳說中的石達(dá)開,在掌控南部中國(guó)的那一陣,悄然派一位心腹攜了大量金銀財(cái)寶藏于故鄉(xiāng)。兵匪之亂了結(jié)后,石姓家族沒有被斬草除根,只是改了姓氏,當(dāng)?shù)毓俑踔吝€容許他們修建了至今仍然顯得宏大奇特的祖祠武威堂,大約是這些錢財(cái)在暗中發(fā)揮作用。身為叱咤風(fēng)云的清代名將,對(duì)于故鄉(xiāng),石達(dá)開想到和做到的,恰恰是鄉(xiāng)村中平常所見的人生境界。
歲月不留人,英雄豪杰也難例外。增城后來再次有了聲名,則是別的緣故。因?yàn)橛辛烁咚俳煌üぞ撸@座叫增城的小城,借著每年不過出產(chǎn)一兩百顆名為掛綠的名貴荔枝之美譽(yù)忽然聲名遠(yuǎn)播。那天,在小城的中心,穿過高高的柵欄,深深的壕溝,站到寵物一樣圈養(yǎng)起來的幾株樹下,靈性中的惆悵如同近在咫尺的綠蔭,一陣陣濃烈起來。
不管我們自身能否意識(shí)到,鄉(xiāng)村都是人人不可缺少的故鄉(xiāng)與故土。在如此范疇之中,鄉(xiāng)村的任何一種出產(chǎn),無不包含人對(duì)自己身世的追憶與感懷。正如每個(gè)人心里,總有一些這輩子不可能找到的替代品,而自認(rèn)為是世上最珍貴的小小物什。鄉(xiāng)村的日子過得太平常了,只要有一點(diǎn)點(diǎn)特異,就會(huì)被情感所輕易放大。鄉(xiāng)村物產(chǎn)千差萬別,本是為了因應(yīng)人性的善變,有人喜歡醇甘,也有人專寵微酸,一樹荔枝的貴賤便是這樣得來的。因?yàn)槌闪素暺罚荒苁峭盏弁酢⑺箷r(shí)大戶所專享,非要用黃金白銀包裹的指尖擺著姿態(tài)來剝食。那些在風(fēng)雨飄搖中成熟起來的粗礪模樣就成了只能藏于心尖的珍愛之物,當(dāng)?shù)厝松踔吝B看一眼都不容易,長(zhǎng)此以往當(dāng)然會(huì)導(dǎo)致心境失衡。
從殘存下來的歷史碎片中猜測(cè),十二歲之前的石達(dá)開,斷然不會(huì)有機(jī)會(huì)親口嘗到那樹掛綠的甜頭,如能一試滋味,后來的事情也許會(huì)截然不同。鄉(xiāng)村少年總會(huì)是純粹的,吃到辣的會(huì)嘬著嘴發(fā)出滋滋聲,吃到甜的會(huì)抿著嘴弄出嘖嘖響,率性的鄉(xiāng)村,沒有爆發(fā)什么動(dòng)靜時(shí),連大人都會(huì)不時(shí)地來點(diǎn)小貓小狗一樣的淘氣樣,何況他們的孩子。石達(dá)開甚至根本就不喜歡荔枝,在這荔枝盛產(chǎn)之地,如果他嘗過所謂掛綠,只要有機(jī)會(huì),便極有可能用其掉換一只來自遙遠(yuǎn)北方的紅蘋果。事情的關(guān)鍵正是他缺少親身體驗(yàn)。絕色絕美的荔枝,或許根就是地方官吏與前朝帝王合謀之下的一種極度夸張。小小的石達(dá)開想不到這一層,而以為那棵只能在夢(mèng)想中搖曳的荔枝樹,那些只能在天堂里飄香的掛綠果,真的就是益壽延年長(zhǎng)年不老之品。
是種子總會(huì)在鄉(xiāng)村在發(fā)芽。難道就因?yàn)槲蛔饳?quán)重,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掠走鄉(xiāng)村的心中上品?后來的石達(dá)開,一定因?yàn)檫@樣想得多了,才拼死相搏,以求得到那些夢(mèng)幻事物。后來的石達(dá)開,得勢(shì)之時(shí)還記得這片鄉(xiāng)村,難道沒有對(duì)少年時(shí)望塵莫及的荔枝掛綠的回想?
在現(xiàn)在據(jù)說是用石達(dá)開捎回來的財(cái)寶修建的宗祠的屋檐上,至今還能見到“當(dāng)官容易讀書難”的詩句。當(dāng)年不清楚的事情,留待如今更只有猜度了。正是由于如此之難,更可以讓人認(rèn)為石達(dá)開當(dāng)然吟誦過杜甫的名句。那些開在唐詩里的鄉(xiāng)村之花,一旦與歷史狂放地結(jié)合,所得到的果實(shí),就不是只為妃子一笑的一騎紅塵,而是一心想著取當(dāng)朝而代之的金戈鐵馬萬千大軍。
沒有記憶,過去就死了,不得再生。沒有記憶,歷史就是一派胡言,毫厘不值。沒有石達(dá)開了,沒有掛綠,荔枝總不至于不是荔枝了吧?將唐詩當(dāng)作花來盛開,最終還得還以唐詩滋味。這樣的荔枝才是最好的。
(選自中國(guó)作家網(wǎng))
- 語文教學(xué)與研究(讀寫天地)的其它文章
- 水調(diào)歌頭[1]
- 尚節(jié)亭記
- 浣花溪記
- 人生當(dāng)架幾座橋
- 蘇軾的審美趣味
- 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