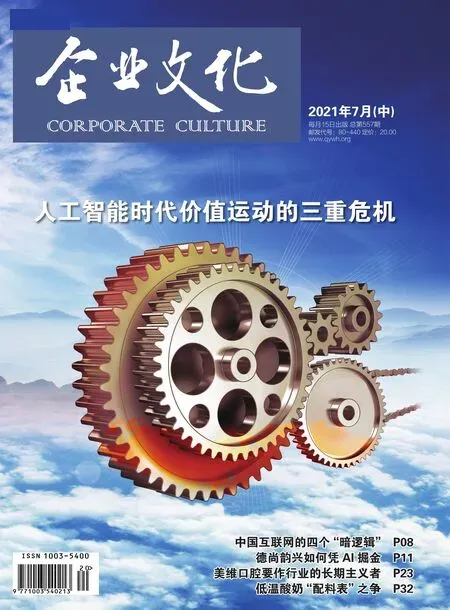國企專業技術人才培養實踐與認識
文|夏江洲
當今社會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上至國家、下至企業,人才已經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性因素。面對日新月異的鉆井市場競爭環境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作為高風險、高投資的鉆井行業,如果專業技術人員的素質偏低,勢必影響企業今后的發展和壯大,所以必須做好人才的培養,才能使企業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在現今和未來的競爭立于永不敗之地。我們鉆井一公司已經建立和實施了培養“三高”人才(高素質經營管理人才、高水平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操作人才)的一系列政策和辦法,且已經收到良好的效果。分公司主要擔負著公司技術質量管理與技術人才的培養及技術服務的職能。下面筆者結合我們分公司實際,就如何抓好“三高”人才中高水平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簡要談一下自己的幾點認識。
一、牢固樹立人才是企業第一資源的觀念,切實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營造人才成長的良好環境
事業要發展,人才是關鍵,一項宏偉的事業,需要無計其數甘于奉獻、富有創新精神的人才來完成。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分公司始終堅持把人力資源當作企業最大的資源看待,牢固樹立人才是企業第一資源的觀念,結合分公司實際,積極創造條件,用事業凝聚人才,用科學的機制激勵人才,切實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使大批專業技術人才脫穎而出,為企業的快速發展提速助力。
企業的興衰與人才的素質教育有著密切的關系,任何一個企業都渴望擁有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但在人才使用過程中,由于國企在體制和機制等方面,確實存在著某些弊病。有時,由于對人才使用不當會使人才產生“無用武之地”的感覺,最終跳槽而去。以往,我們公司也出現類似的情況。比如,有一名學習地質專業的大學生分到我公司,一年實習期滿后,他想回專業對口的地質室,可是正趕上企業定崗定編,他沒能如愿,后來辭職考研離開了公司。隨著管理局分開分立,鉆井行業作為存續企業,一些大學生不愿意來我公司,隨著外拓市場需要大批專業技術人才,許多鉆井隊出現了鉆井工程師不是大中專畢業生而是技校畢業生居多的現象。公司也一度出現石油工程專業類大學生斷檔現象。近年來,情況大有好轉,隨著我們企業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企業發展態勢良好,再有對人才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比如鉆探集團總經理劉富同志在鉆探集團一屆二次職代會上提出的鉆探集團實施五大戰略,其中把“人才強企戰略、科技創新戰略”都放到重要位置上,可見,人才科技創新是企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雙翅膀,而科技創新更離不開專業技術人才的辛勤工作。
為貫徹落實科學人才觀,實施人力資源開發戰略,管理局和鉆探集團都進行了技術專家聘任工作,對聘任的專家都給予一定待遇,大大地激發了科技人才的工作熱情。他們在工作中緊緊圍繞鉆井生產實際提高公司核心技術競爭能力,在科研領銜和開展技術創新以及培養后備人才等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專業技術人才代表,是我們企業無形的寶貴財富,通過他們的典型引領作用,分公司結合實際,做到了學有榜樣,趕有目標,并且因人而異,結合個人素質和能力的實際,詳盡制定出員工遠景職業生涯發展規劃設計,同時通過專家師傅帶徒弟,加大培養核心技術人才和年輕梯隊骨干人才,分公司形成了一支樂于學習,善于學習的職工隊伍。通過這些辦法,為培養好一支高水平的專業技術人才隊伍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進一步在公司范圍內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充分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科學技術加快向生產力轉化,公司也加大了對科研項目的效益提成獎勵金額,用于對科技人才的獎勵,公司用于科技項目和科技創新人員、優秀科技工作者、優秀科技管理者獎勵的額度就達50 余萬元,提高了廣大科技人員努力專研、不斷創新的積極性,不僅積極營造了人才成長的良好環境,也為公司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技術保障。
二、建立和完善人才使用機制,變相馬為賽馬,做到人盡其才,為人才成長施展才能奠定基礎
一個人只有處在最能發揮其才能的崗位上,才會為企業創造出最大的經濟效益,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個人價值。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分公司不斷建立和完善人才使用機制,做到人盡其才,實現最佳的人職匹配。分公司的技術人員大多都是來自各鉆井公司的井隊工程師,有一定的技術實力和經驗,分公司通過對他們的考察和根據各自技術專長,把他們安排到固井監督和定向井及特殊工藝井管理等重要專業技術崗位,適當委以重任,實現了人才資源較好的配置,真正做到了人適其事,事適其人,人盡其才,人盡其用。
不斷完善人才使用機制,分公司通過評選學術技術帶頭人,加強完善公司人才庫、實行科技項目津貼制等方式,變相馬為賽馬,進一步調動了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分公司在鉆井工程等專業技術人員中共有10 名技術人員被評為公司第四屆學術技術帶頭人。同時通過優先推薦“人才庫”中的技術人員外出培訓鉆井前沿技術、外語等形式,使他們的綜合能力得到進步提高,幾年來,為國內外鉆井施工項目部輸送了各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滿足了外拓市場的生產急需,促進了人才發展。在科研項目中建立了項目負責制和課題制,制定完善了項目效益評價辦法,使專業技術人才不僅僅是因為有高級或中級職稱就“拿錢”多,而是看你能否開展好科研項目,是否為公司的鉆井生產真正的作出了貢獻。一個優秀的企業也一定是一個學習型組織,只有通過不斷的學習,企業的戰略思想和理念才不會滯后于時代發展的步伐,永遠走在本行業發展的最前沿。分公司以“爭創學習型企業,爭做知識型職工”活動為契機,采取內部技能培訓和外送學習相結合,對人才隊伍進行強化培訓。分公司培養出了相當一部分人員充實到公司市場開發中心,成為外拓市場的領頭雁。同時分公司利用公司出臺的畢業后實行學費補貼等有關激勵政策,鼓勵職工自學成才和進行學歷性繼續教育。分公司現有7 人參加工程碩士學習,有20 余人在進行各專業的自考本科學習,通過學習很好地提高了專業技術人才的自身業務素質,為人才成長施展才華奠定了基礎。
三、是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才理念,關心人才成長,使人才成長促進企業快速發展
關注人才,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才理念,關心人才成長,不斷優化專業人才隊伍,使人才成長促進企業快速發展。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都在考慮如何把人才吸引住,如何把人才的作用切實發揮好,中國也適時提出了人才強國戰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就是要把人才隊伍建設好,而要把人力資源建設好,就一定要灌輸人性化管理的思想,創新思維,從工作上、生活中關心、愛護人才。用先進的企業文化引導人,以完善的制度約束人,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貫穿于人才成長的全過程。
分公司一直把關心人才成長放到首要位置上,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動心,以情鼓勁。在生活中,始終把技術人員的冷暖放在心頭。比如質量室游耀輝同志是負責公司井架基礎工作的一名技術人員,他在日常工作中,刻苦鉆研技術,圍繞公司效益,在本職工作崗位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幾年來,他先后對8 種鉆機基礎進行革新,其中《改進填石灌漿基礎為毛石混凝土基礎》的技術創新,結束了填石灌漿傳統基礎施工的歷史,獲得公司技術革新一等獎,石油管理局QC 活動一等獎,經大力推廣使用,為公司創造了一定數量的經濟效益。在此期間,他因肺病,左側肺葉切除,術后感染不斷,由于用藥過量,致使腎功能嚴重受損并發炎癥。連續在北京住院一個多月進行康復治療,高額的醫療費用已經給他的家庭帶來經濟拮據。鑒于此實際情況,分公司特為他向公司工會申請了送溫暖基金,緩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使其及家人充分感受到組織的關懷和溫暖。他的身體剛剛有所好轉,就又返回工作崗位。
在新的時期,機遇與挑戰并存,只要在人才培養工作中創新思維,創新工作機制,營造環境,就一定能夠做到尊重人才,人盡其才,逐步建立起企業“為有源頭活水來”的人才蓄水池,為企業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