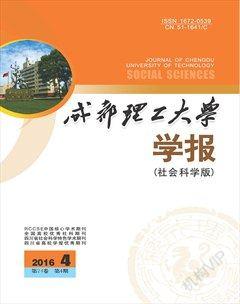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探析お
余紅 劉玉秀
摘 要:
由于我國現行法律規范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規定的模糊與回避,致使學界一直爭議不斷,存在不同的聲音,近年來司法實務也遭遇不同程度的裁判困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亟待解決。通過對現行法規及理論觀點的梳理,認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用益物權、財產權,符合繼承法遺產的特征,可以繼承,并從古今中外立法例、農村土地改革、農村社會保障現狀及農民意愿角度分析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具有現實必要性與可行性,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具體繼承進行了合理構想。
關鍵詞: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用益物權;財產權;繼承
中圖分類號: DF52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6)04002605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直接體現了農民對自身財產權利擁有的期待,不僅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影響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村社會的穩定,而且對完善我國現有農地制度亦具有深遠意義。然而我國法律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并未予明晰,其“模糊定義”與回避姿態,導致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都存在諸多爭議。隨著我國農民權利意識的提高,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價值逐漸顯現,訴至法院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糾紛案件逐年增多,法院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裁判困境,給司法實務帶來了較多的困擾。筆者認為,現行法律與農村經濟發展及司法實務現狀明顯脫節,有必要對其進行明晰及完善,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繼承并合理構建其繼承制度。值得關注的是,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繼承權。”以及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中明確把“引導農村土地(指承包耕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作為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點工作,并“鼓勵承包農戶依法采取入股、轉讓等方式流轉承包地”。出臺這些政策,目的是讓農民更加自由地流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積極參與到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建設中來,從而加快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化農業的實現,而這一目的與承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可繼承性本質相一致,為構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據和方向。因此,在此背景下,本文對現行規范、理論爭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合理構想進行探討,以期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制度的認可及構建提供些許助益。
一 、我國法律規定及理論界爭議
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我國現有法律規范雖有所涉及,但未明確。《繼承法》第4條規定:“個人承包應得的個人收益,依照本法的規定繼承。個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許由繼承人繼續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辦理。”明確承包收益可以繼承,而對承包經營權繼承未予明確,而所說的“依照法律允許由繼承人繼續承包的”具體是依照何法規定,在該法頒布實施之時也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對此進行過明確規定,并且當時的立法明確釋義,承包是合同關系,“繼續承包”不等同于“繼承”,不能按照遺產繼承的方法辦理,否則將對農業生產造成不利影響。由此可見,當時立法者實際上將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定位為合同關系,否定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可繼承性,排除了繼承法的適用。1993年《農業法》第13條第4款規定:“承包人在承包期內死亡的,該承包人的繼承人可以繼續承包”,這是對《繼承法》內容的一個補充,就此有學者樂觀地認為,立法者首次肯定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性,但令學者們失望的是,在2002年修訂《農業法》時卻刪除了該款規定。可見,《農業法》對其繼承性實際上也否定了。2003年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在第31條、第50條分別對農村土地的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承包方式作了具體規定。第31條:“林地的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第50條:“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的,該承包人死亡……在承包期內,其繼承人可以繼續承包。”據此,實際上《農村土地承包法》承認了家庭承包的林地和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地承包經營權的繼續承包性,但遺憾的是,立法者使用的仍然是“繼續承包”而未明確采用“繼承”一詞,而且對耕地和草地的承包人死亡后其承包經營權如何處理也未作規定。2007年《物權法》較為全面具體地規定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明確其為用益物權,平息了多年來理論界對其法律性質的爭論,有利于土地承包法律關系的長時間不變并保持穩定,能激勵農民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也能有效地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防止農村耕地的大量流失,維護廣大農民的合法權利。遺憾的是物權法對“繼承”問題仍采取了模糊回避態度。
我國法律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的模糊規定與回避姿態,理論界一直存在不同聲音,形成了肯定和否定兩種學說。否定說認為:目前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性沒有任何法律明晰過。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承包方是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不是戶里的單個成員。而繼承法規定只有個人的合法財產才能成為遺產,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并不是農戶里單個成員的財產,因此不能作為遺產繼承。“農地使用權可能因繼承事實轉移到非農業人口手中,這顯然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與農業的有效發展”[1]。“人的生死屬自然現象,如土地長時間不調整,再允許繼承,不可避免將導致土地細碎化,不能形成規模效益;還會導致許多新增農村人口得不到這份農村集體成員的基本社會保障,引起社會混亂。”[2]肯定說認為: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法律未明確不可以繼承。“土地承包經營權屬用益物權、財產權,有其使用價值和價值,應允許其同繼承人的其他財產一樣被繼承,保護被繼承人的繼承權實質上是保護原承包人的財產權。”[3]“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公民一項重要財產權,應當可以繼承。欠缺繼承性的財產權是一種不完整的財產權,難以有效流轉。”[4]“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會產生地權穩定性效應,激勵農民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提高農民的生產效率。”[5]可見,雖然學者們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其闡述的理由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不得不說其中有些理由論述并不充分,研究還不全面,說服力也較為薄弱,因此對其深入探討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繼承
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可繼承性,應當允許繼承人在承包期內繼承。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用益物權,既是財產權,又符合繼承法遺產的特征,具備了成為繼承權客體的可能性。再者,從古今中外立法例、農村土地改革的必然要求、農民意愿及農村社會保障現狀角度來論證分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也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從法制史和比較法的角度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應該能成為繼承權的客體,可以繼承,符合我國的歷史經驗和國外普遍立法慣例。從法制史角度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類似于傳統民法中的永佃權(田面權)。永佃權制度最早產生于北宋時期,明朝以后有所發展,清朝逐漸得到完善并普遍化,直至民國時期南京國民政府仍然將其規定在物權一編中,不論古代、近代,都明確規定永佃權可以繼承。可見,允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應是符合我國歷史相關法治理念的。從比較法角度看,雖然國外大多數國家實行農地私有制,但大多都規定了用益權或永佃權制度,如《法國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都設專章規定用益權制度,《法國民法典》規定:“用益權可以通過合同、遺囑等方式設立,規定只能一人享有農地繼承權,只能整體繼承或轉讓,其他繼承人只獲得金錢補償。”(1)《日本民法典》也詳細規定了永佃權制度,明確“權利人可以通過遺囑設定、繼承行為、讓與行為等方式獲得永佃權。”這些國家的法律也都明確允許用益權或永佃權繼承。
第二,從農村土地改革的角度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符合國家全面深化改革農村土地制度的精神以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良性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的政策要求。近年來,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全面深化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陸續出臺了多項政策,力促依法保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穩定并長久不變,以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并主動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如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享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2)國務院2012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也指出:“對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具體實現形式抓緊研究,完善相關立法。在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基礎上,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3)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中還進一步詳細規定了:“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鼓勵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從而使土地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達到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以及農村經濟穩步發展的目的。”筆者認為,既然國家政策一直致力于保障農村土地承包長時間不變,引導、鼓勵有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這就必然會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問題。因此,承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與國家政策導向相一致,是符合農村土地深化改革的本質要求的。
第三,從廣大農民的意愿來看,允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符合農民現實需求和期望。近年來,有許多學者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否繼承的問題進行了田野調查,通過采取實地走訪、發放問卷調查等方式深入了解、知曉廣大農民的實際意愿。多項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被調查的農民認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繼承,也迫切希望土地權利的權能包括繼承權。如學者劉娜的實證調查結果顯示,對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問題,69%的農民認為可以繼承;對于土地使用權是否包含繼承問題,有71.2%的農民認為應包含繼承權[6] 。允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符合農民的意愿,也是對農民土地權益的充分保障和尊重,如果否定其繼承性不僅會破壞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的固有期待,還會嚴重影響農民利益、農業及農村社會的發展與穩定。
第四,從農村社會保障現狀看,承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具有可行性。否認其繼承的學者最主要的理由是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農村土地具有福利性并承載著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而我國未形成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土地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難以替代,以此否認其繼承性[7]。但是,應該看到,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建立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的社會養老、醫療保障,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已經在不斷減弱。據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末我國鄉村人口61866萬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50107萬人,增加357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59774萬人,增加2702萬人;參加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31449萬人,增加1820萬人;參加工傷保險人數20621萬人,增加703萬人,其中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7362萬人,增加98萬人。”[8]由此表明,我國農村正逐漸廣泛地實行社會養老、醫療保險,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農村社會保障的腳步在加快,農村土地具有的福利性及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已逐漸被削弱并漸居次要地位,以農村土地承載社會保障功能為理由否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已與我國社會保障不斷發展的現狀相背離,漸趨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不管是從法制史與比較法、農村土地改革的角度還是從廣大農民意愿、農村社會保障現狀來看,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具有必要性與可行性,承認其繼承性將有利于農民充分利用土地、合理配置土地資源,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與穩定。
三、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的構想
承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可能會產生法律沖突,因此需要綜合考慮相關法律的協調,在堅持有利于農民生活、土地規模經營、防止土地零碎化等原則前提下,筆者對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提出以下構想,以實現最佳的社會效益,更好地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權益。
(一)對繼承客體不應進行限制
我國現行法將農村土地類型分為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方式承包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四荒”土地,對于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土地,承包經營權由于主體無特定的身份限制,也不承載社會保障功能[9],多數學者認為可以繼承,筆者也同意這種說法。而對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由于具有成員性質以及承載農村的社會保障功能,多數學者認為不能繼承,但卻以“林地承包期較長、投資大、收益慢,且林木所有權繼承不能與林地分離,若不允許其繼承,不利于調動承包人積極性,還可能造成濫砍濫伐等破壞生態環境的情況。”[10]為理由,認為家庭承包方式獲得的林地承包經營權可以繼承。筆者認為,對于繼承客體作以上限制是沒有必要的。因為,目前我國農村經濟在各項法律與政策的指引下正獲得長足的發展,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在完善,越來越多的農民獲得了基本生活及醫療保障,農村土地承載的社會福利及基本保障功能已在逐漸減弱,并且耕地、草地、林地承包經營權同屬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范疇,都屬于農民合法的用益物權,在繼承的問題上,應當同樣的對待,不能以土地用途、特殊保護等為理由作區別對待。因此,筆者認為為保持法律體系和立法精神的統一性,不應對繼承客體進行限制,即家庭承包的土地與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土地承包經營權都可以繼承。
(二) 對繼承人不應進行限制
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人是否進行限制歷來是學界爭議的焦點,并逐漸形成了三種觀點:一是主張對繼承人范圍進行限制,有單嗣繼承制、農民繼承制、共同承包人繼承制、法定繼承人繼承制等觀點;二是主張原則上不對繼承人進行限制,但認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人或屬于農業人口的繼承人享有優先分得權;三是主張對繼承人范圍不作任何限制。筆者認為,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主體不應當進行限制。雖然有學者主張對繼承人范圍應進行不同程度的限制,以防止農村土地撂荒、防止土地零碎化,維護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土地利益,從而促進農業穩定生產,但筆者認為,考慮這些因素確屬必要,但如果僅僅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就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人范圍施加限制,剝奪其合法享有的繼承權,不僅與《繼承法》的立法精神相違背,有損法律體系的統一性,而且還有可能嚴重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不利于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穩定。據此,筆者認為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人不應有任何限制,至于怎樣達到上述目的,可以通過對繼承方式的具體設計,并對繼承主體加以適當的約束來實現。
(三)對繼承方式應進行合理設計
為了達到防止農村土地撂荒、防止農村土地零碎化,保障農業穩定生產,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土地權益的目的,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對繼承方式的合理設計實現。為此,學者提出了許多設計建議:如梁慧星教授主編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物權編》一書中就說到:“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人口的繼承人,可優先分得農地使用權;如被繼承人的其他財產不足以與該農地使用權相當時,可對非從事農業或非農業人口的繼承人進行折價補償。繼承人不得對土地進行登記分割,可折價分割。繼承人均為非從事農業生產或非農業人口的,在繼承后一年內,應將其轉讓給從事農業生產者。”[11]還有部分學者提出了具體的繼承方法設計,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分別繼承。繼承的土地適合分割且分割不影響其價值、繼承人人數也較少時采用。(2)部分繼承人繼承。繼承的土地不適合分割,或分割會嚴重影響其價值,由繼承人中一人或數人繼承,且與被繼承人生活在同一農戶的繼承人應優先繼承,對其他繼承人進行折價補償。(3)共同繼承。承包土地不適宜分割,又無法達成部分繼承人繼承的安排時,由所有或部分繼承人繼承同一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人間屬于共有關系。(4)轉讓土地分割轉讓收益。繼承人均無條件或無能力或無意愿經營土地的,可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分割價款予以繼承。”[12]以上學界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方式的具體設計其實都是繼承法中的遺產分割方法在此的具體運用和理論總結,它們對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制度的設計有著重大借鑒意義。然而,農村實際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比理論探討的要更加復雜,要考慮的相關因素很多,涉及的利益主體也非常豐富。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以上述繼承方式為指導,考慮農村土地現狀、繼承人意愿及實際情況,在綜合考量各種因素的基礎上,靈活運用繼承方法,以實現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的最佳社會經濟效益,更好地維護農民土地權利。
總之,盡管法律尚未明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但筆者認為應允許繼承。承認其繼承不僅與國家的政策導向相一致,而且還具有實施的現實必要性和可行性,明確其繼承性并合理構建其繼承制度對解決理論爭議和司法實務困擾,促進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參見《法國民法典》第767條。
(2)參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
(3)參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
參考文獻:
[1]周子良,張豪.農地使用權流轉問題的法律思考[J].理論探索,2002,(2):63.
[2]劉信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法律問題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5):88-92.
[3]張新寶.土地承包經營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06.
[4]郭明瑞.關于農村土地權利的幾個問題[J].法學論壇,2010,(1):33.
[5]汪洋.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研究[J].清華法學,2014,(4):125-149.
[6]劉娜.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問題研究[D].廣州:廣東商學院,2011:25-26.
[7]王金堂.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的困局與解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8-42.
[8]中華人民共和國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15-02-26)[2015-05-01].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9]劉寶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問題探析[J].北方法學,2014,(44):5-14.
[10]胡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通俗讀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71.
[11]梁慧星.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物權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426-427.
[12]王蜀黔.論中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69.
Chinas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of Succession
YU Hong, LIU Yuxiu
(The College of the Law,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China)
Abstract:Fuzzy and avoidance of existing legal norms due to inherit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provisions, resulting in academia has been controversial, there are different voices in recent years, judicial practice also suffered varying degrees of judgment plight of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issue of success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law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order, that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are usufructuary rights, property rights, in line with the law of succession heritage features can be inherited, and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legislation of rural land reform, rural social security status quo and analyzes the wishes of farmers and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to inherit practical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specific inherited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of a reasonable idea.
Key words: rural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usufructuary; property; inheritance
編輯:魯彥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