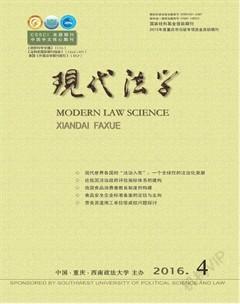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的法律構造
摘要:當事人結構對訴訟激勵的法律構造有著決定性影響。訴訟當事人結構有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之分。在民事訴訟中,表層結構以當事人之間的對抗為其基本特征,決定著訴訟收益的有無;深層結構則表現為當事人在功能上的“三位一體”,決定著訴訟收益的歸屬。二者共同作用,使得民事訴訟的激勵機制內嵌于訴訟制度本身,激勵著當事人的全部訴訟行為。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的差異,不僅表現在表層結構上從對抗走向協作,而且表現在深層結構上“三位一體”的破裂,從而形成社會公眾、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以及原告律師三者之間的雙層委托代理關系,環境公益訴訟的激勵困境由此產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中高昂代理成本的存在決定了原告律師應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激勵對象,而“敗訴方負擔規則”因同時具備正訴激勵、濫訴預防與行為矯正三重功能而成為激勵律師的最佳舉措。
關鍵詞:當事人結構;委托代理理論;代理成本;敗訴方負擔
中圖分類號:DF 468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4.12
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實踐始自2005年,是政府意志2005年12月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國發[2005]39號),首次明確提出“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鼓勵和檢舉各種環境違法行為,推動環境公益訴訟”。自此之后,中國民眾呼吁多年的環境公益訴訟終于從民間期盼上升為國家意志。和草根力量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分公司雙苯廠的苯胺車間發生劇烈爆炸并起火,導致100噸苯類污染物進入松花江,致使江水硝基苯和苯嚴重超標,造成松花江流域生態環境破壞。12月7日,以汪勁、甘培忠為代表的六名北京大學法學院師生向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國內第一起以自然物(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作為共同原告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揭開了中國環境公益訴訟實踐的序幕。雙重推動的結果。經過近十年的發展,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先后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55條、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新《環境保護法》)第58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法律、司法解釋為環境公益訴訟實踐保駕護航。這些法律、司法解釋重在解決接近環境正義的第一步,即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問題。尤其是《環境保護法》的修訂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臺,使近年來飽受爭議的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問題塵埃落定,全國符合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組織也因此陡增到700余家。遺憾的是,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并未如大家所預期的那樣形成“井噴式”增長,反而呈現日趨萎縮之勢。據統計,新《環境保護法》實施的前三個月,全國僅受理三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1];而有的環保法庭甚至出現了一年半時間里環境公益訴訟零受理的窘境[2]。原本以為憑借立案登記制的東風,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會呈現爆發式增長,事實卻不盡如人意:截至11月底,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將近一年,全國范圍內僅有25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立案,預期中的環境公益訴訟井噴現象并未到來[3]。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決了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瓶頸和立案障礙的前提下,環境公益訴訟緣何仍叫好不叫座?實際上,環境公益訴訟是一種供給集體物品的行為,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較為典型的“集體行動”,容易陷入集體行動困境。曼瑟爾·奧爾森曾經不無正確地指出,對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集團成員而言,除非集團成員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集團成員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則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集團成員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4]。中國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之困局,正是源于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的缺位。有疑問的是,對于訴訟構造大體相同的傳統民事訴訟和環境公益訴訟,對激勵機制的要求卻大相徑庭:傳統民事訴訟無需構建額外的激勵機制,而環境公益訴訟沒有激勵就無法運轉。是什么原因導致兩種訴訟對激勵機制的要求迥異?應如何構建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本文認為,兩種訴訟形態在激勵機制法律構造上的分野,源于兩種訴訟形態當事人結構的差異,而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的法律構造,須著眼于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的特殊性進行專門設計。
現代法學陳亮: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的法律構造——以傳統民事訴訟與環境公益訴訟的當事人結構差異為視角一、傳統民事訴訟的當事人結構:內嵌于訴訟本身的激勵構造民事訴訟當事人是指以自己的名義要求法院行使審判權,以維護其自身權利的人及相對人。民事訴訟當事人結構則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的構成要素及其相互結合、相互作用的方式。從不同角度觀之,民事訴訟當事人結構可以分為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兩個層次的當事人結構有著不同的制度意蘊。
(一)相互對抗的原告與被告: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的表層結構
民事訴訟當事人由原告和被告組成,這是民事訴訟當事人最表層也是最基本的結構。民事訴訟以當事人對抗為其基本構造[5],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是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表層結構的最本質特征。
所謂“對抗”,是指“一定的利益主體因利益上的分歧,而產生的彼此對立、相互遏制的一種態勢。”[6]當事人之間的對抗幾乎是現代各國民事訴訟制度共有的特征,不僅西方國家民事訴訟以當事人對抗為其基本構造,審判改革后的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也采用了這一結構[7]。
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以“對抗”為其基本構造的表層結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拋卻歷史文化或法律傳統的考量,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既是發現案件真實的一種專門性訴訟技術,也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在民事訴訟領域的體現或投射[8]。
(二)功能上的“三位一體”: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的深層結構
訴訟當事人的深層結構是指各當事人內部的組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具體到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的深層結構,是指原、被告雙方各自的構成要素以及各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原告與被告的深層結構具有同質性,本文在分析傳統民事訴訟的深層結構時,僅對原告的深層結構進行分析,對被告的深層結構則略而不述。
傳統民事訴訟的原告包括相互關聯的三個構成要素:受害人、代言人和受益人[9]。首先,傳統民事訴訟原告是違法行為的受害人,其權益因他人的違約或者侵權等違法行為而受有損害;其次,傳統民事訴訟原告是訴訟行為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受益人,訴訟收益的絕大部分或者全部歸原告所有;最后,從“經濟人”的利己本性出發,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傳統民事訴訟原告也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代言人,將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不遺余力地維護自身利益。
傳統民事訴訟原告的三個構成要素之間是相互關聯的:原告受益人身份使其因違法行為而遭受的損害能夠得到補償;原告為了補償其所遭受的損害會竭盡全力代言。傳統民事訴訟原告集受害人、代言人和受益人三種身份于一身,實現了三重功能的完美統一。
(三)激勵內嵌: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結構的制度意蘊
經濟學告訴我們,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其全部行為的出發點均在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事訴訟行為的當事人也不例外。他們通常并不關心或者并不特別關心訴訟的社會目的,而是關心其從訴訟中獲得的私人收益[10]。傳統民事訴訟的當事人結構,巧妙地利用了當事人的“經濟人”本性,激勵著當事人在訴訟的各個階段全心全意為自己代言:當事人表層結構決定著訴訟收益的有無,并因此激勵著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攻擊防御活動;當事人深層結構則決定著訴訟收益的歸屬,并因此激勵著當事人發現違法行為、啟動訴訟程序、收集證據、監督律師以及攻擊防御等全部訴訟行為。當事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共同作用,激勵著當事人的全部訴訟行為,使其在訴訟的各個階段全心全意為自己代言。
1.表層結構:決定訴訟收益的有無
訴訟收益的有無維系于訴訟之成敗:當事人勝訴,則享有訴訟收益;當事人敗訴,則訴訟收益為零甚至為負。訴訟的成敗則取決于實體和程序兩方面的因素:從實體角度觀之,訴訟成敗取決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即訴訟請求有無實體法依據;從程序角度觀之,訴訟成敗則取決于當事人通過對抗而展現的案件事實。表層結構之所以能夠決定訴訟收益的有無,是因為審判的基本特征使然,是由審判的“對抗·判定”這一雙重結構決定的 將民事訴訟結構概括為“對抗·判定”,是我國著名學者王亞新教授的貢獻。雖然這一結論是通過分析日本民事訴訟制度得出的,但對于現代各國民事訴訟來說,這一結構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不僅西方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采用這一基本結構,審判方式改革后的我國民事訴訟也采用這一結構。(參見:李浩.民事訴訟當事人的自我責任[J].法學研究,2010(3):120-133.)。
美國學者富勒曾經指出,審判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法官依靠當事人形成審理對象或曰爭點;二是法官依靠既定的法律標準解決這些爭點[11]。審理對象之形成有賴于相互對立的當事人之間展開的攻擊防御活動;而法官依靠既定的法律標準解決爭點則意味著,處于中立地位的法官以法律為依據,對當事人雙方通過攻擊防御展現出來的案件事實作出最終裁判。從這個意義上講,富勒所描述的審判的兩個基本特征可以置換為我國學者王亞新所謂的“對抗·判定”結構[10]56-63。 “對抗”是指“訴訟當事人被置于相互對立、相互抗爭的地位上,他們之間展開的攻擊防御活動構成了訴訟的主體部分”;“判定”則是“由法官作為中立的第三者,對通過當事人雙方的攻擊防御活動而呈現出來的案件事實作出最終裁斷,且這個裁斷一經確定即不允許再輕易更改的強烈的終局性”[10]57。
在審判過程中,“對抗”和“判定”這兩個要件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判定”的存在為當事人的對立抗爭提供了驅動力和調整裝置,而“對抗”的展開則是終局性判決形成的基礎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終局性判決的內容[10]58。也就是說,法院的終局性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事人雙方的對抗性程度,因為當事人之間的相互對抗可以最有效地提供法院裁判所需的案件事實和論據。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當事人表層結構具有決定訴訟收益之有無的功能: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性程度越高,通過攻擊防御展現出來的案件事實越充分,具有實體法依據的訴訟請求便越能得到法官的支持,當事人的勝訴概率也就越大;當事人是否勝訴,則決定著當事人是否享有訴訟收益。需要指出的是,當事人表層結構這種功能的發揮,須以當事人訴訟請求具有實體法依據為前提。
2.深層結構:決定訴訟收益的歸屬
訴訟收益的歸屬取決于當事人深層結構,或者說取決于當事人深層結構三要素之間的結合方式。當事人深層結構是由受害人、代言人和受益人這三個要素結合而成的功能性結構,三要素如果集中于當事人本人身上,那么訴訟收益歸屬于該當事人無疑;如果三要素發生分離,則訴訟收益并不一定歸屬于當事人本人。
如前所述,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深層結構屬于“三位一體”的功能性結構,即受害人、代言人和受益人三重身份完美地集中于原告本人:原告既是違法行為的受害人,又是訴訟過程中自己的代言人,還是訴訟收益的最終受益人。正是原告的受益人身份,決定了訴訟收益最終歸屬于原告本人,而非原告之外的其他人。
由此可見,傳統民事訴訟當事人結構本身便是一個設計精巧的激勵機制:當事人深層結構通過決定訴訟收益歸屬的方式激勵當事人爭取于己有利的判決結果;在以“對抗·判定”結構為其基本構造的傳統民事訴訟中,這種對判決結果的追求又激勵著當事人之間以表層結構為載體的相互對抗。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共同作用,激勵著當事人在訴訟各階段的全部訴訟行為,包括發現違法行為、收集證據、啟動訴訟程序、監督律師、攻擊防御乃至判決的執行等一切有利于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也即是說,傳統民事訴訟的激勵機制是內嵌于訴訟制度本身的,它巧妙地利用了當事人的“經濟人”本性,激勵著當事人的全部訴訟行為。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國內的民事訴訟制度,還是國外的民事訴訟制度,均未見在訴訟制度之外單獨構建訴訟激勵機制的先例。
二、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環境公益訴訟激勵困境之源從表面來看,環境公益訴訟與傳統民事訴訟一樣,其當事人結構均由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組成。不同之處在于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組合方式,由此導致環境公益訴訟激勵困境的產生。
(一)從對抗走向合作: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的表層結構
環境公益訴訟以增進公共利益為己任,而公共利益則是一個“羅生門”式的概念,古往今來中外學者對其孜孜以求也未能達成令人滿意的共識,其中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和盧梭的“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最具代表性。相比之下,盧梭的公共利益概念更具有合理性,它既可以避免邊沁公共利益概念可能導致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又強調了共同體成員在公共利益形成與實現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強調了共同體成員對公共利益之形成與實現所應承擔的積極責任[12]。
公共利益是“全體人的共同利益”,這一概念是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特殊性的根源所在。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都是共同體內不可或缺的一員,都享受著環境公共利益之形成與實現所帶來的好處,同時對環境公共利益之形成與實現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就形成、實現和增進環境公共利益而言,共同體內全體成員的目標是一致的。這種目標追求上的一致性最終導致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從對抗走向合作,因為對抗源于當事人利益的對立,而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之間不僅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對立,反而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二)從“三位一體”到角色分離: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的深層結構
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原本集中于原告身上的受害人、代言人和受益人三重角色發生了解體。違法行為的受害人和訴訟收益的受益人均不再是從事訴訟行為的原告,而是游離于訴訟程序之外的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原告僅僅保留著訴訟代言人的身份,履行著訴訟程序的啟動、證據的收集、對律師的監督以及訴訟過程中的攻擊防御等功能。
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三重角色的解體,使得原告的代言人身份也僅僅具有形式意義。在傳統民事訴訟中,原告的代言行為可以使其獲得于己有利的判決,從而彌補自己因違法行為而遭受的損害。因此,在“經濟人”利己本性的驅使下,我們有理由相信原告能全心全意為自己代言。相反,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的代言行為所產生的訴訟收益并不歸屬于原告本人,而是歸屬于廣大社會公眾,以彌補廣大社會公眾因違法行為而遭受的損害。換句話說,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僅對訴訟結果享有名義上的利益。在“經濟人”利己本性的驅使下,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的代言積極性將大打折扣。
(三)雙層委托—代理:環境公益訴訟激勵之困
在經濟學中,委托代理關系被定義為一種契約,根據該契約,一人或多人(委托人)授權他人(代理人)為了該委托人的利益而從事某些活動[13]。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的變遷,使得原本作為自身利益代言人的原告搖身一變成為社會公眾的代言人,從而在社會公眾、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以及代理律師三者之間形成了雙層委托代理關系,即社會公眾與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之間的初級委托代理關系以及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與其代理律師之間的次級委托代理關系。在這一雙層委托代理關系中,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同時具備雙重身份:既是初級委托代理關系的代理人,又是次級委托代理關系的委托人。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的這一雙重身份,使其類似于集團訴訟的原告,而與傳統民事訴訟的原告迥然有別。也就是說,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與集團訴訟原告一樣,表面上看是提起訴訟的當事人,事實上則是有名無實[14]。
首先,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并不享有訴訟收益,因此大大降低了潛在原告提起訴訟的積極性。經濟學研究表明,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會對激勵作出反應[15]。這一人性假設表明,原告僅在其訴訟收益超過其訴訟成本的時候才會提起訴訟[16]。在傳統民事訴訟中,原告之所以愿意提起訴訟,是因為他們遭受了可以通過訴訟予以救濟的損害,并且其預期損害賠償金將超過其預期訴訟成本[17]。與之不同的是,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不能從環境公益訴訟中獲取巨額經濟收益[18],這是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的。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的結構變遷,使得環境公益訴訟原告成了環境公益訴訟真正受益人(社會公眾)的代理人。盡管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也是社會公眾的一員,也能從環境公益訴訟的訴訟收益中獲得屬于自己的那份收益,但是,社會公眾人數眾多,每一個社會公眾所能享受到的訴訟收益的份額相對較小,環境公益訴訟原告所能享受到的訴訟收益也相對較少,甚至沒有任何收益。在沒有其他額外激勵的情況下,環境公益訴訟潛在原告的起訴積極性自然較低。
其次,即使原告所能分享到的訴訟收益超過其訴訟成本,“搭便車”問題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環境公益訴訟潛在原告提起訴訟的積極性。“搭便車”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在其《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創設的,其基本含義是不支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其根源則在于公共物品消費的非排他性與理性經濟人的存在。環境公益訴訟與集團訴訟一樣,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物品,能讓那些即使沒有支付訴訟成本的人也能分享訴訟所帶來的收益[19]。在這種情況下,環境公益訴訟潛在原告最理性的選擇便是不支付任何成本而坐享其成,“搭便車”現象由此產生,環境公益訴訟潛在原告的起訴積極性由此降低。正如美國學者所證實的那樣:“如果消除違法行為帶來的社會效益被廣為分享,個人的收益往往比較小,每個人就有可能搭其他執法者的便車。其結果是任何人都沒有充分的激勵提起訴訟。”[20]
最后,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中初始委托人的缺位也大大削弱了環境公益訴訟潛在原告提起訴訟的積極性。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委托代理是不同于民事訴訟委托代理的雙層委托代理。從理論上講,在雙層或多層委托代理關系的運行過程中,只有初始委托人具有監督代理人的自我積極性,所有代理人(直至最終代理人)為初始委托人服務的積極性均來源于初始委托人的激勵與監督[21]。換句話說,只要初始委托人激勵和監管到位,作為次級委托人的潛在原告的起訴積極性將不會受到影響。遺憾的是,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的初始委托人角色意識淡化,使得其激勵與監督代理人的積極性不足。這種角色意識的淡化,一方面源于每個初始委托人收益份額較低而具有的“搭便車”傾向,另一方面則與公益訴訟初始委托代理關系的產生機制相關。標準的委托代理關系由委托人與代理人經由自主協商而產生,其權利義務清楚明確。因此,委托人對所形成的委托代理關系及其運行能給自己帶來的效用目標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預期,對代理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代理人問題也十分關注,并想方設法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去激勵、約束代理人的行為[22]。與之不同的是,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的形成則是法律的擬制,由社會公眾通過自己選舉的立法機關以法律規定的方式而形成,作為委托人的社會公眾與作為代理人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之間并沒有以自主協商的方式簽訂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委托代理合同。換句話說,作為委托人的社會公眾完全是因法律的擬制而被推上“委托人”這個位置的,其角色意識的淡化可想而知。初始委托人角色意識的淡化,致使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中初始委托人缺位。初始委托人的缺位,讓作為次級委托人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缺乏激勵與約束,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積極性自然不高。
總而言之,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的特殊性,使得環境公益訴訟原告既無利可圖,也缺乏初始委托人的激勵與約束,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的積極性不言自明。體現在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中,便是環境公益訴訟潛在原告缺乏提起公益訴訟的激勵,環境公益訴訟“零受案率”現象的出現便無法避免。
三、激勵原告抑或激勵律師:環境公益訴訟激勵對象的框定從理論上講,在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中,我們既可以選擇社會公眾(初始委托人)作為激勵對象,又可以選擇環境公益訴訟原告(次級委托人)作為激勵對象,還可以選擇代理律師(最終代理人)作為激勵對象。究竟選擇誰作為公益訴訟的激勵對象,須從環境公益訴訟本身的特征來考慮。
眾所周知,正式糾紛解決機制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當事人須借助律師來解決相互之間的爭議[23]。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最終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代理律師投入到訴訟中的精力[24]。律師投入到案件中的精力,則取決于當事人對律師的控制程度,因為從理論上講,律師不過是當事人的代理人,各方面均受當事人的控制[25]。因此,環境公益訴訟激勵對象的選擇,應以能否實現對律師的有效控制為主要判斷標準。事實上,無論是激勵社會公眾,還是激勵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均因代理成本高昂而無法實現對律師的有效控制。
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人為防止代理人損害自己的利益,以嚴密的契約關系和嚴格的監管限制代理人行為而付出的代價,包括委托人的監督成本、代理人的擔保成本和剩余損失 委托人的監督成本是指委托人激勵和監控代理人,以使后者為前者利益行為的成本;代理人的擔保成本是指代理人用以保證不采取損害委托人行為的成本以及如果采用了那種行為而支付的賠償;剩余損失是委托人因代理人代行決策而產生的一種價值損失,是契約最優但又不被完全遵守、執行時的機會成本。(參見: Michael C. Jensen,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雖然代理成本普遍存在于所有委托代理關系之中,但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代理成本要遠遠高于一般民事訴訟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代理成本。
首先,訴訟結果受益人人數眾多決定了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的監督成本較高。經濟學者在研究公司所有權結構與代理成本相互關系時發現,代理成本隨非管理層持股人數的增加而增大。這是因為“搭便車”問題減少了持股人監督管理層的積極性,而監督越少,代理成本越高[26]。環境公益訴訟的受益人是為數眾多的社會公眾,每個社會公眾僅占全部訴訟收益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每個社會公眾僅對訴訟結果享有名義上的利益。相較于監督代理人所需的巨額成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公眾寧愿放棄對代理人的監督,或者選擇“搭便車”以坐收漁利。事實上,就原告只不過是真正受益人的代表人這點而言,環境公益訴訟與集團訴訟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均屬于代表人訴訟,代理成本高昂是包括集團訴訟在內的所有代表人訴訟的一個重要特征[27],甚至是集團訴訟所固有的特征 早在20個世紀80年代,約翰·C·科菲就曾指出,代理成本高昂是集團訴訟的固有特征,這一特征為集團訴訟原告律師從事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為此,應將集團訴訟原告律師視為獨立的利益追求者,而非原告的代理人。(參見:John Coffee, Jr. The Regul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Litigation: Balanc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rge Class Action[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87, 54: 882-883.)。這一方面是因為真正受益人所具有的“搭便車”傾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將眾多受益人組織起來進行談判并形成一致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27]19-20。由此可見,環境公益訴訟受益人眾多的特性決定了其監督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擔保措施的缺位使得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的擔保成本較高。從理論上講,如果監督成本過高,代理人的最優策略是通過某種形式的擔保讓委托人確信,即使缺乏有效的監督,代理人也能忠實履行對委托人所負的義務[27]15-16。在確保代理人忠實履行委托義務的各種措施中,律師執業行為規范與律師聲譽是兩種行之有效的擔保措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代理律師遵守其忠實義務[27]21-22。然而,這兩種擔保措施卻無法適用于包括環境公益訴訟在內的所有代表人訴訟。律師執業行為規范之所以失去其擔保效果,是因為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僅對訴訟結果享有名義上的利益,缺乏將其代理律師的不良行為報告給有權機關并進行處理的積極性。律師聲譽之所以失去其擔保效果,是因為環境公益訴訟往往是由律師提起并推動的,而非像傳統訴訟那樣坐等當事人找上門來,這就大大降低了律師維持良好聲譽以吸引當事人的積極性[27]21-22。
最后,高昂的監督成本與擔保成本大大增加了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的剩余損失。在委托代理關系中,代理人的決策與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最優決策之間會存在某種偏差,這種偏差會導致委托人福利受到損失,這種損失就是“剩余損失”。剩余損失實際上是最優契約得不到遵守、執行時所發生的損失。因此,監督成本和擔保成本越高,代理人脫離委托人控制而自行決策的可能性就越大,代理人偏離委托人的目標以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可見,監督成本與擔保成本的提高會大大增加委托人的剩余損失。
綜上所述,環境公益訴訟雙層委托代理關系的代理成本,遠遠高于傳統民事訴訟委托代理關系的代理成本。這種高昂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得社會公眾與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均無法有效控制或監督其代理人,從而使代理人脫離委托人的控制而成為獨立的行為人,亦即原告律師幾乎不受其當事人的控制,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利益進行訴訟決策。在這種原告無法有效監督或控制其律師行為的訴訟中,對原告律師的激勵將對訴訟決策產生重大影響[21]677,因此,律師應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激勵對象。
四、敗訴方負擔規則: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法律構造的應然選擇環境公益訴訟激勵對象一旦確定,接來下需要思考的問題便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激勵。從理論上講,激勵律師的方式有三種:(1)環境公益訴訟救濟基金,即無論原告是否勝訴,均從國家或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的公益訴訟救濟基金中支取公益訴訟原告的訴訟成本;(2)勝訴酬金制度,即當事人從案件勝訴所得的財物或者利益中提取代理協議約定的一定比例作為律師費支付給代理律師;(3)“敗訴方負擔”規則,即法律授權法院,在其認為適當的時候,將勝訴原告所應承擔的訴訟成本判給敗訴被告承擔的一種訴訟成本分攤方式[28]。這三種激勵方式的資金來源各不相同:環境公益訴訟獎勵基金一般由國家或地方政府出資設立,亦可由社會捐資;勝訴酬金制度的資金則來源于勝訴方所獲得的賠償金的一部分;“敗訴方負擔”規則的資金來源于對被告的經濟制裁。究竟哪一種方式最適合作為環境公益訴訟激勵規則呢?功能主義者認為,法律并非一種自治的學問實體,其包含的概念和術語只不過是達到某種結果的途徑而已[29]。為此,選擇何種方式作為公益訴訟激勵規則,關鍵在于三種激勵方式在功能欲求上的優劣對比。
敗訴方負擔規則,不僅將律師費的取得與案件的勝訴掛鉤,而且激勵經費也來源于對敗訴方的經濟制裁。這一制度安排,既不會像環境公益訴訟激勵基金那樣增加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又不會像勝訴酬金那樣減少環境公益訴訟原告應得的訴訟收益。尤為重要的是,這種制度安排使得“敗訴方負擔”規則因同時具備正訴激勵、濫訴預防和行為矯正三重功能而成為環境公益訴訟激勵規則的首選。
(一)正訴激勵
“正訴”(meritorious suits)是對“有正當理由的訴訟”的簡稱,泛指根據實體法能夠贏得勝訴判決的訴訟[30],也就是其訴訟請求能夠獲得實體法支持的訴訟。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影響當事人訴訟決策的主要因素是當事人對訴訟成本與訴訟收益的預判,而這種預判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原告估計的自己的勝訴幾率;二是訴訟費用的分擔規則[31]。訴訟費用分擔規則一旦確定,影響當事人訴訟決策的關鍵就在于原告對自己勝訴概率的估計了。排除因法官或當事人自身錯誤而導致的誤判,原告對勝訴概率的估計實際上就是考察自身的訴訟請求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相應實體法的支持。
在敗訴方負擔規則之下,原告對其訴訟收益與訴訟成本將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預判:一旦勝訴,自己的訴訟成本將獲得全額補償;一旦敗訴,不僅自己的訴訟成本付之東流,還得承擔對方的訴訟成本。在這一預判之下,當事人自然會對其訴訟請求進行細致而全面的審視 因為敗訴方要承擔勝訴方的律師費,所以敗訴方負擔規則將會激勵當事人在提起無正當理由的訴訟或進行惡意抗辯之前審慎評價其案件的實體因素。(參見:Thomas D. Rowe, Jr. Indemnity or Compensation? The Contract with America, Loser-Pays Attorney Fee Shifting, and a One-Way Alternative[J]. Washburn Law Journal,1998, 37:319.),經過當事人的“過濾”,能夠進入司法程序的自然而然就是那些能夠充分獲得實體法支持的“正訴”了。也就是說,敗訴方負擔規則“迫使潛在當事人更仔細地權衡其訴訟請求的可行性,從而可以減少無謂的或騷擾性訴訟”[32]。哈佛大學法學教授Lucian Arye Bebchuk 和南加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Howard F. Chang斷言,在敗訴方負擔規則之下,“原告總是會提起有正當理由的訴訟,因為這種訴訟注定會贏,而原告還不必承擔由此產生的訴訟成本” [32]371。不僅如此,敗訴方負擔規則還激勵著原告律師盡量避免代理無謂的或騷擾性訴訟,因為“案件一旦敗訴,律師將承擔喪失其律師費用的風險,由此激勵律師只代理有正當理由的(meritorious)案件”[33]。
不過,敗訴方負擔規則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激勵“正訴”的同時,也抑制了部分合法訴訟[34]。美國學者就曾撰文指出,由于法院的不可預測性、環境訴訟的復雜性以及訴訟過程太長等原因,即使最精明、最負責任的環保組織通常也無法準確預測訴訟的成敗;考慮到敗訴之后可能承擔的對方訴訟費用,這些環保組織往往會放棄一些有勝訴概率的訴訟[34]685。但無論怎樣,敗訴方負擔規則至少可以確保提起的訴訟大都具有實體法上的正當性,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二)濫訴預防
簡而言之,“濫訴”就是無法獲得實體法支持的訴訟[32]371。從訴訟激勵角度看,下述基本原則是不言自明的:法律只需要通過增加敗訴方訴訟成本的方式就能達到阻止當事人進行濫訴的目的[35]。敗訴方負擔規則正是通過增加敗訴成本的方式來預防濫訴的:原告一旦敗訴將面臨支付對方訴訟成本的風險,這將迫使原告方在提起訴訟之際三思而行,以避免案件敗訴而招致經濟懲罰。也就是說,“敗訴方負擔”規則有利于激勵訴訟當事人雙方更加實事求是地評估其訴訟請求和抗辯理由,盡量提起那些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的訴訟,以免承擔案件敗訴而招致的經濟懲罰。Dan Quayle就曾在《美國司法改革議程》報告中指出:“因為敗訴方必須支付勝訴方的訴訟成本,該規則可以激勵當事人在提起騷擾性請求或進行虛假辯護之前更加仔細地評估其案件的是非曲直(merits)。”[36]
不僅如此,“敗訴方負擔”規則還可以促使原告律師更加謹慎地接受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委托。“敗訴方負擔”規則的采用使律師費支付規則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一般情況下,原告律師費的取得是原告與律師談判協商的結果,與案件結果并沒有太大的關系(風險代理除外);在“敗訴方負擔”的情況下,勝訴律師指望的是法院而非當事人給予其律師費,而法院判決的依據則是案件勝訴的結果以及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的成本付出[30]90-92。如此一來,在沒有充分勝訴預期的情況下,律師一般不會輕易提起訴訟;只有那些勝訴把握較大的訴訟才能進入原告律師的視野,從而有利于預防濫訴的發生。
(三)行為矯正
“敗訴方負擔”規則的行為矯正功能,是指“敗訴方負擔”規則通過增加行為人違法成本的方式而預防和制止不法行為。“行為矯正”功能的發揮,源于經濟學關于理性人的假設。理性經濟人會對激勵作出反應[17]19,由此決定了“制定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過提供一種激勵機制,誘導當事人事前采取從社會角度看最優的行動”[37]。這種激勵作用的發揮,主要通過調整反映在法律規則中的違法行為的“價格”——違法行為人從事違法行為所支付的代價——來實現。
敗訴方負擔規則正是通過改變違法行為的價格來實現其行為矯正功能的。在“敗訴方負擔”規則之下,敗訴被告不僅要承擔自己的訴訟成本,還必須承擔勝訴原告的訴訟成本,從而將全部訴訟成本歸于敗訴被告一方承擔。換句話說,“敗訴方負擔”規則大大增加了行為人的違法成本,使其在計算違法行為的全部成本時,不得不考慮潛在原告的訴訟成本,并據此作出最理性的行為選擇,“行為矯正”功能由此得以實現。
“敗訴方負擔”規則的行為矯正功能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認可。美國德保羅大學(DePaul University)副教授Harold J. Krent指出,敗訴方負擔規則可以迫使政府和大型私企內部化其行為成本,從而影響其決策的制定、實施以及訴訟的進行[38]。日本著名學者棚瀨孝雄則認為,“敗訴方負擔”規則通過“對侵害了他人權利還以訴訟形式來抵抗救濟要求的人給以負擔雙重成本的制裁,以期達到抑制權利侵害或不經過訴訟也能恢復權利的目的”[39]。美國馬里蘭州“接近正義委員會”(The Maryland Access to Justice Commission)則在其一篇報告中指出:“如果法律規定了律師費轉嫁制度,那么行為人在計算違法行為的全部成本時,就不得不考慮潛在原告的訴訟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律師費轉嫁規則扮演著制止不當行為的角色。”[35]45-46
“由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包括律師費在內的全部訴訟成本,不僅對權利方的保護更為充分,有利于保護和鼓勵正當訴訟,而且有助于抑制和懲罰濫訟,合理利用緊缺的司法資源,避免當事人受不當訴訟行為的騷擾。”[40]當然,從表面上看,受“敗訴方負擔”規則影響的是當事人,而非律師。但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往往是律師尋找當事人,而非當事人尋找律師,律師尋找當事人不過是為了滿足提起訴訟所必不可少的程序要件。因此,“敗訴方負擔”規則實際上激勵著律師尋找當事人,以便提起那些從商業角度看當事人不愿提起的訴訟[35]38。
總而言之,“敗訴方負擔”規則同時具有正訴激勵、濫訴預防與行為矯正三重功能。“敗訴方負擔”規則的運用,既不會像環境公益訴訟激勵基金那樣增加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也不會像勝訴酬金那樣減少環境公益訴訟原告應得的訴訟收益。
結束語環境公益訴訟切斷了原告與訴爭案件之間的利益關聯,原告不能從案件勝訴中直接獲得經濟或其他利益,因此環境公益訴訟不可能具備傳統民事訴訟所固有的激勵機制。為此,重構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既是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變遷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立法從制度走向實踐的保障。美國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創始國,通過訴訟成本“敗訴方負擔”規則的運用,將原告承擔的訴訟成本轉嫁給敗訴的被告,從而免除了原告對訴訟成本的擔憂,并同時實現了對正訴的激勵和對濫訴的預防[30]90-92。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雖然為環境公益訴訟的繼受國,但這些國家同樣注意到了環境公益訴訟的巨額成本,注意到了訴訟成本對原告起訴意愿的決定性影響,并通過訴訟成本“敗訴方負擔”規則、法律援助以及環境保險等制度設計來消除原告對巨額訴訟成本的擔憂[41]。我國應以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為借鑒,建構出符合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結構特點的激勵機制,以推動我國方興未艾的環境公益訴訟的良性運轉。“敗訴方負擔規則”因其兼具正訴激勵、濫訴預防與行為矯正三重功能而成為重構我國環境公益訴訟激勵機制的最佳選擇。ML
參考文獻:
[1] 劉曉星.環境公益訴訟緣何叫好不叫座[N].中國環境報,2015-03-13(08).
[2] 曹紅蕾.環境公益訴訟一年半零受理[N].云南信息報,2015-06-03(A18).
[3] 吳亞東,王瑩.環境公益訴訟尚需加油提速[N].法制日報,2015-11-29(06).
[4]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
[5] 中村英郎.新民事訴訟法講義[M].陳剛,林劍鋒,郭美松,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1.
[6] 唐力.事實探知:當事人對論構造的法理分析——以裁判形成過程中當事人程序權的保障機制為中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76-81.
[7] 李浩.民事訴訟當事人的自我責任[J].法學研究,2010(3):120-133.
[8] 王亞新.對抗與判定:日本民事訴訟的基本結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59.
[9] Owen M. Fiss. The Forms of Justice[J].Harvard Law Review, 1979,93:18.
[10] Steven Shavell. The Fundament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Social Motive to Use the Legal System[J]. Journal of Legal Study, 1997,24(4): 581.
[11] Lon L. Fuller. 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J].Harvd Law Review,1978,92:363-387.
[12] 陳亮.美國環境公益訴訟原告適格規則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13-17.
[13] Michael C. Jensen,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311.
[14] Jean Wegman Burns. Decorative Figureheads: Eliminating Class Representative in Class Actions[J]. Hastings Law Journal, 1990,42:167-168.
[15] 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M].蔣兆康,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4.
[16] L. Kaplow. Private versus Social Costs in Bringing Suit[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6(15):372-373.
[17] Jill E. Fisch. Class Action Reform, Qui Tam, and the Role of the Plaintiff[J].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997,60(4):170.
[18] Lara Friedlander. Cost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nt[J]. McGill Law Journal, 1995,40:61.
[19] John C. Coffee. Understanding the Plaintiffs Attorney:The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for 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 through Class and Derivative Actions[J].Columbia Law Review,1986,86:680.
[20] Richard B. Stewart,Cass R. Sunstein. Public Programs and Private Rights[J]. Harvard Law Review,1982, 95: 1214.
[21] 張維迎.公有制經濟中的委托人——代理人關系:理論分析和政策含義[J].經濟研究,1995(4):10-20.
[22] 陸建新.雙層委托代理:蘇南模式運行機制的理論實證分析[J].學習與探索,1997(2):4-16.
[23] Ronald J. Gilson,Robert H. Mnookin. Disputing through Agent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Lawyers in Litigation[J]. Columbia Law Review, 1994,94:509.
[24] Bruce L. Hay. Contingent Fees and Agency Costs[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6,25:504.
[25] Jonathan R. Macey, Geoffrey P. Miller. The Plaintiffs Attorneys Role in Class Action and Derivative Litigation: Economic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eform[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91,58:3.
[26] James S. Ang, Rebel A. Cole,James Wuh Lin.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e, 2000,55:87.
[27] Samuel Issacharoff.Litigation Funding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Cost in Representative Actions[J]. DePaul Law Review,2014,63(2):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