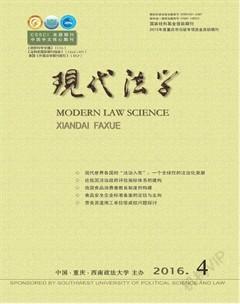論國際投資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審查
摘要:基于國際社會在投資條約內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認定上的嚴重分歧以及在“即便是自我判斷性質的條款(包括明示的自我判斷條款與默示的自我判斷條款),也不能全然置身于爭端解決機構的審查范圍(包括實體與程序方面)之外”問題上的大致共識,建議淡化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區分。國際仲裁庭應在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審查事項上采納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或遵從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
關鍵詞:國際投資仲裁;非排除措施;必要性;最少限制方式
中圖分類號:DF 964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4.13
在國際范圍內,越來越多的投資條約均納入例外條款或曰“非排除措施”(nonprecluded measures)條款,允許締約方基于保護特定價值與利益(包括締約方的安全利益、公共秩序、衛生健康、環境保護、勞工標準、金融體系與機構的完整性和穩定性以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等)之目的而采取特別的行政舉措,其可免除承擔相應的條約義務。的確,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各國一方面應信守其于條約內承諾的國際義務,另一方面亦應被授權于特殊情形下出于保護特定國家利益之目的而采取背離條約義務的措施,可以說,投資條約中的非排除措施條款在要求各國承擔其必要的國際義務與保留其行使相當的國家主權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鏈接與平衡作用。
但遺憾的是,締約方在擬定非排除措施條款時,為了保留主動權,往往借助一些抽象性甚至模糊的語句對具體情形予以高度概括。另外,在對東道國行使非排除措施的條件限制方面規定得也較為寬泛與隨意,表述方式不盡相同。正是這些不太確切或具體的規定,給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容易引發締約方之間的爭端。圍繞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問題,主要存在兩方面的爭端:其一,應否對東道國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其二,東道國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審查標準是什么?
一、非排除措施的自我判斷性質之爭少數學者認為,在回答“應否對東道國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進行審查”這一問題前,必須先弄清楚所適用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self-judging)性質——如果條款具備自我判斷的性質,意味著東道國在采取具體行政監管行動和措施方面擁有自我判斷的權力,即便在爭端發生后,投資仲裁庭對這一條款的適用(包括確定東道國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要求方面)無權審查或者只擁有極少的司法管轄權[1-2]。因此,對投資條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屬性予以辨析可稱得上是正確回答“應否對東道國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進行審查”這一問題的前提條件。
(一)非排除措施條款自我判斷性質的判定
現代法學銀紅武:論國際投資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審查關于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Stephan W. Schill與Robyn Briese認為,就目前而言并不存在一個普遍認同的自我判斷條款的定義。但是,自我判斷條款具備兩個特征:第一,此類條款賦予締約方單方退出一項國際義務的自由裁量權(包括通過條約義務的免責以及證明違約的正當性等方式)。第二,對于是否符合免責條件的評估不能完全客觀地建立在外部觀點的基礎上,而應主要依據當事方的意見而得出結論(盡管仍將保留對當事方援引條款的行為進行一定的審查)[2]67-68。對于非排除措施條款來說,假若在“締約方所采取的措施”前有“其認為必要的”(it considers necessary)之類的修飾語,則可認定此類非排除措施條款具有自我判斷性質[3]67-68。如《美國—烏拉圭雙邊投資條約(2004)》與《美國—盧旺達雙邊投資條約(2008)》第18條第2款的“非排除措施”條款均使用了標志其“自我判斷”性質的典型用語,即“其認為必要的”這一表述“本條約不得解釋為……禁止締約另一方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措施來履行其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義務或保護其根本安全利益。”。
正是基于這一認定標準,在美國投資者針對阿根廷政府于2001年至2003年經濟危機期間所采取的緊急措施向“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提起的一系列國際投資仲裁申請案中,仲裁庭針對阿根廷政府主張免責所依據的1991年《美國—阿根廷雙邊投資條約》第11條的非排除措施條款“該條約不應排除任一締約方采取必要的措施維護公共秩序,履行其關于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或安全的義務,或者保護其自身的重大安全利益。”,基本認定其只具備非自我判斷性質(如CMS v. Argentina案 參見:CMS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65-374.、LG&E v. Argentina案 參見:LG & E Energy Corp., LG & E Capital Corp. and LG & 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 para. 214.、Enron v. Argentina案 參見:Enron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31-339.、Sempra v. Argentina案 參見:Sempra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73-388.與Continental v. Argentina案 參見: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paras. 182-188.)。
仲裁庭關于美阿雙邊投資條約內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非自我判斷性質的認定,引起了較大爭議,部分學者持相反的觀點。如Diane A. Desierto認為,對于像美阿雙邊投資條約中未明文顯示其自我判斷性質的非排除措施條款,應著重考慮相關締約方的國家歷史傳統與締約慣常實踐,從而對其自我判斷性質進行確定。在對美國的相關司法實踐以及政府在對外投資爭端中所持的一貫立場進行了詳細分析后,Diane A. Desierto進而認為,美國雙邊投資條約的非排除措施條款均具有自我判斷性質,即便是對于那些未包含“其認為必要的”用語的條款而言,亦屬于具有“隱性自我判斷”性質的非排除措施條款[4]。BurkeWhite等人也認為,美阿雙邊投資條約的非排除措施條款之所以僅需受非常有限的司法審查,是由于其具有“隱性自我判斷”的性質[1]381-386。此外,美國政府也一直強調該國投資條約中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美國政府認為,即使對于自我判斷屬性尚未明確的非排除措施條款,也應當解釋為具有自我判斷性質。美國政府所持的觀點得到了Kenneth Vandevelde的證實:“可以非常確鑿地認為,自1984年以來,美國對基本安全利益例外的解釋都具有自我判斷性質,盡管直到1986年的美俄雙邊投資條約才第一次明確規定了這一點。”[5]
(二)爭議解決辦法:淡化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與非自我判斷性質的區分
不難理解,各方為何如此看重非排除措施的自我判斷性質問題——對東道國(或該國學者)而言,強調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即便是未含“自我判斷性質”標志用語的條款也主張其為“默示的自我判斷”條款)能為本國在判斷重大國家利益或價值遭遇損害或損害威脅時自主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措施以保護此等利益方面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就國際投資仲裁庭或支持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相關方來說,堅持否定抑或淡化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更有利于自身的價值追求或保護。筆者以為,應堅持淡化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與非自我判斷性質的區分,因為即便是非排除措施條款具備所謂的自我判斷性質,亦不應妨礙仲裁庭對措施行使條件的實質審查,理由如下 作者借助在美國夏威夷大學法學院訪學的機會(2015年8月~2016年8月),與合作導師——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Diane A. Desierto教授就這些觀點進行了交流并向其請教。:
第一,自我判斷性質的語言標志認定標準不科學。雖然投資條約內的典型非排除措施條款大都符合“本條約不得解釋為/不得排除……締約方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措施來履行……義務或保護……根本安全利益”的條文范本,但是也有一些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表述較為寬泛和隨意,如《中國—新西蘭雙邊投資條約(1988)》第11條中“禁止與限制”條款條文內容為:“本協定的規定不應以任何方式約束締約任何一方為保護其基本安全利益、保障公共健康或為預防動、植物的病蟲害而采取任何禁止或限制措施或作出任何其他行為的權利。”根本未使用“其認為必要的”用語,但不能僅憑此而對其非排除措施條款的本質予以否定。畢竟,判斷條約條款是否為非排除措施條款,關鍵還得從其功能與本質上予以認定。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的確定也應如此,不應拘泥于條款條文(或譯文)是否包含相當于“締約方/其/他認為”之類的所謂“自我判斷性質”標志語的表述。換言之,僅從條款的個別短語上判斷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既不可靠,又不科學。
第二,對于投資條約中并未出現任何表明其自我判斷性質的明文表達的非排除措施條款,有關締約方更是應該將其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確實為“必要的措施”的認定問題交由中立的第三方予以裁判。事實上,對于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的認定,應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有關條約解釋的習慣法規則從條約用語所具有的通常意義、條約上下文并結合條約的宗旨與目的進行綜合考慮。若從條約上下文方面考察,以《美國—阿根廷雙邊投資條約》為例,該條約第7條規定,一旦產生關于條約“所授予或創設的任何權利”爭端,應遞交仲裁解決。若將該條約第11條的非排除措施條款認定為具有自我判斷的性質,似乎很難解釋,為何第11條要與該條約內的其他條款予以區別對待,認為其不應受中立第三方的裁判呢?投資條約的宗旨與目的是對不同主體的利益予以調整,因此中立第三方的裁判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中立第三方相較于締約方而言,能更好地避免對相關方所涉利益有所偏袒。
第三,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之爭其實是東道國在適用非排除措施這一問題上應否接受中立第三方的實質審查之爭,對過于強調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的當事方而言,其本意是想逃避仲裁庭的審查。如一些學者主張,非排除措施條款中的允許事項屬非司法管轄事項,因此應排除在國際法院或仲裁庭的審查范圍之外[6]。這一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在國際社會中,一些當事方尚且將涉及國家安全的爭端遞交國際法院裁判,并且國際司法機構(包括國際法院、歐洲法院、歐洲人權法院及其他仲裁機構)從未承認過爭議的政治屬性可以阻卻司法管轄,這無疑就給有關非排除措施條款的允許事項屬非司法管轄問題的論點予以了有力的否定性回擊。其次,該觀點與當事方當初同意接受仲裁機構的全面管轄(這就意味著其已就投資爭端放棄了司法管轄權)并于投資爭端產生后又與投資者達成仲裁合意的舉動是前后矛盾的。況且,在國際習慣法方面并未出現任何有關東道國基于非排除措施條款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可免受外部司法審查的規則,亦未漸進發展成一條關于締約國在對明確具有自我判斷屬性的非排除措施條款適用方面擁有完全的自我判斷能力的準則。再次,主張非排除措施條款應排除國際法院或仲裁庭審查的觀點有悖于條約的統一性理論。因為,現代投資條約中的投資者—東道國仲裁條款通常規定將兩者間所產生的直接與投資相關的法律爭端遞交仲裁解決。若將同一條約內的非排除措施條款排斥在國際仲裁的管轄范圍之外,那么投資條約的整體統一性將受到嚴重破壞。最后,基于東道國的行為必須受制于一般國際義務的習慣法規則,上述觀點也可被證明是錯誤的。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4條,締約方必須善意地履行條約義務。對此,國際司法判例也予以了確認,如Schwebel法官在解釋《美國—尼加拉瓜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基本安全條款時就曾指出,仍然應該由仲裁庭來決定成員援引條款的行為是否出于善意 參見:Case concerning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Merits, 27 June 1986, ICJ Reports 1986, 4, para. 220.。正是基于這點,在CMS v. Argentina案中,針對被申請國阿根廷所提出的美阿雙邊投資條約中的“非排除措施”條款應為“自我判斷性的條款”的主張,仲裁庭予以了澄清,認為對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條件是否成就進行審查應為仲裁庭的職責。仲裁庭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其所依據的是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 v. Slovakia)案,因為在該案中,國際法院在關于“危急情況”抗辯之國際習慣法規則的適用條件問題上曾認為,“有關國家并非是判斷這些條件是否滿足的唯一裁判”。因此仲裁庭堅持認為,應當對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條件進行“實體性審查”,而不僅僅只是“善意原則”的審查 參見:CMS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65-374.。事實上,美國在援引自我判斷性質的非排除措施條款時,也往往會接受仲裁庭的實體審查。美國參議員Helms于2000年9月曾經講到:“盡管美國認為這些條款是自我判斷的,不過在美國政府看來,締約各方都期望相對方善意地適用條款。”最近,美國政府明確表示,即使是明示的自我判斷條款,也不能超脫仲裁庭的司法審查范圍,援引方仍應該就其采取的行動接受仲裁庭的審查。
第四,過于強調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主張東道國非排除措施的實施條件可排除于仲裁庭的管轄范圍之外的觀點,其實是一種狹隘的國家利益保護主義,極易導致國際投資領域不公平現象的產生,當然最終也會侵害東道國自身的利益,畢竟投資條約具有雙邊或多邊的性質。但假若淡化兩種所謂不同性質的條款的區別,對即便是具有自我判斷性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仍然實行審查,將確保東道國行動自由和投資者保護之間的平衡,可對東道國以特殊情形為借口行損害投資者利益之實的行為予以防范與甄別。一旦發現東道國濫用非排除措施條款,則可進一步作出裁決,責成東道國就其惡意行為對投資者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3]121。
第五,過于強調非排除措施的自我判斷性質也很容易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無論是東道國與外國投資者間,還是東道國與國際仲裁組織間,甚或是東道國與投資者母國間)產生緊張局面,甚至滋生單邊主義,因為援引者會在爭端解決活動中極力強調其在采取相應措施方面的自由裁量權,這一權力甚至會超出締約方在締結條約時所能預見的范圍。如此一來,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反而極有可能會對國際經濟合作產生破壞影響,這恐怕與締約方納入非排除措施條款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并且,過于強調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極易導致逆世界潮流的極端觀點產生與蔓延。如Stephan W. Schill與Robyn Briese就提出,自我判斷條款甚至可以起到防御一國不受全球治理機制約束的作用,因其能使一國擺脫國際治理機制(尤其是像國際法院這樣的國際爭端解決機構)對該國所享有的監管權。顯然,此類極端觀點與當今世界的經濟一體化或全球化發展洪流以及強調全球治理、和諧世界等先進理念是格格不入的,理應予以抵制乃至摒棄[2]83。
綜上,與其在有關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和與其關聯的審查標準(部分學者主張,針對不同自我判斷性質的非排除措施條款應實行不同的審查標準[3]118-122)的兩次分歧上糾結不已與爭論不休,還不如淡化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區分,將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直接納入仲裁機構的審查程序。畢竟,各方在“即便是自我判斷性質的條款(包括明示的自我判斷條款與默示的自我判斷條款),也不能全然置身于爭端解決機構的審查范圍(包括實體與程序方面)之外”問題上出人意料地已達成大致共識,淡化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區分也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下一步的關鍵還是要找出甚至創建一個較為科學合理、可操作性強、能為各方樂意接受且最好能實現各方共贏的統一審查標準。下文將具體結合非排除措施“必要性”審查標準的選擇事例予以說明。
二、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審查標準:“唯一辦法”標準、自由判斷余地標準抑或善意原則標準針對東道國所主張的“必要的措施”,仲裁庭應如何判定措施的“必要性”呢?綜合國際投資仲裁實務界與學界的觀點,有幾個可供選擇的“必要性”要求審查標準:“唯一辦法”(only means)標準、自由判斷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標準、善意原則標準以及“最少限制方式”(least restrictive means,簡稱LRM)比例要求標準。這里先討論前面三個標準的適用。
(一)《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的“唯一辦法”標準
在CMS v. Argentina仲裁裁決的申請撤銷案中,撤銷委員會認為該案仲裁庭犯了“很明顯的法律錯誤”,即誤以為《美國—阿根廷雙邊投資條約》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必要性”要求與《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以下簡稱《責任條款草案》)第25條 1. 一國不得援引危急情況作為理由解除不遵守該國某項國際義務的行為的不法性,除非:(a) 該行為是該國保護基本利益,對抗某項嚴重迫切危險的唯一辦法;而且 (b) 該行為并不嚴重損害作為所負義務對象的一國或數國或整個國際社會的基本利益。2. 一國不得在以下情況下援引危急情況作為解除其行為不法性的理由: (a) 有關國際義務排除援引危急情況的可能性;或(b) 該國促成了該危急情況。的“危急情況” 在《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的英語條文中,第25條的標題為“必要性”(necessity),但我國學者均將其譯為“危急情況”。其實正是因為“必要性”(necessity)為非排除措施條款中的“必要的”(necessary)的名詞形式,故在判斷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問題上,自然就會聯想到《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第25條關于“必要性”的要求。要求相同,因此未對這兩個條款的關系予以辨析。撤銷委員會強調,《美國—阿根廷雙邊投資條約》第11條并不享有《責任條款草案》第25條的所有實體性要求,比如第11條并未包含一個類似于《責任條款草案》第25條第1款(b)項的條件要求 參見:CMS v. Argentina, Decision of the Annulment Committee, paras. 129-132.。
關于投資條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必要性”要求是否就等同于“危急情況”國際習慣法規則的“唯一辦法”要求問題,學者們則意見不一。其中,少數學者持贊同的態度。如Alvarez等人認為,通過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第3款(丙)項條文內容如下:“三、應與上下文一并考慮者尚有:(甲)當事國嗣后所訂關于條約之解釋或其規定之適用之任何協定;(乙)嗣后在條約適用方面確定各當事國對條約解釋之協定之任何慣例;(丙)適用于當事國間關系之任何有關國際法規則。”的規定,《美國—阿根廷阿雙邊投資條約》第11條內“必要的”一詞應等同于《責任條款草案》第25條中的“唯一辦法”要求[7]。可是,大多數學者在這一問題上持否定意見。總的說來,多數派學者的主要反對理由如下:
第一,基于投資條約非排除措施條款與“危急情況”之國際習慣法規則的先后適用順序,一般而言,投資條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應優先于“危急情況”國際習慣法規則的適用。導致這一適用順序的原因大致有兩個:其一,根據“特殊法優先于一般法”(Lex specialis derogat generali)的基本法律原理,若作為投資者提起投資者—東道國間國際投資仲裁之訴基石的投資條約包含了非排除措施條款,將直接導致國際習慣法“危急情況”抗辯理由的不可適用性 這也是專門委員會在受理撤銷CMS v. Argentina仲裁裁決案中所使用的第一個解釋方法。(參見:CMS v. Argentina, Decision of the Annulment Committee, para. 133.)。其二,非排除措施條款與“危急情況”國際習慣法規則同時存在且彼此各自獨立發揮作用:前者在審查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事項上屬于基本國際法規則,而后者僅為輔助的國際法規則 該解釋方法是專門委員會在受理撤銷CMS v. Argentina仲裁裁決案中所采納的第二個方法。(參見:CMS v. Argentina, Decision of the Annulment Committee, paras. 134.)另外,在Sempra v. Argentina仲裁裁決撤銷案中,專門委員會也采用了這一解釋方法。(參見:Sempra v. Argentina,Decision on the Argentine Republics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ward, paras. 205-210.)。因此,仲裁庭應先適用投資條約內的非排除措施條款,以此弄清楚東道國所主張的非排除措施是否符合條約的規定。
第二,雖然投資條約內的非排除措施條款類似于“危急情況”之國際習慣法規則 這一解釋方法為Enron v. Argentina案與 Sempra v. Argentina案的仲裁庭明確采納。(參見:Enron v. Argentina, Award, para. 334;Sempra v. Argentina, Award, para. 373-388.),但兩者還是存在明顯區別。在條款的設計方面,《責任條款草案》第25條規定得更為詳細,如提出了“該行為并不嚴重損害作為所負義務對象的一國或數國或整個國際社會的基本利益”方面的要求。另外,在功能層面也存在差別,“危急情況”之國際習慣法規則是為了證明締約方的行為并未構成國際不法行為,而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是締約方出于免除其承擔違反條約責任之目的。
第三,鑒于投資條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適用是確保在公共利益與外國投資者利益間實現一定程度的平衡,若將非排除措施條款中的“必要的”用語等同于《責任條款草案》第25條的“唯一方法”要求,其結果可能會直接導致這一條約目的無法實現,因為“唯一方法”的要求相當難以滿足。試想,只要還存在足以應對當時特殊情況的其他任何方法(即便這些方法的成本更高或許更低效),那么“唯一方法”的要求就無法滿足,從而也就無法主張“危急情況”的抗辯。也就是說,若將“唯一方法”的要求適用于非排除措施條款的“必要性”要求,定會導致投資條約中的此類條款對東道國而言毫無用處[8]251。
由此看來,似乎認為非排除措施條款的“必要性”要求不能完全等同于“危急情況”國際習慣法規則的“唯一辦法”要求的主張更有說服力,本文傾向于接受這一觀點。
(二)歐洲人權法院的自由判斷余地原則
盡管Alvarez與Khamsi極力倡導用“危急情況”國際習慣法規則的“唯一辦法”要求標準來解釋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要求,但Burke-White與von Staden卻主張用另一個外部標準來對非排除措施條款的“必要的”一詞進行解釋,即仲裁庭可適用由歐洲人權法院在實踐中發展而來的自由判斷余地原則。他們認為,自由判斷余地原則是“一種恭順的審查標準,仲裁庭在運用這一標準時,無須對具體情勢下的事實以及內國有權機構就這些事實所做的評判進行嚴格審查,而只須查證被申請國是否已經以一種公正的方式對事實予以了考慮,而且已就此作出了通過合理性檢測的結論”[9]。將自由判斷余地原則作為審查投資條約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要求的標準乍看起來確實具有吸引力,然而,在其具體適用中的確會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問題。
第一,即便是在歐洲人權法院內部,對于自由判斷余地原則本身而言,也存在較大的爭議。如de Meyer法官在Z v. Finland案所出具的不同意見的裁判書中曾較為嚴厲地批評了這一原則:“已經在該院的判決書中存在了太久一段時期的關于各國享有自由判斷余地的空洞語句沒必要說得如此委婉……(自由判斷余地)這一概念,鑒于其原則上的錯誤性正如其于實踐毫無用處一樣,應該立即被摒棄。” 參見:Z v. Finland,EctHR, Reports 1997-I, Judgment (Merits and Just Satisfaction), 25 February 1997, p. 358.
第二,由于自由判斷余地原則的基本原理與歐洲人權法院47個成員各自不同的法律制度以及政策偏好息息相關,所以若成員間在某一事項上缺乏太多的共同之處,歐洲人權法院將會授予各成員較大的自由判斷余地。比如,各成員基于《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歐洲公約》第10條第2款的規定,出于“道德保護”目的而對言論表達自由予以規范時,各國就享有廣泛的自由判斷權[10]。但在通常只涉及雙邊投資條約的投資者—東道國間投資仲裁情形下,自由判斷余地原則的適用范圍(相較于人權領域)顯然要小得多。
第三,將解釋權授予一個中立第三方的做法已構成了國際關系法制化的關鍵性要素之一。對于一部條約而言,若其中一個締約方放棄這樣的授權,而其他締約方也同樣不履行相應的義務,那么對該條約的解釋或適用就會完全成為締約各方(民主)決策過程的結果。爭端產生后,賦予任一締約方自由判斷余地,毫無疑問,只會使得各締約方通過同意中立第三方裁判而使各自的國際義務變得更具有約束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第四,從國際法院的審判法理來看,并未發現太多支持運用自由判斷余地原則的證據。在Oil Platforms案中,當面對一個非常類似于投資條約內非排除措施條款的《美國—伊朗友好、經濟關系與領事權利條約》第20條第1款(d)項條文時(因為后者也規定,締約雙方可采取“保護其重大安全利益而必要的”措施),國際法院法官Higgins對“必要的”一詞的比例要求予以推斷,她順便提到,這并非意味著援引條約第20條第1款(d)項的國家享有“自由判斷余地”:“法院本應該接著審查‘必要的其意思是什么,而不需要提供任何所謂的‘自由判斷余地。在當時事件所發生的情形下,本來就應該注意到,在一般國際法中,‘必要的一詞應理解為也包含一種‘比例需要。” 參見:Case concerning Oil Platforms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6 November 2003, ICJ Reports 2003, 161, para. 48.事實上,在該案判決書中,法庭并未提及自由判斷余地原則。
第五,從理論角度看,似乎很難解釋為何一個單獨由歐洲人權法院所發展起來的原則會與其他地區國家間(比如美洲國家間)的投資條約相聯系,并用來解釋條約中的非排除措施條款。更何況,歐洲人權法院從未聲稱過,自由判斷余地原則已成為一項國際習慣法規則或一般法律原則。關于這一點已為Siemens v. Argentina案所證實,該案仲裁庭就曾明確表示,自由判斷余地原則并不是國際習慣法的組成部分 參見:Siemen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Award, 6 February 2007, para. 354.。
(三)善意原則標準之不確定性
除此之外,也有學者主張,仲裁庭在對具有自我判斷性質的非排除措施條款進行審查時,應適用善意原則的審查標準[3]120-121。但作為國際法核心原則之一的善意原則,由于其可操作性尚待進一步發展,目前國際協定或各類法律文件均未對其內容作出具體規定,學術界也未達成一致共識,且在國際仲裁實踐中利用這一原則對東道國適用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行為進行審查的案例并不多見,故不認為該審查標準在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認定實踐中具有普遍適用價值。
經過以上討論,不難得出結論:無論是“危急情況”國際習慣法的“唯一辦法”要求,還是自由判斷余地原則以及善意原則,似乎都并非為解釋投資條約非排除措施條款中“必要的”一詞的最理想選擇。那么,對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審查,較為適當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呢?考慮到國際投資仲裁的普遍實踐并結合眾多學者的觀點,比例原則分析中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可謂不二選擇。三、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審查盡管各內國法院抑或國際仲裁庭在適用比例原則時會存在些許差異,但裁判者在決定政府某一具體行為的比例問題時通常會考慮三個因素:第一,適當性因素。相關行為必須是為實現合法目的并通過適當方式而采取的行動。第二,必要性或最少限制方式因素。所選擇的行政措施必須是為實現相關目的而采取的最少限制的行為,在實現相關目的時,不存在能將對投資者個人的不利影響降至更低程度的其他任何同等有效的手段。第三,嚴格意義比例因素。所采取的行政舉措必須符合狹義上的比例(proportionality stricto sensu),這就意味著必須對所涉各主體間的不同利益進行估量并試圖加以平衡[8]2。
比例原則分析的方法能對東道國的公共利益與外國投資者的商業利益進行全面和盡量客觀的協調與平衡。以非排除措施的比例審查為例,比例原則一方面尊重締約方希冀通過非排除措施條款的擬定來達到其保護特殊利益與價值目的的做法,使締約方正當合法的締約意圖能得到真正實現;另一方面又對東道國動機不純的、打著非排除措施幌子的行為起到正確甄別與有效約束之作用,從而切實保護外國投資者的現有與預期投資利益。因此,這一審查標準在有關東道國提出非排除措施抗辯的國際投資仲裁活動中得到了廣泛運用。
(一)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審查的法律依據
1.比例原則適用于國際投資仲裁活動的合法性依據
正如Aharon Barak法官所指出的那樣,“在任何法律制度下,希望通過適用比例原則來對案件進行審理,都必須為該原則的適用提供一個法律依據。”[11]211就比例原則用于分析東道國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的審查而言,其所依據的是《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第(寅)項的規定條文內容為:“一、法院對于陳訴各項爭端,應依國際法裁判之,裁判時應適用:……(子)不論普通或特別國際協約,確立訴訟當事國明白承認之規條者。(丑)國際習慣,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卯)在第五十九條規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學家學說,作為確定法律原則之補助資料者。”。根據該項規定,作為“一般法律原則”的比例原則可成為國際法的正式淵源之一。對于ICSID公約框架下的投資爭端,根據公約第42條“投資仲裁適用法”第1款條文內容為:“仲裁庭應依照雙方可能同意的法律規則對爭端作出裁決。如無此種協議,仲裁庭應適用作為爭端一方的締約國的法律(包括其沖突法規則)以及可能適用的國際法規則。”的規定,作為國際法規則組成部分的比例原則自應在ICSID國際投資仲裁程序中被認定為可適用的準據法規則之一。另外,在其他的投資者—東道國非ICSID仲裁活動中,由于國際投資的實體爭議解決可能無關國際法規則(比如東道國僅在受內國法調整的商事合同中作出受仲裁管轄的同意表示),那么再將比例原則作為適用法規則之一予以適用,可能會存在困難。但是,即便在這樣的情形下,仲裁庭仍可將比例原則視為相關國內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而對其進行適用。例如,即使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條關于“適用于爭議實體的規則”條文內容為:“(1)仲裁庭應按照當事各方選擇的適用于爭議實體的法律規則對爭議作出決定。除非另有表明,指定適用某一國家的法律或法律制度應認為是直接指該國的實體法而不是其法律沖突規范。(2)如當事各方沒有任何選擇,仲裁庭應適用其認為可適用的法律沖突規范所確定的法律。(3)仲裁庭只有在當事各方明示授權的情況下,才應按照公允及善良原則或作為友好仲裁員作出決定。(4)在任何情況下,仲裁庭均應按照合同條款并考慮到適用于該項交易的貿易慣例作出決定。”并未明確規定可適用國際法規則,但比例原則依然可以內國法規則的身份適用于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框架下的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活動。
2.比例原則適用于非排除措施“必要性”審查的合法依據
正如Higgins法官所說的那樣,基于“必要的”一詞的解釋而觸發的比例原則分析,其是以“一般國際法”的身份介入的 參見:Case concerning Oil Platforms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6 November 2003, ICJ Reports 2003, 161, para. 48.。因此,鑒于比例原則廣泛被認可的“一般國際法”地位,再加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第3款(丙)項關于“國際法規則亦可用作解釋依據”的規定,從而將這一原則作為一條普遍的國際法規則來對東道國的有關行政措施予以“必要性”審查就具備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換句話講,對于投資條約中的“非排除措施”條款而言,其解釋程序理應將比例原則當作一個適當的工具來判斷締約方的行為是否為“非排除措施”條款所覆蓋,也即東道國所主張的非排除措施是否為最終能通過“必要性”審查的真正“必要的措施”。
(二)“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在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問題上的具體審查運用
1.通常的“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審查的優勢與不足
就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審查而言,“最少限制方式”測試選擇從批判的角度對東道國利益與投資者利益予以平衡或進行比例協調,在這一過程中,比例與平衡關系始終被仲裁員作為首要的與最終的考慮要素予以對待。在“最少限制方式”的具體測試中,仲裁員并不會對援引非排除措施條款的當事國所尋求實現目標的相對重要性作出裁判,其分析只集中于兩點:(1)對主張非排除措施條款免責的當事國而言,是否還存在可以如同所選擇采取的措施一樣能實現相同水平保護的另一替代措施;以及(2)替代措施是否可實現對外國投資只造成更低程度的限制性影響。如果這樣的替代措施是存在的,那么當事國已選擇采取的措施就談不上是“必要的”,因此該國就不可主張適用非排除措施條款來為自己的違約行為開脫責任。
然而,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比例原則的“最少限制方式”檢測標準過于嚴厲,并對此提出了種種批評,其中最突出的是關于仲裁員應如何對替代措施之成本與已采取措施的成本進行比較的問題。如在CMS v. Argentina案中,針對阿根廷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仲裁庭找出了大量的可替代措施,包括“對受影響的人口給予直接補貼” 參見: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May 12, 2005, Award, para. 323.。在通常的“最少限制方式”檢測中,裁判者會注意:替代措施(如對公用服務行業的消費者提供補貼)能否實現與所采取措施已實現的相同水平的保護,并且與已選擇的措施(即對公共服務合同下投資者的權利予以廢止)相比,可替代措施對外國投資所造成的限制可能更少。依照仲裁庭的此種分析邏輯,其結果會是東道國將永遠被要求承擔由采取更少限制的替代措施(即對公用服務行業的消費者提供補貼)而帶來的各種成本。試想,若選擇采取此種極為牽強的替代措施,補貼所帶來的巨大成本必將對被申請國造成難以承受的政府預算開支壓力。基于現實考慮,仲裁庭的分析顯得過于理想化。
2.改進: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或遵從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
(1)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Reasonable LRM)
基于人們對上述通常的“最少限制方式”檢測標準所產生的質疑,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應運而生。該方法對可替代措施所帶來的不同成本實行一種更為科學的權衡,主張在審查過程中不僅要確認是否還有另外的更少限制替代措施,而且還要對實施該替代措施所引發的不同成本予以考慮,從而才能最終得出該替代措施是否合理的評估結果。更確切地說,假設其他替代措施雖然在對外國投資造成最少限制影響的同時也能實現相同的利益保護,但卻會產生不合理的管理與執行成本,那么政府選擇采取的措施仍然為“必要的”。在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之下,仲裁庭還可對東道國在假設采取替代行動的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各種費用以及時間延誤成本進行估算。事實上,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理念并非沒有先例,在WTO的Korea Beef案裁判中就有所體現 Korea: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December 11, 2000) WT/DS161/AB/R, WT/DS169/AB/R, para. 166.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者認為WTO上訴機構在該案審理中所采取的僅是比例審查標準。對此,DH Regan予以了批判,并有力地證明了該案所采用的審查標準為合理性的“最少限制方式”標準。(參見:DH Regan.Judicial Review of Member-State Regulation of Trade within a Federal or Quasi-Federal System: Protectionism and Balancing[J]. Michigan Law Review, 2001, 99(8):1853-1902.)。另外,包括歐洲法院與歐洲人權法院在內的眾多法院以及仲裁機構(特別是在被申請國采取合法行為以應對復雜的社會問題案件中)都表示,比例相當結論的作出并不要求進行嚴格的“必要性”審查,只要東道國政府所采取的應對措施是從大量的合理性可選措施中挑選出來的就足夠了。這一方法也可被描述為一種“合理的必要性”審查標準,因此在“必要性”的裁判方面,應作出比德國有關比例分析的古典理論較為寬松的解讀。
(2)遵從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Deferential LRM)
還有一些學者主張在適用比例原則對仲裁案進行裁判時,應采取遵從的比例分析方法。如Caroline Henckels認為,裁判者在對是否存在合理的可替代措施予以評估時,可以通過降低舉證標準,如針對東道國所得出的認為有必要采取非排除措施的結論,只要求其提供一個合理的依據,以此對“比例原則”審查提供一種遵從(deference)[12]。Stephan W. Schill指出,投資條約仲裁庭經常提及“遵從”這一概念,其含義主要涵蓋以下幾點:首先,遵從指的是國際司法機構必須尊重各主權國家的條約締結權,包括締約方的條約解釋決定權以及仲裁庭即便持不同政見亦不應對條約義務進行“改寫”。其次,遵從亦可指以一種國家友好型(或主權友好型)方式詮釋國際條約(包含投資條約)的解釋原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遵從意味著賦予東道國一定的自由裁量余地或自我操作空間,在此范圍內,其主權行為通常不受國際司法仲裁機構的全方位審查。據此,仲裁庭在審查東道國行為時,其標準可從不可訴原則(non-justiciability-doctrines,即不進行任何仲裁審查)下的完全遵從跨到對內國層面一開始所做的任何事實或法律決定進行重新考慮。在具體仲裁中,各仲裁庭需在上述量程內找到一個恰當點位,并依此審查標準對外國投資者保護與公共利益進行均衡,正是這點為投資條約仲裁注入了更多的合理性因素[13]。
截至目前,在ICSID所有的已審案件中,Continental案的仲裁庭可稱得上對遵從理念下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的認識表現得比較成熟。就該案的裁決書而言,在兩個方面體現了這一點:第一,仲裁庭對是否存在這樣的可替代措施予以關注,該替代措施不構成對雙邊投資條約的違反,而且在東道國采取其所主張的非排除措施時(從2001年11月開始),該替代措施又能夠以較為合理的方式得到施行,并且還能實現相等的效果或救濟。第二,在對這些替代措施事實上可否以合理的方式得到實施,以及可否避免采取該案所審查的措施予以評估時,仲裁庭應牢記,其既沒有義務就阿根廷政府的經濟政策(2001-2002年)作出裁判,亦無需對阿根廷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權選擇行為進行審查。仲裁庭的使命是較為遵從地僅對阿根廷所提出的“必要性”請求是否站得住腳進行評估,從而確定阿根廷政府出于保護其重大利益的目的,除了采取已實施的措施外,在當時再也沒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措施可供選擇 參見: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paras. 198-199.。
另外,其他一些ICSID投資仲裁庭也在審查東道國非排除措施問題上表現出一種遵從的態度。以LG & E案的仲裁裁決書為例,仲裁庭注意到,阿根廷政府的應對行動不是通過對具體公共服務合同予以單個評估,而是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對外國投資者的合同權利全部予以中止 參見:LG & E Energy Corp, LG & E Capital Corp, LG & 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 Award, Oct 3, 2006. para. 241.。個案評估的方法大致會包括對具體公共服務承包合同下的投資者權利是否應予以解除進行評估,依據就是這些權利對阿根廷經濟危機的持續性與覆蓋范圍可能會產生的影響。譬如,授權外國投資者提高電力或天然氣行業服務費率的合同權利就必須與電信服務合同下的權利有所區別。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東道國在維持投資者于前一合同下權利的同時,卻對后一合同下的權利予以解除,也有可能是合乎情理的。假若這樣的話,相較于“一刀切”的行動,個案評估的做法顯然是一種更少限制的替代措施,因為這一做法是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進行審查的,不排除某些公共服務合同有可能會逃過被解除的厄運。更何況,這一替代措施的執行成本明顯少于CMS v. Argentina案仲裁庭所列舉的“采取直接補貼”這種有點極端的可替代措施而產生的高昂開支[14]。但是即便針對阿根廷政府并未采取單個評估的做法,仲裁庭最終還是裁定阿根廷政府的行為符合非排除措施的構成要件。
當然,對于遵從的(或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一部分人也表現出擔憂,認為這一審查標準對于主張非排除措施的東道國而言過于溫和,因為被申請國的主張較為容易通過檢測。面對這樣的質疑,最終需考驗的還是仲裁庭的智慧:如何在均衡東道國與投資者的權益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取舍,畢竟東道國對其領土范圍內的投資活動享有經濟主權。
四、結論在國際投資爭端的解決方面,仲裁方式將變得越來越普遍,仲裁庭的權力也只會變得越來越強大。基于各方在投資條約的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以及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審查標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比較可行的方法就是淡化非排除措施條款的自我判斷性質區分,并為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審查創建一個可行的統一標準。鑒于“危急情況”之習慣國際法規則的“唯一辦法”要求標準、自由判斷余地原則以及善意原則在作為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審查標準事項上的不合適性,建議國際投資仲裁庭繼續采納“最少限制方式”審查標準。當然,仲裁活動的發展也對國際投資仲裁制度本身必須變得越來越完善提出了要求。研究表明,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標準或遵從的“最少限制方式”標準在對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審查問題上,將能更有效地實現公正合理的仲裁結果:一方面,對于東道國正當合法的非排除措施,在通過客觀并準確的審查后定會得到一個有利于東道國的裁決;另一方面,通過對被申請國打著采取非排除措施的幌子,卻行侵害外國投資者利益之實的行徑予以證偽,從而有效地保護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利益。
近些年來,我國越來越多的投資條約納入了非排除措施條款,如2004年重新簽訂的《中國—芬蘭雙邊投資條約》第3條第5款;2012年《中日韓投資協議》第18條“安全例外”條款、第19條“臨時保障條款”與第20條“金融審慎措施”條款;2012年《中國—加拿大雙邊投資條約》第33條“一般例外”條款等。伴隨著我國海外投資者(如Tza Yap Shum v. Republic of Peru案與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imited and Ping An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imited v. Kingdom of Belgium案)甚至是我國政府(如Ekran Berha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卷入國際投資糾紛的廣度和深度與日俱增,國際投資仲裁庭在非排除措施審查事項上的動態發展對我國的借鑒意義與研究價值亦將日益凸顯。ML
參考文獻:
[1] W.Burke-White, Andreas von Staden. Investment Protection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n-Precluded Measures Provision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J].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2): 381-386.
[2]Stephan W. Schill, Robyn Briese. “If the State Considers”: Self-Judging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J].Max Plan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2009(13): 61-140.
[3]楊福學. 國際能源投資相關條約中的“非排除措施”條款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4.
[4]Diane A. Desierto. Necessity and “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for Non-precluded Measure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3): 827-934.
[5]Kenneth Vandevelde. Of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Shifting Ideology of the BITs[J].International Tax & Business Lawyer, 1993(11): 159-170.
[6]Thomas J. Bodie.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Activist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M].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95:221.
[7]Jose E. Alvarez, Kathryn Khamsi. The Argentine Crisis and Foreign Investors: A Glimpse into the Heart of the Investment Regime[G]// Karl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