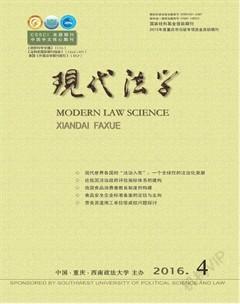美國論文開放存儲的推動及其啟示
摘要:論文開放存儲所面臨的核心法律問題在于,作者或他人是否具有將論文存檔傳播的權利基礎。針對該問題,美國《Sabo法案》以及美國NIH、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的開放存儲政策及其實施向我們展示了不同的應對努力。分析這些典型或較具影響力的法案與政策實施,可以窺視論文開放存儲推行中核心法律問題產生的根源、涉及的利益關系以及解決的可能與方向,并對我國機構開放存儲政策的發布與實施提供有益的經驗啟示。
關鍵詞:美國;開放存儲;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DF 523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4.14
一、引言開放獲取是指在網絡范圍內任何人都可以免費的、及時的、永久的、全文的聯機獲取數字科技與學術資料,主要是在同行評議的期刊上發表的研究資料,其意味著任何用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互聯網以鏈接、閱讀、下載、存儲、打印等方式使用這些研究資料。關于開放獲取的起源與發展,部分學者將其雛形追溯到1963年“超文本(hypertext)”的問世 See Pamela Bluh, “Open Access,” Legal Publishing, and Online Repositories, 34 J.L. Med. & Ethics., (2006). p.126. 甚至有學者認為開放獲取是伴隨著1665年英國《倫敦皇家哲學會刊》的問世而出現的。(參見:初景利. 開放獲取的發展與推動因素[J]. 圖書館論壇,2006,(6):238-242.),但開放獲取運動遲至20世紀90年代末始獲得巨大發展,其肇因于如下因素:期刊訂購費用快速上漲,圖書館不得不取消訂購大量學術期刊,導致了信息獲取危機與學術交流危機 在此期間,因價格高企,中國學術機構訂購國際著名期刊及其數據庫也非常有限。;互聯網與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電子數字資源爆炸性地涌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傳播科學知識和文化遺產的傳統;作者希望改變過往耗時費力的出版模式,在保留論文同行評議的同時,尋求能更快速發表與更廣泛傳播的出版模式。當然,開放獲取的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也根源于人們對于其確保知識信息全球共享以助益人類文明進步等價值目標的肯定 有學者認為,開放獲取的運行法則之一是知識自由原則,其精髓在于對超越了國界的知識和文明的“開放”,一種兩千多年前雅典和羅馬人就已經驕傲地擁有的人類智慧。(參見:劉麗君. 對法律“信息烏托邦”的現實考察與應對策略[J]. 法學,2009,(7):67.) 。
科學論文的開放獲取,主要依賴于開放獲取期刊的建設與論文開放存儲兩種路徑。開放獲取期刊的建設主要涉及期刊改制與發展、論文質量控制等資金、技術與操作問題;而開放存儲政策的實施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則來自于法律層面,即即使因有利于學術交流與學術聲譽提升使得作者普遍同意論文的存檔傳播,但在作者發表論文時與出版商簽署出版合同讓渡著作權或其中的復制傳播等主要權利后,作者是否仍有權自行或授權他人將經期刊同行評議后的論文最終審定稿提交某個機構知識庫存儲,并即時或延時向社會開放公共獲取。這是論文開放存儲傳播所面臨的核心法律問題,是順利推動開放存儲關鍵之所在。
當前,無論是開放獲取期刊的發展,還是開放存儲政策的發布實施與相關機構知識庫的建設,美國均已取得較為矚目的成績 開放獲取期刊、開放存儲政策與機構知識庫的有關數據,可以參見:李武,梁小建,楊琳. 近五年來開放獲取運動的國際進展分析[J]. 科技與出版,2013,(8);李書寧. 國外大學開放獲取政策研究[J]. 圖書情報工作,2013,(10).。本文將以法律分析的視角,針對前述論文開放存儲的權利基礎問題,擇取《Sabo法案》、NIH、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應對努力作為典型評述,分析借鑒其中有益的經驗舉措,借以推動我國當前尚屬落后的論文開放存儲。
二、《Sabo法案》的啟示2003年6月2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員Sabo在美國國會會議上提交了一份名為《公共獲取科學法案》(Public Access of Science Act,以下簡稱《Sabo法案》)的議案。法案的實質內容是要通過修改美國《著作權法》第17章第105節,使得受聯邦政府實質性資助的科學論文成為公共領域的作品,能為公眾免費獲取,以免除這類作品的著作權保護。其目的是要擴大美國著作權法中美國政府作品 根據美國《著作權法》第105節的規定,屬于美國政府的作品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范圍,將受聯邦政府實質性資助而產生的作品也納入其中。該法案還提出,政府部門在資助一項研究時,應與受資助方簽訂“資助協議”,應寫明根據該協議產生的任何研究成果均不受著作權保護,以自由方便地為科學家、學者、醫師和公眾免費獲取 Public Access to Science Act, H.R. 2613, 108th Cong. § 3(a)(2) (2003) (to amend Title 17, United States Code).。
現代法學鄭永寬:美國論文開放存儲的推動及其啟示——基于法律視角的研究顯然,《Sabo法案》提出的促進科學論文開放獲取的方案,要比開放獲取期刊建設與自存檔路徑激進得多。該法案引發激烈的爭論,但并沒有獲得太多的支持,最終也沒有在國會獲得通過。商業出版商的激烈反對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擔心在全球范圍內政府資助科學研究日漸增多的背景下,該法案的實施及其擴張將嚴重損害他們的出版收益;他們甚至質疑一般公眾獲取科學論文的必要性 See Samuel E. Trosow,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Necessary Incentive or Double Subsidy?, 22 Cardozo Arts & Ent. L.J. (2004). pp.648-649. 對于一般公眾免費獲取專業性科學論文的可能性與必要性的質疑,有論者反駁認為,科學研究人員本身就是公眾的一部分,且醫護人員對于相關科學論文的即時獲取將有助于提升社會醫療健康與疾病救助水平,此外,科學論文的即時免費獲取可以節約資助研究中不免要發生的訂購費支出。(參見:Editorial, Open Acces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N.Y. Times, Aug. 7,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3/08/07/opinion/07THU3.html. (last visited January 22, 2015). See also Kristopher Nels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mandated Public Access to Biomedical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IH Depository Requirements, 19 Alb. L.J. Sci. & Tech. (2009). p. 426.。)大學或學會主辦的非盈利出版社雖認同科學論文傳播存在的問題及《Sabo法案》推動科學論文開放獲取的目標,但質疑方法的可取性,因為它們擔心,取消公共資助論文的著作權保護,將削減它們用于支持學會各項工作與學術發展的期刊訂購費收入[1]。也有大學聯合會懷疑法案對于促進開放獲取的必要性,并擔心法案沖擊傳統著作權保護及其在學術出版中的作用[2]。諸多的利益相關者,甚至包括作者及開放獲取的提倡者[3]認為,法案倡導的路徑可能迫使所有的出版商均轉變為開放獲取模式的出版商,在經驗證明法案的路徑及其引發的出版模式轉變成功有效之前,貿然嘗試通過立法廢除傳統的以訂購費為基礎的出版模式,并不明智[4]。所以,人們更希望“有序的轉變。”[5]盡管《Sabo法案》提出后不乏學術界支持的聲音 See Samuel E. Trosow,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Necessary Incentive or Double Subsidy?, 22 Cardozo Arts & Ent. L.J. (2004). pp.613-681. 甚至有學者更進一步主張取消所有學術作品的著作權。See Steven Shavell, Should Copyright of Academic Works Be Abolished?, 2 J. Legal Analysis. (2010). pp.301-358.,但在前述的質疑反對聲中及美國利益博弈的政治立法生態中,該法案的最終命運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NIH(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的開放存儲政策及其施行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是全球最大的醫學研究資助機構。2004年9月,美國NIH在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建議和指導下制定了公共獲取政策草案——《促進NIH科研信息開放獲取政策草案》。該草案被提交給全社會征求意見。在廣泛征詢并考慮對該草案的評論意見基礎上,NIH于2005年2月3日正式發布開放獲取政策[6]。該政策請求并強烈鼓勵所有受NIH基金資助的研究人員在發表研究成果的時候,應將其已被期刊接受出版的研究成果的最終電子版本向NIH國家醫學圖書館所屬的PubMed Central (PMC)提交,該版本包括所有經同行評議所作的修改;作者可以自主決定該文章對公眾開放的時間,但NIH建議最遲不應晚于發表12個月后開放獲取。該新政策從2005年5月2日起正式生效。
由于該政策只是請求和強烈鼓勵受資助者自存檔,并不具有強制性,其實施的效果并不理想。2006年NIH發布的數據顯示,受資助者提交論文的總數低于4%[7]。在2007年財政撥款中,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要求NIH應將“請求”改為“強制要求”。2007年7月1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NIH強制要求開放獲取的提案。該政策于2007年12月26日得到了美國布什總統的簽署,并納入到2008年“統一撥款法案”中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08, PL 110-161, tit. II, § 218 (Dec. 26, 2007).。2008年1月,NIH發布了“促進NIH資助研究的存檔出版物開放獲取的修訂政策”,并于5月25日開始實施[8]。該政策要求受NIH資助的研究人員必須將其經過同行評議的最終版本論文存放在美國醫學圖書館PMC(PubMed Central)知識庫中,在不晚于發表12個月后開放獲取;NIH執行的開放獲取政策與版權法相一致。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hall require that all investigators funded by the NIH submit or have submitted for them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s PubMed Central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ir final, peer-reviewed manuscript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o be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no later than 12 months after the official date of publication: Provided, That the NIH shall implement the public access policy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copyright law. 順帶說明的是,NIH開放獲取政策并不溯及既往。See Eve Heafey,Public Access to Science: The New Policy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 Light of Copyright Protection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15 UCLA J. L. & Tech., (2011). p.56. 2009年3月11日,奧巴馬總統通過2009年的《綜合撥款法案》簽署了NIH開放獲取政策,使得該政策得以長期化。 Omnibus Appropriations Act of 2009, H.R. 1105, 111th Cong. § 217, at 259 (2009) (enacted). 200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綜合撥款法案》繼續支持NIH的開放獲取政策,并延續至其后的財政年度。
NIH自存檔開放存儲政策的目標,是使得納稅人資助的科研成果能夠被包括醫生、教師、科學家在內的一般公眾免費獲取,而不是只服務于出版商的利益,其背后的基礎是這些科研成果的開放獲取將有助于與死亡和疾病作斗爭的科研發現 See Kristopher Nels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mandated Public Access to Biomedical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IH Depository Requirements, 19 Alb. L.J. Sci. & Tech. (2009). p. 440. See also Eve Heafey,Public Access to Science: The New Policy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 Light of Copyright Protection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15 UCLA J. L. & Tech., (2011). p.20.但也有論者質疑以國內公共納稅資金支持作為開放獲取政策的基礎與全球免費獲取目標的不一致。See Jorge L. Contrera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Latency, Licensing, and Access, 53 Santa Clara Law Review. (2013). p.539.就此,筆者認為,在信息高效互聯傳遞的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全球科學界互惠互利與共同提升的目標,以一國公共資助的國界性反對全球開放獲取本身就是保守狹隘的不充足理由。。在全球公共資助科學研究占有很大比例且日趨加大的背景下,這種植基于公共利益基礎上的開放存儲主張的實踐與擴張,無疑將對以訂購費及鏈接許可收費等維持經營并獲利的傳統期刊出版商的利益造成沖擊。所以,從一開始,NIH的開放存儲政策就遭到出版商及其協會的質疑反擊。它們認為NIH的政策是非法無效的,是對著作權設置的限制或過于寬泛的例外[9],將損害學術研究出版及其同行評議機制,威脅美國在知識產權領域長期以來的領導地位,使得出版商經營利潤受損,[10]因此,出版商及其協會積極游說,試圖通過廢除NIH政策的法案 See Fair Copyright in Research Works Act, H.R. 801, 111th Cong. (2009). (prohibiting federal agencies from adopting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policies). ,或通過修改出版合同以施加更多開放存儲的限制。[11]與此同時,出版商廢除NIH政策的法案動議則不時遭受學者群體的聯合抵制[12] 。
事實上,NIH開放存儲政策是傳統付費獲取模式與公共資助研究成果完全免費獲取這種理想模式的折衷,[13]通過允許自論文發表之日起最長12個月推遲開放獲取的遲滯期來平衡出版商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14]所以,出版商認為NIH政策的施行將削減他們的訂購費收益 See Martin Frank, Free Access for All! Can We Afford It?, 21 Physiology 372 (2006), available at http:// physiologyonline.physiology.org/cgi/content/full/21/6/372.出版商認為圖書館能夠通過取消訂購剝奪出版商享有的收益。 ,此反對理由并不具有充分的現實說服力。因為,科學期刊最大比例和最重要的消費群體是研究人員,所以,大學科研機構的訂購費一直是期刊出版商最主要的收益來源,而科學家的研究需要及時獲取科學前沿信息,因此,一年遲滯期的存在使得大學圖書館基本不會為了等到遲滯期過后的免費獲取而取消訂購科學期刊,所以,出版商的訂購費收益基本不會減少 See Kristopher Nels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mandated Public Access to Biomedical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IH Depository Requirements, 19 Alb. L.J. Sci. & Tech. (2009). p. 442. 有學者較詳細比較分析后認為,對于出版商而言,因為一年遲滯期的存在,其訂購費和廣告費收入基本不會因開放存儲而減少,可能減少的主要在于轉載收入,但這部分并非出版商收益的主要來源。See Jorge L. Contrera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Latency, Licensing, and Access, 53 Santa Clara Law Review. (2013). pp.559-561.。而且,一直以來,美國科學期刊出版商都無需為獲得論文和同行評議付費,其主要成本僅存在于組織評議與出版的費用。所以,一年遲滯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兼顧了出版商的商業利益,但也因為這種平衡妥協,使得大學及其他科研機構圖書館借以降低科學期刊訂購費預算的目標基本無法實現,所謂的開放存儲很大程度上只能為學生、交叉學科或外圍研究人員,以及無力支付訂購費及時獲取科研信息的發展中國家科研工作者等“社會公眾”提供“免費公共品” See Kristopher Nels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mandated Public Access to Biomedical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IH Depository Requirements, 19 Alb. L.J. Sci. & Tech. (2009). p. 440. 肌肉萎縮癥雙親計劃基金會的會長兼執行總裁CEO,Pat Furlong甚至表示:對于那些努力與科學家發展保持一致以便為他們的治療和生活作出決定的個人和家庭而言,獲取可信的、可靠的和實時的信息通常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但是,12個月的等待對我們而言還是太長了。(參見:付晚花,肖冬梅. 美國NIH公共獲取政策及對我們的啟示[J]. 圖書館雜志,2008(10):61.)。
對于出版商商業利益的這種妥協,除了利益集團政治游說的壓力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基本均以學術論文或著作的發表作為衡量學者學術成績的最重要指標,所以,各大學往往通過與職稱、待遇、獎勵或課題申請等相掛鉤激勵研究人員在最著名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在良好同行評議機制運作的基礎上,這些知名期刊長久以來已積累奠定了自身極佳的學術品牌與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成為科學界高質量的最新研究成果的發布平臺。這進而促成這些知名期刊在學術出版界形同壟斷的地位,在有限的時間內無法尋獲可靠的學術替代品,市場機制在此領域基本失靈。這些知名期刊的需要價格彈性因此很小[15]。這也就為這些期刊出版商要求轉移著作權及征收獲取論文的高額費用提供了可能。正因為如此,早在2004年12月8日,布什總統在簽署《綜合撥款法案》時,要求NIH在發布最終政策前充分公正考慮各種評論意見,并和科學論文期刊出版商繼續合作以維持同行評議機制的完整和有效性[16]。而NIH最終發布的開放存儲政策也提及“NIH執行的開放獲取政策與版權法相一致”。所以,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NIH開放獲取政策并沒有改變美國的著作權法或試圖剝奪出版商在著作權法框架下可能享有的專有權利,并沒有因該政策被納入國會財政撥款法案中而自然解決受資助者自存檔的權利基礎問題。NIH開放獲取政策強制性只是指向于NIH作為資助機構對受資助者的要求,但并沒有使得自存檔成為“不需要出版商同意的政府特權”,[17]自存檔仍須取決于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版權合同。[18]實踐中,作者在發表論文前提出保留自存檔的權利或作其他相應的權利安排,出版商可以選擇拒絕。所以,NIH開放獲取政策事實上給受資助者施加了與出版商進行出版合同協商的義務。也因此,NIH建議作者在與出版商簽訂的出版合同中增加類似內容的格式化條款:期刊出版商承認作者保留在論文發表后不晚于12個月內將論文最終版本向NIH的PubMed Central自存檔的權利。
自2008年實施以來,NIH開放獲取政策的現實施行情況總體是理想的,其也逐漸成為其他國家、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資助機構制定實施開放獲取政策的參考模板 例如,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2013年2月發布行政指令,要求所有研發資助達到1億美元的聯邦機構也要實行類似NIH的開放存儲政策。
案》,要求美國勞工部、健康與人類服務部、教育部等所屬年度資助超過1億的聯邦資助機構實行類似于NIH的資助項目論文開放存儲政策,覆蓋了年度聯邦科研資助的一半以上。。但如上文所述,NIH開放獲取政策之所以能有效付諸實施,并非其為受資助者解決了自存檔的權利基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NIH在美國醫療生物等領域研究資助中所占的重大比例以及由此催生出了諸多高質量研究成果,使得NIH在美國乃至全球學術研究領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當然,出版商欠缺協同一致的應對行動也使得出版商無法因NIH的開放獲取政策而拒絕出版合同的自存檔保留或因而拒絕發表受資助者的論文[19][20]。然而,在不得不接受NIH政策施行的前提下,有些出版商也試圖以一些迂回的方式尋求更好保護自身利益,如有些出版商并不同意作者保留或授予作者自存檔的權利,而是承諾按期將論文的后印本(PostPrint Version)提交NIH的PubMed Central存檔,如此將僅保存后印本,且可保持出版商自身著作權的完整,并在NIH政策一旦被廢棄的情況下可更主動地應對[21]。可以說,在法律框架內,出版商與資助機構、作者之間的利益博弈與彼此現實的力量對比緊密相關。
四、哈佛大學開放存儲政策的施行評析開放存儲政策的制訂主體大致有兩類:資助機構與研究者所在機構。這兩類主體主張開放存儲的具體理由與實施路徑不盡相同,但旨在實現的目標及施行中面臨的障礙基本相同。本文選取較為典型的哈佛大學開放存儲政策以作評析,嘗試了解其運作過程與面臨的具體問題。
在美國,自從20世紀中期學術期刊商業出版占據主導地位以來,很多大學和學者指責學術期刊日漸高昂的訂購費、限制論文獲取的政策以及作者發表論文時的著作權轉移要求。尤其是,大學為其研究人員發表科學論文提供辦公場所、科研設施、研究資助和高額薪酬等,但最后作者在期刊發表論文時出版商無需支付研究者貨幣補償,而大學卻需要支付高額的訂購費給出版商以獲取大學資助研究的論文,這相當于大學須為這些科學論文的生產及利用多重付費[22]。如此的不滿以及對科學論文開放獲取理念的認同,促使出現大學試圖將其職員創作的論文開放存儲的政策指令,哈佛大學開放獲取政策即屬其中的典型。2008年2月12日,哈佛大學文理學院以匿名投票方式,一致通過將每位教師以后的學術論文存檔開放獲取的政策Harvard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pen Access Policy (Voted February 12, 2008):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disseminating the fruits of its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as widely as possible. In keeping with that commitment, the Faculty adopts the following policy: Each Faculty member grants to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ermission to make available his or her scholarly articles and to exercise the copyright in those articles. In legal terms, the permission granted by each Faculty member is a nonexclusive, irrevocable, paid-up, worldwide license to exercise any and all rights under copyright relating to each of his or her scholarly articles, in any medium, and to authorize others to do the same, provided that the articles are not sold for a profit. The policy will apply to all scholarly articles written while the person i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except for any articles completed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is policy and any articles for which the Faculty member entered into an incompatible licensing or assignment agreement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is policy. The Dean or the Deans designate will waiv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for a particular article upon written request by a Faculty member explaining the need. See Harvard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pen Access Policy, harv. U. libr. off. for scholarly comm. (Feb. 12, 2008), http:// osc.hul.harvard.edu/hfaspolicy.。與NIH的自存檔政策一樣,借鑒哈佛大學此政策指令的一些大學的開放存儲政策,仍規定一定時間的開放存儲遲滯期以協調出版商與大學之間的利益[23]。但與NIH開放存儲政策要求作者自存檔不同,哈佛大學的該政策嘗試通過教員賦予學院非排他性的存檔傳播論文的權利以實現論文的存儲傳播,除非就特定論文其作者解釋“除外”的必要而書面請求不實施該政策。盡管哈佛大學也鼓勵其教員在與出版商簽署出版合同時,通過提出修改如此標準化合同的附錄或條款,以使得作者能夠保留包括復制傳播論文的一系列權利[24]。如此,在作者因未能保留或獲取自存檔的權利或其他原因而沒有將論文自存檔的情況下,學校將擁有將論文存檔傳播的主動權,甚至在作者發表論文時依通常作法將著作權轉移給期刊出版商之后,學校仍可以將存檔傳播論文的權利回授予作者本身[25]。此外,還必須注意的是,通過哈佛大學式的授權存檔傳播論文的政策指令,其旨在存儲傳播的論文并不局限于如NIH開放存儲政策所針對的公共資助項目科研論文,而是試圖涵括大學所有教員在授權政策實施后的所有科研論文。
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該開放獲取政策在美國大學與研究機構層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于科學論文的開放獲取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迄今為止,已經有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杜克大學、北德克薩斯大學、堪薩斯大學、埃默里大學、三一大學、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以及哈佛大學其他六個學院在內的數十所大學院校采納類似的政策[26]。哈佛大學此政策指令對于開放獲取運動之所以能產生較大的推動作用,原因在于哈佛大學是美國第一所實施強制性開放獲取政策的大學,而該政策是教師匿名投票支持通過而非校方強制性推動的,而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制定實施該政策的是哈佛大學,[27]其在科學研究領域的強大影響力使得被觸動利益的出版商無法堅定地對它說“不”。
但是,該政策指令仍然引發諸多法律效力層面的不確定性,包括:(1)這種非專有存檔傳播權利的授予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而生效;(2)即使生效,在作者其后將著作權轉讓給出版商后,這些授權是否仍然有效;(3)此外,該政策“經解釋同意的除外(opt-out)結構”是否損害教師的學術自治[28] 。
對于這些問題,首先必須明確,依照美國著作權法 美國對于著作權,通常以“版權”指稱,與我國的著作權概念基本相同,為保持全文的統一,在涉及美國版權與版權法時,仍以著作權與著作權法相應表述。,作品一經完成,只要系屬原創且存在于有形載體,作者就自動取得著作權,[29]且擁有處分該權利的自由。所以,作者授予學校非專有的存檔傳播論文的權利,只要是其真實意思表示,這種授權即可生效。關于這種授權,美國沒有明確規定須采納與著作權轉移一樣的書面形式,[30]法院的判例解釋為非專有授權可以采納默示或口頭形式 See, e.g., Effects Assocs. v. Cohen, 908 F.2d 555 (9th Cir. 1990). 。而且,美國著作權法的205(e) 明確規定,書面形式的非專有授權具有對抗其后相沖突的著作權轉移的效力 17 U.S.C. § 205(e) (2011). Section 205(e) provides:A nonexclusive license, whether recorded or not, prevails over a conflicting transfer of copyright ownership if the license is evidenced by a written instrument signed by the owner of the rights licensed or such owners duly authorized agent, and if—(1) the license was taken before execution of the transfer; or(2) the license was taken in good faith before recordation of the transfer and without notice of it.。該條款的立法過程略有爭論。電影產業等利益集團通過游說,試圖僅使已登記的在先非專有授權具有對抗效力,否則不利于知曉在先的授權。而登記部門則更關心登記的實施成本,甚至主張任何在先的非專有授權都可以對抗其后的著作權轉移,無論是否已經登記或采用書面形式。最后通過的法律作了折衷,規定書面形式的非專有授權可以對抗其后的著作權轉移 See Eric Priest, Copyright and the Harvard Open Access Mandate, 1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2). p.70. 事實上,美國著作權法205(e)的規定僅從正面肯定書面形式的非專有授權具有對抗效力,卻沒有明確規定口頭或其他非書面形式的非專有授權不具有對抗效力。這難免會引發一定的爭論。 。
實踐中,哈佛大學除了制定實施該開放獲取政策指令外,還要求教師職員單獨簽署書面形式的授權協議,因此,該授權符合上述規定的形式要求,即使其后教師(作者)在發表論文時依通常作法將著作權轉讓給出版商,此授權仍然有效。但是,除了哈佛大學及其他一些學校外,仍有大部分采納類似開放獲取政策的美國大學院校,因要求所有或絕大多數教師職員分別簽署書面授權協議的實施成本較高或其它原因,僅依賴于學校制定的授權指令來推行其教員論文的存檔傳播[31]。而單純依賴學校的授權指令是否足以使授權生效且可對抗相沖突的著作權轉移,這恰恰是此類非專有授權法律效力上的真正疑難。
關于上述情形授權的法律效力,至少有如此幾方面的質疑:授權人身份、授權作品及授權意思表示的明確性[32];205(e)所要求的書面形式的滿足;以及授權人署名的體現。對此,肯定論者試圖回應如下:(1)授權人身份與論文無需逐一列舉明確,只要系屬采納政策指令的院校的教師,政策指令實施后發表的論文,均屬這里的授權人與作品;而政策指令多依投票表決的方式通過,教師投票贊成表明其認同授權的政策,而且,大學與教師的雇用合同通常包含要求教員遵守大學所有規章政策的條款,如此,也可推定教師認同學校非專有授權的要求。(2)大學非專有授權的政策指令通常包含明確的授權記載及其具體條款,而且,這些政策通常會公開發布在學校的網站上,因此就授權的確定性、可證明性以及告示非專有授權的存在以降低其后權利受讓者的風險等方面,其作用效果并不會比僅具有相對性的合同個別授權更差。(3)如前所述,雇傭合同通常包含有須認同學校各種規章政策的條款,這些規章包含授權學校存檔傳播論文的政策,教員的署名即可視為同意非專有授權的個人署名;即使雇傭合同沒有明確包含遵守學校政策相關條款,也可以基于職業關系及學校與教師間對于遵循學校規章制度的相互信賴,推定包含認同學校政策的條款[33] 。
盡管肯定論者試圖論證支持單純依賴包含論文存檔傳播非專有授權條款的政策指令,可以使教員對學校的非專有授權生效,且可以對抗其后效力相沖突的著作權轉移,但這種論證更多地是學理上的努力,其并不能完全消除司法裁判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來自兩個方面:教師對學校的非專有授權是否已經生效以及學校將論文存檔傳播是否侵犯期刊出版商經論文作者轉讓取得的著作權。實踐中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后一層面,已經有三個大出版社就論文的存檔傳播起訴佐治亞州立大學[34][35]。很顯然,出版商因擔心大學這種授權政策的擴張損害他們的商業利益,甚至可能侵毀整個學術出版的商業模式,所以,他們更愿意針對學校這種政策指令的實施訴諸訴訟,希望借此阻嚇大學管理層發布和實施該類政策[36]。所以,就大學的政策實施而言,更為妥當的做法應該是借鑒哈佛大學的施行方法,去分別尋求每一位教師書面的非專有授權,如此,至少在美國著作權法實踐層面,采納此類政策的大學不會面臨被出版商起訴的風險。
最后,針對哈佛大學此類政策是否侵害教師的學術自由與自治,一般認為,因為科學論文的傳播對于學術問題的探討及作者學術聲譽的傳播有利;而且,學術論文并非商業利益追逐工具,并不存在學術論文單純的交易市場,所以,教師通常希望學術論文更快更廣泛的傳播。這種傳播對于學術共同體及其知識生產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單純自教師與學校的關系上看,教師通常不會反對這種非專有授權。此類授權傳播論文的政策實施,并不會侵害教師的學術自由。
五、麻省理工學院推動論文開放獲取的努力 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都清楚,造成當前學術期刊訂購費高企及科學論文難以獲取的直接原因,在于作者發表論文時期刊出版商均要求從作者處取得論文的著作權。一些知名期刊長久經營形成的學術品牌和影響力,使得這種要求獲取著作權的“傳統”作法無法被簡單否定與拒絕。所以,一些大學在發布開放獲取政策要求作者存檔傳播論文的同時,也通過自身的努力,試圖幫助作為其教員的作者與出版社談判,以使得作者能夠保留將論文存檔開放獲取所需的權利,其中,較典型的如麻省理工學院。2006年1月27日,麻省理工學院發布了“版權修正案”,在承認作者“不得不”將論文的著作權轉移給出版商的同時,希望通過附加該“版權修正案”,能夠使得作者保留授權論文開放獲取所需的權利 其他一些大學,包括哈佛大學,也都指示其教員通過增加著作權附錄等方式來修改補充與出版商的出版合同。See Eric Priest, Copyright and the Harvard Open Access Mandate, 1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2). p.32.。而且,麻省理工學院設有專門的機構幫助作者與出版商談判或代表作者與出版商談判,從而可以增加作者方談判的交涉力[37] 。
這種努力構成美國科研機構推動開放獲取較早的嘗試。大學通過為其教員擬定統一的“版權修正案”,寄望于作者在簽訂出版合同時附加此“修正”條款,借以保留授權開放獲取所需的權利。這種努力能否成功,取決于出版商同意與否;而出版商是否同意出版合同的修正,很大程度上考量的則是作者所在機構的學術影響力。這種力量博弈的微妙,恰好也解釋了美國開放獲取政策實施的如此場景:到目前為止,推動實施論文開放獲取政策的多為知名的、影響力大的大學或科研機構,而一些學術地位或影響力較低的大學則擔心知名期刊“報復”而拒絕發表其教員的論文,較消極應對開放獲取運動。
六、 比較總結與啟示總體而言,開放存儲政策在美國較早得到推動施行,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這很大程度上與它們較先進的科學研究水平與較多的科研成果產出有緊密關聯,也受益于對開放獲取的理念認同。而科學論文開放存儲的實施反過來也進一步推動促進了美國科學研究的發展與進步。
開放獲取運動最初最直接的肇因在于,傳統以訂購費為基礎的學術期刊,尤其是其中較具學術影響力的知名期刊,憑借其在學術領域近乎壟斷的地位,一再調高學術期刊的訂購價格,增加學術論文獲取使用的成本,這進而妨礙了學術信息的傳播交流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犧牲了社會共同體的福祉。而學術期刊壟斷地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卻是根源于各學術機構基本趨同的學術評價機制。大學鼓勵研究人員在知名期刊發表論文并以其作為學術評價與學術地位晉升的重要考量指標,如此評價機制長期作用的結果是,這些較知名的學術期刊越發知名,控制了越來越多的學術資源,學術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其在學術出版領域的地位益發不可取代、不可或缺,而這些期刊也就幾乎無一例外的“強制”要求作者在發表論文時讓渡論文的著作權。所以,可以說,科學論文的傳播獲取危機最深層的根源還是“傳統的”學術評價機制,某種程度上是學術機構的“作繭自縛”。傳統學術期刊這種壟斷地位的存在,使得它們的核心利益無法被忽視,開放存儲政策在短期內始終無法以較“徹底”或“理想”的形式推動施行,否則,在當前學術評價機制下,學術出版與評價將陷于癱瘓。
當前,美國開放存儲政策的發布實施主體主要包括資助機構與大學兩大類,實施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是作者自己存檔傳播論文與作者授權大學等機構存檔傳播論文。前者以NIH的開放存儲政策最具影響力,但在學術期刊普遍要求作者轉移論文著作權的背景下,該種政策的實施面臨的最大障礙是作者可能欠缺自存檔的權利基礎。為了解決該問題,NIH通過提供統一的“版權合同條款”鼓勵研究人員修改與出版商簽訂的出版合同,但此舉措只是給研究人員增加了商談的負擔,最終的決定權仍在于出版商。至于作者授權機構存檔傳播論文,主要是以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開放存儲政策為典型。該政策其后被很多美國大學所效仿。盡管依美國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該政策實施中得到教員書面授予存檔傳播論文的非專有權利的學院,可以以該授權對抗其后作者對出版商的著作權轉移,但基于前述的傳統出版商在學術出版評價中暫時難以被替代的地位,這些政策在制定實施中一般也通過遲滯期條款來兼顧出版商的核心利益。兩類政策在實現路徑上略有不同,但均遭受出版商的反對,都面臨出版商不愿配合作者授權存檔傳播或因此拒絕發表將被存檔傳播的論文的風險。而在美國開放存儲政策現實施行中,如此風險沒有普遍現實化,其原因并非開放存儲政策本身的規則效力或出版商對開放存儲的認同配合,而在于大型資助機構與知名大學對于科學研究資助、成果產出與發表的強大影響力,所以,開放存儲政策最終得以施行實際上是利益相關方利益博弈與妥協的結果,強行推動開放存儲政策的資助機構和大學基本以一定時限的遲滯期而非即時獲取,作為換取出版商“忍受”而非“魚死網破”式反擊的代價。所以說,開放存儲政策的推動是在利益沖突與實力博弈的情境中展開的,需要適當的利益兼衡與妥協,因為即使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開放獲取運動已是大勢所趨,但在學術研究、出版與評價場域內,學術機構、作者與出版商仍然互有所需,利益交纏。這就使得如《Sabo法案》般的激進努力,旨在廢除公共資助作品的著作權來實現完全的開放獲取,最終注定了失敗的命運;使得機構在發布實施開放存儲政策的同時,與出版商的談判妥協常常成為現實的需要;也使得開放存儲旨在實現的科研信息即時獲取與成本降低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打了折扣。
我國開放獲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認知到實踐的歷程。2004年5月,路甬祥院長與陳宜瑜主任分別代表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簽署了《柏林宣言》,表明中國科學界和科研資助機構支持開放獲取的原則立場。其后,一些圖書館、大學、研究所推出了一系列促進開放獲取的舉措,創建了一些機構知識庫,其中較受矚目的是,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于2014年分別發布了自己的開放存儲政策 關于我國開放獲取政策發布與實施的概況,具體可參見:初景利. 國內外開放獲取的新發展[J]. 圖書館論壇,2009,(6):86;趙曉瑞. 英美公共資助研究的公共獲取及對我國的思考[J]. 圖書館學研究,2011,(1):66;李武,梁小建,楊琳. 近五年來開放獲取運動的國際進展分析[J]. 科技與出版,2013,(8):74. 。但總體而言,我國目前自主發布開放存儲政策的機構還很少,與英美德澳加等國的差距較大。而就開放存儲政策的實施,盡管有學者研究認為,我國當前施行開放存儲受出版商掣肘較小,因為學術期刊多由大學或研究機構經營,尚未如歐美國家形成出版商商業規模化和壟斷的局面,因此,推行開放存儲的難度較小[38]。但我國目前的政策導向也是鼓勵研究人員在國外高水平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而且,絕大部分期刊在決定發表論文時均要求作者讓渡著作權或相關的復制傳播等權利,因此,機構開放存儲政策的實施面臨著與其他國家相似的法律困境與現實風險。本文從法律層面就美國論文開放存儲推動的介紹分析,相信對于我國機構開放存儲政策的發布與實施中具體法律問題的應對解決,將能提供有益的經驗啟示。
若超脫于機構的具體開放存儲政策而在國家層面考量開放獲取的問題,在全球化視野下,開放獲取政策能否成功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國的整體科研實力緊密相關,為了消除我國當前科學研究與西方科研發達國家的差距造成的負面影響,首先需要將開放獲取提升至國家戰略的層面。開放獲取國家戰略的制訂與實施對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將有重要影響;對于提升個人與機構的認識高度并認同開放獲取的價值理念有重大意義;也將有利于促動我國科研機構、資助機構的聯合協作,甚至是通過與國外相關機構的合作,來應對出版商的抵觸對于我國開放存儲推行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同時也可以帶動“小”大學或科研機構加入有力的科學共同體與政策施行環境中,消除他們因發布實施開放存儲政策產生的來自于出版商“報復”的顧慮。相信,在世界范圍內開放存儲政策推行日漸擴張以及我國科研實力整體趨強的大背景下,我國論文開放存儲政策的實施發展將能產生良好的科學社會效益。ML
參考文獻:
[1] Samuel E. Trosow,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Necessary Incentive or Double Subsidy?, 22 Cardozo Arts & Ent. L.J. (2004). pp.651-653.
[2] Samuel E. Trosow,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Necessary Incentive or Double Subsidy?, 22 Cardozo Arts & Ent. L.J. (2004). pp.658-659.
[3] David W. Opderbeck, The Penguins Paradox: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aradox of Op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dels, 18 Stan. L. & Poly Rev. (2007). p.111.
[4] Samuel E. Trosow,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Necessary Incentive or Double Subsidy?, 22 Cardozo Arts & Ent. L.J. (2004). pp.652.
[5] Catherine Zandonella, Sabo Bill Assessed, The Scientist (July 16,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22323/title/Sabo-bill-assessed. (last visited January 21, 2015).
[6] Natl Insts. of Health, Policy on Enhancing Public Access to Archived Public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NIH-Funded Research, Public Notice NOT-OD-05-022 (Feb. 3, 2005), available at http:// grants.nih.gov/grants/guide/notice-files/NOT-OD-05-022.html.
[7] Natl Insts. of Health, U.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s., Report on the NIH Public Access Policy 3 (2006), available at http:// publicaccess.nih.gov/Final_Report_20060201.pdf.
[8] Natl Insts. of Health, Revised Policy on Enhancing Public Access to Archived Publications Resulting from NIH-Funded Research, Public Notice NOT-OD-08-033 (Apr. 7, 2008), available at http://grants.nih.gov/grants/guide/notice-files/NOT-OD-08-033.html.
[9] Eve Heafey,Public Access to Science: The New Policy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 Light of Copyright Protection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15 UCLA J. L. & Tech., (2011). pp.47-48.
[10] Kristopher Nels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mandated Public Access to Biomedical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IH Depository Requirements, 19 Alb. L.J. Sci. & Tech. (2009). p. 441.
[11] David W. Opderbeck, The Penguins Paradox: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aradox of Op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dels, 18 Stan. L. & Poly Rev. (2007). p.119.
[12] Research Works Act, H.R. 3699, 112th Cong. (2011)
[13] Kristopher Nels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mandated Public Access to Biomedical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IH Depository Requirements, 19 Alb. L.J. Sci. & Tech. (2009). p. 422.
[14] Robin Feldman & Kris Nelson, Open Source, Open Access, and Open Transfer: Market Approaches to Research Bottlenecks, 7 Nw. J. Tech. & Intell. Prop. (2008). p.29.
[15] Stephen Pinfield, Libraries and Open Access: The Implications of Open-Access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for Librar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Rae Earnshaw & John Vince eds., Digital Converence: Libraries of the Future, (2008). p.123.
[16] David W. Opderbeck, The Penguins Paradox: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aradox of Op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dels, 18 Stan. L. & Poly Rev. (2007). p.112.
[17] 付晚花,肖冬梅. 國際開放獲取政策及其研究進展綜述[J]. 圖書館雜志,2010,(3):25.
[18] Am. Library Assn et al., Mandatory Public Access to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Does Not Violate Copyright Obligations 1 (2007), http:// www.arl.org/sparc/bm~doc/nih_copyright.pdf.
[19] Eve Heafey,Public Access to Science: The New Policy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 Light of Copyright Protection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15 UCLA J. L. & Tech., (2011). p.59.
[20] Jorge L. Contrera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Latency, Licensing, and Access, 53 Santa Clara Law Review. (2013). p.540.
[21] Jorge L. Contrera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Latency, Licensing, and Access, 53 Santa Clara Law Review. (2013). p.541.
[22] Eric Priest, Copyright and the Harvard Open Access Mandate, 1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2). p.13.
[23] Jorge L. Contreras, Data Sharing, Latency Variables, and Science Commons, 25 Berkeley Tech. L.J. (2010). p.1654.
[24] Author Rights: Using the SPARC Author Addendum to Secure Your Rights as the Author of a Journal Article, http://www.sparc.arl.org/resources/authors/addendum.
[25] Stuart M. Shieber, A Model Open-Access Policy, Harv. U. Libr. off. for Scholarly Comm. 2 (2010), http:// osc.hul.harvard.edu/sites/default/files/model-policy-annotated_0.pdf.
[26] Eric Priest, Copyright and the Harvard Open Access Mandate, 1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 Intellectual. (2012). p.1.
[27] 初景利. 國內外開放獲取的新發展[J]. 圖書館論壇,2009(6):85.
[28] Eric Priest, Copyright and the Harvard Open Access Mandate, 1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 Intellectual. (2012). p.5.
[29] 17 U. S. C. § 102(a) (2011).
[30] 17 U. S. C. § 204(a) (2011)
[31] Eric Priest, Copyright and the Harvard Open Access Mandate, 1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2). pp.73,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