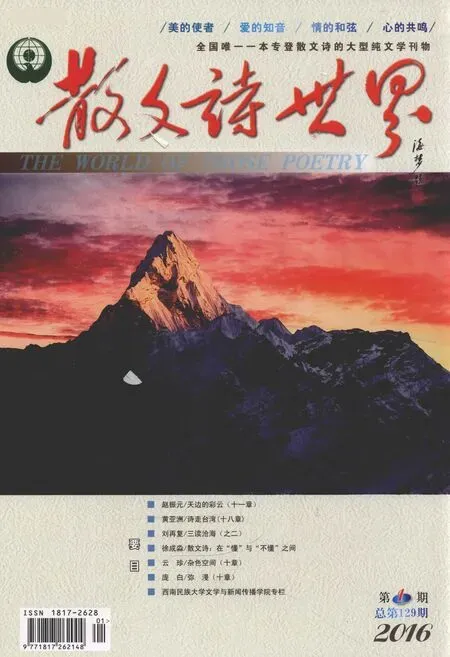在喀什河兩岸生成的哲思(四章)
新疆 王東江
?
在喀什河兩岸生成的哲思(四章)
新疆王東江
我多想變成喀什河里的一尾魚
陽光朗照喀什河的時候,我看見河水周身裹滿了錦緞。
我的臉被陽光照著,我感到了撫慰與溫暖;我的心被河水漾著,我感到了錦緞的柔滑和飄逸。
河水抖動錦緞的時候,錦緞也抖動我的身體。
我多像河底的一尾魚。我渴望成為那個族群里的一員。
陽光從黎明的夢里走來,喀什河從雪山的牽掛里走來,我從河水的柔情里走來。
走近喀什河,水里映著真實的我,岸上站著虛無的我——我的魂魄早被河水攝走了,那遠去的喧嘩正是我靈魂的呼救,我佯裝沒聽見。我知道,它是屬于喀什河的,我的身體不過是它的暫居地,河水歸不歸還,我都無所謂。一個把歸宿化入清澈和湛藍的人,是上天的垂愛和生命的升華。
此刻,我覺得,我的體內流動的不再是黏稠的血液,而是清冽的喀什河水。我的肉體也不是娩自母腹,而是打撈自喀什河。
我容忍我的叛逆,喀什河也容忍。因為我的靈魂早就皈依喀什河。
我確認,我的前生就是暢游在喀什河底的一尾魚。每當走在岸邊,我便感到錦緞裹身的柔滑和飄逸。
我和岸邊的胡楊林一起選擇堅守
喀什河水喂大了岸邊的胡楊林,一株株感恩的族群,以留守的方式,報答喀什河的養育。
Kosambi & Gokhale 1957: D.D. Kosambi & V.V. Gokhale, Vidyākara’s Subhāitaratnako?a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4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先以三千年的葳蕤,染綠河水的容顏,讓母親河永駐青春;再以三千年的站立,撐起河水的骨氣,讓母親河日夜奏響錚錚強音;最后以三千年的抗爭,護佑河水清的清白,讓母親河免受枯枝腐葉的玷污。人子的孝心,使一種植物的人格,升華為精神的巔峰。
我的身體也是喀什河水喂大的,我是這片胡楊林的近親。對喀什河,我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叛逆。我知道,我生命的根是借喀什河扎下的,離開岸邊的這塊土地,我將枯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不想陷入最慘淡的人生。
當人們紛紛把逃離故土作為一種時髦的生存方式時,我和岸邊的這片胡楊林一起選擇了固守。也許,在許多人眼里,我們是迂腐的。但我覺得,每種植物都有它適合扎根的土壤,人也一樣,固守和逃離,只是換了一種扎根方式,其意義,無非是使生命得以延續和繁衍。
當有些人把“適合的才是選擇的”作為遠離故鄉敷衍塞責的借口時,我沒有指責這是對故土的背叛。但我依然固執地認為堅守是對故土的尊重和敬仰,是感恩的最佳方式。
所以,我和岸邊的胡楊林一起選擇堅守。
喀什河岸邊的馬蓮草
與喀什河岸邊的泥土關系最為密切的,要數那一叢一叢匍匐在草原胸膛上的馬蓮草。它的根毫不留情地摳緊泥土,不放過一點一滴的營養源。岸邊草原的命運被它緊緊抓在手里。
那么多的羊啃過。那么多的牛嚙過。那么多的馬嚼過。馬蓮草沒喊痛,它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獻身這片草原。在草原里做一棵草,比在其他地方委身,更能體現做草的價值;在動物腸胃里消化,比在田埂上腐爛,更死得其所。人有人的歸途,草有草的使命。高貴與卑賤,偉大與微瑣,生命重意義而不重過程。一棵馬蓮草的人生,把一種價值觀詮釋的愈加完美。
岸邊的一棵胡楊和一棵馬蓮草都是喀什河的寵兒,生死三千年和一歲一枯榮殊途同歸。喀什河的幽夢籠罩胡楊林時候,也籠蓋著馬蓮草。手心手背,什么時候,喀什河都不厚此薄彼——這是一位母親對兒女的公正。因此,喀什河被兩岸蒼生稱作母親河,那是實至名歸。
在喀什河岸邊的草原上做一棵草是幸運的。
在喀什河岸邊的草原上做一只羊一頭牛或一匹馬是幸福的。
在喀什河岸邊的草原上做一個人是幸運加幸福的。
一滴雨的人生
喀什河上空的云一直藏有愿望,把雨滴播進河水,完成從想象一滴水到現實一滴水的嬗變。
九九歸一,葉落歸根,落入河水里的那部分雨滴,才算真正回家。
作為組成喀什河水最基本的微粒,一滴雨是幸運的——它在一個瞬間體驗了從個體弱勢到集體強勢的落差。轟鳴的濤聲有它參與的吶喊;激流漩渦有它制造的險象;沖破阻撓有它拼力的掙扎;浪花四濺有它跳躍的身影。現在,它有足夠的底氣和能力炫耀它是一條大水的子孫,它的終極目標就是參加一次沒有歸途的悲壯遠征。
但我從未認定落在喀什河岸邊胡楊林的雨滴就是不幸的,這些水通過另一種方式找到了歸家的途徑。它們巧妙地鉆進泥土,借助一條根系爬上胡楊樹干——這也是一條潺湲的小河,雖然不夠波瀾壯闊,但亙古作為流動的形式存在著。由此,一滴雨,在一條樹干上成全了自己的人生。
每個人都是一滴雨,作為自由落體來到塵世,無論匯入人流如潮的城市大河,還是注入三五一行的鄉村小溪。只要存在,就有體現人生價值的籌碼。
一滴雨和一個人,一條河和一道溪。流動著,便是活著;奮斗著,便是體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