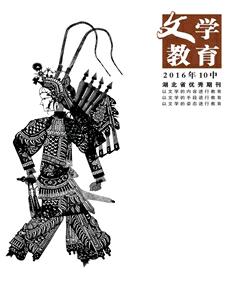解讀翻譯等值理論
梁凱凱
內容摘要:等值是西方翻譯理論中的核心概念。自從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許多翻譯理論家均把“等值”這一概念作為自己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并對其進行詳盡的論述。本文通過分析等值理論的理論基礎,主要代表人物和內容,概述等3A值理論的發展過程,指出其對原文和譯文互譯過程中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并嘗試性探究等值理論在翻譯實踐中的局限性。
關鍵詞:等值理論 對等 翻譯理論 奈達 功能對等
一.等值理論的理論基礎
“對等”一詞,源出于數學。作為數學專業術語,意指一種絕對對稱和平等的關系。而在《牛津英語詞典》里,它是指“具有相似性的事物”或“基本相同”的模糊意義。那么翻譯理論中引進的“對等”概念,是借用它作為數學術語時的絕對意義還是它作為普通語言詞匯時的模糊意義呢?
根據西方翻譯理論史,“對等”的翻譯思想是在18世紀中葉開始顯膝端倪并一直持續到19世紀的。那段時間出現的對等觀,大多是針對翻譯藝術和技巧而論的。翻譯對等論得以突破藝術的規范而成為具有科學性質的理論話語并得到廣泛的探討,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現象了。[10]
翻譯等值理論在西方雖然可以說是現代語言學派翻譯理論研究的成果,但其歷史源頭早在18世紀就已出現。1789年,坎貝爾把詞義與用詞目的聯系起來進行探討,有人認為這就是“靈活對等”等理論的先導。[9]他和泰特勒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三個原則,即:(1)譯作完全復制出原作的思想內容;(2)譯作盡量移植原作的風格和手法;(3)譯作應和原作一樣流暢。這事實上已經涉及到了等值論。后來,蘇聯文學家斯米爾諾夫于1934年更進一步提出了“等同翻譯”的概念:“譯文要能夠傳達作者的全部意圖,即作者在對讀者產生一定的思想感情上的藝術作用這個意義上的全部意圖,而且要盡可能地保全作者所運用的形象、色彩、節奏等等全部表達手段”。[11]
作者對讀者的意圖也就是作品對讀者的作用,即作品的效果,而所用的各種手段也就是原作“值”的一部分。這一提法基本上將等值、等效都涉及到了,而且論述比較明確,已初具現代等值論的雛形。[6]
二.等值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內容
等值作為西方現代翻譯理論中的一個概念,是由里烏在1953年首先提出的。自此,它總是與翻譯的實質、可譯性、翻譯單位、翻譯評估等這些翻譯理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的探討緊緊聯系在一起。
卡特福德提出了篇章等值概念。他在界定翻譯的性質時說:“翻譯可作如下定義:一種語言(原語)的篇章材料用與其等值的另一種語言(譯語)的篇章材料來替換。”[1]他的等值概念從某個側面反映出翻譯的本質在于確立原語和譯語的等值關系,而對這種等值關系的把握應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
對翻譯等值概念做出較為全面論述,提出見解且在學界產生較深影響的要推奈達。早在1964年,他在《翻譯科學探索》中就提出了形式等值和動態等值兩個概念。而在《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1986)里,奈達又用功能等值概念取代動態等值提法,按作者自己的說法,此舉是為了“突出翻譯的交際功能并且避免誤解。”可見,奈達對翻譯等值概念的探討不是僅僅停留在語義層面上,而是更注意對翻譯中語用和交際等因素的考慮,如強調譯文讀者的接受與反應等。[5]
奈達還指出要注意語言的通暢自然,“自然”不僅指語言,還指在文化上、思維習慣上行得通,能夠被譯語讀者所接受。例如:“她認為離開了辦公大樓,離開了政工部門,就是離開了政治,就聽不到那些閑言碎語了,誰知是離開了咸菜缸又跳進了蘿卜窖”。“離開了咸菜缸又跳進了蘿卜窖”是漢語文化中特有的表達方式,形容每況愈下,越來越糟。若將其直譯成“to jump out of the pickles vat into radish cellar”,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英語讀者就會感到不知所云,這樣的譯文也不能傳達原文的準確含義。[8]
三.等值理論的發展過程
縱觀等值理論的發展,可初步歸納出以下三個特點:
1.等值理論的發展過程是翻譯研究與各門學科相結合的過程,是從經驗總結到科學分析的過程。等值理論的發展,從斯米爾諾夫籠統的等同概念到奠定翻譯語言學基礎的費道羅夫的等值定義,從巴爾胡達羅夫建立在語義學基礎上的等值觀到與交際學、語用學密不可分的動態等值,再到科米薩羅夫的等值模式,形象地演繹了學科發展的時代特征。
2.現代等值理論無論是“動態等值”、“語用等值”,還是“交際等值”,都是把語言的功能,而不是把語言的形式特征放在首位。現代語言學從靜態描寫語言的內在特征轉變到揭示語言與現實的關系,解釋語言的交際功能,有力地推動了翻譯研究的發展。
3.立體的等值模式是目前最實用的模式。20世紀后半期,隨著生產、科技的發展,國際交往的密切,翻譯活動迅猛發展,個別經驗之談和主觀分析都難以用來指導如此面廣、量大的實踐活動,這就需要我們對翻譯等值有一定的規范以對其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立體等值模式無疑最接近這一要求。[7]
四.等值理論的不足之處
等值理論的不足和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等值論的倡導者所從事的大多是西方語言之間的互譯工作,他們所說的等值理論都是從這些語言的共性中推導出來的。卡特福德論及等值論的時候,舉的例子大多是英法互譯的例句;奈達舉的多是希臘語和英語互譯的例子。西方語言都屬于印歐語系,相互間有可能建立不同程度的等值,而漢語與西方語言間互譯要建立嚴格的等值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西方人喜歡按主—謂—賓模式思考,而中國人傾向按漢字偏旁去思考。
在文學翻譯中,等值論的局限性就更明顯了。文學翻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譯者不僅要譯出原作的內容,而且要譯出原作的形式,有時還要注意原作的言外之意。像對《紅樓夢》的翻譯,因為它是一篇巨著,所以更是難譯,例如:“怡紅院”譯為“Green Court”,將“怡紅公子”譯為“Green boy”。[8]
與中國譯論相比,等效論的另一不足之處是對原文文本中審美信息的傳遞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也是有的中國譯論家對等效原則持否定態度的一大原因。例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采薇》)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lean near;
I come back at last, snow falls fast.(屠岸譯)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a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許淵沖譯)
原詩看似平淡,其味卻深,真正達到了“字字無華,字字有華”的地步,被譽為詩三百中的絕唱。相比而言,屠譯雖然達到了奈達所言的意義、文體對等,但較之原詩,味似太淡;許譯雖大膽作了變動,表面意思似乎不等,卻把老戰士回家的復雜心情表達的淋漓盡致。[8]
斯乃爾·霍恩貝指出:“等值不適合用作翻譯理論中的一個基本概念:術語equivalence,除了本身含義含糊不清外,還給人一種各種語言之間對稱的錯覺,而這種對稱除了那種含糊的近似度外是幾乎不存在的,因此,它歪曲了翻譯中的基本問題。”
紐馬克則認為:“其它諸如翻譯單位、翻譯等值、翻譯恒值等之類的論題,我認為也應當擯棄—它們要么太理論化,要么隨機性太強。”[3]
貝克在其代表作《換種說法—翻譯教科書》的導言中說:“本書采用術語equivalence是為了方便起見—因為絕大多數譯者已經習慣這個術語,而并非因為它有任何理論地位。術語equivalence在這里的用法還有如下限制條件:雖然等值在某種程度上通常能夠實現,卻受到各種各樣語言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此總是相對的。”[2]
綜上所述,翻譯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就可以解決得事情。正如紐馬克所言,對等僅僅是翻譯中最理想的狀態,而不是任何翻譯都必須實現的目標。“‘equivalent effectis the desirable result, rather than the aim of any translation[4]”。因此,把等效原則作為衡量一切翻譯的唯一標準是站不住腳的。
參考文獻
[1]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Baker,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in Translation)[M].New York:Routledge,1992.
[3]Newmark,P.ApproachesTo Translation[M],Oxford: Pergamon,1981.
[4]Newmark,Peter. 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Prentice Hall,1988.
[5]Nida,E.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
[6]韓滿子.翻譯等值論探幽[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2):68.
[7]華莉.對翻譯等值理論的再思考[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0(4):80.
[8]馬會娟.對奈達的等效翻譯理論的再思考[J].外語學刊,1999(3):77-79.
[9]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91:172-273.
[10]楊柳.西方翻譯對等論在中國的接受效果[J].中國翻譯,2006(3):3.
[11]張今.文學翻譯原理[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7:6-14.
(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新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