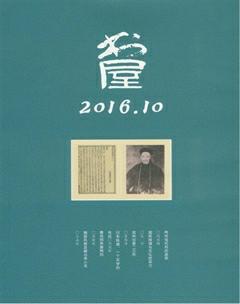苦難世界的一絲幽光
趙一瑾
文學世界里作家、詩人幾乎從未停止對自由的暢想和思考。追溯到幾千年前的先秦社會,莊子以《逍遙游》發聲,向世人展示心無所待、肆意馳騁的波瀾壯闊的精神自由世界。回到工業文明,物質文明極度發達的當代社會,人的身體和靈魂被無數的外物所累,人們開始懷念更加純凈的自由。可是社會進步的腳步不能停歇,社會固有的秩序不能被打破,人生而為人,免不了要在社會里按照既定的秩序生活。真實而苦難的生活似乎警告著世人“烏托邦”的破滅和無望,也呼喚著人們向內尋求“烏托邦”。正如哲學家薩特所說:“你從來沒有失去過自由,你一直是自由的,你感到不自由,是因為你自由的選擇了不自由。”
最早為我們描畫“烏托邦”的哲學家當屬莊子。莊子在《逍遙游》的開篇就大手筆為我們鋪張了一幅鯤化為鵬、大鵬展翅扶搖直上的壯闊畫卷。“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大鵬的翅膀猶如天邊的云,海動風起,他便乘風破浪飛向南方的盡頭。大鵬盡情遨游天地之間,是何等的逍遙自在。可我們終究是凡人,沒有翅膀,不能如大鵬一樣自在飛翔。莊子提倡的也絕非肉體無約束這般的簡單膚淺,而是擺脫了名利與欲望枷鎖的“無所待”的精神自由,是“無己”、“無功”和“無名”的無牽無掛和無所羈絆。莊子提倡“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之外”的逍遙狀態,贊美絕對的精神自由和獨立人格,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烏托邦”藍圖。人離開紛擾的世間追求絕對的精神獨立,莊子更在此基礎上加入了“齊物”的理論。在絕對自由的精神面前,一切似乎都平等沒有差別了。物與我、是與非、善與惡都不能夠成為擾亂心的外物。劉笑敢總結莊子的思想就是“‘游乎無人之野(《山木》)、‘無何有之鄉(《逍遙游》)、又說要‘游乎四海之外(《逍遙游》)、‘游乎塵垢之外(《齊物論》)。”無為而無不為,逍遙天地間。這就是“烏托邦”的至高境界。
可是莊子描繪的境界畢竟只是理想境界,人非鯤鵬,處于世中,又有幾人能做到真正的齊物和逍遙。包括莊子身處亂世之時創作出來的《逍遙游》,也是向外尋求自由美好的“烏托邦”失敗而催生出向內逍遙的曠世經典。莊子所恣意的世界不是客觀的外在世界,而是自我的精神世界,是沒有摻雜任何現實因素的純粹的自由。回歸到現實的語境之中,“烏托邦”不能擺脫現實的影響因素。社會物質文明飛速發展,其對人心靈的戕害也成為了許多文人所關注的一大問題。林語堂在《奇島》里建立一個中西語境融合下的世外桃源——“奇島”,來表達他對現代物質工業文明下人類該何去何從的思考。小說中,尤瑞黛一不小心闖入了勞思和阿山諾波利斯合力創建的一個新的文明之地。在這個小島上,每個人的意愿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人平等快樂,物質文明和精神世界不存在沖突和相互污染,猶如一片天堂。小島上的人甚至去除了衣服和鞋子的束縛,可以赤身裸體地行動,個體得到極大的釋放和尊重。小島上猶如古代希臘雅典時代一樣,追求藝術,追求哲思,追求個人自由,追求美。勞思是這個小島上的精神領袖,也是林語堂本人的代言人;林語堂的想法都通過他的嘴展現給世人。勞思在書中并不否定進步,他認為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是必然的,也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好的進步不是飛速的發展下,人來不及思考自己何去何從,從而導致精神世界空白和迷惘的狀態。“由于工業化,人類改變了很多……人性不再完整了,有些東西失落了。人類原始而豐盈的人性被禁錮、壓榨、脫水,在角落里皺縮成一團。”
《奇島》點明了人類在物質膨脹下的紙醉金迷并不是真正的“烏托邦”,物質的繁榮并沒有換來人類更大的自由;相反的,人類卻在發展中不斷倒退到遠離“烏托邦”的狀態。林語堂試圖啟發世人,每個人都應該停下腳步想一想自己的目的和方向,想一想自己靈魂的棲身之所。林語堂繼承了莊子《逍遙游》重視人的精神自由和獨立的一面,同時更為實際地認為人和物質并無法做到真正的分離。其實《奇島》中的人們雖然離開了所謂的大眾社會,可是他們并沒有脫離物質。相反的,勞思為了讓人們精神富足,第一要義就是也在物質上極大地滿足島民。島上甚至還在不斷地進行科學實驗,為這個島的舒適度增添色彩。縱然這個島上社會似乎試圖為每一個居民創造出一片“烏托邦”的樂土,盡可能地尊重個體的意愿和自由,但離《逍遙游》的境界也是差出十萬八千里。真正的“烏托邦”自然包括個人欲望的實現,但更為重要的還是精神世界的自由和豐沛。
若說《逍遙游》是莊子在先秦紛亂的戰火中綻放出來的一朵閃耀的思想奇葩,那么《奇島》也是林語堂在戰爭環境下對于未來社會的一次“桃源”想象。他指明個體被社會發展摧殘的自我空間和空虛心靈,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探尋個體“烏托邦”存在的條件,就必須直面社會發展帶來的問題。林語堂的“烏托邦”揭示出了人的絕對自由和社會發展的不可調和性,也突出了莊子式的個人烏托邦過于浪漫主義化。
提及“烏托邦”,絕對自由的賦予可能是一個必要條件。可是絕對自由的條件下,人沒有了任何藩籬的束縛,不斷地探索道德的邊界、人性的邊界、自由的邊界。這樣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會滋養人性之中的惡之花,醞釀出極度的惡。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的作品《發條橙》也被歸入“反烏托邦”小說之列:“由于小說的暴力與反暴力主題和它對現實的冷靜而悲觀的分析,它被歸為‘反烏托邦小說,并被稱作對當代世界的夢魘式預見。”
小說的第一部就向我們展示了亞歷克斯尋求自由過程中的罪孽深重。一個放蕩不羈的十五歲少年每天無惡不作,卻總是逃脫法律的懲罰和制裁。可是后來一次殺人罪行的敗露,讓亞歷克斯從極度的自由轉變到極度不自由的境地。他成為試驗的用品,被迫注射藥物之后觀看各類暴力影片,在藥物的作用下產生嘔吐感,形成條件反射之后變成一個所謂的“善人”。每當他再度浮現作惡的念頭,他就會產生極度的嘔吐感,這種不適感會阻止他的惡念。這引發人們對于道德選擇權的思考,善和惡是個人的選擇,沒有選擇的善難道不也是一種極大的惡?人之所以渴望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渴望自主選擇的權利。正如《發條橙》引言所說:“人在定義中就被賦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來選擇善惡。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惡的人,就成了發條橙……徹底善與徹底惡一樣沒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選擇權。”所以,絕對自由其實就是不自由,“烏托邦”的實現絕不是荒誕的毫無約束,而是有序的自主選擇。
從另一個側面來看,《發條橙》中所展現的社會是對“烏托邦”的極端摧殘。一個人無論選擇是善是惡,都是個體的自主選擇。沒有選擇余地而出現的善本來就是惡,沒有選擇權的所謂自由也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以賽亞·柏林曾經探討過“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這個社會總是在鼓吹積極自由的,鼓勵人們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更可貴的是對人消極自由的尊重。以賽亞·柏林將“消極自由”描述為“個人自由一定要有一個最小范圍,它是無論如何都不可侵犯的;假如給越了界,人就會感到自己身處的范圍,狹窄得甚至連自己的天賦能力也無法體現最起碼的成長;而只有體現了,才讓他可以追求(甚至只是立志去追求)人類認為是好的、正確的、神圣的各種目標”。換句話說,人既有選擇做什么的自由,也應該允許選擇不做什么的自由,“消極自由”“意味著不被別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領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大”。在《發條橙》里,亞歷克斯的消極自由就被剝奪了。他道德選擇權的喪失就是對他消極自由的否定,他成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發條橙”。
《發條橙》的故事告訴我們,沒有尺度的積極自由并不是完美的“烏托邦”,而是強大的荒誕和虛空。它會把人引向一個自我放縱的極端,催生出邪惡的花蕾。約束并不是不自由,而是讓你的積極自由可以有序地健康地得到實現和發揮。另一方面,它所提出的道德選擇權的問題其實可以引申到人的消極自由的權益。在小說中,亞歷克斯從未選擇向善,他骨子里都是在渴望暴力和放縱。自由并不是鼓勵惡的張揚,而是鼓勵人們應該被賦予“可以不去做什么”的權利。縱然全世界都選擇走這一條路,個體也應該擁有坦然選擇另一條路的自由。
劉劍梅老師在《莊子的現代命運》一書中提及《靈山》為“內心的自由象征”和“現代莊子的凱旋”。之前我們所談及的問題都是外界賦予個體的自由,比如物質文明世界的自由,包括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本身就是相對于外界和自我的關系。但是真正的自由其實是來自自我,“烏托邦”或許不在什么遙遠的地方,就在你的內心,等待你去發現。
《靈山》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個身患癌癥的主人公在中國的土地上上下求索,想要找到傳說中的“靈山”。他的這段旅程看到了很多沒有被現代文明所侵染的民族文化和民間人物,看到了更加純粹的自然,也遇到了很多奇女子。小說甚至沒有一個具體的名字,全部都是人稱代詞完成全書。“你”、“我”、“他”其實都是一個主人公的各種側面,是這個主人公不斷向內心走去的不同側面的展現。主人公在不斷尋找靈山,可一切正如這部小說展現給讀者的感覺一樣,玄妙、朦朧帶著一點點小小的混亂。高行健的《靈山》在開篇幾章就向我們解密了“靈山”的真正含義:“靈山,靈魂的靈,山水的山。”尋找靈山的過程就是探索靈魂的過程,整個過程就是精神漫游的歷程。那么,主人公是否真的找到“靈山”這個問題,高行健給出了一個看似驢唇不對馬嘴的回答:青蛙眼里的上帝。換而言之,高行健是在啟發讀者“靈山”不在他處,就在你內心里;你以為這世界上沒有屬于你的“烏托邦”,其實這世界處處都是“烏托邦”。按照高行健《靈山》的思路,真正的“烏托邦”也應該不在他處,就在每一個個體的內心中。哲學家薩特認為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不自由是個體自我的選擇,而非真正來自于外界。真正的自由不是外界給予的,而是自己給予自己的。劉再復先生在《高行健論》提出了他對于“靈山”的理解:“靈山原來就是心中的那點幽光。靈山大得如同宇宙,也小的如同心中的一點幽光,人的一切都是被這點不熄的幽光所決定的。人生最難的不是別的,恰恰是在無數艱難困苦的打擊中仍然守住這點幽光,這點不被世俗功利所玷污的良知的光明和生命的意識。有了這點幽光,就有了靈山。”如果說“靈山”就是“烏托邦”的象征,那么真正拯救人生的其實就是劉再復先生筆下所謂的“那點幽光”。換言之,真正的自由或許已經超脫了我們之前談的所謂積極自由或者消極自由,而是內心的一方凈土。即使身在鬧市,即使有枷鎖有束縛,但你內心的這點幽光是永遠的依靠。守得住這點幽光,也就守住了靈魂深處的自由,也就永遠不會喪失你的“烏托邦”。或許這才是“烏托邦”的真諦,充滿了拯救的禪意,現實卻又不失浪漫主義。正如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一段飽含深情的闡述:“所謂拯救,并不是祈求一個來世的天國,而是懷著深摯的愛心在世界上受苦受難。”超脫痛苦的人世是不存在的,脫離現實的烏托邦也是不存在的,真正的超脫者是懂得如何在俗世中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烏托邦”的找尋是一個由外向內的過程。無論是在物質文明社會里找尋自由還是回歸精神世界尋覓靈山都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意義和人文意義的。林語堂的《奇島》則傾向于探尋“烏托邦”與高速發展的社會之間的關系。在林語堂的眼中,社會發展帶來的泡沫一般的現實已經侵蝕了人的生活甚至精神世界。他認為這樣的發展并不是讓人更加自由,而是更加不自由。所以,正確的看待社會發展和人類的心靈豐富是林語堂關注的話題。西方文學作品《發條橙》是探討絕對自由與相對自由以及自由與選擇之間的問題。自由猶如一汪水,有容器的限定才能更好的讓水存在。如果毫無邊際,水無所依附自然也就無法存在。有約束的自由才不荒誕,無約束的自由只能導向罪惡的深淵。他所探討的道德選擇權也與以賽亞柏林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理論相呼應,強調消極自由,也就是“放棄”的權利的重要性。而高行健的靈山是站在一個比前二者都更加超脫的角度來拷問自由究竟在何方。前兩者更加傾向于將“烏托邦”的建立依附于外界環境的改變和寬容,而《靈山》直接引入心靈世界,啟發世人真正的“烏托邦”就藏在你的內心深處。猶如一片早已建立好的“桃花源”,你只要能夠守得住,你就擁有你的“烏托邦”。從高行健的角度,《逍遙游》就不只是莊子帶給世人的一個美好的夢。“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之外”的逍遙境界即可在心間完成。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也有一千個向往的個體“烏托邦”。無論是在外界還是內心,苦難世界的一點幽光都是人們苦苦渴求的,上下求索的“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