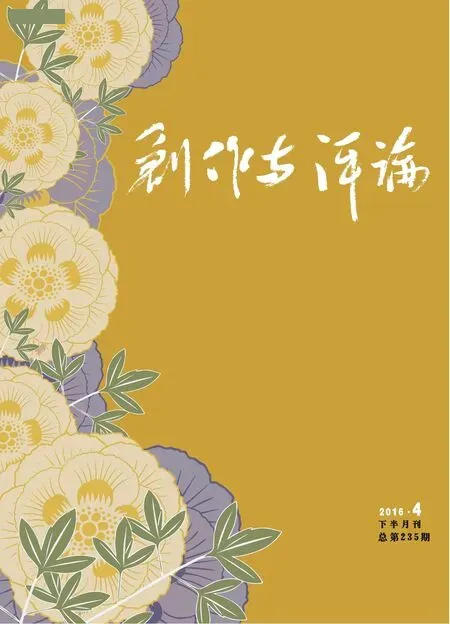1990年代以來臺(tái)灣散文的海洋書寫
○王泉
?
1990年代以來臺(tái)灣散文的海洋書寫
○王泉
臺(tái)灣島形似一枚樹葉,漂浮在太平洋上,因臺(tái)灣海峽的阻隔,臺(tái)灣成為一個(gè)名副其實(shí)的孤島。海成為其主要的自然地理景觀,讓這里的人們浸染在海上升明月的空曠之美中,文人更是信手拈來,到達(dá)了“物與神游”①的境界。1990年代以來,臺(tái)灣海洋散文的勃興,預(yù)示了海洋時(shí)代的到來。蔣勛、林清玄、楊牧、廖鴻基、簡(jiǎn)媜、席慕蓉等作家的散文在書寫海洋時(shí)把自己的人生體驗(yàn)融入博大的海洋意識(shí)之中,形成了開闔自如的藝術(shù)世界。
一、書寫海洋景觀與傳統(tǒng)文化
“柔軟的水承天載地的偉力,富于哲理意味,其傾注于大壑之中造成海洋,海洋生成的神話的象征意義,在先民的生活中反復(fù)運(yùn)用,同陸地神話一樣,升華出豐富的哲學(xué)思想,分別成為儒道釋諸學(xué)說體系的構(gòu)成部分。”②海洋在有形與無形之中給予人類想象的空間,因此形成了海洋文化的多樣性。臺(tái)灣作家身處臺(tái)灣島,自覺把周圍的海洋當(dāng)成人生成長(zhǎng)的坐標(biāo),在感悟海洋文化中認(rèn)同傳統(tǒng)文化。
美學(xué)家蔣勛在詩(shī)歌《愿》中這樣表達(dá)了自己對(duì)于海的感悟:“如果你是島嶼/我愿是懷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張起了船帆/我便是輕輕吹動(dòng)的海浪。”③海洋的博大與無私奉獻(xiàn)已經(jīng)沁入到他的血脈之中,成為人生的航標(biāo)。他的散文《望安即事》寫海中干旱的小島,有對(duì)古宅被冷落的唏噓,更有對(duì)求偶云雀的特技表演的感嘆,對(duì)生命奇跡的發(fā)現(xiàn),也是對(duì)美的發(fā)現(xiàn)。
對(duì)于海,林清玄有著獨(dú)特的體悟:“我們看待海的事物——包括海的本身、海流、海浪、礁石、貝殼、珊瑚,乃至海邊的一粒沙——重要的不是知道它歷經(jīng)多少時(shí)間,而是能否在其中聽到一些海的消息。”④他把從海邊帶回來的珊瑚礁養(yǎng)在淡水里,結(jié)果長(zhǎng)出了水母。即使后來水母死了,但能見到海洋的石頭復(fù)活的奇跡,也算一段因緣。他試圖告訴我們:世界上任何東西,只要存在過,就有機(jī)會(huì)重發(fā)光芒。作家借水母的自生自滅,道出了人生無常、隨遇而安的佛家思想。
楊牧的《設(shè)定一個(gè)起點(diǎn)》從不同的角度看海洋,給予海洋時(shí)空意義上的觀照。“現(xiàn)在和過去重疊,海水融為一體,潮汐隨月陰晴起落,發(fā)出的石子散布灘上,累積,向前無限延長(zhǎng);風(fēng)從四方吹到,起點(diǎn)和終點(diǎn)同時(shí)存在于我自己的心,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超越了航海人指北針的限定。”⑤“潮汐”“石子”和“風(fēng)”與海洋時(shí)刻相伴,自我的想象也在這一空間中得到了無限膨脹。海洋不只是外在的存在,內(nèi)心的真實(shí)跨越了時(shí)空的限制,人生便以海洋為參照物,獲得了自由的發(fā)展。
小野的《海星的故鄉(xiāng)》中澎湖的西衛(wèi)海灘上成群結(jié)隊(duì)的海星給予人類生命的啟迪。20多年間的臺(tái)灣人“就像潮間帶的動(dòng)物,用自己的肉足或螺殼存活下來”。⑥無論世事如何變化,臺(tái)灣人總能從時(shí)代的潮起潮落中找到自己的落腳點(diǎn),讓生命之火延傳。因此,這里的“海星”既是大自然本色的生命,又象征著臺(tái)灣人自強(qiáng)不息奮斗的軌跡。李鼎的《冬天要去夏天去過的地方》寫在小島蘭嶼的冒險(xiǎn)經(jīng)歷,在暴風(fēng)雨中走進(jìn)山洞,“聽見海浪用一種安靜的方式在周圍環(huán)繞,更讓我全身舒緩下來的是,我聽見自己身體里面的心跳,在大自然產(chǎn)生的洞中,有著無法想象的巨大共鳴。”⑦“空”并非無,而是讓人無法滿足的自然之力的誘惑。大自然是人類最好的老師,它告訴了人存在的空間,并讓人在充分釋放自我中獲得自由。
李崗的《萬里漁港》寫海邊小漁村的富足及當(dāng)年拍電影《條子阿不拉》的熱鬧,流露出懷舊情緒。李明相的《我的柴山秘密基地》則用流浪者的心態(tài)去尋找少為人知的悠閑。無邊無際的海洋與夕陽(yáng)的余暉交會(huì)出動(dòng)人的景色,讓讀者陶醉于自然美景中無法自拔。褚士瑩的《東嶼坪——臺(tái)灣的復(fù)活島》,突出了在美麗與蕭條的奇異組合的環(huán)境中,人與自然共生的哲學(xué)意蘊(yùn)。這契合了佛家“眾生平等”的理念,表現(xiàn)了對(duì)大自然的敬畏。
廖鴻基的海洋散文在臺(tái)灣別具一格,這與他的職業(yè)密不可分。“他以中年之身退出政界返回故鄉(xiāng)當(dāng)漁民,與漁民們一起出海捕魚,是寄托了人生極高的理想。”⑧他從1990年代至今已創(chuàng)作出版了近百萬字的散文作品。他在新世紀(jì)創(chuàng)作的《領(lǐng)土出航》描寫了“單調(diào)、清冷、寂寞”的船員生活。這不是一部簡(jiǎn)單的航海志,而是以47天航程中的故事和個(gè)人潛意識(shí)中的隱痛折射出航海人心中的夢(mèng)想,帶給讀者不一樣的體驗(yàn)。在他的筆下,不停變幻的海洋環(huán)境,給人不一樣的審美體驗(yàn)。“亞丁灣,如鑲進(jìn)陸塊的一只漏斗。航入灣里,仿如跨進(jìn)陸地門檻:那啜泣嚎嘯的海上風(fēng)雨,那與風(fēng)作浪撼搖船只的手中,都被灣口那道無形的門扉攔擋在外。”⑨海洋與陸地的聯(lián)合,創(chuàng)造出亞丁灣的獨(dú)特美,也成就了航運(yùn)的奇跡,自然的美與航海文明組合出人生的啟示錄。有評(píng)論者認(rèn)為:“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廖鴻基再次提出了‘海運(yùn)’——如血脈的流通作為島嶼生機(jī)之啟示:島嶼所意味的絕不僅是土地本身,而是一方蘊(yùn)含流動(dòng)生機(jī)的領(lǐng)土/夢(mèng)土,‘海運(yùn)’所踐履的是我們最為深情的‘領(lǐng)土’之夢(mèng),于是,以‘領(lǐng)土’之名,‘海運(yùn)’啟程。”⑩
海上航行離不開漂泊之苦,《領(lǐng)土出航》把航海人在時(shí)間中的煎熬之苦展示在讀者面前:“一旦離岸,失去節(jié)拍的日子將無限延伸回頭的距離,讓自己成為一只背離花蕊的蜜蜂,再如何擅飛的翅膀,再熱烈的胸膛,伸得再長(zhǎng)的手臂,艦尖孜孜犁浪如在切割,船槳輕易地便絞斷了所有和陸地的牽連。一旦離岸,時(shí)間和距離已無法估算。”?這樣的漂泊是對(duì)意志的考驗(yàn),在對(duì)時(shí)空的思考中凸顯生存之道。很顯然,這不同于無名氏在《海艷》和《金色的蛇夜》中的海洋書寫。無名氏著眼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及人性的復(fù)雜多變,而廖鴻基書寫的是人在海洋面前的命運(yùn)。在無名氏的筆下,海顯得神秘而多情。“有時(shí)候,人與人的關(guān)系,并不像鐵鏈連著鐵鏈,深密聯(lián)系;常常的,那倒似北極黑暗海上的碎冰塊,狂風(fēng)沖過,冰塊碰在一起了,新風(fēng)新浪卷來,黑暗中,冰塊又離開了。一切是斬絕、冷酷、黑暗無情。”?黑暗中的“冰塊”象征的是人際關(guān)系的冷漠和生活中突然而至的厄運(yùn)。無名氏以海況寫出了世事變遷中的人情冷暖,在愛與恨、聚與散的矛盾沖突中表現(xiàn)出浪漫的情思。而廖鴻基以客觀寫實(shí)之筆書寫海員的生活,但沒有流水賬似的枯燥乏味。他從細(xì)節(jié)出發(fā),闡釋著“海味”人生的境界。
他在紅海上尋找紅海之所以“紅”的原因,感覺到了窮途末路之時(shí),才解開了對(duì)“紅”的困惑。“兩岸黃土山丘環(huán)抱,海底、海面平整空曠。隱約,岸線有些黃褐色山影倒映在藍(lán)色的灣里,忽然,明白了!”?這才是航海者的發(fā)現(xiàn),無不透露出人生的境界之美。人的一生光陰在不經(jīng)意間流逝,尋找與發(fā)現(xiàn)的美妙往往在身心疲憊之時(shí)。“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王國(guó)維借用辛棄疾之語(yǔ)道出了“無我之境”的美妙。這在廖鴻基的散文中得到了演繹。那便是,人與海洋在混沌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洋的廣闊無垠象征著人的冥想的無邊無際,人類的海上冒險(xiǎn)則給海洋平添了人文的景觀。海洋賦予人類生命的源泉,人類的活動(dòng)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海洋文明,世界地理的大發(fā)現(xiàn)正是航海文明的成果。
他這樣寫上岸后的感覺:“刻意放空自己,放棄感覺,什么都無所謂。街燈于是朦朧、行人無魂、車影漂浮…然而,思想和回憶交錯(cuò)如潮汐漲退,一旦動(dòng)念,兩個(gè)世界立刻又壁壘分明。”?這里刻畫的是航海人在長(zhǎng)期漂泊后無法“上岸”的感覺,一種恍若隔世的深切體會(huì)。想當(dāng)初,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正是緣于他對(duì)海洋和外面世界的心馳神往。可見,好奇心激發(fā)了人類走向海洋的夢(mèng)想,也促進(jìn)了世界文化的交流。
總的來看,《領(lǐng)土出航》延續(xù)了廖鴻基自己在《鯨生鯨世》《來自深海》《漂島——一趟大洋記述》等作品的紀(jì)實(shí)風(fēng)格與自傳色彩,把人生的歷練與海洋書寫融合在一起,體現(xiàn)出海洋人樂觀向上與豁達(dá)的胸懷,豐富了海洋書寫的生態(tài)主義內(nèi)涵。這樣的書寫可以說開辟了臺(tái)灣當(dāng)代海洋散文的寫實(shí)風(fēng)格,也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散文的發(fā)展提供了參照。他的作品不同于《魯濱孫漂流記》《老人與海》等西方文學(xué)靠獵奇來取悅讀者,而是貼近海洋生活的實(shí)際,以散點(diǎn)透視揭示了人與海洋命運(yùn)的息息相關(guān)。也許有人會(huì)擔(dān)心這樣的散文由于過于實(shí)在會(huì)使讀者放棄閱讀,其實(shí)不然。隨著全球化的推進(jìn),海洋面臨的危機(jī)愈來愈明顯,人類生產(chǎn)活動(dòng)對(duì)海洋的污染加劇。發(fā)達(dá)的科技在創(chuàng)造生產(chǎn)力的同時(shí),也在將大自然的資源消耗殆盡,這一不容忽視的事實(shí)呼喚作家高度關(guān)注海洋。通過海洋紀(jì)實(shí)的書寫,能夠讓生態(tài)意識(shí)深入人心,使大眾從昔日試圖靠對(duì)海洋的無盡掠奪來實(shí)現(xiàn)自身自由的幻想中解放出來,實(shí)現(xiàn)與海洋的和平相處。
海洋的自然天成,使人產(chǎn)生了望洋興嘆之悟;海洋的無私奉獻(xiàn),則催人警醒。1990年代以來的臺(tái)灣散文對(duì)海洋之美的描摹,并非為了滿足大眾旅游的需要,而是從內(nèi)心出發(fā)、從生活實(shí)踐出發(fā)的一種藝術(shù)真實(shí)。這樣的散文往往以小見大,是作家人生理想的投影。同時(shí),他們的海洋書寫傳承了傳統(tǒng)文化追求和諧美的理念,恢復(fù)了長(zhǎng)期以來被人類陸地意識(shí)所遮蔽的海洋視域。這樣的書寫有利于堅(jiān)定全球化時(shí)代人類對(duì)于海洋文化的自信。長(zhǎng)期以來,以人類自我為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嚴(yán)重制約了人類向海洋邁進(jìn)的進(jìn)程。隨著生態(tài)主義意識(shí)在全球的迅猛崛起,人們開始把眼光轉(zhuǎn)向海洋。這一方面是無奈的選擇,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人類的覺醒。
二、海洋書寫中的生命體驗(yàn)與家園意識(shí)
女性天性溫柔,在社會(huì)的歷史進(jìn)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女性的成長(zhǎng)又無不在生命的潮汐中起伏不定,正如海洋的神秘莫測(cè)。在以簡(jiǎn)媜和席慕蓉為代表的一些女作家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海洋的原型意義得到了升華。
簡(jiǎn)媜的散文集《天涯海角》以海洋為背景,書寫家族的歷史、臺(tái)灣的歷史及個(gè)人的奇遇,再現(xiàn)了時(shí)代變遷中的女性對(duì)于童年和故鄉(xiāng)的留戀之情。《浪子:獻(xiàn)給先驅(qū)》追尋簡(jiǎn)氏家族從大陸遷徙到臺(tái)灣的歷程,將迷霧一層層撥開。“仿佛一只蜘蛛回到昔年海邊,尋找當(dāng)年被風(fēng)吹落大海的那張網(wǎng)般困難,我探求先祖軌跡,只得到五字訣。”?這是時(shí)代的宿命,還是命運(yùn)使然?“五字訣”代表家族的秘密,卻無法鎖定時(shí)代瞬息萬變的軌跡。海洋才是通向家族的密碼,作家借海邊的“網(wǎng)”,象征人生的機(jī)緣與挑戰(zhàn),捕捉歷史縫隙遺留的族人的堅(jiān)韌,凸顯了生命的一次次輪回。她將鄭成功收復(fù)臺(tái)灣的壯舉與簡(jiǎn)氏家族冒險(xiǎn)到臺(tái)的經(jīng)歷進(jìn)行交叉敘述,從而將家園的興盛與國(guó)家的強(qiáng)大聯(lián)系在一起,升華出家國(guó)同構(gòu)的哲思。這篇散文以自己創(chuàng)作的詩(shī)歌《浪子之歌》收尾,突出了海洋對(duì)簡(jiǎn)氏家族的誘惑。“藍(lán)色海洋,鷗鳥回飛,白浪裝飾著海岸/海中有一座小島與你對(duì)望,問名字/答曰‘龜嶼’/你因此埋一個(gè)吉兆在心底當(dāng)作秘密”?這顯然不同于拉家常式的絮叨,它在情緒的自然流動(dòng)中隱現(xiàn)著對(duì)自己家族的崇拜與感激之情。
《朝露:獻(xiàn)給1895年抗日英魂》從漳州市一塊簡(jiǎn)大獅的石碑中尋找家族的集體記憶。當(dāng)神圣的文物與周圍堆滿的垃圾相伴時(shí),英雄的沒落已成為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作家在淡淡的憂傷中追憶發(fā)生在臺(tái)灣海域的近代中日之戰(zhàn),如泣如訴。簡(jiǎn)大獅的義舉與悲慘結(jié)局已成為歷史的塵埃,但歷史也會(huì)像海洋一樣,也有潮起潮落之時(shí),昔日中華民族之痛應(yīng)成為今日國(guó)人不能忘卻的記憶。
《天涯海角:給福爾摩沙》是一曲寫給投海自盡的母親的哀歌。第一部分《春之哀歌》以一名叫“春”的婦女的自述,把女性的獻(xiàn)身精神與大海融為一體,激越而悲愴,令人感慨。
潛藏海底,我隱居在紅珊瑚隙,以海草結(jié)廬,采紫苔鋪塌;居鯨與豚魚已分頭清理海路,以迎接?jì)胫聘苟N野察o地躺臥,不食不飲,不喜不懼。咸波中,我紅潤(rùn)的女體逐漸溶解,化成魚群身上斑斕的紋彩。繁華洗盡,我素樸如一顆海底的人淚。?
臺(tái)灣曾經(jīng)是荷蘭的殖民地,“福爾摩沙”(Formosa)是歐洲人對(duì)臺(tái)灣的舊稱。在這里,簡(jiǎn)媜以女人死后化身為魚在海底繁衍的神話,隱喻了臺(tái)灣人曾經(jīng)蒙受的被掠奪與侵占之痛,展現(xiàn)了臺(tái)灣沉痛的歷史。同時(shí),借海洋的美麗與豐饒表現(xiàn)出生態(tài)女性主義的訴求。“不少生態(tài)女性主義學(xué)者視自然/大地為[地母](Mother Earth),如默茜(C. Merchant)、葛瑞(E.Gray)和魯詩(shī)(R. Ruether)等,雖然他們的論點(diǎn)有些差異,但是皆覺得自然猶如母親一樣生育、滋養(yǎng)、保護(hù)著萬物。”?在這篇散文中,女性與大海融為一體,顯示出博大的情懷。而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人們似乎早已忘記了臺(tái)灣曾經(jīng)的苦難與古老的海洋民族,這令作家深感憂慮。
這篇散文的第二部分《蘭嶼古謠》借太平洋上紅人頭的傳說,敘述了雅美族人手持鬼頭刀在海上捕魚的習(xí)俗,神秘而令人神往。但都市化的噩夢(mèng)時(shí)刻都在威脅著他們自給自足的生活,古老的信仰在現(xiàn)代化面前顯得多么的脆弱。第三部分《港都夜曲》和第四部分《臺(tái)北搖滾》則是后現(xiàn)代生活的寫照,與前面的敘述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第五部分《夏之獨(dú)白》以抒情見長(zhǎng),在獨(dú)白中發(fā)出了“我要借母親的靈魂越過海洋而去”?的呼聲。面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大潮,作家痛感到了海洋面臨的危機(jī)。“雅美族人有很獨(dú)特的空間概念。雅美人所畫的地圖,位居中央的并不是蘭嶼島,而是大海,蘭嶼島與小蘭嶼、巴丹群島及其他想象的島嶼則環(huán)繞中心的海洋排列。這一點(diǎn)完全不同于所謂現(xiàn)代人的自我中心觀,無論哪一個(gè)國(guó)家繪制的地圖一定都是把自己的國(guó)家置于世界的中心。一生都生息于小島上的雅美老人似乎認(rèn)為世界就是一個(gè)一個(gè)像蘭嶼一樣的小島。”?可見,雅美人給我們開啟的是一個(gè)面向大海的理想王國(guó)。簡(jiǎn)媜以雅美族的信仰來反襯出現(xiàn)代人的愚昧,凸顯批判的鋒芒。同時(shí),她在追溯海洋文化中反觀現(xiàn)代文明的弊端,顯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家園意識(shí)。時(shí)代在前進(jìn),對(duì)傳統(tǒng)和歷史的漠視導(dǎo)致了現(xiàn)代人的狂妄自大,終究會(huì)失去賴以生存的海洋與精神家園。
《煙波藍(lán):給少女與夢(mèng)》這樣寫道:
海洋在我體內(nèi)騷動(dòng),以純情少女的姿態(tài)。
那姿態(tài)從忸怩漸漸轉(zhuǎn)為固執(zhí),不準(zhǔn)備跟任何人妥協(xié),仿佛從地心邊界向上速?zèng)_的一股勢(shì)力,野蠻地粉碎古老的珊瑚礁聚落,驅(qū)趕繁殖中之鯨群,向上躥升,再躥升,欲摑上天的臉。卻在沖破海平面時(shí)忽然回身向廣袤的四方散去,嬌縱地把自己摜向瘦骨嶙峋礫岸。浪,因而有哭泣的聲音。?
海洋是狂暴的,同時(shí)在躁動(dòng)不安中孕育了奇特的生命,這與人類生命的孕育過程具有同構(gòu)性。在這里,“海洋”象征自然生命的經(jīng)久不息。作家借“海洋”寫兩個(gè)少女在追求藝術(shù)過程中的煎熬,演繹出女性生命由量變到質(zhì)變的飛躍過程。就這樣,女性的成長(zhǎng)在自我與社會(huì)、藝術(shù)與現(xiàn)實(shí)的博弈中得到了詮釋。
簡(jiǎn)媜的另一部散文集《女兒紅》也不乏書寫海洋的篇章。《在密室看海》寫一對(duì)姐妹的童年記憶。潮濕的老屋,無助的媽媽,黑的海,都把她們推向命運(yùn)的邊緣。“夜使她超越六歲孩子的視界,向上攀升、盤旋、俯瞰,看到成人世界凌亂不堪的景致,她的感官活絡(luò)起來,攫住那近乎絕望的黑,捕獲令人有暈眩感的怒吼,最后,鮮明地記住一個(gè)少婦與雙胞胎的女兒被不知名的力量扔在黑色海灘的處境。她后來隱約明白,接著發(fā)生的事是她自己觸動(dòng)宿命關(guān)鍵,遂使一生無法出脫暗海,注定獨(dú)自仰望永夜的星空。”?茫茫無際的夜與海象征女性成長(zhǎng)的艱難。面對(duì)成人世界的駁雜,女孩看到了自己的宿命,這是作家感性世界里的經(jīng)驗(yàn),也是她表達(dá)理想訴求的誘因。兒童有與生俱來的孤獨(dú)感,女孩更是有著天生的依賴感。但殘酷的生活反過來也拯救了女孩,使她們比男孩成熟得早。簡(jiǎn)媜善于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女性生命的悲愴與自我救贖。妹與姐不同,具有叛逆的性格。從小就能覺察到“在媽媽巧手布置的家里,有一個(gè)幽靈男童存在。”?這里暗示了妹妹朦朧的性幻想。成年后的妹妹放蕩不羈,也印證了她的早熟。這篇散文借姐妹不同的性格,寫出了女性的兩面性。一方面,她們迫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shí)的壓力,表現(xiàn)出柔弱而被動(dòng)的一面;另一方面,她們?cè)谶m應(yīng)時(shí)代與環(huán)境中學(xué)會(huì)了以柔克剛、任性而為,成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把握自我命運(yùn)的強(qiáng)者。
“唯有水才能保持著美而睡去;唯有水能靜止地保持著倒影而死去。水在倒映著忠于偉大的回憶,忠于唯一的映象,它使各種回憶又有生命。這樣便產(chǎn)生了給予我們?cè)鵁釔鄣乃械娜艘悦赖哪欠N委派的和重復(fù)的自戀。人陶醉在過去中,對(duì)于他而言任何形象都是一種回憶。”?簡(jiǎn)媜的散文在回憶中試圖重返少女時(shí)代,其中的“海洋”具有一定意義上的自戀色彩,逝去的青春在“海洋”的意象中得以復(fù)活,隱喻出女性不竭的生命渴望。無論書寫家族歷史或雅美族的傳說,還是少女的成長(zhǎng),都在海洋的鏡像世界里呈現(xiàn)出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huì)屬性的交融。她追求一個(gè)與海洋共舞的世界,簡(jiǎn)氏家族以海為鄰,雅美族人以海為生,少女在封閉的環(huán)境中渴望外面的世界,都是臺(tái)灣人與海洋密不可分的命運(yùn)寫照。但現(xiàn)代人留戀都市的快節(jié)奏,幾乎淡忘了昔日先輩奮斗的足跡,也失去了相對(duì)自由的空間。這正是世紀(jì)的憂慮,作家在海洋書寫中完成了自我的蛻變,也把問題擺在了世人的面前,令人欽佩。
此外,席慕蓉的《海洋》借一個(gè)遠(yuǎn)洋輪上的希臘水手與一個(gè)法國(guó)女教授的婚姻變故,演繹了婚姻如海洋般起伏不定的命運(yùn)。希臘水手感到自己的生命只有在海洋上拼搏才變得有意義,回到海洋是他明智的選擇。同樣,她的另一篇散文《給我一個(gè)島》從小島上一個(gè)女人的愜意生活中看到了船在海上自由行走的后面對(duì)家不變的依戀之情,這里的“島”象征著女人渴求的理想家園。可見,席慕蓉與簡(jiǎn)媜散文的海洋書寫達(dá)到了異曲同工之妙。
臺(tái)灣作家書寫海洋,將海洋內(nèi)化為自我成長(zhǎng)的客觀對(duì)應(yīng)物,人生的況味與生命的體驗(yàn)?zāi)酥翚v史意識(shí),都轉(zhuǎn)化為一種海洋意識(shí),表現(xiàn)了他們對(duì)人類原初生命激情的追尋,還原了人類自身的自然元素,是一種返璞歸真心態(tài)的自然流露。這在21世紀(jì)的今天具有啟迪意義。因?yàn)楹Q螅藗兲旄饕环剑纬闪瞬煌难y(tǒng);因?yàn)楹Q螅藗兛释角笪粗氖澜纾藗兎窒砹怂鶐淼纳衿妗I⑽淖鳛橐环N靈活多樣化的文體,可以比較全面地表現(xiàn)海洋的大千世界。令人欣慰的是,1990年代以來臺(tái)灣散文的海洋書寫接納了西方生態(tài)主義的文化,讓人們看到了浪漫主義冒險(xiǎn)精神之外的一種審美態(tài)勢(shì)。臺(tái)灣散文的海洋書寫無論是以敘事為主,還是以抒情見長(zhǎng),都沒有都市散文中激烈的批評(píng)。如果說駱以軍和唐諾等作家的新都市散文凸顯出的是后現(xiàn)代都市社會(huì)里人與物、人與人的沖突的話,那么,蔣勛、廖鴻基和簡(jiǎn)媜等作家的海洋散文則表露了臺(tái)灣人渴望回歸自然的赤子情懷。
注釋:
①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賴力行:《中國(guó)古代文論史》,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317頁(yè)。
②徐明德:《中國(guó)海洋文化的原型傳統(tǒng)及流變(下)》,《大海洋》1998年詩(shī)畫展特刊。
③蔣勛:《此時(shí)眾生》,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頁(yè)。
④林清玄:《養(yǎng)著水母的秋天》,《感性的蝴蝶》,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頁(yè)。
⑤楊牧:《奇來后書》,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yè)。
⑥⑦蔣勛等:《行走臺(tái)灣:臺(tái)灣文化人說自己的故事》,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版,第58頁(yè)、第219-220頁(yè)。
⑧陳思和:《試論90年代臺(tái)灣文學(xué)中的海洋題材創(chuàng)作》,《學(xué)術(shù)月刊》2000年第11期。
⑨???廖鴻基:《領(lǐng)土出航》,聯(lián)合文學(xué)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3-94頁(yè)、第27頁(yè)、第104頁(yè)、第264頁(yè)。
⑩蕭義玲:《海洋流域,如夢(mèng)之夢(mèng)》,廖鴻基:《領(lǐng)土出航》,聯(lián)合文學(xué)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8頁(yè)。
?無名氏:《金色的蛇夜》(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頁(yè)。
?辛棄疾:《青玉案·元夕》,白華、林水選注:《青玉案》,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yè)。
?????簡(jiǎn)媜:《天涯海角》,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yè)、第40頁(yè)、第151頁(yè)、第160頁(yè)、第220頁(yè)。
?馮慧瑛:《自然與女性的辯證:生態(tài)女性主義與臺(tái)灣文學(xué)/攝影》,《中外文學(xué)》1999年第5期。
?余光弘,李莉文主編:《臺(tái)灣少數(shù)民族》,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頁(yè)。
??簡(jiǎn)媜:《女兒紅》,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yè)、第42頁(yè)。
?[法]加斯東·巴什拉著,顧嘉琛譯:《水與夢(mèng)——論物質(zhì)的想象》,岳麓書社2005年版,第74頁(yè)。
(作者單位:湖南城市學(xué)院文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佘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