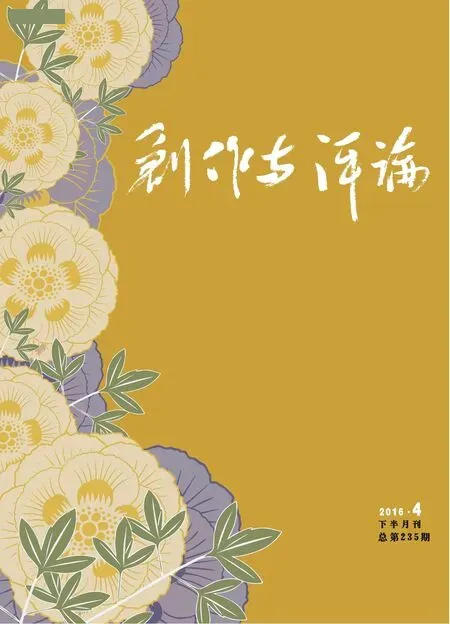從本土意識(shí)到家國想象
——論陳可辛電影的文化身份流變
○李寧
?
從本土意識(shí)到家國想象
——論陳可辛電影的文化身份流變
○李寧
新世紀(jì)以來,大批香港電影人“北上”內(nèi)地尋求合作拍片機(jī)會(huì),成為中國電影最令人矚目的風(fēng)潮之一。在這其中,陳可辛可謂一位代表性人物。12歲隨家人移居泰國、18歲赴美研讀電影理論、21歲返港的陳可辛,早年有多年漂泊他鄉(xiāng)的經(jīng)歷。這種人生體驗(yàn)也深刻影響到了他的影片創(chuàng)作。對(duì)于懷舊的渲染與對(duì)于漂泊者的書寫,成為陳可辛現(xiàn)代題材電影如《甜蜜蜜》《如果·愛》《中國合伙人》等一以貫之的主題。正如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所言,“懷舊本身具有某種烏托邦的緯度”①。在對(duì)漂泊歲月難以割舍的回望之中,陳可辛以一種想象性建構(gòu)的途徑,對(duì)影片中的漂泊者、也對(duì)他自己的文化身份進(jìn)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追問。懷舊,本質(zhì)上乃是一種身份認(rèn)同的手段。而文化身份的尋找與建構(gòu),也由此成為陳可辛電影的一個(gè)精神內(nèi)核。
電影《如果·愛》(2005)與《中國合伙人》(2013)是陳可辛北上合拍的兩部現(xiàn)代題材電影,如果將兩者與導(dǎo)演早期成名作《甜蜜蜜》(1996)放置在一起,能夠從中發(fā)掘出陳可辛文化身份的有趣嬗變。作為創(chuàng)作者或文本所持有的一種精神底色與文化歸屬,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流動(dòng)的、建構(gòu)的和不斷形成的。正如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指出的那樣:“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經(jīng)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實(shí)踐加以再現(xiàn)的事實(shí),而應(yīng)該把身份視做一種‘生產(chǎn)’,它永不完結(jié),永遠(yuǎn)處于過程之中,而且總是在內(nèi)部而非在外部構(gòu)成的再現(xiàn)。”②將《甜蜜蜜》《如果·愛》《中國合伙人》視為一條脈絡(luò)來考察陳可辛電影文化身份的流變,能夠看到新世紀(jì)前后內(nèi)地與香港電影合拍過程中的文化交往狀況,更能夠從更深層次上窺見不同歷史情境下內(nèi)地與香港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交往關(guān)系的流變。
一、《甜蜜蜜》:“九七”前夕的香港意識(shí)與自我身份建構(gòu)
《甜蜜蜜》誕生于1996年。1996年對(duì)于香港來說,是一個(gè)微妙而緊張的重要?dú)v史時(shí)刻。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政治原因,兩岸四地的文化身份問題,總是呈現(xiàn)出駁雜迷離的復(fù)雜情狀。而香港自開埠以來社會(huì)變遷多元而劇烈,獨(dú)特而尷尬的殖民地身份令其常常陷于認(rèn)同困境與身份焦慮之中。尤其是1984年《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簽署,給香港民眾蒙上了一層回歸的焦慮與恐懼,也喚醒了香港民眾的本土意識(shí)與對(duì)自我身份的追問。因此可以看到,1997年前后的香港電影常常在“九七”癥候的陰影籠罩下,站在本土主義的立場上,嘗試著重新界定香港與中國的關(guān)系,尋求自我身份的認(rèn)同。影片《甜蜜蜜》正可謂“九七”前夕一則想象與建構(gòu)香港身份的寓言。
《甜蜜蜜》講述的是黎小軍與李翹兩個(gè)大陸人努力融入香港社會(huì)、尋求“香港身份”的故事。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香港的身份想象是在與內(nèi)地的對(duì)立中建構(gòu)起來的。20世紀(jì)70年代以后,香港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讓長期處于漂泊失據(jù)狀態(tài)的港人開始有了對(duì)于本土文化的自信心與認(rèn)同感。“城市”身份也成為寄身國族邊緣的香港對(duì)抗內(nèi)地的“家國想象”,從而界定自己文化身份的武器。王德威在《香港——一個(gè)城市的故事》一文中便指出,香港“以一個(gè)城市的立場,與鄉(xiāng)土/國家(country/country)的論述展開了近半個(gè)世紀(jì)的拉鋸”。③可以看出,在影片《甜蜜蜜》中,鄉(xiāng)土內(nèi)地與城市香港構(gòu)成了對(duì)立的兩極。來自內(nèi)地的黎小軍與李翹所努力尋求的,正是擺脫鄉(xiāng)土身份,獲得城市身份。影片開始時(shí),初到香港的黎小軍扛著行囊從黑暗的電梯口緩緩向上,走進(jìn)一個(gè)散發(fā)著耀眼光芒的世界,充滿了從低層鄉(xiāng)土世界步入高級(jí)現(xiàn)代都市的隱喻。影片中,剛到香港的黎小軍著裝土里土氣,哼唱著意識(shí)形態(tài)意味濃郁的大陸歌曲,說著一口與香港都市環(huán)境格格不入的普通話,對(duì)取款機(jī)、麥當(dāng)勞等現(xiàn)代化產(chǎn)物一無所知。為了融入更先進(jìn)的香港社會(huì),他開始努力學(xué)習(xí)英文,試圖通過改變“語言”這一外在“能指”而擺脫“內(nèi)地人身份”這一內(nèi)在“所指”。而會(huì)說一口流利粵語的李翹則看似更早融入香港,她以會(huì)說粵語為由對(duì)黎小軍隱瞞自己的內(nèi)地人身份,努力變身成一個(gè)“喝著維他奶長大的香港人”。片中,許多大陸人為避免被他人低看一等而隱瞞自己的普通話口音與出身,姑姑讓黎小軍稱呼她的英文名字、大陸人為避免暴露身份而不買鄧麗君的卡帶等等行為,都是對(duì)于香港身份的一種不無辛酸的找尋。
那么,在影片《甜蜜蜜》的言說中,到底什么是香港的文化身份?陳可辛以黎小軍與李翹的漂泊生活給出了答案。從小漁村發(fā)展為國際都市,作為一座典型的流動(dòng)性極強(qiáng)的移民城市,香港居民主體由內(nèi)地遷入的新舊移民及其后代所構(gòu)成。為了給自己和媽媽在香港和廣州分別買一套房子,女主人公李翹以一種近乎瘋狂的方式拼命工作,從麥當(dāng)勞餐廳、花店到英語補(bǔ)習(xí)班的兼職,到賣音樂卡帶、炒股、按摩,她嘗試過各種各樣賺錢的機(jī)會(huì),也經(jīng)歷過血本無歸的困境。但在香港這座競爭殘酷的現(xiàn)代化都市中,她始終堅(jiān)韌如一棵蒲草,隨風(fēng)起伏,卻又始終不倒。香港精神,正是奮發(fā)進(jìn)取的移民精神。漂泊無根,是香港移民難以言說的痛楚,但漂泊無根中為改變命運(yùn)而不懈奮斗的堅(jiān)韌精神,正構(gòu)成了香港人最內(nèi)在與根本的精神氣質(zhì)。“可見《甜蜜蜜》之所以觸動(dòng)香港人的懷舊情懷,因?yàn)樗ㄟ^對(duì)已逝年代‘香港故事’的追憶,建構(gòu)著香港自己的歷史記憶并試圖確立和修正自我的身份認(rèn)同。”④最終,在充滿著身份焦慮與認(rèn)同危機(jī)的“九七”前夕,影片《甜蜜蜜》立足于本土主義立場,高揚(yáng)香港意識(shí),通過兩個(gè)大陸移民努力“香港化”的敘事,完成了對(duì)于香港地域的文化身份的營構(gòu)。
二、《如果·愛》:“后九七”與“北上”初期的身份迷思
《如果·愛》創(chuàng)作于2005年,這是香港回歸的第8個(gè)年頭,也是陳可辛第一次到內(nèi)地拍攝電影。此時(shí)的陳可辛所面臨的,首先是“九七”這一香港人還沒有完全跨越過的政治、心理和文化的界線,其次是首次北上拍片時(shí)兩種文化的碰撞。盡管“九七”之后,香港電影正在想方設(shè)法抹平香港與內(nèi)地之間因“時(shí)間”與“歷史”的斷裂而形成的巨大裂隙,但李道新在2007年的《“后九七”香港電影的時(shí)間體驗(yàn)與歷史觀念》一文中仍然指出:“迄今為止,無論表現(xiàn)記憶與失憶,還是闡發(fā)因果與循環(huán),‘后九七’香港電影的時(shí)間體驗(yàn),都沒有跨越‘九七’這個(gè)巨大的裂縫;也正因?yàn)槿绱耍缶牌摺愀垭娪埃尸F(xiàn)出來的是一種將懷舊的無奈與懷疑的宿命集于一身的歷史觀念與精神特質(zhì),并以其根深蒂固的缺失感,界定了香港電影的文化身份。”⑤一面是還未完全跨過的“九七”裂縫,一面是充滿誘惑的內(nèi)地市場,初次北上的陳可辛在自己所依據(jù)的香港文化與內(nèi)地文化的碰撞中,表現(xiàn)出了文化身份的游移與迷茫。
《如果·愛》講述了林見東與孫納兩位“北漂”在成為演藝明星后,共同拍攝導(dǎo)演聶文執(zhí)導(dǎo)的一部歌舞片的故事。盡管同《甜蜜蜜》一樣,《如果·愛》中充滿了懷舊的意味,但“遺忘”卻僭越“懷舊”成為敘事的重心。正是在記憶與失憶的反復(fù)徘徊中,影片為漂泊者身份的缺失而備感焦慮。《甜蜜蜜》中,兩位主人公一直在不斷找尋自己的身份,鄧麗君的一曲《甜蜜蜜》也成為兩人建構(gòu)身份的象征符號(hào)。而《如果·愛》中,主人公的身份卻一再遭受否定與遺棄,貫穿影片的是一首無奈與悲涼的《外面的世界》。女主人公孫納與男主人公林見東有著相濡以沫的過往,然而面對(duì)林見東試圖喚起其記憶的努力,孫納卻一直有意識(shí)地回避與否定。當(dāng)有記者詢問孫納的人生經(jīng)歷時(shí),她簡潔地回答“沒有愛情”;當(dāng)新聞發(fā)布會(huì)上被問到對(duì)林見東的看法時(shí),她的回答是“我不認(rèn)識(shí)他”;當(dāng)她與林見東一起乘車時(shí),她提醒后者“我們沒見過”。女主人公對(duì)于原有身份的刻意“失憶”,構(gòu)成了影片文化身份的模糊。有趣的是,影片《如果·愛》采取了“戲中戲”的結(jié)構(gòu)。孫納與林見東出演的歌舞片劇情與兩人相濡以沫的過往驚人地相似;而在孫納與林見東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兩人卻形同陌路。影片中的“戲中戲”,仿佛孫納與林見東過往的一個(gè)鏡像。在拉康的“鏡像理論”看來,自我的建構(gòu)離不開自身,同時(shí)也離不開自我的對(duì)應(yīng)物,即來自于鏡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過與這個(gè)影像的認(rèn)同而實(shí)現(xiàn)身份的建構(gòu)。然而當(dāng)孫納一再否定“戲中戲”所呈現(xiàn)的故事時(shí),她的自我身份也就失去了建構(gòu)與認(rèn)同的可能性。
影片《如果·愛》中,地理空間的邊緣化進(jìn)一步加劇了影片文化身份的模糊。在《甜蜜蜜》中,香港這一都市空間是作為敘事的重要背景出現(xiàn)的,承載著重要的文化含義。而《如果·愛》中所展現(xiàn)的只是由潮濕的地下室、雜亂的地?cái)偂⑵婆f的公共汽車組合成的北京的邊緣外圍,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某種意義上是缺失的。這種對(duì)于北京城市空間的邊緣化處理,顯露出陳可辛作為香港電影人在北京的政治中心身份籠罩下流露出的些許無力感,以及作為外來者感受到的一種不確定性與漂泊感。正如香港著名影評(píng)人列孚指出的那樣:“第一次回到內(nèi)地拍片的香港導(dǎo)演陳可辛,其影片《如果·愛》凸顯了它文化身份和地理身份的模糊性……全片我們也看不到任何香港,只有一句梅艷芳的粵語歌歌詞。同樣,影片寫了北京等內(nèi)地城市,又是因?yàn)榛氐娇桃鉅I造的懷舊意境,導(dǎo)演幾乎將一切都模糊了。”⑥于是,在“后九七”與“北上”合拍初期的雙重文化語境中,《如果·愛》在記憶與失憶的反復(fù)徘徊中,凸顯了文化身份的游移與迷茫。
三、《中國合伙人》:文化交流新格局下的家國想象與民族認(rèn)同
上映于2013年的影片《中國合伙人》的奇特之處,在于陳可辛作為香港電影人,來講述一段內(nèi)地改革開放進(jìn)程中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經(jīng)歷了十余年的合作拍片之后,香港電影已經(jīng)逐漸進(jìn)入中國這一民族國家的產(chǎn)業(yè)與文化體系之中,成為華語電影新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而隨著全球化與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不斷加速,新世紀(jì)以來的中國復(fù)興崛起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令人血脈賁張的事實(shí),國人包括港人對(duì)于民族與國家的認(rèn)同感也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升騰與發(fā)酵。影片《中國合伙人》所呈現(xiàn)出的,正是在這一新的歷史情境中,以陳可辛為代表的香港人通過家國想象與民族認(rèn)同的方式,建構(gòu)“中華民族一份子”這一新的文化身份的努力。
影片對(duì)“孟曉駿”這個(gè)漂泊者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陳可辛在《甜蜜蜜》《如果·愛》中遵循的路徑,只不過漂泊之處從香港、北京轉(zhuǎn)移到了美國。影片中,孟曉駿這個(gè)“美國夢”的積極倡行者,在他本以為“在夢想面前人人均等”的美國收獲了現(xiàn)實(shí)的冰冷與殘酷。自己喂養(yǎng)小白鼠的工作被人擠掉,淪落至連小費(fèi)都沒有資格拿的刷盤工,同樣出身優(yōu)越的女友也屈身于洗衣店里打工,二人只能租住在狹小而昏暗的房間里。有趣的是,孟曉駿的“美國夢”在美國功敗垂成,回國后他以奮斗、公平、自由等“美國夢”的精神在中國實(shí)現(xiàn)了事業(yè)的成功。他不是在美國,而是在中國建構(gòu)起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與《甜蜜蜜》中通過內(nèi)地與香港的對(duì)立來建構(gòu)“香港身份”如出一轍,《中國合伙人》中“國人身份”的建構(gòu)也是通過對(duì)立來完成的,那就是傳統(tǒng)/現(xiàn)代與東方/西方的兩組對(duì)立。影片中,代表著中國與傳統(tǒng)的無疑是出身于農(nóng)村的成東青,代表著西方與現(xiàn)代的則是深受西式教育濡染的孟曉駿。成東青對(duì)于孟曉駿的依賴與傾慕,是落后的中國對(duì)領(lǐng)先的西方的仰望。然而隨著成東青的成長與獨(dú)立,隨著中國追趕西方步伐的加快,影片中東方與西方不平等的關(guān)系也在不斷發(fā)生著變化。影片開始時(shí)有這樣一個(gè)場景:在新夢想學(xué)校的辦公室里,墻上懸掛著的巨幅美國地圖上已經(jīng)被小紅旗插滿。手持雪茄的成東青、孟曉駿與王陽三人意氣風(fēng)發(fā)地品味著“攻陷”西方的喜悅。《中國合伙人》故事的高潮,發(fā)生在影片末尾劍拔弩張的談判桌上。成東青在飛往美國的十幾個(gè)小時(shí)里,將整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條例背了下來,令美國起訴者目瞪口呆。最終,兄弟三人以“中國夢”“攻陷”西方,完成了家國想象與民族認(rèn)同。
值得深思的是,從《甜蜜蜜》中對(duì)于香港身份的建構(gòu),到《中國合伙人》當(dāng)中的民族認(rèn)同,陳可辛電影的文化身份一直在變遷,但更深層次的思維模式卻一以貫之,那就是后殖民主義文化影響下的二元對(duì)立模式。無外乎有論者指出:“再強(qiáng)烈誠懇的動(dòng)機(jī),也無法改變作為香港導(dǎo)演的陳可辛的深層意識(shí),對(duì)于他而言,觸摸中國內(nèi)地改革開放三十年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痛苦蛻變是非常艱難的,但表現(xiàn)香港深入骨髓的東方/西方的主題,卻游刃有余。《中國合伙人》因此成為這樣一部略顯奇妙的集合體:《投名狀》中的兄弟情誼,《甜蜜蜜》中的懷舊和溫柔質(zhì)感,《黃飛鴻》《霍元甲》《葉問》的中華必勝主題。”⑦在兩種文化的交融中,二元對(duì)立模式存在的對(duì)抗性,值得我們思考與警惕。
當(dāng)下華語電影正呈現(xiàn)出多元文化沖突和文化跨地融合的濃烈態(tài)勢,兩岸三地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共同營造了多元化的電影生態(tài)與文化格局。從《甜蜜蜜》《如果·愛》再到《中國合伙人》,從香港身份的追索、文化身份的模糊到民族文化的認(rèn)同,陳可辛電影的文化身份呈現(xiàn)出清晰的嬗變軌跡。這一軌跡,能夠讓我們看到內(nèi)地與香港合拍過程中文化交往的情狀,看到歷史的變遷在電影中留下的難以抹去的深刻痕跡。更重要的是,它能為我們提供一種發(fā)展的視角,來看待未來兩岸三地文化更頻繁的碰撞與交流。
注釋:
①斯維特蘭娜·博伊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
②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羅剛、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頁。
③王德威:《如何現(xiàn)代,怎樣文學(xué)?》,臺(tái)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82頁。
④詹慶生:《懷舊鄉(xiāng)愁與“香港”的身份想象——<甜蜜蜜>的文化解讀》,《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2年第3期。
⑤李道新:《“后九七”香港電影的時(shí)間體驗(yàn)與歷史觀念》,《當(dāng)代電影》2007年第3期。
⑥列孚:《地理文化·文化密碼·類型電影后港產(chǎn)片、香港與內(nèi)地合拍片的根本問題》,《電影藝術(shù)》2006年第2期。
⑦田卉群:《<中國合伙人>:傳統(tǒng)/現(xiàn)代?東方/西方?》,《當(dāng)代電影》2013年第7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孫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