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佛珠
文_孔淑茵
父親的佛珠
文_孔淑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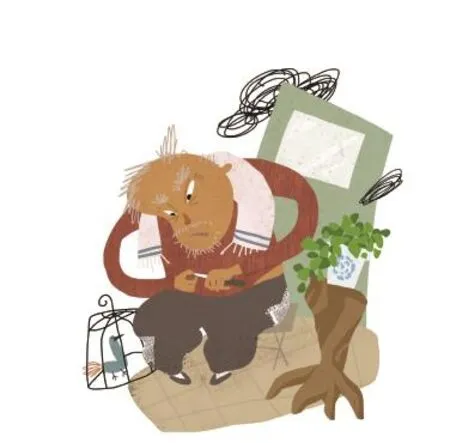
一
父親正在和一截木頭倔強對視,彼此互不相讓。
他顯然做了充分的準備,鋸子、銼刀、刻刀、電鉆、砂紙等武器輪番上陣,刺刺啦啦攻城略地。木頭卻波瀾不驚,它有自己在山中修煉多年的智慧,懂得以靜制動。它只祭出自己的堅硬與平滑,便足以讓父親手忙腳亂。
這無疑是一場不動聲色的戰斗。
木頭是降龍木,來自太行山深處。盤根錯節的老樹根,以扎根泥土的姿態穩穩地站在乳白色的地板上,山野的氣息頓時四處張揚彌散。父親立刻眉眼放光。降龍木,單聽這名字他就喜歡—《穆桂英掛帥》里大破天門陣的神奇法寶,單這一條就足以滿足他旁逸斜出的回憶與想象。
父親無法破譯降龍木的基因里那層隱秘的佛性。他既不知道這塊木頭上那六條淡綠色的紋絡代表著文殊菩薩的六把智慧劍,也不知道六道子佛珠象征著六道輪回。但這絲毫不影響他想做幾串佛珠的打算。老樹根的主體已經被他做成了花架,這花去了他不少時間,他的體力跟不上了,好在他不急。到了他這個年紀,已經沒有多少事需要風風火火了。他抽著煙斗慢悠悠地合計,給家里每個人做一串佛珠的話,需要多少粒珠子,做花架剩下的那些材料似乎不大夠用,需要精打細算才行。
現在,來說說我父親的手,蒼白的、青筋暴露的手。他左手捏緊一粒初具雛形的珠子,右手拿著木銼,他必須小心翼翼—有六道紋絡的地方木質比較軟,稍一用力就會凹進去一塊。更何況,他的手實在顫抖得厲害,他盡量屏氣凝神也無濟于事—不可救藥的老年性震顫。他的手抖的時候,他手背、手臂上的陽光便一朵一朵跟著晃,手中的珠子趁機拼命掙扎,又是一番激烈較量。他的胳膊開始發麻,氣息有點兒短促,他終究還是敗下陣來。珠子躺在茶幾上,氣定神閑地對老頭兒喊話:“看吧,你老了!”老頭兒氣哼哼地不搭理它,汗珠子啪嗒一聲砸進碎木屑里。
二
我父親開始做第五粒珠子的那天,接到一個電話。他接電話的時候把聲音壓得很低,一點兒也不像平時那樣高聲大嗓,我甚至看見他對著電話微彎著腰。
他說:“別急,有話慢慢說。”
他說:“好,好,好,我馬上給他打電話,看我怎么罵他。你安心照顧好孩子。”
他說:“你別找他們,他們都上班,忙著呢。找我就行。”
父親口中的“他們”,是指我們兄妹幾個。老三兩口子每次鬧別扭,我們都是弟妹固定的哭訴對象,盡管我們根本無能為力。父親放下電話,將自己重重斜著放進沙發里。看得出來他很生氣。老三他們每次吵架都弄得一大家子不得安生,任誰都生氣。他喘著粗氣對自己發誓,以后再也不管他們的事了。
我說:“好,那就不管。”我選擇忽略了他的口不對心。
到傍晚的時候,父親有些沉不住氣了,他催促我給老三打電話。老三肯定又拒接他的電話了—每次惹了事,老三都不接他的電話。父親也許被這個事實打擊到了,有些悻悻的。但馬上,他便又遭受了來自我的打擊:我不肯打這個電話。將是非對錯放到一邊,我只是煩了。父親有一剎那的錯愕,他以為,為了這個家,我會努力去幫他們和解,可我選擇了旁觀。我想,他對我很失望。
我再次回家的時候,父親正戴著老花鏡打磨木珠子,蒼涼從他的眉目間、骨頭縫里漫無邊際地溢出來。我想他真的老了,老到即便在自家的地盤上,也無法再像過去那般生氣了拍桌子、聲若洪鐘地吼我們幾個不聽話的小崽子了。我忽然就有了流淚的沖動。
三
父親每天與木頭較勁,與不服管教的老三較勁。他每天都給老三打一個電話,然后坐下來鋸木頭、銼木頭。他銼木頭的時候,掛鐘就在他對面的墻上滴答滴答地響。他喜歡聽時間行走的聲音,聽著就覺得心里很平靜,仿佛萬千景象全在里面了。
父親做完第十七粒珠子的時候,將它們穿成了第一串佛珠。老三挑剔地說:“十七算個什么數,佛珠的粒數可是有講究的。要么十四粒,表示十四種無畏的功德;要么十八粒,代表六根、六塵、六識。還有,新做好的珠子最好別直接上手玩兒,應該先放在小布袋里盤。”父親自動屏蔽了老三的喋喋不休,正如老三總是自動屏蔽父親恨鐵不成鋼的說教。
那天,父親心情相當不錯—老三兩口子有說有笑地回來吃飯了。父親心情好的時候就愛和老三下棋。
“下棋,你不行。”老三用嘴角的微笑挑釁他。
“別得意,鹿死誰手還不知道呢。”父親立刻瞪著眼珠子反擊。
父親果然不是對手,他的腦子慢慢就跟不上節奏了。他佝僂著身子,顫抖的手捏著一枚棋子,久久不能落下。他有些茫然無措,卻依然固執地堅守著每一寸陣地,他以昂揚的姿態節節敗退。
但父親敗北的場面不荒涼,一切似乎都在相愛相殺中得到體諒與和解。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我們其實都是父親手里的木頭珠子,被他打磨,想從他手里逃脫,卻最終被他緊緊地串在一起。
我很難想象這個家沒有父親的樣子。
圖_孫 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