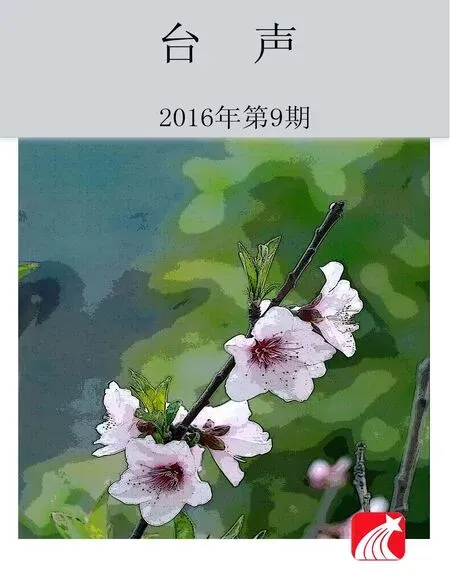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臺生吳婷盈與保生大帝有緣的大齡本科生
作者丨記者 程朔
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臺生吳婷盈與保生大帝有緣的大齡本科生
作者丨記者 程朔
“我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她們都非常優(yōu)秀,但是在學(xué)習(xí)方面,三姐妹中還是我總能拿到最好的成績,所以父親對我的期待非常高,他那時總盼著我能夠?qū)W醫(yī),成為一名西醫(yī)。”
“但是我小時候認(rèn)為那些學(xué)醫(yī)的人就是想要賺錢,很討厭,所以非常排斥學(xué)醫(yī)。我喜歡心理學(xué),所以在學(xué)政治心理學(xué),之后去美國,先后讀取藝術(shù)治療碩士、臨床心理學(xué)博士。”
許多人初見這位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的在讀本科生,都會一下子在心里打個問號,“從她的外貌上看,真的不像是一位大學(xué)本科在讀學(xué)生啊,哄人開心吧?抑或是她的長相實(shí)在是很顯年長?”都錯!這位吳婷盈同學(xué)現(xiàn)在就是一名在讀本科生。
關(guān)于吳婷盈的具體年齡,當(dāng)然要保密,不過公開的資料顯示,這位大齡本科生,在到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上學(xué)之前,已經(jīng)獲得藝術(shù)治療碩士學(xué)位和臨床心理學(xué)博士學(xué)位。這樣的學(xué)歷,一般情況下,都不會是“而立”以前就能擁有的。感興趣的話,就聽聽她講自己的故事吧。
記者:先介紹下您與保生大帝的緣分吧。
吳婷盈:這故事要從我父親說起。我爸爸是家里第三個兒子,也是最小的兒子。我記得在我小學(xué)三年級的時候,我爸爸在整理東西時拿出了兩張A4紙,上面寫滿了字,他說這是我們家的族譜,那時候我還蠻好奇的,拿起來一翻,看不懂,但大概知道了我的祖先是來自大陸的福建;留下的印象里還有個家族圖表,圖表頂端書寫的那個人,感覺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不曉得他究竟是誰。給我看完之后,我父親就將那兩張紙跟家里的金子一起藏到天花板上去了。
取得博士學(xué)位后,我先回島內(nèi)工作了兩年,之后辭去教職到北京學(xué)中醫(yī)。事有湊巧,那時我因?yàn)榧易迨乱伺c各房親屬聯(lián)絡(luò),當(dāng)時聯(lián)系到我祖父的三哥的一位女兒、一位已經(jīng)80多歲的姑母,聊天中,我談到馬上就要辭去大學(xué)老師的工作去北京學(xué)習(xí)中醫(yī),那位姑母回應(yīng)說:“哦,我們家族的人不是老師,就是醫(yī)生。”我隨口問句“為什么呢?”她竟然答說:“你不知道嗎?我們的祖上與保安宮的大道公是親兄弟呢。”
其實(shí)那時候我還沒去過保安宮,對于家族的背景也幾乎什么都不知道。不過,透過那位姑母,我拿到1978年我家族重修的《白礁吳氏族譜》的副本。這冊有200多頁的族譜現(xiàn)在也珍藏在臺灣臺北的圖書館。族譜里面記載了大道公的父親通公,也就是我家族的一世祖,延陵吳氏因避亂遷徙到福建同安白礁村。通公有兩個兒子,保生大帝、大道公吳真人就是他的大兒子;次子,也就是吳真人的弟弟吳根,就是我的直系祖先。算來,我父親是白礁吳氏第34世子孫,我家族的第30世祖先紹惠公在乾隆年間遷臺定居,我就是渡臺以后的第6代。

吳婷盈
記者:就是因?yàn)楸I蟮鄣脑虿艣Q定學(xué)習(xí)中醫(yī)?
吳婷盈:父親曾經(jīng)對我期待很高,總盼著我能夠?qū)W醫(yī)。但是我小時候喜歡心理學(xué)。父親沒有勉強(qiáng)我,后來我成為了一名心理學(xué)博士。
然而在美國上學(xué)期間,我因緣際會地接觸了中醫(yī),接觸之后,我感覺中醫(yī)神奇的療效不僅不可言喻,還不可思議,我也因此開始對中醫(yī)感興趣了。獲得博士學(xué)位后,回臺灣教書的日子里,工作非常忙碌,我對中醫(yī)的態(tài)度就一直停留在“生病時,看中醫(yī)”這樣的一個層次上。
到2008年,我父親突然去世,我非常傷心,意識到自己忽視了他老人家的健康問題。父親病逝,我不僅對我自己非常失望,也對父親接受的醫(yī)療體系感到失望,所以學(xué)習(xí)中醫(yī)的念頭就在我心里萌發(fā)了。之后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準(zhǔn)備,我辭去工作到北京學(xué)中醫(yī),從本科開始念起,扎扎實(shí)實(shí)地學(xué)。
所以可以簡單概括說,學(xué)中醫(yī)是在追求自我的成長。當(dāng)然,在知道我自己的家族背景后,我更堅定了學(xué)習(xí)中醫(yī)的信念。我想,雖然是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但事實(shí)上我也背負(fù)起了家族使命。相傳大道公吳真人醫(yī)術(shù)高超、醫(yī)德高尚,生前被尊為神醫(yī),去世后受到人民供奉與祭拜,歷代帝王加以褒封,最后封到“保生大帝”。我希望承繼祖先風(fēng)范,傳承中華文化的精髓,結(jié)合中醫(yī)療法與心理治療,將中醫(yī)發(fā)揚(yáng)光大,幫助更多的人。我也希望,能進(jìn)一步推動兩岸共同關(guān)注中醫(yī)的傳承,共謀中醫(yī)的推廣與發(fā)展,從而也加強(qiáng)兩岸的交流互通,拉近兩岸的距離。
記者:為什么會想到通過中醫(yī)拉近兩岸距離呢?
吳婷盈:首先我有考慮過兩岸之間的距離的問題;其次我發(fā)現(xiàn)中醫(yī)藥是目前兩岸現(xiàn)存最重要的共同語言之一。
從我自己家族的經(jīng)歷就可窺見,現(xiàn)在臺灣居民多系遷徙自大陸。遷徙路線的長度就是臺灣與大陸間地理上的距離。這個地理距離有多遠(yuǎn)呢,他們之間隔了一個臺灣海峽,這個海峽的平均寬度是150公里,臺灣所屬的小金門,距離大陸僅有5公里多一點(diǎn)。大陸北京到天津有100多公里,快火車30分鐘到達(dá),北京到上海近1500公里,快火車4個多小時到達(dá)。
隔著臺灣海峽,兩岸間的地理距離并不那么遙遠(yuǎn),也不會改變。可是由于歷史因素,兩岸人民心靈之間距離的數(shù)值,有如海潮時漲時落。繼明朝中葉唐山過臺灣之后,鄭成功大軍來臺,給臺灣帶來了新的一撥移民,再次拉近了兩岸的心理距離。我的祖先大概是在鄭成功渡海100年后從福建同安遷徙到臺灣、定居于臺北。艋舺,就是現(xiàn)在的臺北萬華,是當(dāng)時同安人聚集的地區(qū),是當(dāng)時臺灣3個重要商港、繁榮城市之一,也是福建移民群居的處所。那些地方的居民就與福建百姓間有著斬不斷的親情。1895年后,兩岸百姓間,又有很長一段時間,距離被拉得很遠(yuǎn)。本世紀(jì)初以來,隨著雙向的直接通郵、通商、通航,海峽兩岸間的關(guān)系一度得到拉近,但2016年以來,兩岸關(guān)系發(fā)展再度出現(xiàn)困擾。
事實(shí)上,人和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是可以改變的,但拉近這個心理距離,僅有“三通”是不夠的。想克服它的話,需要更多的對話、更多的溝通,更多兩邊人民互相了解的機(jī)會。而更多對話與溝通往往需要從雙方所共有的起點(diǎn)出發(fā),從共有記憶、共同語言入手,才更容易達(dá)成“互信”,從而拉近雙方的心理距離,推動攜手共創(chuàng)未來。而中醫(yī)藥作為兩岸共有的重要文化遺產(chǎn),是最好的起點(diǎn)之一。
記者:關(guān)于兩岸百姓間“互信”的話題,您有什么觀點(diǎn)呢?
吳婷盈:我記得第一次接觸到大陸的人是在1991年,那時候我在美國念書,遇見大陸來的留學(xué)生,總覺得自己必須要提防著他們,具體防什么,其實(shí)也并不大清楚。
但是經(jīng)過不長時間的接觸之后,我發(fā)現(xiàn)大陸留學(xué)生,大家盡管有時想法不同、有些生活習(xí)慣不同,甚或是說話的用語不同,但其實(shí)在更多的方面,大陸留學(xué)生與我們臺灣留學(xué)生是有著很多共同點(diǎn)的。比如最基本的,我們都用筷子、都吃餃子面條,都學(xué)習(xí)刻苦、生活勤儉、工作勤奮。知道了這些共同點(diǎn)之后,就感覺大陸人也沒什么可怕,這讓我交到許多大陸的好朋友。
多年后的現(xiàn)在,我在北京讀書了,在人性的層面我更有發(fā)現(xiàn),兩岸同胞之間有著太多的共同點(diǎn),這些共同點(diǎn)里面,既有正面的、也有負(fù)面的,簡單說就是好的人文傳統(tǒng),比如儒家提倡的溫良恭儉讓,大家都有遺傳;而相對不那么正面的人文傳統(tǒng),比如詭辯術(shù)、權(quán)謀術(shù)等等,大家也都有“繼承”。
記得上個世紀(jì)90年代初期,大陸改革開放還沒有實(shí)施太久的時候,我見到的大陸留學(xué)生大都非常節(jié)儉,他們身上穿的從大陸帶出的服裝,樣式款型都相對單調(diào)。現(xiàn)在可是大不同了,如今在北京,單看年輕人身上的著裝,你很難分辨出他們是大陸人、臺灣人、抑或香港,甚至韓國人。這說明,至少在追逐時尚潮流方面,年輕人們的意識和方向都相當(dāng)接近或說比較統(tǒng)一了。
共同點(diǎn)多,不是說就沒有思想意識上的差異,這是歷史造成的,我覺得要勇于承認(rèn)、敢于面對,現(xiàn)在尤其需要我們兩岸調(diào)動足夠的智慧,用足夠的耐心去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