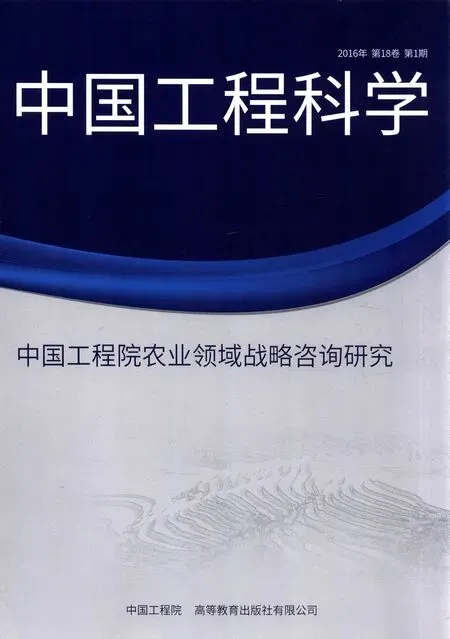我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碳匯結構現狀與優化途徑
佘瑋,黃璜,官春云,陳阜,陳光輝
(1. 南方糧油作物協同創新中心,湖南農業大學,長沙 410128;2. 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100094)
我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碳匯結構現狀與優化途徑
佘瑋1,黃璜1,官春云1,陳阜2,陳光輝1
(1. 南方糧油作物協同創新中心,湖南農業大學,長沙 410128;2. 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100094)
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引起的全球氣候變化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大難題。農作物的碳匯功能對氣候變化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農作物的生產過程既是碳源也是碳匯。本文收集整理分析了我國主要農作物農作系統的相關碳排放參數,估算了農田碳匯碳源效應及其動態變化特征,對作物生產系統的碳投入產出進行定量評價。為我國發展低碳農業規劃、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據,并提出了我國農田碳匯結構的優化途徑。
農作物; 碳匯;碳排放;優化途徑
DOI 10.15302/J-SSCAE-2016.01.014
一、前言
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引起的全球氣候變化,已經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類活動向大氣中排放過量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亞氮(N2O)等溫室氣體[1,2]。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減少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積累,其途徑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減少碳源,即溫室氣體的排放;二是要增加碳匯,即增加對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的吸收[3]。
森林一直被公認為具有明顯的碳匯功能,能夠幫助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除森林碳匯以外,在地球上面積最大的農作物同樣也具有碳匯功能,對氣候變化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
農作物的生產過程既是碳源也是碳匯。碳源主要包括農作物生產過程中化肥、 農藥、電力、柴油等投入物生產形成的碳排放,農田土壤呼吸碳排放以及作物的秸稈焚燒碳排放。 碳匯主要包括作物自身生長碳吸收、農田土壤固碳和秸稈還田的固碳效應。農作物的碳匯和碳源相抵可得到凈碳匯。在當前全球溫室效應加劇、環境不斷惡化的背景下,農作物的碳匯作用具備了顯著的生態環境價值。農田生態系統作為受人類影響最大的自然生態系統,其固碳能力歷來受到關注。
本項目根據我國不同農作區的差異,將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西北、長江中下游、西南、華南六大區域,各區域作物生產農田投入量來源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匯編》、試驗及調研數據、文獻等。化肥、農藥、電力、柴油等農資生產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于中國生命周期數據庫(CLCD)和Ecoinvent 數據庫。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表1 各區域農作物生產凈碳量及其組分單位 (kgC·hm–2)
二、我國農田生態系統碳匯分析
(一)我國農田生態系統表現為固碳效應
我國各區域主要農作物的農田生態系統主要表現為固碳效應,即凈碳量為正值(見表1)。在研究的作物中,只有西北的棉花和西南的油菜表現為碳源,凈碳量分別為–531.3 kgC·hm–2和–33.3 kgC·hm–2,其他作物的凈碳量差異較大,分布在404.7~40 725.9 kgC·hm–2。同一區域內不同作物的凈碳量差異明顯,同一作物在不同區域之間凈碳量差異也較大。以水稻而言,凈碳量數值以
長江中下游地區最大,為3. 584 3×103kgC·hm–2,西南地區數值最小,為1.571 7×103kgC·hm–2。以小麥而言,西北地區數值最大,達3.222 7×103kgC·hm–2,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數值僅為6.043×102kgC·hm–2。以玉米而言,凈碳量以西北地區數值最大,達3.891 7× 103kgC·hm–2,碳匯功能明顯;而在西南地區數值僅為4.047 ×102kgC·hm–2。
(二)我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系統碳效率呈基本穩定并提升的趨勢
在我國農業從粗放到集約的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主要農作物生產碳效率基本大于1,農田生態系統動態的碳平衡始終處于正平衡狀態(見圖1)。1952—1980年為以牛耕鐵犁為代表的傳統農作階段,1980—2010年為以半機械化為代表的半現代化集約農作階段,進入21世紀后,我國部分地區開始向準現代化農業階段過渡,對這段時間我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碳效率分析可知:無論是低水平的傳統農作還是較高水平的準現代農作,農田生態系統碳平衡都是作物生產固碳大于碳成本,農田生態系統都表現為“固碳效應”。另外,縱觀主要農作物生產碳效率隨時間的變化情況可以發現,隨著時間推移,作物生態碳效率變化并不太大,較為穩定,同時有緩慢增長的趨勢。

圖1 我國不同年份全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的碳效率
三、我國各區域主要農作物碳結構分析
(一)各區域主要農作物生產的碳成本
表2為各區域主要農作物生產的碳成本。東北地區水稻的灌溉量較大,造成其碳足跡遠大于玉米和大豆。水稻的單位面積碳足跡最高,為1.860 68×103kgC·hm–2,遠高于玉米(4.522 8× 102kgC·hm–2)和大豆(1.423 4 ×102kgC·hm–2)。單位產量的碳足跡也表現為單位面積碳足跡類似的情況,以水稻最高,大豆最低。大豆的碳足跡最低主要是由于其施肥量較小,以及其他農田投入品使用量低造成的。

表2 各區域主要農作物生產的碳成本
華北地區玉米的產量碳足跡和面積碳足跡都要低于小麥,即0.252 kgC·hm–2<0.476 kgC·hm–2,1 446 kgC·hm–2<2 248 kgC·hm–2,主要原因為玉米的產量水平較高,而需要的灌溉量較少。小麥碳足跡比較高,是由于其灌溉需要的電力較多。
由于地膜的使用,西北地區玉米和棉花的面積碳足跡均較高,分別為1.431 64 ×103kgC·hm–2和2.122 99×103kgC·hm–2,小麥的面積碳足跡最低,為8.165 ×103kgC·hm–2,而棉花由于農藥施用量較大,其碳足跡水平遠高于其他作物。作物產量碳足跡與面積碳足跡情況類似,仍以棉花(1.28 kgC·hm–2)最大,小麥(0.159 kgC·hm–2)最小。
由于農資投入水平較高,西南地區水稻和玉米
的面積碳足跡較高,均在1.5 ×103kgC·hm–2以上。油菜的面積碳足跡(1.002 09×103kgC·hm–2)處于中等水平,而產量碳足跡(0.543 kgC·hm–2)卻高于其他作物,主要由其單產過低引起的。
華南地區甘蔗的面積碳足跡較高,為3.841 54× 103kgC·hm–2,大于水稻的8.888 2×102kgC·hm–2。但由于其單產水平遠遠高于水稻,致使其產量碳足跡較低,只有水稻產量碳足跡的三分之一左右。
長江中下游地區玉米面積碳足跡(1.040 5× 103kgC·hm–2)高于其他三種作物,油菜產量碳足跡(0.210 kgC·hm–2)高于其他三種作物。與其他地區相比,水稻表現出了相對較低的碳足跡,說明該地區水稻灌溉等投入量水平并不高。
(二)作物碳足跡的構成因素
如圖2所示,西北地區的作物碳足跡普遍較高,主要是由地膜的使用引起的。構成華北地區作物生產的碳足跡主要為電力,這與華北平原的灌溉方式有關,其他地區的作物生產的碳足跡主要是化肥的施用。
(三)我國各區域主要糧食作物生態系統凈生產力
如圖3所示,水稻生態系統凈生產力在各區域變異不明顯,在東北地區表現最好為5.174 ×103kgC· hm–2,其次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水稻生產生態系統凈生產力為4.327×103kgC·hm–2,說明這兩個地區種植水稻具有較強的作物生產固碳能力。玉米生產的生態系統凈生產力變化較大,在西北地區最大達到5.560×103kgC·hm–2,而在西南地區只有1.768×103kgC·hm–2。小麥生態系統凈生產力同樣表現出了不同區域的明顯變化,在西北地區最高為4.271×103kgC·hm–2,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只有1.136×103kgC·hm–2。從全國平均水平來看,三種主要糧食作物的生態系統凈生產力差別不大,表現為玉米>水稻>小麥。
四、我國糧食主產區作物系統碳匯功能典型實證研究
(一)華北平原糧食作物生產的碳匯結構與功能評價
1.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足跡大小及構成
華北平原糧食作物生產系統近32年的碳足跡大小和變化趨勢見圖4。總體上,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的碳足跡呈增加趨勢,從1978年的2.926 8× 102kgC·hm–2增加到2009年的4.679 9×102kgC·hm–2,年均增長率為7.02 kgC·hm–2·a–1。
依據碳足跡在年季間的變化特征,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的碳足跡變化可分為4個時期:第一穩定期(1978—1984年,簡寫為“S1”)、快速增長期(1984—1997年,簡寫為“S2”)、第二穩定期(1997—2002,簡寫為“S3”)和緩慢增長期(2002—2009,簡寫為“S4”)。4個時期的碳足跡大小見表3,第一個穩定期的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足跡在290 kgC·hm–2上下波動;快速增長期間,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的碳足跡從2.870 2 ×102kgC·hm–2增加到4.238 2×102kgC·hm–2,年均增長率為12.69 kgC·hm–2·a–1,12年間增加了近1倍;第二個穩定期碳足跡基本停滯在4.25×102kgC·hm–2;2003年后碳足跡處于緩慢增長期,糧食作物生
產系統的碳足跡從4.233 1×102kgC·hm–2增加到4.679 9×102kgC·hm–2,年均增長5.85 kgC·hm–2·a–1,增速僅約為快速增長期的1/2。

圖3 各地區主要糧食作物生態系統凈生產力

圖4 1978—2009年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足跡的變化趨勢

表3 糧食作物生產系統不同時期碳足跡大小及構成
1978—2009年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足跡構成情
況見表3。總體上,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足跡的大小為367.81 kgC·hm–2,其中化肥、灌溉、機械、人工、種子和農藥的碳足跡分別為129.02 kgC·hm–2·a–1、105.23 kgC·hm–2·a–1、39.69 kgC·hm–2·a–1、36.66 kgC· hm–2·a–1、49.41 kgC·hm–2·a–1和7.80 kgC·hm–2·a–1,化肥所占的比重最大,約占總量的1/3,灌溉約占總量的近1/3,化肥和灌溉兩項占總量的63.69 %;機械、人工和種子所占碳足跡總量比重差異不顯著,均約占10 %;農藥所占比重最少,不足3 %。
2.糧食作物生產系統固碳量歷史動態
由圖5可知,總體上近30年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的固碳量呈增長趨勢,從1978年的1.778 91× 103kgC·hm–2增加到2009年的4.609 02×103kgC·hm–2,增加1倍多,年平均固碳量增加了91.42 kgC·hm–2·a–1。1978—2009年華北平原糧食作物生產系統中,經濟產量、秸稈和根的固碳量分別為(1251.71± 332.76)kgC·hm–2、(1394.58±378.28)kgC·hm–2和(582.29±166.16)kgC·hm–2,分別占糧食作物生產系統固碳量的38.77 %、43.19 %和18.04 %,經濟產量和秸稈的固碳量差異不顯著,但均顯著高于根的固碳量。

圖5 1978—2009年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的固碳量

圖6 1978—2009年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效率
3.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生態效率動態變化
由圖6可知,1978—2009年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的生態效率為(8.67±1.15)kgC·kg–1·CE。依據糧食生產系統碳的生態效率的變化趨勢,可以將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的生態效率分為3個時期,第一增長期(1978—1985年)、穩定期(1985—2000年)和第二增長期(2000—2009年)。第一增長期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的生態效率為(7.19±1.39)kgC·kg–1·CE,平均年增長率為0.51 kgC·kg–1·CE;穩定期碳的生態效率為(9.07±0.32) kgC·kg–1·CE;第二增長期糧食生產系統碳的生態效率為(9.27±0.58) kgC·kg–1·CE,
平均年增長率為0.19 kgC·kg–1CE。穩定期和第二增長期糧食生產系統碳的生態效率差異不顯著,均顯著高于第一增長期。

圖7 1978—2009年糧食作物生產系統碳的生態效率

表4 2004—2012年長江中下游地區雙季稻生產系統碳足跡構成 (kgC·hm–2)

表5 2004—2012年長江中下游地區雙季稻生產系統固碳量構成 (kgC·hm–2)
(二)長江中下游雙季稻作物生產系統的碳匯結構與功能評價
1.雙季稻作物生產系統碳足跡數值大小及構成變化
2004—2012年長江中下游地區雙季稻生產系統碳足跡數值大小及構成情況見表4,雙季稻作物生產系統碳足跡呈增長趨勢,從2004年的1.839 26×103kgC· hm–2增加到2012年的2.200 08×103kgC·hm–2,年平均碳足跡增加了25.9 kgC·hm–2·a–1,其中化肥、種子、農藥、農膜、灌溉和機械近十年碳足跡平均值分別為968.0 kgC·hm–2·a–1、9.9 kgC·hm–2·a–1、218.6 kgC· hm–2·a–1、35.1 kgC·hm–2·a–1、818.4 kgC·hm–2·a–1和22.2 kgC·hm–2·a–1。碳足跡構成中化肥所占的比重最大,約占總量的45 %,灌溉約占總量的40 %,兩者數值占總碳足跡的85 %左右,其次是農藥,所占比例為10.5 %,機械、農膜和種子所占碳足跡總量的比重最少,合計不足4 %。
2.雙季稻作物生產系統固碳量大小及構成動態變化
2004—2012年長江中下游地區雙季稻生產系統固碳量大小及構成情況見表5,總體上看,雙季稻作物生產系統固碳量年際間變化不明顯,年均固碳量在1.06×104kgC·hm–2上下波動。作物生產系統固碳量由籽粒、秸稈和根的固碳量組成,其中以籽粒和秸稈的固碳量所占比例較多,均占到約40 %以上,籽粒固碳量呈緩慢上升趨勢,年均增加量為14.9 kgC·hm–2·a–1,雙季稻根系固碳量相對最少,占到15.3 %左右。
3.長江中下游地區雙季稻作物生產系統碳效率動態變化
由圖7可知,2004—2012年長江中下游地區雙季稻作物生產系統碳生態效率持續大于1,表明雙季稻作物生產固定碳量大于投入碳量,農田生態系統表現為碳匯。隨著年份增加,雙季稻作物碳生態效率呈下降趨勢,由2004年的5.8 kgC·kg–1C下降到2012年的5.0 kgC·kg–1C,年均下降0.09 kgC·kg–1C·a–1,
下降趨勢并不明顯,碳匯功能保持較為穩定。
五、我國農田碳匯結構評價與優化途徑
1. 農作系統碳匯功能提升的技術方向
一是選擇優良品種,研究表明超級稻不僅增產而且利于稻田CH4的減排。二是耕作栽培的調整,研究表明增密減氮不僅穩產而且可使溫室氣體減排。增密指的是擴行縮株;減氮指的是控前促后。三是土壤增碳,研究表明有機肥增碳明顯,但常規的秸稈還田、免耕、大豆輪作的增碳效果不顯著。
2. 各區域作物生產減排需要因地制宜
通過對我國各區域主要作物生產的碳成本的構成分析,針對性地提出各區域作物生產節能減排的重點。
東北。水稻生產碳足跡明顯高于其他兩種作物,該區域應當在優化生產技術減少化肥和農膜的基礎上重點研究采取高效的灌溉措施,提高效率減少灌溉等的耗電量,降低水稻生產的碳足跡。
華北。小麥、玉米系統生產的碳足跡主要可以通過提高灌溉效率和肥料利用效率來實現區域作物生產的碳成本的減少。
西北。該地區減排的重點應在減少農膜、化肥以及農藥的使用量,提高效率,降低該區域棉花、玉米、馬鈴薯生產的碳足跡,尤其棉花通過優化農膜的使用而減少碳足跡的潛力明顯。
西南。各主要作物的生產碳足跡差別不明顯,且都主要為化肥投入貢獻,該區域應當重點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減少作物生產的碳足跡,降低碳成本。
華南。該區域減排重點應在研究如何減少作物生產的化肥投入量,降低甘蔗,水稻生產的碳足跡以降低區域作物生產的碳成本。
長江中下游。本區域通過減少肥料和農藥投入而實現減排的潛力較大,應當重點提高其利用效率減少實物使用量。
六、提高我國作物固碳減排能力的建議
(一)提高區域固碳減排能力
1.發揮宏觀布局與調控的作用
應對氣候變化,調整我國作物優勢產業區(帶),將耗水作物南移,高效水分利用作物北移、西移;在滿足國家進口糧油產品需求的前提下,鼓勵進口高碳產品、高水足跡產品、低廢棄物產品。
2.加強抗逆研究與成果應用
加強抗逆種質資源,特別是抗旱種質資源的挖掘,培育抗旱高產品種、推廣抗旱品種;加強抗旱栽培技術研究并加大推廣力度,包括節水、保水、蓄水技術,以增加作物種植面積、提高作物單產,實現固碳減排。
(二)提高碳生產效益
1.技術推廣和政策扶持并重,穩定南方雙季稻種植面積,開發利用南方冬閑田
要推進冬閑田開發的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體系,構建支持以發展冬季農業為導向的專業合作組織,提高社會化服務水平和訂單農業,切實保障冬季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建議切實增加南方冬閑田開發利用的科技研發和技術推廣投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土地流轉,實施冬閑田開發利用專項補貼和政策性保險制度,促進作物面積,特別是多熟制面積的增加,增強碳匯的功能、提高碳生產的效率。
2.推進水稻–小麥、小麥–玉米、水稻–油菜等主體種植模式的全程機械化進程
有效推進農業主產區水稻–小麥、水稻–油菜、小麥–玉米等主體種植模式的全程機械化生產,完善農田全程機械化周年高產技術集成、作物秸稈還田配套耕作機械及種植方式、栽培耕作技術等,是現階段我國耕作制度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建議加大相關技術研發和示范推廣力度,在糧食、油料主產區快速推動作物生產全程機械化進程,促進主體種植模式的發展,提高碳匯功能。
3.建立聯合攻關機制,實現主體種植制度的節本高效
結合國家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及商品糧基地建設,建立聯合攻關隊伍,研究制定相應的技術規程和技術補貼政策,將多熟高產高效、秸稈還田與地力提升、旱作節水與養分管理等集成配套,探索建立適合不同類型區域的資源低耗高效耕作制度,增加生物產量,提高碳匯功能。
4.重視南方水網密集地區的環境保護型耕作制度建設
在農業面源污染嚴重的水網密布農區,要在確保高產高效前提下進行作物周年優化配置,進行農
田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有毒物質阻控和消減綜合控制、農田流失性養分減排,構建環境友好的標準化種植模式與技術規范,建立基于生態補償機制的新型環保型耕作制度。
(三)提高產后碳利用的效率
1.啟動實施國家秸稈成型燃料產業示范工程
選擇秸稈資源能源化利用基礎條件較好、市場需求量大的地區,建設一批秸稈成型燃料產業開發示范點,培育一批秸稈成型燃料龍頭企業,支持關鍵技術和設備升級研發與示范應用。
2.采取財政補貼措施引導農戶使用秸稈成型燃料
將秸稈成型燃料設備、配套爐具和使用成型燃料的農戶納入財政轉移支付補貼的范圍,引導和鼓勵農民使用節能爐具和成型燃料,擴大農村生物質能源的消費需求。
3.適當降低秸稈成型燃料企業補貼的政策門檻
調減秸稈能源化利用補貼企業的注冊資金和秸稈量的消耗量標準,使大、中、小秸稈成型燃料企業都能夠納入財政的補貼范圍,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到秸稈成型燃料產業,快速壯大這一新型產業的發展。
[1]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董紅敏, 李玉娥, 陶秀萍. 中國農業源溫室氣體排放與減排技術對策[J].農業工程學報, 2008, 24(10): 269–273. Dong H M, Li Y E, Tao X P. China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its mitigation strategy [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08, 24(10): 269–273.
[3] 李穎,葛顏祥,劉愛華,等. 基于糧食作物碳匯功能的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 2014, 35(10): 33–40. Li Y, Ge Y X, Liu A H, et al.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based on the carbon sink function of grain crops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4, 35(10): 33–40.
The Current Carbon Sink Structure of China's Staple Crop Production and Its Optimization Approach
She Wei1, Huang Huang1, Guan Chunyun1, Chen Fu2, Chen Guanghui1
(1. Southern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rain and Oil Crops in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The global warming caused by heavy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has posed a great threat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carbon sink function of crops has an important regulating effect on climate changes. Actually the production of crops can be seen as the carbon source as well as the carbon sink.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gather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carbon emission parameters of the staple crop production system in China, estimate the carbon sink effect of farmland and its dynamic change feature 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carbon input and output of these crop production systems. In this way, the paper provides a basis for making the low-carbon agriculture planning and policies and proposes the approach to optimizing the carbon sink structure of the farmland in China.
crop; carbon sink; carbon emission; optimization ways
S3
A
2016-01-05;
2016-01-09
佘瑋,湖南農業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作物學;E-mail: clregina@163.com
中國工程院咨詢項目“我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碳匯結構現狀與優化途徑”(2014-XY-33)
本刊網址:www.engin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