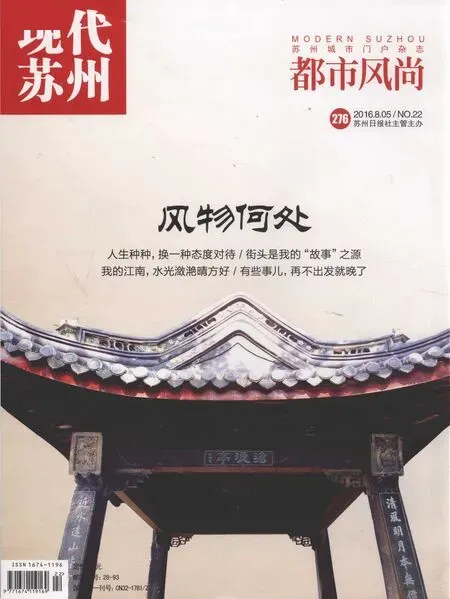愛蘇州,怎能忘了那一曲吳儂軟語
記者 陶瑾
愛蘇州,怎能忘了那一曲吳儂軟語
記者 陶瑾

古老的山歌只有被一代代人傳唱,才能獲得生命力
炎炎夏季,聽一首能夠“解暑”的歌那該有多棒!這歌,不是當下的流行音樂,而是傳統的樂曲,比如咱蘇州老百姓原汁原味的“山歌”。她,軟糯清麗,含蓄纏綿,讓當代人的心能夠沉淀,靜下來。
“啥個飛來節節高,啥個飛來像雙刀?啥個飛啦青草里畔,啥個飛過太湖梢?叫天子飛來節節高,燕子飛來像雙刀,野雞飛喇青草里畔,水湖鷺飛過太湖梢。”白洋灣山歌是吳歌的一個分支,這首“盤答歌”,刁鉆的問,妙趣的答,加上山歌手天然質樸的唱腔,聽來讓人回味無窮。
古老的山歌只有被一代代人傳唱,才能獲得生命力。從山歌到吳歌,其中的歷史、流變不得不談。當孕育山歌的自然環境逐漸喪失后,吳地山歌又是怎樣一路艱辛從歷史中走來的呢?
吳歌史話
如果提起一些老歌,恐怕連今天的80后、90后都能哼唱一兩句出來,比如《四季歌》、《天涯歌女》。這些民國時期乃至于今天流行的動聽旋律,最初都源于太湖流域的山歌,或者叫做吳歌。
吳歌,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水鄉吳地民歌民謠的總稱,多是人們田間勞動休息時創作的。它清新、拙樸,表達著民眾的意愿和情感。吳歌口口相傳,代代相襲,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蘇州藝壇上的昆曲、評彈、蘇劇,其淵源都離不開吳歌。
吳歌的歷史源遠流長。古時候的吳地土著是越人,說著百越語。從《越人擁楫歌》的越漢對譯中可以看出其非漢語,不過這首歌卻當之無愧地成為了吳地歌謠的“先祖”。《楚辭·招魂》中有“吳歈蔡謳,奏大呂些”的記載。歈,歌也。“吳歌”的名稱在戰國時第一次出現。雖然我們今天不知道當年吳歌的模樣,但這肯定了吳歌的開始。
到了魏晉南北朝,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時,將搜集到的吳歌編入《清商曲辭》的《吳聲歌曲》中,以《子夜歌》最具當時民歌的特點。這是吳歌的第一次高峰。到了明朝末年出現吳歌的第二次高峰——馮夢龍的山歌。馮夢龍,蘇州人,他對吳歌的搜集和整理做過很大貢獻。他編了《掛枝兒》、《山歌》等民歌專集,有許多篇幅都是謳歌勞動人民生活與愛情的優美詩篇。
清末民初,吳歌日趨繁衍發展,保存了大量的長篇敘事吳歌,曲調也更為豐富多彩。20世紀80年代以來,吳歌得到了大量的搜集、整理、研究,特別是長篇敘事吳歌的發掘。吳江蘆墟山歌手陸阿妹唱的《五姑娘》長達兩千多行,曾轟動一時。
進入21世紀,有關部門又編輯出版了《白茆山歌集》、《蘆墟山歌集》、《吳歌遺產集粹》等吳歌口述和研究資料。2006年,吳歌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經過幾千年的傳承演變,吳歌早已經滲透到當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見景而歌,遇事而歌,勞作而歌。

吳歌早已經滲透到當地百姓的生活里,隨時隨地見景而歌,遇事而歌,勞作而歌
蘇州也有“山歌帶”
山歌是百姓的歌,誕生于人們的生產勞動,并在日常生活中豐滿成熟。唱山歌是那個年代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逐漸成為勞動時“沖困懶”、“同心力”的一個法寶。“山歌”的“山”實際上點出了歌的質樸、真實和濃郁的鄉土氣息。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風情唱一方歌。魚米之鄉的江南蘇州,形成了幾種不同地域文化的山歌流派。
白洋灣山歌
白洋湖畔,阡陌縱橫、水網密布,千百年來,居民世代進行著“三耕”(稻耕、魚耕、花耕)勞作,造就了百姓純樸的性格,也孕育了清新軟糯的白洋灣山歌。
一曲山歌,傳唱不絕。白洋灣山歌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時期。如今白洋灣流傳的山歌大多是清末至民國間的作品,比較老的山歌基本以兒歌、情歌為主。如膾炙人口的《月子彎彎照九州》,至今已有八百多年歷史。大部分山歌雖無法考證其確切成歌年代,但可以從歌中情節或者風物推測其流傳的大致時代。比如《十二月花開》唱到“長毛、忠王”大概知道成歌于清末。
據白洋灣街道文化站的實地調查結合以往資料,發現白洋灣山歌是蘇州城北“陽澄——陽山”山歌帶上的重要一環,在街道轄區內主要分布在北部的申莊、新漁、張網、顏家等村。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民進城,漁民上岸,花農也沒有地種花了,如此一來,山歌賴以生存的“土壤”在消失。于是,從2008年開始,街道文化站對山歌進行挖掘和整理。深入田間地頭和村民家里,采用現場錄音的方式采集山歌。兩年多來,累計尋訪山歌手70余人,搜集山歌200余首,特別是記錄到了“趙圣頭”、“日落西山洋知哥”等敘事長歌,填補了民間敘事長歌的空白,采取記詞、記音、記譜“三合一”的方式,原汁原味保留了山歌風范。
為了讓山歌文化真正走進當代生活,白洋灣街道還成立山歌研究會,組織山歌表演隊,出版山歌專著等,并開設了山歌傳承班,開展“娃娃學山歌”活動。十幾位老歌手走入課堂,幾十首白洋灣山歌在孩子們的心中生根發芽。

蘆墟山歌參加文化部在武當山舉行的第六屆中國原生民歌大賽(最中間為楊文英)
蘆墟山歌
“嗚哎嗨嗨,嗚哎嗨嗨嗨——”
這是鱸鄉吳江特有的山歌調。那一聲聲曲調,像小河流水,像空谷鳥鳴。這就是蘆墟山歌。據史料記載:蘆墟山歌始于明,盛于清,清末民初,是蘆墟山歌最興盛的時候。分布于原蘆墟鎮和環分湖四周的鄉鎮以及滬浙毗鄰地區鄉村。
蘆墟山歌究竟有多豐富?作為吳歌中一個突出品種,蘆墟山歌竟然有七種曲調:滴落聲、落秧歌、大頭歌、羊騷頭、嘿羅調、急口歌、平調。蘆墟山歌在吳江人智慧的長河中,有著水鄉人生活的節律、吳地文化的呼吸、太湖風俗的氣象……
西晉詩人張翰癡迷家鄉的鱸魚和莼菜,是否聽一曲蘆墟山歌獲得靈感?詩壇巨擘柳亞子年少時往返汾湖,是否在悠悠漂蕩的船上吟幾句詩、吼幾聲蘆墟山歌呢?
陽澄漁歌
阿公站船頭,甩開膀子,緩緩劃槳向湖中,一搖一推間,清亮的嗓音敲開了暮色的沉寂。你方唱罷,站在船尾的阿婆,順勢接上,一邊整理漁網,一邊以歌聲回應,你來我往間,盡顯濃情蜜意……漁歌唱晚,漁家人曾經最熟悉的場景,現下仍在陽澄湖一帶傳唱。
陽澄漁歌,是吳歌的一個支脈,以其委婉的曲調和吳儂軟語的聲腔形成了鮮明的地方特色。陽澄漁歌分為地方風情歌、勞作歌、苦歌、戲文山歌等。形式為獨唱、男女對唱和一人領唱眾人伴唱。短的為四句或十來行,長的一般不超過百行。
這兩年,陽澄湖鎮組織年長的漁歌手帶著年輕人,學唱漁歌、改編漁歌,試圖讓流傳了千年的漁歌,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口味,一代代傳唱下去。
白茆山歌
在常熟古里鎮塢坵村秀麗的白茆塘畔、塢坵山旁,一群頭戴斗笠、手戴袖套的男女在田間一邊插秧一邊對唱山歌,山歌聲伴著歡聲笑語響徹田野,再現了當年蒔秧山歌的場景。
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吳歌的杰出代表,常熟白茆山歌至今傳唱了已有4500多年歷史。先后走進北京城,唱進中南海,多次出國交流。
以前白茆山歌,家家戶戶會唱,現在唱的越來越少。好在當地政府早就開始對白茆山歌進行保護傳承,在幼兒園、小學課程中加設白茆山歌的教程,從娃娃開始培養對山歌的喜愛。
……
吳地山歌今何在
曾有人評價吳歌的意趣不外乎“語言、風土、藝術三項”,而這三項正是民族文化的靈魂。蘇州市民間文藝家協會顧問、江蘇省吳歌學會會長馬漢民對此深以為然,他說吳歌是山歌,沒有訣竅,唯有積累。“這種用方言演唱的地方小調,若失去了土味,不貼近百姓就無意義了。吳歌不是‘陽春白雪’,而是普通百姓自己的‘下里巴人’。”
然而,山歌是百姓的歌,也是時代的歌,要讓更多年輕人喜歡才是正道。因此,在變與不變中探求平衡,創作“新吳歌”也是值得深思的。
聽聽蘇州“好聲音”楊文英:從吳江田頭唱到央視舞臺
過去,百姓邊干農活邊唱山歌,或隔田隔港放聲對歌,其樂無窮。對于這樣的場景,吳歌國家級非遺傳承人、蘆墟知名山歌手楊文英記憶猶新。她說,那個年代,沒有廣播,沒有娛樂設備,山歌成了勞動人民抒發情感的主要方式。
“山歌勿唱忘記多,搜搜索索還有十萬八千九淘籮,吭嗨吭嗨,扛到吳江東門格座垂虹橋浪去唱,壓坍仔格橋墩塞滿東太湖……”當69歲的楊文英唱起長篇敘事山歌《五姑娘》的歌頭,一陣淳樸、自然、清新的田野之風撲面而來。
楊文英說,她的山歌是聽會的。楊文英上小學時,學校里有個叫陸阿妹的校工,她是浙江人,后來嫁到吳江。她隨口哼唱的悠揚山歌調吸引了楊文英。由于對山歌十分癡迷,每逢周末、寒暑假,她都會來學校聽陸阿妹唱山歌。久而久之,那些旋律、歌詞就深深印在了楊文英的心里。
陸阿妹肚子里有唱不完的山歌,上世紀80年代,吳江文化部門發掘、整理的長篇敘事山歌《五姑娘》,就是由陸阿妹演唱的。1997年,楊文英從企業退休后,進入蘆墟鎮文體站成為一名文化志愿者。近年來她致力于蘆墟山歌的收集、整理、傳唱和教學工作。
1997年,蘆墟實驗小學開辦少兒山歌班,楊文英義無反顧地擔任起山歌班校外輔導員。一屆一屆的山歌班畢業了,到今年,楊文英教過的學生早已數不清。
“山歌不能總活躍在中老年人的生活中,為了讓更多年輕人,特別是中小學生喜歡蘆墟山歌,我們在山歌的傳承方式上,一方面堅持原生態山歌的保護與傳承,把原汁原味的蘆墟山歌傳授給學生;另一方面,保留蘆墟山歌的精髓,對山歌曲調進行適度改編,在唱法、表演上更多元化,并且編排、設計與山歌相吻合的舞蹈、服裝,讓山歌更容易被現代人所接受。”楊文英告訴記者。
保持原生態唱法受到專家肯定,改編后的新山歌又受到了觀眾的歡迎。根據蘆墟山歌編排的《水鄉飛出金鳳凰》、《蘆墟風情歌》等先后獲得吳江、蘇州市的大獎。2014年,由楊文英主唱的蘆墟山歌《夢里吳歌》亮相央視中秋晚會,向全球觀眾展示了蘆墟山歌的魅力。
眼下,楊文英還在挖掘、整理一些失傳的蘆墟山歌曲調,她想盡全力恢復這些原生態的民間聲音。“吳歌的生命力是有的,但會慢慢弱化,這是不可扭轉的社會現象。我們要做的,就是讓它活態傳承。”楊文英坦言。

在朱文華夫婦的努力下,沉寂多年的陽澄漁歌又在姑蘇大地上傳唱開來
朱文華、蔡金娣:因歌結緣的“吳歌夫妻檔”
早就聽說蘇州相城區有對“吳歌夫婦”——朱文華、蔡金娣。因歌聲結緣的他們,十幾年來,一直致力于收集、傳唱陽澄漁歌,在他們的努力下,沉寂多年的陽澄漁歌終于又在姑蘇大地上傳唱開來。
撥通朱文華手機時,接電話的是老伴蔡金娣:“我們在演出呢。你聽,老頭子正在臺上唱呢。”“姐在河邊洗青菜,郎在對河采紅菱……”聽筒里,傳來了朱老那悠揚的歌聲。
朱文華和蔡金娣同年出生,今年都是71歲。當年,朱文華的父親是地方上有名的文藝骨干,他從小就跟著父親的劇團跑碼頭,學會了不少吳歌。蔡金娣從小也是個“吳歌迷”,長大后,兩人都成了村上的文藝骨干,經常一同外出表演。就這樣,兩人在歌聲中相識、相戀,結為伉儷。
由于一些客觀原因,陽澄湖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后就慢慢沉寂了下來,會唱的人越來越少。面對這一情況,朱文華和蔡金娣心里挺不是滋味,兩人一合計,決心把“失傳”的歌聲唱起來。1993年,夫妻倆成立了一個業余文藝隊,節假日走上街頭唱吳歌、打連廂、挑花籃,每次總能吸引一大群老老少少。
在為鄉親們表演的同時,他們不忘收集吳歌。四處尋訪,聽到哪個老人會唱就登門請教。幾年下來,兩人收集整理了200多首流傳在陽澄湖地區的吳歌。他們把這些曲調都記錄了下來。朱文華自己還創作了幾首吳歌,如《陽澄湖大閘蟹開捕節民間蟹歌》、《社區就是我的家》等,表現了當代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他們還應邀走進小學,教唱陽澄漁歌,為學生編寫《媽媽的孩子聽黨的話》等不少民間小調。
顧鳳珍:清音流芳,一把好嗓子唱盡百年故事
“頭一只臺子四角方,岳飛槍挑小梁王。第二只臺子湊成雙。轅門斬仔楊六郎……”當顧鳳珍唱起這首《十只臺子》的山歌,記者著實感受到了白洋灣山歌的味道。她告訴記者,這是一首詠史山歌,借臺子起興,每段唱的都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歷史故事。
作為蘇州市第四批非遺文化傳承人,顧鳳珍是白洋灣地區一位名符其實的“山歌達人”。“小時候,家里人下地、打草鞋時都會對唱山歌來提神,有時一天要干十幾個小時的農活兒,不唱山歌哪來的勁。”顧阿婆回憶,“上世紀七十年代,白洋灣地區幾乎家家戶戶的老一輩人都會吟唱山歌。父親是山歌迷,高興時可以連唱好幾個鐘頭。那時候打草包、草鞋,父親總會唱山歌,頓時睡意全無,于是就能多干點活。夏天晚上在外邊乘風涼,幾家人坐在一塊聊天,這時候也會唱上幾首山歌互動一下!”
就這樣,她從父親那里聽會了好多首山歌,并牢記于心。后來又從家里的長輩那學了一些山歌,再加上自己長期的搜集整理,最多的時候,她會唱各類題材的山歌200多首。
目前,白洋灣地區的山歌手有十多位,顧鳳珍今年65歲,是其中年紀最小的。前幾年,她和村里其他幾位“山歌手”,跑遍村里每一戶,尋訪每一位老人,還跑到黃橋等地搜集山歌。在街道文化站的幫助下,他們搜集整理出了260余首流傳鄉間的白洋灣山歌。
2009年白洋灣街道文化站首次開展“山歌傳承活動”,每年顧鳳珍都會走進校園、社區,教唱山歌,通過“娃娃學山歌”、“山歌文化進校園”、“山歌文化進社區”等形式,讓更多人了解原生態的白洋灣山歌。
“我想用這種最傳統的口口相傳的方式,把我會的山歌教給年輕一輩,讓他們繼承白洋灣地區的這一民俗文化。”顧鳳珍坦言。

顧鳳珍是白洋灣地區一位名符其實的“山歌達人”

陳巧娥每年要教不少孩子學唱白洋灣山歌
陳巧娥:會唱山歌會編扇的“巧手”阿婆
陳巧娥原是白洋灣張網村人,村里深厚的山歌文化底蘊熏陶了這位嗓音清亮、溫柔綿長的山歌手。如今她住進新小區,也把白洋灣的山歌唱進了城市。
她最拿手的是《十送郎》,“送啊我的郎,送到你梳妝臺。送啊我的郎,送到你出房門……”這是一首離別情歌,三步一回頭,唱的是送別情郎時的依依不舍。
“記得那時候,父親去吳江平望、八坼做生意,我和姐姐一起搖著船去看父親。姐姐在船上燒飯,等父親晚上回到船上,我們邊吃飯,邊聽父親唱山歌。”父親的一首《新打龍船剃包頭》至今讓陳巧娥印象深刻。
十幾歲在田里收小麥、拾麥穗、挑麥種,她就會唱好多首山歌了。到現在能完整唱出來的山歌大約有五六十只。如今,陳巧娥也是白洋灣“山歌班”的一個老師,每年要教不少孩子學唱老山歌。
不僅如此,陳阿婆還會手工編織麥秸扇。十幾歲就開始跟著家里人做麥秸扇,做好的成品拿到景區賣。“當時一個村民小組有三四十家,家家戶戶都會做麥秸扇,而現在基本沒人會做了。”陳阿婆略帶惋惜地說:“這也算是家里的祖傳手藝,但到我兒媳這里,已經不會做了。”為此,她很愿意像教山歌一樣,呼吁年輕人來學傳統手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