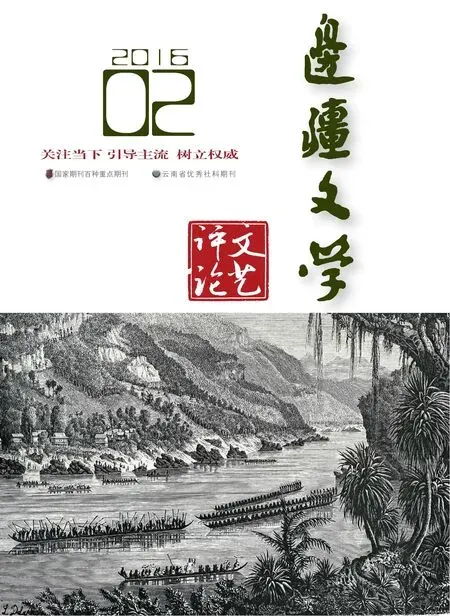獨特地域下的女性書寫
——以汪曾祺《大淖記事》為例
◎楊 雨
獨特地域下的女性書寫
——以汪曾祺《大淖記事》為例
◎楊 雨
汪曾祺先生創作的《大淖記事》,給我們展現了一幅充滿田園牧歌式的生活畫面,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不小的震動。在作品中,作者以一群生活在大淖東頭的女性為表現對象,用充滿詩意的語言表現了她們對生活的樂觀心態。小說中所表現的人物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敢愛敢恨的普通勞動人民,作品寫出了她們的勤勞和勇敢,同時,對她們在生活中所謂“有傷風化”的行為也進行了肯定性的描述。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洗禮之后,作家們都不同程度地對“文革”期間的錯誤進行了反思,“文革”期間文學中失掉的人性,成為這一時期的重點表現對象。《大淖記事》是汪曾祺先生為我們展現的一幅充滿生活情調的民間畫卷,而作品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意蘊,無疑是《大淖記事》最有魅力的書寫。
一、女性書寫界定
女性書寫作為伴隨著女性主義崛起后的一種書寫方式,它本身是對女性本體存在的確認,同時也是對以男性主導下形成的話語權的挑戰。在以男性為主宰的社會中,男性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各種生存的話語權,使男性社會活動中形成的價值判斷成為左右社會的價值判斷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女性具有壓迫性的“父權制”。“父權制”確保男人對女人實行統治的各種制度及相應的價值觀念,父權制是普遍的、無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中,并非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婦女的解放并不是國家在法律上承認婦女的權利后就能實現,也不是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領域、一切社會體制中改變男女之間的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1]“父權制”使男性在社會及家庭中占有絕對優勢,男性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制定出一系列能夠體現自己意志的,能夠使所進行的活動順利完成的規則。這些規則,對于男性來說,可以以性別優勢,順理成章地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和裁判者。而作為弱勢群體的女性,只能作為男性社會下的附屬品,既沒有參與男性活動的權利,也沒有切實可行的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途徑。
由此可見,男性主宰下的社會對女性帶來的壓迫是無所不在的,為此,女性的反抗在男性建構的話語體系下顯得富有挑戰。女性文化運動的方向,不是要向男性看齊,而是要認清自身的女性品質——被男性文化壓制、排斥了的“女人性”。[2]西美爾認為,女性“更傾向于獻身日常要求,更關注純粹個人的生活”。[3]這樣的書寫模式在林白、陳染等作家的作品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女性書寫更關注女性的主體性建構,用自身的體驗和感知創造一種有別于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
同樣,男性作家筆下也表現出類似的女性書寫,就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記事》來說,他對女性的書寫沒有女性作家那樣的激進和具有批判性,他將女性置身于作家創造的美的世界中,通過女性形象的生動塑造來表現出男性作家筆下女性的生活狀態。自古以來,生活于以男性為主導力量的社會中,女性都在以自身的生存狀態表現出對男權社會的反抗,只是在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下,這樣的反抗是不自覺的。汪曾祺將《大淖記事》的背景設置在一個遠離喧囂的鄉村世界,目的是通過鄉村世界的寧靜和淳樸,將人生存的原本狀態還原出來。通過一個遠離社會主流的生存環境,使女性對欲望的追求合理化,其人性美的創作傾向得到彰顯。作家將一系列女性的生存狀態置于一個沒有道德禮教束縛的世外桃源中,透過女性的“男人化”書寫,張揚了女性的主體性,使男性的主體地位被架空。
二、女性書寫的獨特性體現
(一)女性書寫中的男性缺場和女性獨特性的表現
在《大淖記事》的女性書寫中,男性的存在是被刻意消解了的,被置于一種可有可無的狀態。正如文章所言:
“這里的姑娘媳婦也都能挑。她們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挑鮮貨是她們的專業。大概覺得這種水淋淋的東西對女人更相宜,男人們是不屑于去挑的。”這樣的描述,無疑是把女性“男人化”,通過女性“男人化”的書寫方式,把男性在社會中的支配地位架空,以達到解構男權社會的目的。又如:“她們像男人一樣的掙錢,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路來一陣風,坐下來兩條腿叉的很開。……打起號子來也是‘好大娘個歪歪子咧!’——‘歪歪子咧……’”。
在以男性為主導力量的社會中,女性的主體性總是被忽略,不被社會予以重視,而男性的主體性卻與社會生活融為一體,制約和影響著社會中的所有活動及其形成的后果。《大淖記事》對女性的“男人化”書寫,打破了男性在社會活動中的主體地位,架空男性主導權的同時,使女性的強勢面得到體現。當然,汪曾祺也注意到了女性所具有的獨特性:“這些‘女將’都生得頎長俊俏,濃黑的頭發上涂了很多梳頭油,梳得油光水滑(照當地說法是:蒼蠅站上去都會閃了腿)。腦后的發髻都極大。發髻的大紅頭繩的發根長到二寸,老遠就看到通紅的一截。她們的發髻的一側總要插一點什么東西。”女性所具有的“女性美”在作品中也得到了足夠的重視。小說通過作品中的男性缺場和女性具有的獨特美的書寫,顛覆了以男性主宰社會的傳統觀念,消解男性主體地位的同時,使女性的主體性得到彰顯。
(二)對“賣弄風情”的獨特敘述
獨特的地域和鄉土風情,使女性具有了彰顯女性本色的舞臺,通過對女性形象的細致且傳神的刻畫,使女性美在作品中得到表現。尤其是巧云形象的塑造,成為表現女性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品以充滿鄉野氣息的大淖,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作為女性本該有的生活狀態:“這里人家的婚嫁極少明媒正娶,花轎吹鼓手是掙不著他們的錢的。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們在男女關系上是比較隨便的。姑娘在家生私生子;一個媳婦,在丈夫之外,再‘靠’一個,不是稀奇事。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準:情愿。有的姑娘、媳婦相與了一個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錢買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們的錢,反而把錢給他花,叫做‘倒貼’”。作者以男權社會下形成的言說方式。表現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該有的與傳統女性不一樣的生存狀態:她們像男人一樣會爆粗口,享受著勞動帶給她們的快樂,無拘無束,毫無顧忌,把“小家碧玉,大家閨秀”的古訓褻瀆得一文不值。除此之外,她們在男女關系的自由,也使傳統的婚嫁習俗徹底無用:媳婦不用媒人說媒,自己便會跑了來,可以在家生私生子,即便結了婚,在外頭還可以靠一個男人,管他們要錢花,或干脆給他們錢花。諸如此類的敘述,作者從男性的視角出發,將本該屬于女性的權利交還給女性。一改往昔女性處于被壓迫、被附庸的局面,使女性從傳統的貞潔觀念中解脫出來,對自己的身體享有支配權,即以情愿的方式選擇伴侶。私生子、出軌等被看作是女性身上最骯臟、最邪惡的代名詞,使諸多女性成為貞潔觀念的殉道者,按男性社會賦予她們的“貞潔”苦苦度日,而男性則可以為所欲為。汪曾祺通過女性生存狀態,將女性在男權社會下享有的權利獲得了實現。甚至作者自己以敘述者的口氣說:“因此,街里的人說這里‘風氣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風氣更好一些呢?難說。”
作品成功塑造了巧云這一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了作為一個女性本該具有的“女性之美”,這也使得她成為眾多男子追求的對象,作品中的巧云,已然實現了女性在男女關系上由被動轉為主動的顛覆。巧云與十一子的愛情承續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古訓。不同的是,作品中的巧云對自己身體的認知已擺脫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成為了一個具有女性意識的新女性:內心深愛著自己的戀人,卻能把自己的身體交給別的男人,這本身就是對女性“貞潔觀念”的挑戰。在特定地域下形成的女性意識,是一種男性視角下的女性書寫方式,而作為巧云來說,通過支配自己的身體,達到自己對欲望的渴求。
女性通過打扮自己,讓自己從外表看起來美麗動人;通過肢體語言和嫵媚動作的展現,讓女性在近似游戲的狀態中使男性沉浸在對異性的渴望當中。“一個東西之所以對我們來說充滿魅力,令我們渴望,經常是因為它要求我們付出一定代價,因為贏得這個東西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需要付出犧牲和辛勞才能成就的事情。這種心理轉變的可能性導致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發展成了賣弄風情的形式。”[4]的確,女性越是徘徊于由肯定與拒絕形成的中間狀態中,越發使男性對女性具有好感,越能在兩性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女性通過移開注意力,從事其他活動,使關注者(男性)感覺到她的美無處不在,以至于讓追求者甘心徘徊于其左右,或甘心為其承受一切。
(三)男性社會下性別的相對與絕對
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兩類男性:一類是以代表了正義和道德的錫匠群體,他們秉持著男性社會的道德準則,以“仁義”作為做人行事的準則。另一類是一群住在煉陽觀里的水上保安隊員,他們雖擔負著保衛大淖水上安全的責任,卻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作者之所以要安排這兩類截然相反的男性形象,一方面是在書寫男權社會下男性的生存狀態,強調對正常秩序的遵守和對責任意識的擔當。另一方面,也在強調作為一個普通人所該有的生存狀態。以老錫匠為代表的錫匠群在小說始末都在堅守著人所該具有的道德準則。但另一類男性代表劉號長之流,他們雖然在人欲上體現出不懈的追求和敢于實現的勇氣,可是,男權社會下形成的痞子習氣,使他們在犯了大錯后選擇了逃避,暴露男性社會下男人的虛偽和懦弱。小說中,筆者看到的男性是一個逐漸被弱化的男性,雖然責任意識的強調在作品中有所體現,但這種意識是被弱化的,在其背后隱喻著作者對女性意識的彰顯。
女性形象,不論是作為特殊環境下的女性團體,還是作為以巧云為代表的具有女性意識的新女性,她們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彰顯出作為一個女性本該有的“女人性”。她們享受著性別帶給她們的優越感,能夠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之事。但是,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作者設計十一子和劉號長沖突的深層內涵:巧云內心深愛著十一子,作為報答,只想把自己的身子交給十一子。可是,巧云的身子卻偏偏給了一個帶有痞子氣的男人,巧云表示接受的同時,這種身體上的交易維持了一段時間。當然,巧云并非毫無顧忌,由于對十一子的愛戀,使她產生了深深的愧疚之心。最終導致了十一子與劉號長的直接沖突。
女性的人性美,主要通過其身上具有的“女人性”體現出來,而且,在社會生活中,女性對女性的認知不會因為何種原因而遭到質疑。但是在男性社會中,女性是被制造出來的。因此,社會價值判斷傾向于男性一方就變得不那么難以理解。筆者認為,汪曾祺筆下的女性書寫是以男性的眼光來審視男性社會中女性的生存狀態,無論是對于獨特背景下的女性群體的書寫,還是作為獨特個體的女性書寫都是如此。巧云和十一子的結合本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雖然心靈的相通,也沒能實現巧云的心愿(將自己的身子交給十一子)。女性意識使巧云有權利支配自己的身體,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但是,傳統觀念始終在巧云的內心回蕩,使她在與劉號長的私會中對十一子心懷愧疚。當十一子與巧云的事被劉號長得知后,十一子對巧云發自內心的愛卻成為了男女關系上的受害者。由此可見,在肯定女性勇于追求自由,敢于挑戰男性權威的過程中,作家還是持男性立場,肯定男性社會中女性應有的生存狀態。
綜上所述,《大淖記事》的女性書寫,始終以男性視角下的女性生存為關照對象,肯定女性在男權社會中該具有的女性生存權利。通過作品中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對比,意在對男性社會中的男性生存狀態的貶抑,以此達到張揚女性主體性的目的。當然,作家在對女性書寫時加入了主流價值判斷的因素,使筆下的女性去掉了女性書寫中本該具有的激進和挑戰性,而變得溫婉和富有人文關懷,這也是汪曾祺筆下女性書寫的獨特之處。
三、結論
眾所周知,作家的創作和時代背景有著深刻的聯系,也就是說,文本的產生與社會是分不開的,它間接地反映了時代思潮和社會走向。“文革”十年的沖擊,將人本該具有的自由抹殺殆盡,當人們沉浸在對“文革”進行反思時,汪曾祺卻為我們創造了一個遠離喧囂的鄉村世界,并且表現了一群不受傳統道德束縛,自己對自己具有絕對掌控權的女性形象,這除了響應當時提倡“人性復歸”的呼聲,還體現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逃離。“大淖”是一個沒有被道德文化熏染過的鄉村世界,在某些布道者眼中,這種生存狀態是一種有傷風化的,不道德的,因為作品中的“大淖”女人所具有的種種“不良風氣”。但是,作家的創作目的并不在于對這一種風氣的展覽式的賞玩,而是要通過這些充滿野性的女性表現一種與傳統觀念迥異的生存狀態。即沒有禮教的束縛和三綱五常的硬性規定,沒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嫁習俗的制約。她們可以僅憑自己的意愿享受女性所該有的快樂和自由,而不用去顧及旁人的看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種傾向可視為80年代“尚古主義”思潮的思想淵源之一,這一思潮“反對現代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和束縛,轉而崇尚古代社會以及現代社會中相對落后地區的生活狀態和民風民俗,贊賞那種狀態中人們無法無紀、無拘無束、為所欲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兩性關系上的自由放縱,以為這才是沒有受到現代文明污染的人性的本真”。[5]
汪曾祺以男性的視角對男權社會下女性生存狀態的書寫,摒棄了以往男性作家眼中表現女性的傳統套路,用溫婉、平和的方式書寫女性在男權社會下的生存。這種獨特的書寫方式顯然是對長期積淀下來的男性對女性書寫方式的反叛,這種反叛還可以在汪曾祺此前所創作的作品中得到印證。作家將另類女性作為書寫對象,放棄當時大部分作家所堅守的創作理念,這種創作姿態是作家對主流創作意識反叛,在創作上擺脫的公式化傾向。從隱性層面看,《大淖記事》是作家對主流意識介入文學創作的一次實踐,為當時的讀者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文學世界。
對于當下流行的下半身寫作、身體寫作等以女性視角來對女性本體的書寫,以女性本身具有的獨特性將女性的生存狀態赤裸裸地呈現給世人,通過對女性本體的認知達到對男權社會的解構,這從女性解放的層面來說具有進步意義。對女性意識的張揚和對“女人性”的認知,使女性書寫成為一道獨特的文學風景線。但是,文學創作一旦與社會環境脫離,勢必使文學敘述走向瑣碎化、媚俗化。作家作為社會中的人,應該對社會的觀察采取理性的方式,若文本脫離了社會,作家也會陷入到無話可說的地步。
《大淖記事》的女性書寫方式,可以對當下盛行的女性主義寫作起到一定的引領作用,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生存狀態,不但可以使女性本身的“女人性”得到更好的體現,也可以使女性書寫更具審美深度。
【注釋】
[1]諸慧《挑戰男權傳統:來自女性主義者的聲音》,復旦政治學評論·2005年第00期,第225頁。
[2]西美爾《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0頁。
[3]西美爾《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0頁。
[4]西美爾《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58頁。
[5]王澄霞《〈大淖紀事〉人性解放主題的當代反思》,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12年第五期,第208頁。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學2015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
責任編輯: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