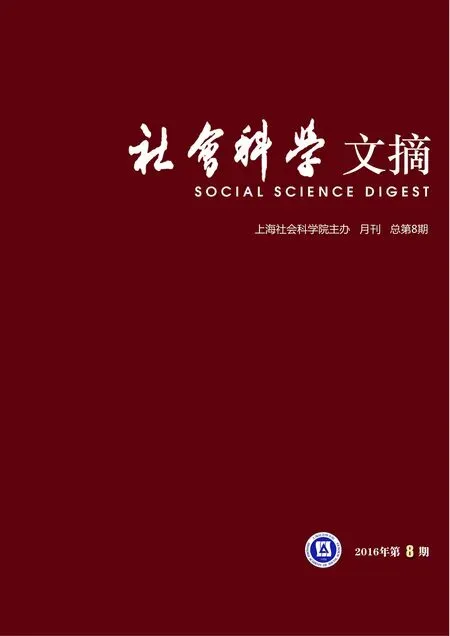政府信息公開的憲法邏輯
文/秦小建
政府信息公開的憲法邏輯
文/秦小建
在憲法體制的組織和運行邏輯下,政府信息公開不能為一個單維度的“政府—公民”關系所涵括,公民知情權所對應的“國家”義務,也不能被狹隘地理解成“政府”的公開義務。同時,“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限制性框架,只能置于憲法體制的組織和運行邏輯中,結合各個國家機構與公民的關系進行具體化的理解。否則,這一原則及對應的政府公開義務就是空洞的,空洞的原則當然無法約束政府。憲法體制的組織和運行邏輯,決定了信息公開國家義務的具體類型和體系結構。只有在此視野下,才可領會以公民知情權為基礎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所具有的重大憲法功能,而不是局限于一種以公開促進自我規約的狹窄認知。
主權邏輯與治理邏輯
依據《憲法》第2條、第3條、第三章,憲法體制的組織和運行邏輯以公式表達為“人民—人大—國家機構(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公民”。“人民—人大—國家機構”是主權邏輯的彰顯,“國家機構—公民”是治理邏輯的體現。二者耦合成我國憲法實施的兩個互動層次。其一,基于人民主權,作為主權者的人民選舉產生權力機關,產生國家機構,并制定法律,從而組織和規范國家的整體運行。主權邏輯構造了國家的主權結構,這一主權結構,既保證主權權威的恒在,又以制度化的方式抑制主權者出場所不可避免的無序和激情。其二,包括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在內的國家機構在主權邏輯構建的憲法體制中各司其職,遵守和適用法律,以強制性的權力為保障,通過授予權利、賦予義務具體調整個體公民之間、個體公民與國家機構之間產生的法律關系。所謂治理邏輯,是通過法律的憲法實施,即由人大產生的國家機構遵守和適用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實現人民意志。主權邏輯為治理邏輯輸送正當性,治理邏輯為主權邏輯實現價值理性。
在這一憲法邏輯中,政府承擔的信息公開義務可對應分解為兩個層次。一是在“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權邏輯下,政府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向人大報告工作。據此,政府應當向人大主動報告信息,而人大作為人民意志的代議機構,有權代表人民要求政府公開社會大眾所普遍關注的信息。二是在“政府—公民”的治理邏輯下,政府因職權行使與公民形成行政法關系,公民的權利義務因此受到影響,行政行為與公民個體之間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利害關系。此時,遵循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要求,有關行政行為的信息,應當向公民公開,公民亦有權向行政機關申請公開。依據憲法體制的職權配置關系,如果政府公開義務存在偏差,那么公民有權向上級政府舉報、申請行政復議,并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兩種邏輯的混淆及其后果
現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賴以建構的“知情權—政府信息公開義務”邏輯,混淆了作為主權者的“人民”與作為政府治理相對方的“公民”,因而也混淆了有關憲法體制組織和運行的“人民—人大—政府”之主權邏輯與“政府—公民”之治理邏輯。
這一混淆,漠視了“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權邏輯,忽略了政府與作為權力機關的人大在信息公開領域的職權關系及義務配置,致使現行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與整體憲法體制相脫節,難以形成制度合力。同時,由于無法受到憲法體制的有效規約,政府的信息公開職權極易僭越憲法體制的職權配置,違反國家機構分工原理。其后果是,既可能因其職權所限而無力滿足民眾信息需求,也可能因越權而陷入恣意,更可能將蘊含于分工背后的制約和監督消解于無形。
這一混淆,還為本不應在代議政治中直接出場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使得“人民”超越人大而直接與政府形成關聯,從而與主權邏輯相抵牾。由于缺乏代議制的整合和過濾,有關信息公開的“民意”在“沉默的大多數”的映襯下,本源是少數群體和精英階層訴諸抽象的“人民”概念所進行的單方面“加工包裝”,看上去擁有強大的道義力量,實則難以將多元認知下的分散民意訴求匯聚成絕大多數所認可的體制性共識,更無法轉換成實質性的制度壓力,自然難以有效施壓政府。與此同時,忽略代議渠道而動輒訴諸主權者的民意號召,常常摻雜著民粹傾向的非理性指責,擲地有聲的建設性討論和訴求主張淹沒其間。加之政府治理(尤其是基層)受制于壓力機制而難以保持常規化運作,信息公開底氣本就不足,民意回應體制還不健全,正常的民意表達和溝通交流管道由此不斷窄化。以主權者身份自居所發出的指責,一旦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寬容和理解喪失了土壤,交流和溝通沒有了意義,結果被提前預設,本意在于強化溝通的公開不免演化為情緒化的對立。
這一混淆,還干擾影響了治理邏輯下“政府—公民”的知情權實現,而這恰恰是公民需求最為迫切、利益關聯也是最為直接的方面。由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下稱《條例》) 對主權邏輯和治理邏輯的混淆,沒有意識到不同邏輯下信息所具有的不同性質及其功能,也無法體會到不同性質的信息對不同邏輯下的公民的不同意義,因此沒有設置有針對性的制度對其予以區分。而籠統的公開義務,雖增大了那些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獲取信息的機會,但降低了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獲取相關信息的公開強度,乃至于發生錯位,沖淡了直接利害關系背后的合法性關聯,使得那些關乎行政行為合法性的信息,得以借助《條例》中有關例外事項不公開的制度管道從容規避。當下土地規劃開發項目中涉關公民利益的信息公開不足,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此種混淆獲得極大的義務豁免空間。
這一混淆,還可解釋當下行政訴訟針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救濟實效不足的困境。行政訴訟是憲法在治理邏輯下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監督的制度設置,它理所當然地遵循與治理邏輯相對應的以直接利害關系為基礎的合法性審查模式。僅僅通過人為主觀定性,就將某個與公民無直接利害關系的行為認定為具體行政行為,實際上等同于將主權邏輯硬性塞入治理邏輯,行政訴訟無法接納,基于“特殊需要”的不設限申請模式和泛化的知情權需要,遭遇了行政訴訟圍繞“法律上直接利害關系”的合法性審查框架的抵抗。
政府信息公開是防范行政專斷的一種具體方式,可謂扣在政府頭上的“緊箍咒”。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兼具議會控制與公民參與兩大制度方案,既基于主權邏輯向代議機構報告工作,接受代議機構監督,又順應治理邏輯下的公民知情權訴求履行公開義務。二者本應有序分工,協調并致。然而,我國的這一制度設計,卻人為割裂了上述邏輯關聯。《條例》一方面通過自我立法全然超脫人大控制,無視有關政府信息公開的既定人大體制安排;另一方面則曲解了行政過程中公眾參與的應有定位,透射出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合法性悖論”:以鼓勵公眾參與為初衷的政府信息公開,本意在于矯正行政過程的“民主赤字”,但由于與作為正當性來源的主權邏輯的自我割裂,以及自身的運作偏差,陷入一種更深刻的合法性危機中。
對應制度構造
有鑒于此,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應當回歸憲法體制的運作邏輯,分別對應“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權邏輯和“政府—公民”的治理邏輯進行制度化構造,實現其在憲法體制中的特殊價值和功能承擔。
基于主權邏輯,對于那些與公民個體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信息,政府信息公開的首要維度是向人大公開,而人大作為人民的意志代表,經過是否屬于“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權衡之后,向人民公開。這一方式,可借助于人大權威回應實踐中以“公共利益”為由的義務規避困境。另一方面,在“政府—公民”治理邏輯中,區分直接利害關聯的三層次,確證信息與公民個體的利益關聯程度,據此分別構建公開模式。具言之,在基于“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具體行政行為下,信息是行政主體做出行政行為的基本依據,直接關系到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基于正當程序原則,行政行為的所有信息應當全部向行政相對人公開,至于其中可能存在的泄露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問題,應當通過《保守國家秘密法》《檔案法》及相關保密協議等配套制度予以解決。在基于“大范圍法律上利害關系聚集并與公共利益共存”的土地規劃開發等職權行為下,涉及行為合法性的信息也應完全公開,但如與公共利益形成沖突,應對接主權邏輯交由人大平衡。在基于“公共利益的反射關系”的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監管、產品質量監管等情形下,如反射關系可落實至特定時空的公民個體,則采取“聚合型法律上利害關系與公共利益并存”模式;如不能落實到公民個體,則回歸主權邏輯的公開模式,并在治理邏輯下借鑒檢察機關公益訴訟模式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申請。
現行《條例》作為行政法規,是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規定或履行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而制定的,尚可對應于傳統的以公開促進規范的制度定位。然而,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顯然無法包容主權邏輯,因為這一關系已經涉及憲法體制安排。并且,公民知情權與政治權利的密切關聯,決定了以行政法規作為規范載體,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此時,有必要向作為憲法性法律的《政府信息公開法》升級。但需要補充的是,如果沒有特別的需要,其實并沒有必要專門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法》來規范這一關系,因為在既有的組織法體系和《監督法》中,已經對這一關系做出了具體的制度安排。尤其是《監督法》規定的專項工作報告制度,實際上就是這一邏輯的制度化表達。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摘自《中國法學》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