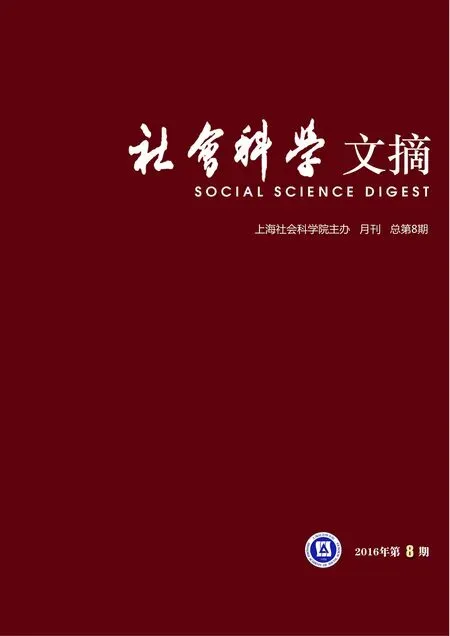老舍對“國民性”書寫的開拓與反思
文/遲蕊
老舍對“國民性”書寫的開拓與反思
文/遲蕊
關于老舍對“國民性”的書寫,以往許多研究者都談到了他與魯迅的契合、魯迅對他的影響。事實上,他不僅與魯迅有著不同的思考,還對魯迅的、他本人的以及整個的“國民性”書寫有過許多的反思。
與魯迅“國民性”書寫的對話
《我怎樣寫〈貓城記〉》發表于1935年12月1日的《宇宙風》(第6期),是老舍一篇重要的創作談。它與其說是總結失敗的教訓,不如說是在申明自己在“國民性”書寫上的另一種抱負。
盡管,文中并未直接表明,但從字里行間仍能窺見老舍與魯迅的對話關系。他寫道:“越是毒辣的諷刺,越當寫得活動有趣,……把諷刺埋伏在底下,而后才文情并懋,罵人才罵到家。……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厲害的文筆,與極聰明的腦子,一個巴掌一個紅印,一個閃一個雷。我沒有這樣厲害的手與腦……《貓城記》就沒法不爬在地上,像折了翅的鳥兒。”
那么,老舍通過這種對話想要強調什么呢?據這篇文章看來,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感到諷刺的功夫固然重要,但幽默才是最根本的手法。他寫道:“說真的,《貓城記》根本應當幽默,因為它是篇諷刺文章:諷刺與幽默在分析時有顯然的不同,但在應用上永遠不能嚴格的分隔開。……它得活躍,靈動,玲瓏和幽默。必須幽默。”第二,覺得從思想的高度找出國民性的病根固然高明,但從常識的角度如實地表現國民性本身卻更加重要。他說:“眼前的壞現象是我最關切的”,只想“老老實實的談常識”。可見,老舍與魯迅所走路子的確不甚相同。
至于,為什么要如此強調這兩點,老舍也做了一些交代。只不過,都是以調侃的口吻,講得很委婉。一是因為擅長幽默,一旦舍去了他“較有把握的幽默”,《貓城記》也就失敗了。二是由于缺乏高明的思想,僅有普通人的見識。他說:這篇小說“毫不留情地揭出了我有塊多么平凡的腦子”;“既不能有積極的領導,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為什么有這種惡現象呢?我回答不出”。
這番解釋值得玩味。難道老舍僅僅是因為擅長幽默,就推崇幽默?因為“缺乏思想”,就只“關切眼前的壞現象”嗎?對此,這篇文章沒有涉及,但從老舍其他文章中能夠體味出,實際上另有深因。
開辟“國民性”書寫的另一種路徑
老舍看重幽默,首先是源于寬厚的心態。在他看來,幽默不僅僅是一種藝術技巧,“它首要的是一種心態”,一種“人生里很可寶貴的”“一視同仁的好笑的心態”。當然,形成這種認識的原因十分復雜,既與其豁達的天性、旗人詼諧的生活情調、英國紳士幽默風度的影響有關,又與他貧苦的遭遇和被雙重遺棄的獨特感受密切相關。此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他對“人”的根本看法。老舍認為人無完人,人人都有可笑之處,必須承認人類的缺點,這是常態。他說:“我恨壞人,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人人有可笑之處,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一想,人壽百年,而企圖無限,根本矛盾可笑”。因此,他主張對待人應以寬厚的心態,“既不呼號,看別人不是東西,也不顧影自憐,看自己如一活寶”;看待世事,應“如入異國觀光,事事有趣”;對于創作則應笑罵“又不趕盡殺絕”。
顯然,這與魯迅對人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與老舍的寬容不同,魯迅主張“一個都不寬恕”。于是,對于幽默和諷刺他們也就各有倚重。而且,在老舍看來,諷刺與幽默雖然有相通之處,但在心態上卻極為不同:“諷刺必須幽默,但比幽默厲害。它必須用極銳利的口吻說出來,給人一種極強烈的冷嘲”;“幽默者的心是熱的,諷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諷刺多是破壞的”。
至于,老舍為什么自稱“缺乏思想”,只“關切眼前的壞現象”,就涉及許多更深層的原因了。老舍沒有像魯迅那樣以精英的姿態,站在啟蒙思想的高度,運用豐贍的學養思考國民性問題,而是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和見識,從真實的底層生活經驗出發,來觀察它的種種表現。
老舍認為,“國民性”就是“民族性”,這兩個概念完全通用,這從他在不同文章中對《二馬》的談論中就可看出。一處說:“寫它的動機是在比較中英兩國國民性的不同……”;另一處說:“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同時,通過對滿人的觀察,老舍還認為中國的國民性不僅有缺點,還有優點,二者是一體的兩面,無法截然分開。雖然,他也同意國民性是文化的產物,但對于將病根歸于傳統文化的看法卻持保留意見。他發現這種文化雖然導致了怯懦、柔順等民族弱點,但也培養了堅韌、義氣等非常可貴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說,許多由它所造成的可笑之處,從另一角度看卻恰恰是可愛之處。所以,他認為“中華民族是好是壞,一言難盡”,不可輕下判斷。因此,閱讀老舍的作品會發現,他幾乎不談什么國民性的改造,更不把文學當成什么“人類改造丸”,而只是希望通過揭示它的可笑處,起到一種規勸的作用;也不像魯迅那樣去挖掘它的病根,借以攻擊傳統文化的弊端,而總是著重于表現“壞現象”本身。甚至,老舍偶爾還流露出對傳統文化的眷戀。
另外,市民出身也深刻地影響了老舍對國民性的思考。他常常在文章中談及自己窮苦的出身。老舍之所以一再談到這一點,并非顧影自憐,引人同情,而是為了表明一種獨特的姿態和趣味。與那些知識精英不同,他雖然也會跳出來“俯視”底層市民,客觀地觀察他們,但所持的卻不是高高在上的啟蒙姿態,而是更為平等的、體貼的姿態。因而,相比之下,老舍對底層市民的把握和洞察就更加精細到位,帶有人間煙火氣。
再者,滿族身份也造成了他的這種思考特點。經過辛亥革命滿族的統治被推翻,身為滿族遺民的老舍,對漢族的統治有很深的疏離感,甚至是恐懼感。假如設身處地去想也不難理解,一個底層的滿人在異族的統治下,他最關心的大概不會是有關政治改革一類的宏大話題,而是能否過上安安穩穩的生活。更何況,當老舍目睹了滿人被歧視、侮辱甚至是殘害的現實后,他對這各種社會運動和改革就更加失望,提不起興趣。對他而言,無論國家發生怎樣的變革,恐怕都遠不及有個穩定的國家秩序更重要。
事實上,老舍的表現也正是如此,早年一直表現出與社會運動的隔膜。他說:“五四運動時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有機會參加。……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更不明白的是國內青年們的思想。”當然,老舍在這里想強調的更主要的是一種思想上的隔膜,以及由此帶來的許多獨特的發現。那時他不僅早已不是缺乏社會經驗的學生了,還從鼓蕩著各種新思潮的社會中,看到了許多被遮蔽的風景。他說:“我在解放與自由的聲浪中,在嚴重而混亂的場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縫子。”所謂的“縫子”,指的也就是政治視野之外的生活本相。因此,他不僅自稱“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覺得“五四”運動那時出的新書并不怎么驚奇,甚至還倔強地認為搞創作“用不著開口‘吶喊’,閉口‘怒吼’的去支持我的文字”,“只須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生活經驗就夠了”。生活的本相才是老舍最關注的地方,才是他在作品里最想呈現的風景。這與魯迅那種吶喊式的、與復雜的社會斗爭密切相關的小說有著不小的距離。
其實,這也是老舍大半生都有些排斥理論的原因。在他看來,事實比理論更有說服力,而且思想總是蘊含在生活里。這還是他的一種文學觀。老舍堅信感情是文學的特質之一,而思想、知識、哲學都不是文學所表現的重心。關于這一點,老舍在他的論著《文學概論講義》中闡述得非常清楚。他說:“思想只有一時的價值,沒有文學的永久性”;“感情是文學的特質是不可移易的,人們讀文學為是求感情上的趣味也是萬古不變的”;“讀文藝作品不是為引起一種哲學的駁難,而是隨著文人所設下的事實而體會人生”。因此,難怪對于國民性的表現,老舍不像魯迅那樣偏重于表達一種深刻的思想,而是更看重能否通過對種種壞現象的寫實,來達到“極大的情緒感訴力”,為讀者“懸起一面鏡子”,“向人心擲去炸彈”。也就是說,并不是老舍缺乏思想,而是他根本就無心于在作品中表達什么精深的思想。
事實上,他在自己的創作中,也是努力踐行著這樣的觀念。從《二馬》到《貓城記》,再到《四世同堂》以至其他創作,老舍不僅大大拓寬了“國民性”書寫的表現領域,還用幽默細膩的筆觸刻畫了尋常百姓生活的角角落落,烘托了各類普通民眾的辛酸哀樂。由魯迅所關注的鄉村,延伸到了更為廣闊的市民世界,乃至英國的市民階層;由知識分子圈子,擴大到政界、商界、教育界、文化界,可謂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尤其可貴的是,老舍不僅諷刺了國民性的種種弱點,還挖掘和謳歌了中國人身上許多閃光的品質。這可以說是對以往“國民性”書寫的重要補充。
當然,魯迅后來對國民性的表現也有一些變化,也挖掘了中國人的一些精神優點。比如他在《中國失掉自信力了嗎》《學界三魂》等文章中,就稱贊過中國的脊梁精神、可貴的民魂等,這和老舍有不少相近之處。不過,需要辨析的是,盡管二者十分相似,卻略有不同。老舍是將這些優點作為傳統文化正面價值來挖掘的;而魯迅則認為那是中國人本有的性質,是被傳統文化束縛下幾乎要喪失殆盡的品質。也就是說,老舍是意在從傳統文化中發揚這種品質,而魯迅是希望通過批判傳統文化來將其恢復回來。總之,老舍在“國民性”書寫上,的確走出了一條與魯迅不同的道路。
對“國民性”書寫的反思
首先,與魯迅作品的對話,實際上就隱含著一種反思。在老舍看來,魯迅的作品雖然辛辣深刻,但也有他不太贊同之處,比如,從高處俯視民眾的姿態、否定傳統的偏激、諷刺有余寬厚不夠,以及由于缺乏對底層生活深切的體驗而帶來的藝術上不足等。因此,他不得不感慨“新文藝并沒有在民間生了根”,始終“與一般人中間隔著一層板”;“五四以來,一切都寫新的,文藝只在學生隊伍里,只知道魯迅、茅盾、《吶喊》、阿Q等名字,要是到了鄉里,誰也不知道這些人與這些作品了”;“一個村子里連魯迅這個光耀的名字都不知道……”
其次,老舍對《貓城記》也有很多反思。他說:“《貓城記》,據我看,是本失敗的作品。”對此,以往有兩種常見的理解。一是屈服于某種政治壓力下的“違心話”,已被證明不足采信;二是檢討思想不足和對進步的人物的嘲諷。此外,根據前文的分析,本文認為還可有另一種解讀,就是申辯之義。所謂申辯,就是為自己的“缺點”進行辯護,表達自己在“國民性”書寫上的抱負。關于幽默和缺乏思想這兩個“缺點”,前文已作闡明,這里還有需要補充的一點是,老舍還談到了這篇小說像“報告”的毛病。而這一點,實際上也是他所推崇的一種手法。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中曾這樣講解過:“俄國的寫實作家有時只給我們一些報告似的東西,……然而這究竟不是報告,而是藝術家眼中的一片真實,……能使別人看到我們自己所看到的,便不是件容易的事。……由觀察人生,認識人生,從而使人生的內部活現于一切人的面前,應以小說是最合適的工具。”這樣,再結合《我怎樣寫〈離婚〉》中所說的“《貓城記》是但丁的游‘地獄’,看見什么說什么”,就更能體會到這里所謂“報告”并不是什么缺點,而是他所追求的一種文學境界。
至于老舍為什么否定這篇小說,本文認為除了因為嘲諷了進步人物之外,還有四個原因。一是“缺乏寫實本領和情緒感訴力”;二是“故意禁止了幽默”;三是流于“說教”;四是體裁上“是諷刺文章最容易而曾經被文人們用熟了的”,缺乏新意。很明顯,與他的抱負相對照,這四點可以說全部事與愿違。所以,老舍雖然對自己的追求多有辯護,但還是否定了這篇小說。同時,他還流露出不得不失敗的無奈。因為經過這次創作,他發現作為一種諷刺型創作,“國民性”書寫本身就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局限。這是老舍的又一個重要的反思。
他認為:第一,這種書寫破壞有余,建設不足;第二,即便開了藥方也難以奏效;第三,人物描寫易流于表面,對人性缺乏深刻的表現。他曾在評價英國作家時特地談論過這一點,認為這類意在“揭發人物的某種特質”的作品,“都有相當的趣味與成功,但都夠不上偉大”;“主旨既在表現人物的特色,于是人物便受他所要代表的那點東西的管轄”;“這樣,人物似乎由生命的中心移到生命的表面上去。這是揭發人的不同處,不是表現人類共同具有的欲望和理想;這是關于人的一些知識,不是人生中的根本問題”。此外,老舍通過《二馬》和《貓城記》也認真地反思過這個問題,多次反省到《二馬》“立意太淺”,《貓城記》也“正中此病”。
那么,老舍為什么要對“國民性”書寫進行反思?他的反思又導致了什么樣的結果呢?首先,直接的原因是老舍對自己以往創作的全面總結。1935年9月到1936年8月,老舍在《宇宙風》雜志上,共發表了九篇系列創作談——“打《老張的哲學》說到《牛天賜傳》”,后收錄到文論集《老牛破車》中。在這些文章中,老舍為了在創作上有所突破,找到屬于自己的風格,回顧并全面總結了以往創作的經驗與教訓。《二馬》和《貓城記》這兩篇著重于表現國民性的小說,自然也就在“自評”之內。其次,是有感于當時文壇對幽默手法的壓制。1933年而后,關于幽默問題魯迅與林語堂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論爭。魯迅連續發表了《從諷刺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等文章極力地反對林語堂,而老舍卻堅決地擁護后者。當時林語堂先后共創辦三份刊物即《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老舍在這些刊物上都擔任了長期或特約撰稿員,可見老舍對林語堂的支持。而老舍之所以在文章中那么反對魯迅對幽默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再者,老舍對魯迅的反思可以說是由來已久,從前文的論述可見老舍自從事小說創作以來就不大贊同那種吶喊式的創作。
至于,老舍反思的結果如何?筆者認為首先對于他創作上的突破起到了非常關鍵作用。如果正如學者趙園所分析的,《離婚》的問世才標志著老舍創作的真正成熟,那么這種成熟其實正是經過對《貓城記》的反思才達到了。從那之后,老舍終于找到了自己的風格,不僅加強了寫實的能力,還恢復了自己擅長的幽默,提高了幽默的水準。以至于在創作《離婚》之后,他接連又拿出了《牛天賜》《柳家大院》《黑白李》等佳作,直到創作出《駱駝祥子》《四世同堂》那樣的具有里程碑式的經典之作。其次,此后老舍放棄了《貓城記》那種寓言,特別注意將對于國民性表現與人物個性相融合。另外,他愈加堅信了自己小說在“表現與批判市民社會”方面的價值與意義,逐漸匯入了推動大眾文藝運動的洪流中,后來還投身到了發展通俗文藝的事業中。
綜上所述,老舍在“國民性”書寫上既有開辟,又有反思。如今,當我們重新來審視新文學中國民性問題時,他的這些經驗仍具有啟示意義。
(作者單位:沈陽大學文法學院;摘自《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叢 刊》2 0 1 6 年第 7 期;原題為《老舍對“國民性”書寫的思考及與魯迅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