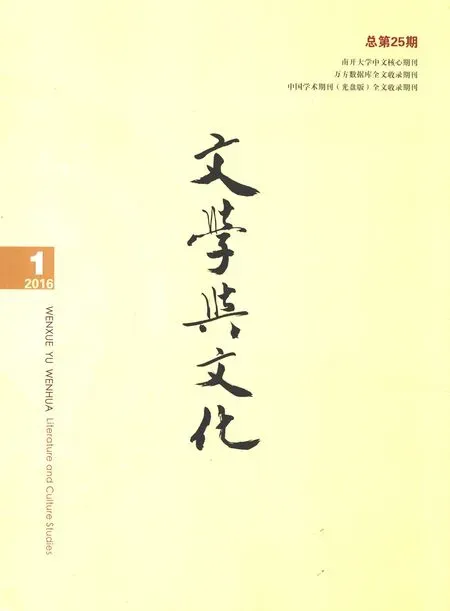施耐庵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辨
——兼與歐陽(yáng)健先生商榷
楊大忠
施耐庵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辨
——兼與歐陽(yáng)健先生商榷
楊大忠
施耐庵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說(shuō)法,因元朝至順辛未年(1331)沒(méi)有開(kāi)科的記錄,加上官方史料與地方史料中從未有進(jìn)士施耐庵的記載,所以是不能成立的。劉冬先生認(rèn)為“辛未科進(jìn)士”之說(shuō)出自施氏后人誤記,或是因?yàn)椤霸目婆e制度及其執(zhí)行,十分混亂”所致。這種說(shuō)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陳建華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實(shí)為“鄉(xiāng)貢進(jìn)士”,這種說(shuō)法亦是想當(dāng)然之論。歐陽(yáng)健先生則認(rèn)為施耐庵本為至順?biāo)哪辏?333)進(jìn)士,出現(xiàn)“辛未進(jìn)士”之說(shuō),是由燕鐵木兒操縱下的科場(chǎng)舞弊案的惡劣影響所致。這種說(shuō)法似禁不起推敲。
施耐庵 “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 鄉(xiāng)貢進(jìn)士 科場(chǎng)舞弊案 商榷
蘇北興化施氏始祖施彥端究竟是不是《水滸傳》作者,這個(gè)問(wèn)題已經(jīng)爭(zhēng)論了半個(gè)多世紀(jì)。蘇北施氏不僅將始祖施彥端與“錢(qián)塘施耐庵”合二為一,而且他們這位始祖還有一個(gè)特殊的身份——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這就不能不引起學(xué)界的懷疑:因?yàn)閺摹对贰酚涊d來(lái)看,“辛未”之年并未開(kāi)科,施彥端的進(jìn)士身份從何而來(lái)?自上世紀(jì)50年代開(kāi)始,針對(duì)人們的懷疑,也有學(xué)者也從多個(gè)角度對(duì)施彥端的“進(jìn)士”身份作了闡釋?zhuān)噲D打消人們的疑慮。然而這些闡釋?zhuān)軠y(cè)成分多,詳加推敲,即破綻連連,不能令人信服。
一 “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不能成立
由蘇北施氏第十四世裔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修、后于民國(guó)七年(1918)由施氏第十八世裔僧施滿家抄錄的《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是記載施氏家族代系延續(xù)的真文物,這一點(diǎn)無(wú)可置疑。但這樣一部家譜卻有著疑竇叢生之處,那就是在世系記載“第一世始祖彥端公元配季氏申氏生讓”之“始祖彥端公”的天頭位置,添加了眉批“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這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懷疑。
除了《長(zhǎng)門(mén)譜》,提及施彥端——即蘇北學(xué)者所說(shuō)的“施耐庵”——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材料尚有施氏宗祠內(nèi)神主木牌,上也寫(xiě)施耐庵為“元辛未進(jìn)士”;1943年錄入《興化縣續(xù)志》中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更是明確記載施耐庵“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
翻檢《元史》,元朝以“辛未”紀(jì)年的有兩年,一為世祖至元八年(1271),一為文宗至順二年(1331)。前者尚在宋亡之前,并且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說(shuō)施耐庵“生于元元貞丙申歲(1296)”,顯然施耐庵“辛未科進(jìn)士”之“辛未”,指的是文宗至順二年(1331),這與《施耐庵墓志》說(shuō)施耐庵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完全相合。查《元史·選舉志》,自延佑二年乙卯(1315)至元統(tǒng)元年癸酉(1333),一共開(kāi)科七次,分別是:延佑二年(1315)、延佑五年(1318)、至治元年(1321)、泰定元年(1324)、泰定四年(1327)、天歷三年(即至順元年,1330)、元統(tǒng)元年(1333)。這七次開(kāi)科都有一定的規(guī)律,即三年一次,根本沒(méi)有例外,很明顯不存在記載遺漏的情況。而施耐庵中進(jìn)士的年份至順二年辛未(1331),則根本不在七次開(kāi)科之內(nèi)。很顯然,說(shuō)施耐庵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與歷史記載完全相悖。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duì)這一記載的懷疑。茲舉兩例加以說(shuō)明:
戴不凡先生說(shuō):
查元至順二年辛未(1331)沒(méi)有舉行過(guò)進(jìn)士考試。元末只有兩個(gè)壬午、乙酉兩科進(jìn)士,怎么弄出個(gè)辛未科進(jìn)士來(lái)呢?從中進(jìn)士而引伸出施耐庵在杭州做過(guò)兩年官之類(lèi),我看根本不可靠。舊社會(huì)的某些宗譜,有的就象《紅樓夢(mèng)》里的賈雨村和賈政、王狗兒家和王熙鳳家聯(lián)宗認(rèn)親一樣荒唐。①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勛》,《小說(shuō)聞見(jiàn)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2~113頁(yè)。
蔡美彪先生說(shuō):
元朝仁宗時(shí)始行科舉,順帝時(shí)一度罷廢,至正十一年恢復(fù),先后只舉行科舉考試八次,每次取士不過(guò)百人。元制:蒙古色目與漢人南人分榜。元朝一代,南人而得為進(jìn)士者只有百余人。然而,在現(xiàn)存元代文獻(xiàn)中,并無(wú)至順間進(jìn)士施某的記述。在咸豐修譜(筆者注:指咸豐四年施氏十四世后裔施埁修《施氏族譜》)前一年成書(shū)的梁園棣《興化縣志》只載有元朝進(jìn)士顧氏,也無(wú)施氏。施氏文獻(xiàn)中《施廷佐墓志》和乾隆譜也都不見(jiàn)有進(jìn)士之說(shuō)。更為重要的是:如大家所指出的,至順辛未即至順二年,元朝并未舉行科舉。在最近的討論中,有的同志提出,可能是在至順?biāo)哪昕疲芍扑阒抡`。但這也是不可能的。至順?biāo)哪昙丛y(tǒng)元年,十月改元。此年的進(jìn)士錄現(xiàn)仍留存,有徐乃乾復(fù)刻本,題為《元統(tǒng)元年進(jìn)士名錄》。錄中備載此科進(jìn)士的姓名、字號(hào)、生辰、籍貫以及曾祖以下三代名氏。此科進(jìn)士滿百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人,是元朝取士最多的一次。但漢人南人進(jìn)士中既無(wú)彥端或施耐庵的姓字,也沒(méi)有任何一個(gè)施姓。②蔡美彪:《白駒施氏文獻(xiàn)與施耐庵傳說(shuō)辨析》,《江海學(xué)刊》1983年第2期。
應(yīng)當(dāng)說(shuō),戴不凡與蔡美彪二先生對(duì)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否定非常具有代表性。尤其是蔡美彪先生,不僅指出了“辛未科進(jìn)士”之說(shuō)與《元史·選舉志》的記載相悖,還查閱了《興化縣志》和《元統(tǒng)元年進(jìn)士名錄》,發(fā)現(xiàn)其間根本沒(méi)有施耐庵中進(jìn)士的記載。
可是在一些學(xué)者看來(lái),與《元史·選舉志》記載相悖的所謂施耐庵為“辛未科進(jìn)士”之說(shuō)可能是記載有誤所致。如劉冬先生在20世紀(jì)50年代也承認(rèn):“這(筆者注:指“辛未科進(jìn)士”)是一個(gè)疑點(diǎn)。”但他又說(shuō):“我們覺(jué)得這仍是可以解釋的。可能是他的后代的推算錯(cuò)誤,就是誤至順元年當(dāng)了辛未。因?yàn)槟怪局姓f(shuō)是至順的進(jìn)士,而至順年代一共只有這庚午(筆者注:指1330年)一科。那么錯(cuò)把這一科當(dāng)做辛未,是有可能的。”③劉冬、黃清江:《施耐庵與〈水滸傳〉》,載《文藝報(bào)》1952年第21號(hào)。
劉冬先生之論被一些學(xué)者繼承,如:針對(duì)有人懷疑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施耐庵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一事,周建明先生力辨《施耐庵墓志》非偽,就發(fā)揮了劉冬先生之論:
查《元史·選舉志》,至順二年確實(shí)沒(méi)有舉行過(guò)廷試,但前一年和后二年,都考過(guò)進(jìn)士。《施耐庵墓志》的作者是淮安人,與施耐庵住得很近,長(zhǎng)大后又曾在福建旅途中遇到施耐庵的門(mén)生羅貫中,聽(tīng)他說(shuō)了許多施耐庵的軼事,因此他能夠獲得很多可靠的材料。但他畢竟出生晚一點(diǎn),施耐庵死時(shí),他“尚垂髫”,施耐庵的生平事跡,大都還是間接得來(lái)的,因此他在編寫(xiě)墓志過(guò)程中,錯(cuò)把天歷三年當(dāng)成至順二年是可能的。施耐庵中的可能是天歷三年(庚午)這一科。由于王道生推算的錯(cuò)誤,誤寫(xiě)為至順二年(辛未)。這種年數(shù)的誤記,在后人所作墓志中是常見(jiàn)的,如果僅僅根據(jù)這點(diǎn)說(shuō)明墓志系偽造,無(wú)法叫人信服。①周建明:《〈水滸傳〉札記》(二),《湘潭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82年第2期。
筆者按:周建明先生把偽作的《施耐庵墓志》當(dāng)作信史看待,這本身就不夠嚴(yán)謹(jǐn)。托名明初淮安人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是徹頭徹尾的假文物,在何心、何滿子、曹晉杰、朱步樓、章培恒、劉世德、張國(guó)光、李偉實(shí)、袁世碩、劉操南、馬成生、洪東流、楊子華、陳遼諸位先生的辨證下,《施耐庵墓志》早就體無(wú)完膚,完全不能征信。②至于辨別《施耐庵墓志》之偽,筆者也曾撰文《〈施耐庵墓志〉再辨?zhèn)巍獜摹此疂G〉原名“江湖豪客傳”談起》,見(jiàn)山東省社科聯(lián)和山東省水滸研究會(huì)編《〈水滸傳〉與儒家文化全國(guó)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2014年10月,第255~277頁(yè)。周建明先生說(shuō)王道生把施耐庵中進(jìn)士的“天歷三年”(1330)錯(cuò)記成“至順二年”,也只是想當(dāng)然之論,沒(méi)有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就算《施耐庵墓志》真的作于洪武初年,墓志寫(xiě)好后,王道生當(dāng)然要交給施耐庵后人過(guò)目,看看其中可有什么不妥或訛誤之處,絕沒(méi)有王道生自說(shuō)自道、不經(jīng)施氏后人寓目的道理。既然如此,王道生寫(xiě)錯(cuò)了施耐庵中進(jìn)士的年代,難道施氏后人也看不出來(lái)嗎?像先祖中進(jìn)士這樣光耀門(mén)楣的大事,子孫后代當(dāng)然會(huì)牢記于心,絕沒(méi)有糊涂到連年代都忘記的程度。《施耐庵墓志》說(shuō)施耐庵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根本不可信。
張惠仁先生也信奉劉冬先生之論,他說(shuō):
查《元史》,至順辛未的確沒(méi)有開(kāi)科。但是在辛未的前一年庚午(1330年)和辛未的后兩年癸酉(1333年),卻是開(kāi)科的。我認(rèn)為,這可能是耐庵的后人推算時(shí)的錯(cuò)誤,因?yàn)橥醯郎鸀槭┠外肿珜?xiě)“墓志”時(shí),距離施耐庵中進(jìn)士的年代已經(jīng)有了至少六七十年之久了。不管是施的子孫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推算的錯(cuò)誤或者是王道生從羅貫中處得到的記憶,發(fā)生一年或兩年的誤差都是可能的,是可以理解的。③張惠仁:《關(guān)于〈施耐庵墓志〉的真?zhèn)螁?wèn)題》,《水滸與施耐庵研究》,延邊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第81頁(yè)。
張惠仁先生也認(rèn)為之所以出現(xiàn)施耐庵“辛未科進(jìn)士”之說(shuō),很可能是施氏后人誤“庚午”或“癸酉”為“辛未”所致。這與周建明先生之論異曲同工,沒(méi)有實(shí)質(zhì)性的區(qū)別;然而按照張惠仁先生本人的推論,施耐庵生于元仁宗延佑七年(1320),卒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歲享80歲。④張惠仁:《施耐庵的名、字、號(hào)及其生卒年新論》,《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1999年第4期。既然施耐庵生于1320年,我們不妨考慮一下辛未的前一年庚午(1330)和辛未的后兩年癸酉(1333),此時(shí)施耐庵的年齡為10歲或13歲。大家可以設(shè)想10~13歲的施耐庵有沒(méi)有中舉的可能。張惠仁先生之論是自相矛盾的。
把施氏后人或王道生的推算失誤當(dāng)做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理由,帶有想當(dāng)然的成分,顯然不能令人信服。劉冬先生也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于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初又改變了口風(fēng),且看他的說(shuō)明:
查《元史》確是辛未無(wú)科。但是我近來(lái)查《浙江通志》卻明明記載著:“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張宗元(開(kāi)化人),劉基(青田人,御史中丞),徐祖德(青田人,中書(shū)省管局),樂(lè)蜆(筆者注:當(dāng)為“葉蜆”)(青田人)。”不僅辛未,也記載著上一年庚午王畢(?)榜,賜進(jìn)士者有陸景能等十三人,下面是至順三年壬申,有宇文公諒。綜觀該府志科舉記錄,自至元二十三年,到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楊輗榜共二十三次。時(shí)間間隔,極為紊亂。余闕《元史》有傳,云元統(tǒng)元年(1333)進(jìn)士。但《浙江通志》為什么有同時(shí)四人“辛未(1331)進(jìn)士”的記載呢?
我以為這證明元代的科舉制度及其執(zhí)行,十分混亂。如果辛未無(wú)進(jìn)士榜的發(fā)布,《浙江通志》不可能有四個(gè)人的具體記載。①劉冬:《施耐庵生平探考》,《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輯。
《浙江通志》對(duì)浙江地區(qū)元代進(jìn)士錄取時(shí)間的記載的確大成問(wèn)題,非常紊亂。尤其記載了自至元二十三年到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楊輗榜,開(kāi)科次數(shù)竟然達(dá)到了驚人的二十三次,遠(yuǎn)遠(yuǎn)高于《元史·選舉志》中開(kāi)科次數(shù)的記載;更嚴(yán)重的是,在至順辛未年(1331)余闕榜,竟然記錄了本年錄取的以劉基為代表的四名進(jìn)士,此次開(kāi)科時(shí)間和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年代“辛未”相符。劉冬先生由此得出結(jié)論:施耐庵絕對(duì)是辛未進(jìn)士,這無(wú)疑義。
由于《浙江通志》與《元史·選舉制》記載的開(kāi)科次數(shù)迥異,劉冬先生進(jìn)而懷疑《元史》的記載是大有問(wèn)題的,反而認(rèn)為《浙江通志》的記載較為客觀。這是沒(méi)有道理的。劉冬先生根本沒(méi)有想到其實(shí)存在問(wèn)題的是《浙江通志》而非《元史》。歐陽(yáng)健先生經(jīng)過(guò)對(duì)材料的比對(duì)歸納,認(rèn)為《浙江通志》記載元代廷試科目,錯(cuò)誤連連,原因有二:一是沿襲舊志之誤;二是編纂意識(shí)之誤。②歐陽(yáng)健:《〈浙江通志〉元代選舉科目正訛——兼辨“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之由來(lái)》,《明清小說(shuō)研究》2012年第1期。劉冬先生沒(méi)有意識(shí)到《浙江通志》記載有誤,反而認(rèn)為《元史·選舉制》記載的開(kāi)科年代不夠客觀,顯然是喧賓奪主,本末倒置。
說(shuō)《元史·選舉制》的記載較為客觀,是因?yàn)樗涊d的自延佑二年乙卯(1315)至元統(tǒng)元年癸酉(1333)進(jìn)士開(kāi)科年份呈現(xiàn)出規(guī)律性,即三年一次。這從無(wú)例外;同時(shí),像《浙江通志》“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說(shuō)劉基、徐祖德和葉蜆三人都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然按照《元史·選舉制》的記載,至順辛未年并未開(kāi)科。而在雍正《青田縣志》卷九“選舉”中卻分明地記載三人中進(jìn)士的年份為“至順癸酉(1333)”,這和《元史·選舉制》記載完全相符,顯然《浙江通志》記載有誤。另外,劉冬先生自己也說(shuō)《浙江通志》存在“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而余闕在《元史》本傳中卻說(shuō)其為“元統(tǒng)元年(1333)進(jìn)士”。“元統(tǒng)元年”也就是“至順癸酉”,本年的確開(kāi)科進(jìn)行了廷試,這也符合《元史·選舉制》的記載。這些都從側(cè)面說(shuō)明了《元史·選舉制》記載的客觀性,而《浙江通志》記載的“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是錯(cuò)誤的。
既然《元史·選舉志》的記載較為客觀,“至順辛未”并未開(kāi)科考進(jìn)士就是不容置疑的歷史真實(shí)。無(wú)論怎么解釋?zhuān)诟鞣N歷史資料中找不到施耐庵中進(jìn)士的記錄是誰(shuí)也改變不了的事實(shí)。妄圖否定《元史》的記載,靠篡改歷史的方式使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身份得以確認(rèn),只能是徒勞。
二 “鄉(xiāng)貢進(jìn)士”之說(shuō)不成立
既然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身份與記載不符,于是有的學(xué)者另辟蹊徑,認(rèn)為施耐庵所謂的“進(jìn)士”身份,其實(shí)并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廷試進(jìn)士,而是“鄉(xiāng)貢進(jìn)士”,即鄉(xiāng)試及第的“舉人”。這種把“舉人”稱(chēng)為“進(jìn)士”的說(shuō)法其來(lái)有自。如《四庫(kù)全書(shū)總目》卷五十史部六別史類(lèi)存目《十八史略》二卷,解題云:
元曾先之撰。先之字從野,廬陵人。自稱(chēng)曰前進(jìn)士,而《江西通志·選舉》中不載其名。蓋前明之制,會(huì)試中試稱(chēng)進(jìn)士,鄉(xiāng)試中試者稱(chēng)舉人,皆得銓選授官。自唐宋至元,則貢于鄉(xiāng)者皆稱(chēng)進(jìn)士。試禮部中選,始謂之登第。不中選者,次舉,仍由本貫取解。南宋之季,始以三舉不中選者一體徑試于禮部,謂之免解進(jìn)士。先之所謂進(jìn)士,蓋鄉(xiāng)舉而試不入選者,故志乘無(wú)名也①[清]紀(jì)昀等編:《欽定四庫(kù)全書(shū)總目》,中華書(shū)局,1997年。。
《四庫(kù)全書(shū)總目》此條解題說(shuō)得非常清楚:唐宋至元,“貢于鄉(xiāng)者”,即“舉人”,也被稱(chēng)為“進(jìn)士”;南宋末年,舉人考進(jìn)士,三次考不中,皆試于禮部,稱(chēng)為“免解進(jìn)士”。
此外,尚有“歲進(jìn)士”的說(shuō)法。如周夢(mèng)莊先生曾和冒鶴亭談及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問(wèn)題,冒氏說(shuō):“如果我們承認(rèn)有施耐庵這個(gè)人的話,那末施耐庵可能是辛未年的歲進(jìn)士。”周夢(mèng)莊緊承冒氏結(jié)論后考證說(shuō):“考隋朝始設(shè)進(jìn)士科,唐宋因之,明朝始以舉人中式者為士,明初凡貢生入監(jiān),必由生員選擇各學(xué)文理優(yōu)者。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即歲進(jìn)士。《清會(huì)典》說(shuō):凡生員食餼久者,各以其歲之額貢于太學(xué),曰歲貢,查明清之制如此。”②周夢(mèng)莊:《〈水滸傳〉作者問(wèn)題》,江蘇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大豐縣《耐庵學(xué)刊》編輯部編《施耐庵研究》(續(xù)編),1990年5月印刷,第211頁(yè)。
無(wú)論“鄉(xiāng)貢進(jìn)士”、“免解進(jìn)士”還是“歲進(jìn)士”,都不同于真正意義上的“廷試進(jìn)士”。對(duì)于施耐庵非“廷試進(jìn)士”的論述,當(dāng)以陳建華先生的觀點(diǎn)為代表。陳建華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確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但這是‘鄉(xiāng)貢進(jìn)士’,在元代及明初被習(xí)稱(chēng)為‘進(jìn)士’。”“按元人習(xí)慣,‘進(jìn)士’不僅指會(huì)試及第者,亦常指領(lǐng)鄉(xiāng)薦者。有時(shí)呼他們?yōu)椤l(xiāng)貢進(jìn)士’,有時(shí)呼為‘進(jìn)士’。這樣稱(chēng)呼乃是沿宋人舊習(xí),而明、清以來(lái)呼鄉(xiāng)試及第者為‘舉人’,會(huì)試及第者為‘進(jìn)士’,兩者并不相混。”③陳建華:《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試證》,《明清小說(shuō)研究》第1輯,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5年8月。
陳先生之論,似乎非常有道理;并且陳先生經(jīng)過(guò)對(duì)大量材料的比對(duì)梳理,證明元朝至順二年辛未(1331)也的確舉行過(guò)鄉(xiāng)試。但問(wèn)題是:經(jīng)過(guò)陳先生證明的那些名為“進(jìn)士”實(shí)則名不副實(shí)的“鄉(xiāng)貢進(jìn)士”,有關(guān)他們的資料尚保存在不同的傳世文獻(xiàn)中,這些資料對(duì)他們身份的記載常常迥異,或以“進(jìn)士”稱(chēng)之,或以“鄉(xiāng)貢進(jìn)士(或舉人)”稱(chēng)之,故陳建華先生能夠通過(guò)元明時(shí)期《選舉志》的相關(guān)年代記載,對(duì)這些材料進(jìn)行比對(duì)探析,找到真正的答案,確定有些“進(jìn)士”的真實(shí)身份實(shí)為“鄉(xiāng)貢進(jìn)士”,絕非經(jīng)過(guò)會(huì)試的“進(jìn)士”。如對(duì)張羽“鄉(xiāng)貢進(jìn)士”身份的確認(rèn),陳先生的論證根據(jù)是:
高啟《高太史大全集》卷六有《詠雨酬張進(jìn)士羽見(jiàn)寄》一詩(shī),《明史》卷二八五有《張羽傳》,謂張羽“領(lǐng)鄉(xiāng)薦”。章冀《太常司丞張來(lái)儀墓志銘》有“擢科第,聲遂揚(yáng)。長(zhǎng)一山,安定學(xué)”等語(yǔ),謂張羽鄉(xiāng)試中式后授安定書(shū)院山長(zhǎng)之職,與《元史·選舉志》所載下第舉人“悉授以路府學(xué)正及書(shū)院山長(zhǎng)”之例合,知張羽確為舉人,然高啟稱(chēng)之為“進(jìn)士”。
《明史》、《太常司丞張來(lái)儀墓志銘》皆稱(chēng)張羽為“領(lǐng)鄉(xiāng)薦”之“舉人”,而高啟稱(chēng)之為“進(jìn)士”,結(jié)合《元史·選舉志》的相關(guān)記載,陳建華先生斷定張羽確曾為“舉人”,即“鄉(xiāng)貢進(jìn)士”而非真正意義上的“進(jìn)士”。
反觀稱(chēng)呼施耐庵為“進(jìn)士”的材料,全部稱(chēng)其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無(wú)一例外,根本沒(méi)有什么稱(chēng)其為“鄉(xiāng)貢進(jìn)士”的哪怕一絲記載;并且這些材料全部出自施氏家族內(nèi)部,從沒(méi)有官方資料的記載(詳見(jiàn)下文)。既然如此,說(shuō)施耐庵“辛未科進(jìn)士”實(shí)則為“鄉(xiāng)貢進(jìn)士”,就如同在沒(méi)有確實(shí)證據(jù)證明蘇北施彥端曾到過(guò)杭州的情況下①許多學(xué)者都把《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中的“播浙遂”當(dāng)作施彥端曾流寓杭州的證據(jù),但“播浙遂”的辨識(shí)較為武斷,不能令人信服,見(jiàn)拙作《〈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正可作為蘇北施耐庵之否證》,《水滸論議》,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2013年,第345~368頁(yè)。就以所謂施彥端曾寄居杭州為由將蘇北施彥端與“錢(qián)塘施耐庵”聯(lián)系起來(lái)一樣,是不是有點(diǎn)憑空臆測(cè)的意味?
不僅如此,由推斷施耐庵為至順辛未年的“鄉(xiāng)貢進(jìn)士”,陳建華先生還進(jìn)而認(rèn)為《浙江通志》中關(guān)于劉基等人名列“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這一不符合《元史·選舉志》的記載是有著一定理由的,他說(shuō):“我們?cè)賮?lái)看《浙江通志》關(guān)于劉基等人為至順辛未余闕榜的記載,就容易理解了。原來(lái)劉基和余闕都是至順辛未科‘鄉(xiāng)貢進(jìn)士’,他們?cè)谠y(tǒng)癸酉都登進(jìn)士第。關(guān)于劉基等人中辛未科進(jìn)士的記載,當(dāng)是舊志原有,而《浙江通志》的編者不知此指‘鄉(xiāng)貢進(jìn)士’,便誤入‘進(jìn)士’表。”
究其實(shí)際,劉基、余闕等人何嘗有過(guò)“鄉(xiāng)貢進(jìn)士”的記載。說(shuō)劉基、余闕等人為“鄉(xiāng)貢進(jìn)士”,在傳世文獻(xiàn)中找不到半點(diǎn)影子。《浙江通志》將劉基、余闕等人納入“至順辛未科”,分明就是記載有誤,而絕非劉基、余闕等人在至順辛未年(1331)中過(guò)什么“鄉(xiāng)貢進(jìn)士”。《浙江通志》置劉基、余闕等人為“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和施氏家譜記載施耐庵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一樣荒唐;劉基、余闕和施耐庵除了共同具有“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這種荒唐的頭銜外,還有一個(gè)共同點(diǎn),即從沒(méi)有任何材料說(shuō)過(guò)他們?cè)羞^(guò)“鄉(xiāng)貢進(jìn)士”。陳建華先生雖然意識(shí)到將劉基、余闕等人置身“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不合常規(guī),但竟然將其歸因于《浙江通志》的編者“不知此指‘鄉(xiāng)貢進(jìn)士’,便誤入‘進(jìn)士’表”,顯然也具有想當(dāng)然的意味。
三 歐陽(yáng)健先生之論及商榷之處
施耐庵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之說(shuō),與《元史·選舉志》的記載全然不符。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lái),歐陽(yáng)健先生在劉冬、陳建華二先生之論的基礎(chǔ)上,撰文《〈浙江通志〉元代選舉科目正訛——兼辨“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之由來(lái)》,發(fā)表于《明清小說(shuō)研究》2012年第1期,重新對(duì)施耐庵“辛未科進(jìn)士”的身份作了闡釋。
歐陽(yáng)健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其實(shí)不是“元朝辛未科(1331年)進(jìn)士”,而是至順?biāo)哪辏?333)進(jìn)士。那為什么在施氏各類(lèi)家譜、施氏宗祠“蘇遷施氏宗”神主以及《興化縣續(xù)志》載《施耐庵墓志》都說(shuō)施耐庵是“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呢?歐陽(yáng)健先生認(rèn)為主要是當(dāng)時(shí)的政治因素所致,即:“元文宗至順三年八月駕崩,至順?biāo)哪陼?huì)試,秉政者是悖逆比董卓更甚的燕鐵木兒。此科后被政敵攻為科場(chǎng)舞弊與腐敗,導(dǎo)致科舉的罷廢。故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要撇清與燕鐵木兒的關(guān)系,不致留下‘附逆’與‘行賄’的惡名。”②歐陽(yáng)健:《〈浙江通志〉元代選舉科目正訛——兼辨“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之由來(lái)》之《摘要》,《明清小說(shuō)研究》2012年第1期。以下所引歐陽(yáng)健先生之論,若不加以說(shuō)明,皆出此文。也就是說(shuō),施耐庵本為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但因?yàn)橹另標(biāo)哪暝l(fā)生權(quán)臣燕鐵木兒操縱下的科場(chǎng)舞弊案,導(dǎo)致當(dāng)年錄取的進(jìn)士名聲大受影響。為了撇清與燕鐵木兒的關(guān)系,不致被其壞名聲所累,施耐庵將自己身為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的身份隱藏得諱莫如深。但進(jìn)士身份畢竟是無(wú)法掩飾的,而且是家族的榮耀,不能不提,于是施耐庵就以一個(gè)根本沒(méi)有開(kāi)科的年份至順辛未年(1331)錄取的進(jìn)士自居;同理,施氏后人為了保持先祖的清譽(yù),也就以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稱(chēng)呼始祖施耐庵了。
為了證明至順?biāo)哪甑目茍?chǎng)舞弊案是存在的,歐陽(yáng)健先生對(duì)《浙江通志》、《元史·選舉志》、《元統(tǒng)元年進(jìn)士名錄》、《明史》以及各類(lèi)地方志的記載進(jìn)行了仔細(xì)的比對(duì)與歸納,確證在至順?biāo)哪甑臅?huì)試中,燕鐵木兒為了擴(kuò)充己力,將進(jìn)士名額擴(kuò)至百人,并廣受賄賂,以肥其家,“在這種大氣候下,‘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就不是什么桂冠,而是臭名四溢的惡謚了。當(dāng)此之際,得中進(jìn)士的心理狀態(tài),已經(jīng)沒(méi)有多少文獻(xiàn)可供鉤索;他們最本能的反應(yīng),便是模糊了之:既不否認(rèn)進(jìn)士身份(這是十分要緊的),又不確認(rèn)在至順?biāo)哪昕贾小薄@鐒⒒堊谠陀钗墓彛际窃?333年春二月參加會(huì)試,當(dāng)時(shí)所用的年號(hào)仍舊是至順,應(yīng)當(dāng)稱(chēng)為“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才對(duì),可是劉基《明史》本傳卻含糊地寫(xiě)作“元至順間,舉進(jìn)士,除高安丞”。“劉基連同張宗元、徐祖德、葉峴,不承認(rèn)是‘元統(tǒng)癸酉李齊榜’,而說(shuō)是‘至順二年辛未余闕榜’,可能都是劉基的主意。”
歐陽(yáng)先生的剖斷,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既然以劉基為代表的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都羞于提及“至順?biāo)哪辍笔菚r(shí)代因素所致,故歐陽(yáng)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中的也是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而絕非至順辛未(1331)科進(jìn)士:“明明中的是至順?biāo)哪辏?333)進(jìn)士,為什么要說(shuō)成是‘至順辛未進(jìn)士’?因?yàn)樗温毜牡胤绞清X(qián)塘,要和劉基為代表的江浙行省同科進(jìn)士在履歷上保持一致。”
歐陽(yáng)先生將劉基等人羞于提及“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的苦衷推及施耐庵身上,那施耐庵就是和劉基等人同榜的進(jìn)士了。這究竟有沒(méi)有可能性?
先來(lái)看一看施耐庵為至順辛未年進(jìn)士的依據(jù)。歐陽(yáng)健先生認(rèn)為依據(jù)有二:第一,“施耐庵為‘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見(jiàn)錄于《施氏家譜》、‘施氏族譜世系’,施氏宗祠‘蘇遷施氏宗’神主與《興化縣續(xù)志》所載《施耐庵墓志》等”。第二,《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施封之序,署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謂‘自明迄清,相沿不墮’,可知第一世耐庵公為‘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之說(shuō),其來(lái)有自。”我們來(lái)看一看這兩類(lèi)依據(jù)是否客觀。
(一)《施氏家譜》、施氏族譜世系及施氏宗祠神主,都出自蘇北興化施氏家族;至于《興化縣續(xù)志》所載《施耐庵墓志》,歐陽(yáng)建先生也說(shuō):“《施氏家譜》附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系1919年《興化縣續(xù)志》坐辦兼分纂人劉仲書(shū)從《施氏家譜》中抄得,載入《興化縣續(xù)志》。”可見(jiàn)《施耐庵墓志》也出自施氏家族。也就是說(shuō),所有關(guān)于施耐庵為元朝進(jìn)士的材料,全部出自蘇北施氏家族,而不是出自官方史料或地方史料。這就令人難免對(duì)這些材料的客觀性產(chǎn)生懷疑。尤其是托名明初淮安人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更是徹頭徹尾的假文物,引用其中的材料作為證據(jù),更是令人不敢茍同(詳見(jiàn)下文)。
(二)至于《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本是蘇北興化施氏第十四世裔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修,但在流傳過(guò)程中原件失去。現(xiàn)在我們見(jiàn)到的《長(zhǎng)門(mén)譜》,是民國(guó)七年(1918)施氏第十八世裔僧施滿家抄錄之本。《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的內(nèi)容可分為三部分:一是世系延續(xù)的實(shí)錄。自元末明初的始祖施彥端開(kāi)始,一直到第十八世僧滿家,代次的延續(xù)脈絡(luò)相當(dāng)清楚,時(shí)間跨度達(dá)五百多年;二是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撰寫(xiě)的《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序,三是淮南一鶴道人楊新于明景泰四年為施彥端之子施讓?zhuān)ㄗ忠灾t)撰寫(xiě)的《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但就是這樣一部文物真品,其中也有令人疑竇叢生之處,那就是在世系記載“第一世始祖彥端公元配季氏申氏生讓”之“始祖彥端公”的天頭位置,添加了眉批“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這個(gè)眉批究竟是施封所寫(xiě),還是后人添加。筆者以為出自后人添加,原因是:第一,施封為《長(zhǎng)門(mén)譜》所寫(xiě)之序,根本沒(méi)有提到始祖施彥端中進(jìn)士之事。正如歐陽(yáng)健先生所言,序中的確提到了施氏譜系手抄筆錄“自明至清,相沿不墮”的情況,但這說(shuō)的只是譜系的承接沿襲,而沒(méi)有任何一句提及施彥端中進(jìn)士。故僅僅依據(jù)施封序中“自明至清,相沿不墮”之句來(lái)證明《長(zhǎng)門(mén)譜》中的眉批“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其來(lái)有自,恐是徒勞。第二,附錄于《長(zhǎng)門(mén)譜》的明景泰年間楊新為施彥端之子施讓所寫(xiě)的《故處士施公墓志銘》,提及彥端,僅有“先公彥端,積德累行,鄉(xiāng)鄰以賢德稱(chēng)”,也根本沒(méi)有中進(jìn)士之事。
這里必須提及另一件事。在咸豐四年(1854)由施埁所修《施氏族譜》中也有一篇楊新的《故處士施公墓志銘》,銘文中說(shuō)到施彥端的文字竟然是“先公耐庵,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高尚不仕。國(guó)初,征書(shū)下至,堅(jiān)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積德累行,鄉(xiāng)鄰以賢德稱(chēng)”。與《長(zhǎng)門(mén)譜》中的楊新之銘相比,《施氏族譜》將“先公彥端”改為“先公耐庵”,并且多出了“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高尚不仕。國(guó)初,征書(shū)下至,堅(jiān)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共計(jì)二十八字。歐陽(yáng)健先生認(rèn)為《施氏族譜》中的楊新之銘是可信的,《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中少了二十八字,是被施滿家抄錄施封之譜時(shí)刪去了:“為什么要?jiǎng)h?滿家為一僧徒,他既不會(huì)贊成‘誨盜’,也不會(huì)贊成魯智深式的大鬧五臺(tái)山。滿家為諱言著《水滸》事,可能不僅刪去楊新的墓志銘中的那段話,將‘先公耐庵’改為‘先公彥端’,而且連世系中‘字耐庵’三字也棄而不書(shū),從而將與《水滸》有關(guān)的痕跡全部清除干凈。這樣一個(gè)明顯的改動(dòng),大約當(dāng)即遭到族人的非議,于是只得在行邊添上‘字耐庵’三字以補(bǔ)救。楊新的墓志銘,則因字?jǐn)?shù)太多,而終于沒(méi)法添上。”①歐陽(yáng)健“《關(guān)于〈水滸〉作者施耐庵之我見(jiàn)》,江蘇省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施耐庵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52~353頁(yè)。
很顯然,歐陽(yáng)健先生的滿家刪除之說(shuō)也是其認(rèn)為“第一世耐庵公為‘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之說(shuō),其來(lái)有自”的重要證據(jù),但歐陽(yáng)健先生的說(shuō)法,遭到了許多學(xué)者的否定。章培恒先生說(shuō):
有同志認(rèn)為:自“元至順”至“自遣”二十八字為墓志銘所原有,但被滿家刪掉了,因?yàn)椤皬钠洹鍪馈挠^點(diǎn)來(lái)看,上述諸事是應(yīng)該‘為親者諱’的。”按,佛家講究“慈悲”,而《水滸》則對(duì)殺人放火頗多贊同,也許確為滿家所不滿。但是,“高尚不仕”、“征書(shū)下至,堅(jiān)辭不出”這樣的行為,即使“從其‘出世’的觀點(diǎn)來(lái)看”,不也是無(wú)可非議的嗎?為什么也要“諱”、要?jiǎng)h?在《施氏家簿譜》的世系表上,滿家端端正正地寫(xiě)著:其始祖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假如《墓志銘》確有“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之語(yǔ),他又為什么要加以刪除呢?所以,把兩者的不同歸于滿家的刪削,是說(shuō)不過(guò)去的。②章培恒:《施彥端是否施耐庵》,《復(fù)旦學(xué)報(bào)》1982年第6期。
章培恒先生的話的確非常有道理。如果施耐庵真有“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高尚不仕”和“著《水滸》”等榮光,因滿家是出家人,不贊成梁山好漢的殺人放火及魯智深大鬧五臺(tái)山的行徑,他只要?jiǎng)h去“隱居著《水滸》自遣”即可,怎么可能將先祖“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高尚不仕”等無(wú)限榮耀盡皆刪去?隱晦先祖的榮耀,難道也是“為親者諱”?
說(shuō)楊新之銘中絕沒(méi)有“中進(jìn)士”、“著《水滸》”之事,尚有另一證據(jù)。施埁于咸豐四年所修《施氏族譜》,抽去了施封之序,以陳廣德的《施氏族譜序》取而代之。陳廣德在序中雖然已將“彥端”替換為“耐庵”,但提及楊新之銘,仍舊說(shuō):“銘所云:‘積德累行,鄉(xiāng)鄰以賢德稱(chēng)’者,信可徵也。”并沒(méi)有提及彥端“中進(jìn)士”、“高尚不仕”、“著《水滸》”的事跡。針對(duì)這種情況,趙振宜、張丙釗、施恂清三先生分析道:
從陳廣德所撰《譜序》中,還可以看出原《長(zhǎng)門(mén)譜》(筆者注:指的是施封序中提到的原《長(zhǎng)門(mén)譜》)和《咸豐譜》,所錄楊新作的《墓志銘》,同新發(fā)現(xiàn)的《長(zhǎng)門(mén)譜》抄本所載是相同的,并未有“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隱居著《水滸》自遣”的話。為什么能這樣說(shuō)呢?因?yàn)殛悘V德作《序》時(shí),是想極力把施氏家族譜褒頌一番的,但他是個(gè)治學(xué)嚴(yán)謹(jǐn)?shù)娜耍瑢?xiě)文務(wù)求詳實(shí)。他按族譜世系上字諱,改彥端為“耐庵”,盡量引用楊新所撰《墓志銘》中原有的贊頌之詞,引用了“積德累行,相鄰以賢德稱(chēng)”。試想,如果見(jiàn)到“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高尚不仕。國(guó)初,征書(shū)下至,堅(jiān)辭不出”的話,豈能不加引用呢?盡管咸豐初年《水滸》仍被列入禁書(shū),但避開(kāi)“隱居著《水滸》自遣”,其它話是完全可以引用的。何況,他把名“彥端”,換用字“耐庵”,這實(shí)際上等于說(shuō)彥端即著《水滸》的作者耐庵。正由于陳廣德所撰“譜序”的可信,故于一九五二年調(diào)查時(shí)得以發(fā)現(xiàn)楊新所作《墓志銘》中那段話,有“后人竄入之嫌”。三十年后的今天,新發(fā)現(xiàn)的《長(zhǎng)門(mén)譜》恰恰證實(shí)了這一點(diǎn)。如果是《長(zhǎng)門(mén)譜》轉(zhuǎn)抄者滿家有意刪去的話,他只要?jiǎng)h去有犯佛門(mén)戒律的那句“隱居著《水滸》自遣”就行了,怎么能把前面門(mén)庭引以為榮的話刪去?①趙振宜、張丙釗、施恂清:《〈施氏族譜〉考略》,《施耐庵研究》,第137~138頁(yè)。
趙、張、施三先生的剖析非常在理。咸豐四年施埁建祠修譜,邀請(qǐng)陳廣德為《施氏族譜》作序,如果此時(shí)楊新之銘中真有施氏先祖施彥端“中進(jìn)士”的榮光,陳廣德又怎能在《施氏族譜序》中毫不提及,而僅說(shuō)彥端“積德累行,鄉(xiāng)鄰以賢德稱(chēng)”?這說(shuō)明陳廣德作序時(shí),其看到的楊新之銘尚沒(méi)有添加施耐庵“中進(jìn)士”、“高尚不仕”及“著《水滸》”的事跡。既然咸豐四年的陳廣德都沒(méi)有看到楊新之銘中添加的內(nèi)容,乾隆年間的《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中附錄的楊新之銘又怎么可能有施耐庵的種種事跡呢?由此類(lèi)推,滿家和尚于民國(guó)七年抄錄《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時(shí),見(jiàn)到的楊新之銘當(dāng)然也沒(méi)有施耐庵“中進(jìn)士”、“高尚不仕”及“著《水滸》”的種種事跡,又何來(lái)滿家刪除之說(shuō)?
除了章培恒、趙振宜等人,否定歐陽(yáng)先生之論的尚有盧興基、石昌渝二先生。盧興基認(rèn)為:“楊新的墓志銘和地券年月完全一致,其中著《水滸》一段話沒(méi)有,有同志相信是刪掉的,我的分析是加上去的。”石昌渝也說(shuō):“楊新墓志銘中的一段話是后人竄入的,不是刪去的。”②歐陽(yáng)健記錄整理:《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問(wèn)題座談會(huì)發(fā)言紀(jì)略》,載《理論研究》1982年第6期。《施氏族譜》附錄的楊新之銘,比《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中附錄的楊新之銘多出的二十八字,包括施耐庵“中進(jìn)士”,都不是施封原譜中的楊新之銘所有。
如此看來(lái),《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中的施封序和楊新銘,根本沒(méi)有提到始祖施彥端中進(jìn)士的光榮事跡。而中進(jìn)士是何等隆重之事,正如葉元章先生所言:“倘始祖彥端確為進(jìn)士,那就非同小可,自應(yīng)大書(shū)特書(shū)。楊新志、施封序乃至《施廷佐墓志銘》中,豈能一字不提?”③葉元章:《關(guān)于施耐庵文物史料的幾個(gè)問(wèn)題》,《施耐庵研究》,第316頁(yè)。既然《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中的施讓墓志銘、施封序中沒(méi)有提及彥端中進(jìn)士之事,顯然“中進(jìn)士”也是子虛烏有,由此也可推論《長(zhǎng)門(mén)譜》中第一世始祖“彥端公”天頭上的眉批“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顯然是后人所加,而非出自施封之筆。歐陽(yáng)健先生認(rèn)為蘇北施氏“第一世耐庵公為‘元至順辛未進(jìn)士’之說(shuō),其來(lái)有自”,是沒(méi)有令人信服的證據(jù)的。
再來(lái)看一看官方資料。在20世紀(jì)50年代上海文聯(lián)召開(kāi)的《水滸》作者座談會(huì)上,據(jù)洪瑞釗先生發(fā)言,他查過(guò)《元史·選舉志》、《興化縣志》和《淮安縣志》。在1854年(咸豐元年)所刻的《興化縣志》元末明初的進(jìn)士表里沒(méi)有施耐庵;在1884年(光緒十年)所刻的《淮安縣志》元末明初的進(jìn)士表里面也沒(méi)有施耐庵。④原載《曉報(bào)》1952年12月3日,收入趙景深《中國(guó)小說(shuō)叢考》,齊魯書(shū)社,1980年,第136~137頁(yè)。
也就是說(shuō),關(guān)于施耐庵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的依據(jù),全部來(lái)自蘇北施氏家族內(nèi)部,沒(méi)有任何官方材料的記載可以證明。而這些依據(jù),無(wú)論施氏家譜、“蘇遷施氏宗”神主還是《施耐庵墓志》,都眾口一詞、無(wú)一例外地說(shuō)施耐庵是至順辛未(1331)進(jìn)士,從沒(méi)有其他的說(shuō)法。這和劉基、宇文公諒等人不同。如對(duì)于劉基中進(jìn)士的情況,歐陽(yáng)健先生先后引用了《明史》、《浙江通志》、雍正《青田縣志》等各類(lèi)材料;對(duì)于宇文公諒中進(jìn)士的情況,歐陽(yáng)健先生先后引用了《元史》、《浙江通志》、光緒《歸安縣志》等各類(lèi)材料。這些材料對(duì)劉基、宇文公諒中進(jìn)士的年份記載往往有參差,故將這些出處不同、記載各異的材料進(jìn)行比對(duì),再聯(lián)系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歐陽(yáng)先生才得出劉基等人羞于提及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身份的結(jié)論。而反觀施彥端,提及他的進(jìn)士身份,都是“至順辛未進(jìn)士”,從沒(méi)有其他說(shuō)法,更沒(méi)有記載不同的材料可以比較參照。既然如此,歐陽(yáng)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不是“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而是至順?biāo)哪辏?333)進(jìn)士的結(jié)論,是不是有點(diǎn)想當(dāng)然?究其實(shí)際,施耐庵為元辛未進(jìn)士,完全是施氏家族自說(shuō)自道,借以夸耀先祖身份而已。
而歐陽(yáng)健先生則認(rèn)為施耐庵的科第有充分的根據(jù)。根據(jù)是朱希江《水滸外傳后記》中提及的《周鐸筆記》中的一段記載:
施耐庵于元朝泰定年間曾赴元大都科舉,滿以為一舉成名,不料名落孫山。當(dāng)時(shí)大都有他一位好友名叫劉本善,官居國(guó)子監(jiān)司業(yè)。施耐庵投奔他后,便百般周旋。恰逢山東鄆城縣訓(xùn)導(dǎo)有缺,便去赴任。
《周鐸筆記》究竟是一部什么書(shū)?不得而知,反正在明清所有目錄學(xué)著作中不見(jiàn)記載。此書(shū)究竟是誰(shuí)發(fā)現(xiàn)的,誰(shuí)傳抄的,一概不知;據(jù)說(shuō)此書(shū)在“文革”期間燒掉了,是真是假,誰(shuí)也說(shuō)不清楚。就算真有此書(shū),這段記載,也完全不可信。
《周鐸筆記》說(shuō)施耐庵曾于泰定年間赴大都科考,此處“泰定年間”究竟是什么時(shí)候?歐陽(yáng)健先生認(rèn)為是泰定四年(1327):“施耐庵之應(yīng)試,當(dāng)在此時(shí)。落第后得劉司業(yè)薦,至鄆城任訓(xùn)導(dǎo)……則施耐庵之中舉,當(dāng)在泰定元年(1324年)之前的延祐、至治年間。至順元年(1330)或至順?biāo)哪辏?333),施耐庵赴大都會(huì)試,他之中進(jìn)士,應(yīng)為至順?biāo)哪辏?333)。”
這里必須要解釋一個(gè)問(wèn)題:施耐庵泰定四年(1327)中舉及至順?biāo)哪辏?333)中進(jìn)士時(shí)年庚究竟是多少?
歐陽(yáng)健先生一直是相信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記載的,并且還引用了《施耐庵墓志》對(duì)施耐庵生年的記載:“(施耐庵)生于元貞丙申歲,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曾官錢(qián)塘二載,以不合當(dāng)?shù)罊?quán)貴,棄官歸里,閉門(mén)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終。”至于施耐庵的卒年,《施耐庵墓志》也寫(xiě)得很清楚:“蓋公歿于明洪武庚戌歲,享年七十有五。”元貞丙申至洪武庚戌,即1296—1370,施耐庵正好享年75歲。以此類(lèi)推,泰定四年(1327)施耐庵中舉時(shí)30歲,至順?biāo)哪辏?333)施耐庵中進(jìn)士時(shí)38歲,這似乎沒(méi)有什么破綻。但歐陽(yáng)健先生完全忽略了一個(gè)問(wèn)題。
據(jù)楊新為施耐庵之子施讓撰寫(xiě)的《故處士施公墓志銘》記載,施讓生于明洪武癸丑(1373)。《故處士施公墓志銘》可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文物,是誰(shuí)也翻不了的鐵證。既然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說(shuō)施耐庵的生卒年為1296—1370,則出現(xiàn)了一個(gè)天大的漏洞:這個(gè)施耐庵不僅要活到78歲其子施讓方才出生,而且施讓出生還在施耐庵死后3年。這種情況不僅不可想象,而且極大地侮辱了施耐庵之妻季氏與申氏。雖然劉冬先生曾對(duì)這種異常的情況竭力辯解:“施耐庵無(wú)子,死后三年或更多幾年,才由未亡人決定,過(guò)繼讓為子。”①劉冬:《施耐庵生平探考》,《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輯。但1978年出土的《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卻明明白白地寫(xiě)著:“(曾)祖彥端會(huì)元季兵起”,播遷,“家之及世平懷故居興化(還)白駒生祖以謙”。由“生祖以謙”,可知施讓是施彥端的親生子,這絕無(wú)異議。顯然《施耐庵墓志》所謂施耐庵生于1296年的說(shuō)法乃信口雌黃。歐陽(yáng)健先生以《施耐庵墓志》記載的施耐庵的生卒年為依據(jù),推斷施耐庵30歲中舉、38歲中進(jìn)士,能夠服眾否?
我們來(lái)看看當(dāng)今學(xué)者依據(jù)施讓之銘和《施廷佐墓志銘》的記載對(duì)施耐庵生年的推斷:王同書(shū)先生認(rèn)為是1328年①王同書(shū):《〈水滸〉作者施耐庵生平研究》,《鹽城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年第3期。;李偉實(shí)先生推算大約1333年②李偉實(shí):《施彥端到底是不是〈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學(xué)術(shù)研究叢刊》1984年第1期。,陳遼先生認(rèn)為是1332年③陳遼:《水滸作者施耐庵之謎再解》,《鹽城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年第6期。,李、陳二先生的結(jié)論幾乎一致;李靈年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大概生于元文宗天歷、至順年間,至遲不會(huì)晚于元惠宗元統(tǒng)初年(約1329—1334)④李靈年:《施耐庵雜考》,見(jiàn)《施耐庵研究》,第182頁(yè)。;張惠仁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出生于1320年⑤張惠仁:《施耐庵的名、字、號(hào)及其生卒年新論》,《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1999年第4期。;洪東流先生認(rèn)為施耐庵出生于“大元甲申”,即1344年⑥洪東流:《水滸解密》,學(xué)林出版社,2007年,第498~499頁(yè)。;馬成生先生認(rèn)為“若據(jù)其(筆者注:指施彥端)‘享年七十有五’推算,他當(dāng)出生于十四世紀(jì)三十年代(1330年之后)”⑦見(jiàn)馬成生為拙著《水滸論議》所作之序(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2013年)。另,馬成生先生后又在《未免有浮夸之嫌——且說(shuō)“弄〈水滸〉惹大禍”》文中,進(jìn)一步推斷施彥端“約生于1334年左右,卒于1409年左右”,與李偉實(shí)、陳遼二先生的結(jié)論幾乎一致,見(jiàn)浙江三國(guó)演義專(zhuān)業(yè)委員會(huì)、浙江水滸專(zhuān)業(yè)委員會(huì)編:《三國(guó)水滸研究與欣賞》第十輯,第317頁(yè)。。比較而言,1320年的說(shuō)法不大可信,因?yàn)榘凑者@種說(shuō)法,施讓洪武癸丑(1373)出生時(shí),施耐庵已經(jīng)54歲了,可謂老來(lái)得子。如此大喜事,楊新為施讓所寫(xiě)的《墓志銘》中竟然沒(méi)有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實(shí)在不大可能。其他幾種說(shuō)法,將施耐庵的生年集中于1328年到1344年之間,最大誤差僅為16年,應(yīng)當(dāng)說(shuō)是比較客觀的。但無(wú)論采取哪用說(shuō)法,歐陽(yáng)健先生所謂的施耐庵中舉的泰定四年(1327),施耐庵根本沒(méi)有出生;施耐庵中進(jìn)士的至順?biāo)哪辏?333),施耐庵根本沒(méi)有超過(guò)11周歲。說(shuō)施耐庵泰定四年中舉、至順?biāo)哪曛羞M(jìn)士,沒(méi)有任何可能性。
我們從上述學(xué)者對(duì)施耐庵生年的推論中,還可以看出歐陽(yáng)健先生深信不疑的一系列材料的問(wèn)題:《周鐸筆記》說(shuō)泰定年間(1324—1328),劉本善推薦施耐庵擔(dān)任鄆城訓(xùn)導(dǎo),而此時(shí)施耐庵尚未出生,怎么可能受到劉本善的推薦?由此可見(jiàn)《周鐸筆記》的記載根本不可信,純屬一筆糊涂賬。⑧《周鐸筆記》內(nèi)容荒唐,根本沒(méi)有可信性,見(jiàn)拙文《如何看待蘇北地區(qū)施耐庵的傳說(shuō)——兼與歐陽(yáng)健先生商榷》,《水滸論議》,第242~273頁(yè)。劉基為至順?biāo)哪辏?333)進(jìn)士,此時(shí)施耐庵尚是稚嫩的少年或嗷嗷待哺的嬰幼兒,焉能有和劉基同榜的機(jī)緣?蘇北傳說(shuō)中關(guān)于施耐庵和劉基的“同門(mén)”之誼,完全沒(méi)有歷史依據(jù),在史書(shū)上見(jiàn)不到任何記載,不足為據(jù)。
姑且循著歐陽(yáng)先生的思路走下去。就算施耐庵真是至順?biāo)哪辏?333)進(jìn)士,為什么施氏家譜中認(rèn)為他是“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呢?歐陽(yáng)健先生回答說(shuō):“因?yàn)樗温毜牡胤绞清X(qián)塘,要和劉基為代表的江浙行省同科進(jìn)士在履歷上保持一致。”
說(shuō)施耐庵曾任職錢(qián)塘,又是出自偽《施耐庵墓志》。可是我們查找今天所有的杭州地區(qū)的方志,無(wú)論是《浙江通志》、《杭州府志》還是《錢(qián)塘縣志》,從沒(méi)有施耐庵為官錢(qián)塘的記載。施耐庵任職錢(qián)塘的說(shuō)法,別說(shuō)他人不相信,就是有些相信蘇北施彥端和《水滸》作者施耐庵“合一”的學(xué)者,例如陳遼、袁世碩、章培恒等先生都對(duì)此表示否定。就現(xiàn)今發(fā)現(xiàn)的可靠的文物與史料來(lái)說(shuō),還從沒(méi)有看到過(guò)蘇北施彥端曾任職錢(qián)塘的記載。今天許多學(xué)者都把1978年出土的《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中的“播浙遂”當(dāng)作蘇北施彥端與錢(qián)塘施耐庵“合一”的依據(jù),甚至將其斷為施耐庵曾任職錢(qián)塘的根據(jù)。可是就如同筆者所論,將《施廷佐墓志銘》“(曾)祖彥端會(huì)元季兵起□□□家之”中“兵起”后的三個(gè)“□”固定解讀為“播浙遂”似乎略顯輕率武斷。⑨見(jiàn)拙文《〈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正可作為蘇北施耐庵之否證》,《水滸論議》,第345~368頁(yè)。
可是歐陽(yáng)健先生卻提供了施耐庵錢(qián)塘為官的材料,且看他的說(shuō)明:
能證明施耐庵錢(qián)塘為官的材料,有1952年10月文化部調(diào)查組得自顧明府石蓀手抄先人九苞公遺墨的施耐庵遷興化詩(shī)和顧逖贈(zèng)施耐庵遷興化詩(shī)。施耐庵遷興化詩(shī)曰:
年荒亂世走天涯,尋得陽(yáng)山好住家;
愿辟草萊多種樹(shù),莫教李子結(jié)如瓜。
顧逖贈(zèng)施耐庵遷興化詩(shī)曰:
君自江南來(lái)問(wèn)津,相逢一笑舊同寅。
此間不是桃源境,何處桃源好避秦。
按顧逖為至正間進(jìn)士,嘉靖三十八年(1559)《興化縣志》(胡志)《名賢列傳》謂:“顧逖,字思邈,至正兵后,同知松江府事。”他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九年(1359—1362)任松江同知,后遷嘉興路同知,都在張士誠(chéng)治下,傳中晦不明言。施耐庵后亦投張士誠(chéng),適可稱(chēng)為“同寅”。
筆者按:所謂施耐庵遷興化詩(shī),庸俗鄙陋,文無(wú)足采,哪像《水滸傳》中的詩(shī)詞文風(fēng)。這首軼詩(shī)據(jù)說(shuō)是顧逖后裔、曾于清朝光緒二十六年任河南蘭封知縣的顧碩號(hào)石蓀所藏,宣統(tǒng)三年五月初一在興化創(chuàng)刊、由金逸園主編的石印《楚陽(yáng)》雜志曾發(fā)表過(guò)。而張國(guó)光先生認(rèn)為,即使有顧逖此人,也不能據(jù)此推論就有施耐庵本人:“因此詩(shī)不見(jiàn)于元人詩(shī)集,乃僅見(jiàn)于1913年出版的《楚陽(yáng)十日?qǐng)?bào)》。而該刊編者則說(shuō)得自顧石蓀手抄的乾隆時(shí)進(jìn)士顧九苞的遺墨。這分明是胡編瞎造叫你無(wú)從調(diào)查。”①?gòu)垏?guó)光:《魯迅的“施耐庵”為繁本〈水滸傳〉作者之托名說(shuō)無(wú)可置疑——兼析關(guān)于施耐庵的墓志、家譜、詩(shī)文、傳說(shuō)之俱難征信》,《水滸爭(zhēng)鳴》第一輯,1982年。所謂施耐庵贈(zèng)送顧逖之詩(shī),來(lái)歷可疑,不足征信。
再來(lái)看顧逖的年庚。從萬(wàn)歷《興化縣志》或康熙《松江府志》的記載來(lái)看,顧逖為元大德間舉人。按照李偉實(shí)先生的看法,姑且將其定為大德五年(1301年,大德共十一個(gè)年頭),則顧逖當(dāng)時(shí)起碼二十歲(實(shí)際上很可能不止二十歲),上溯十九年,則顧當(dāng)生于1282年左右。②李偉實(shí):《施彥端到底是不是〈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學(xué)術(shù)研究叢刊》1984年第1期。按照上文所說(shuō)施彥端的生年1328—1344年的范圍來(lái)看,當(dāng)1359年施耐庵寄詩(shī)給松江同知顧逖時(shí)③浦玉生:《施耐庵生平探考》,《鹽城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年第4期。,顧老先生大約77歲左右,而此時(shí)的施耐庵大約15—31歲,兩人完全是爺孫輩,顧老先生對(duì)自己孫子輩的施耐庵還能“相逢一笑舊同寅”,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生七十古來(lái)稀,77歲的顧老先生乃垂死之人;施耐庵回到興化,此時(shí)天下已經(jīng)平定。施耐庵和顧逖,究竟是誰(shuí)還需尋找什么“桃源境”好避“秦”?顧逖1359年至1362年任松江同知,后又遷嘉興路同知,始終在張士誠(chéng)手下做官。這聽(tīng)起來(lái)本身就有點(diǎn)荒謬,因?yàn)榘凑疹欏焉?282年來(lái)推算,1359年至1362年,顧氏已經(jīng)是年近八十歲的老人了,還要嘔心瀝血地?fù)?dān)任地方的同知,張士誠(chéng)會(huì)這樣對(duì)待老年人嗎??jī)H此就可以看出所謂顧逖與施耐庵交往的真假來(lái)。兩人之間的贈(zèng)答詩(shī),又有幾分可信性?
由此可見(jiàn),從元朝政治背景出發(fā),推斷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實(shí)為“至順?biāo)哪赀M(jìn)士”之誤,這種說(shuō)法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綜上可知,所謂施耐庵為“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之說(shuō),主要破綻體現(xiàn)在三方面:一是至順辛未年(1331)根本沒(méi)有開(kāi)科的記錄;二是官方史料與地方史料中從沒(méi)有進(jìn)士施耐庵的記載;三是“辛未”中進(jìn)士與施耐庵的年庚根本不相吻合。施耐庵為“至順辛未進(jìn)士”根本就是子虛烏有。如同前文所論,這種說(shuō)法出自蘇北興化施氏家族,在各類(lèi)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依據(jù),當(dāng)是蘇北施氏向壁虛構(gòu)的產(chǎn)物。施耐庵“元朝辛未科進(jìn)士”之說(shuō)出現(xiàn)于《施氏長(zhǎng)門(mén)譜》,其實(shí)質(zhì)恰如王利器先生所說(shuō):“研究家族譜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態(tài)度,在中國(guó)封建朝代里,族譜絕大部分是假的。清初的大文學(xué)家黃宗羲就說(shuō)過(guò),天下最不可信的書(shū)之一,就是氏族譜。明代以來(lái),修家譜拉名人的情況很多,作假風(fēng)氣太盛,所以我們格外要慎重對(duì)待。”①見(jiàn)楊志廣整理:《文學(xué)所召開(kāi)施耐庵文物史料問(wèn)題座談會(hu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1982年第6期。
A Fallacy that Shi Nai’an Was a Jinshi in the Year of Xinwei in the Yuan Dynasty——A Different Idea from Mr.Ouyang Jian
Yang Dazhong
The assertion that Shi Nai’an became a Jinshi in the year of Xinwei in the Yuan dynasty is arbitrary because there was no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feudal examination in the year of Xinwei (1331) during the reign of Zhishun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no official or local record shows that Shi Nai'an was a Jinshi.Mr.Liu Dong believes that the assertion is originated from the descendents of Shi Nai’an, who mistakenly recorded that“Shi Nai’an became a Jinshi in the year of Xinwei in the Yuan dynasty”, or from the fact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was not in good order.This view can't be accepted, either.Mr.Ouyang Jian maintains that Shi Nai'an became a Jinshi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reign of Zhishun (1333)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at the assertion that Shi Nai’an became a Jinshi in the year of Xinwei in the Yuan dynasty was the result of examination Fraudulence controlled by El-Temur.This conclusion is also groundless.
Shi Nai’an; a Jinshi in the Year of Xinwei in the Yuan Dynasty; Feudal Examination Fraudulence Case; Discussion
(楊大忠,浙江傳媒學(xué)院副教授,桐鄉(xiāng)市高級(jí)中學(xué)教師發(fā)展中心副主任)
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