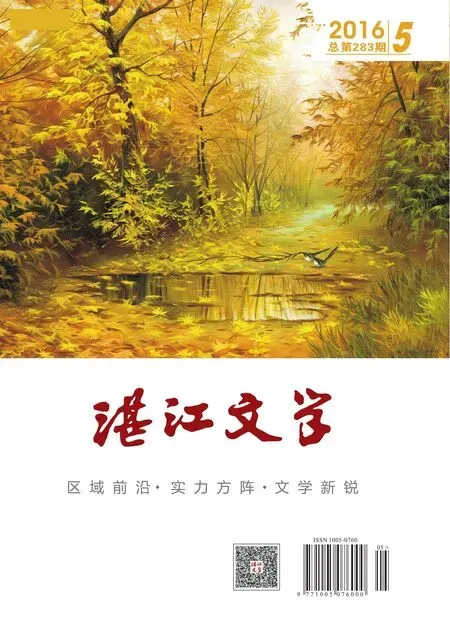漫長的婚約
※ 譚 巖
漫長的婚約
※ 譚 巖
什么,要你拿錢?!那先是怎么說的?房子就沒有本事弄好,還想娶老婆?!
沒有想到,男朋友借錢裝房的事還沒說完,搖著扇子搧風的母親就跳了起來,一柄芭蕉扇在茶幾上拍得啪啪響:
一分錢都不能給!還說是借,那是劉備借荊州,一借永不還!你這么大了也不自己想想,他說借你就借?我看你是豬腦殼——
葉心怡的男朋友朱大明在江心花園購了一套房子,兩家商量好了,房子一裝修完,倆個就辦結婚。可是房子才裝到一半,錢就用完了,朱大明問她能不能想想辦法。葉心怡這幾年節吃儉用,也存了幾萬塊錢,可是這錢卻不能由她自己做主,她要跟媽商量。她的存款不僅被媽管著,她的生活也是被媽管著,在母親的眼中,她就是一只長不大的小雞,永遠需要她這只老母雞張開翅膀訶護著。
無端地受了一頓母親的臭罵,葉心怡又急又惱,腳一跌,飯也沒吃就回學校了。一人在辦公室,想一想,還擦一下鼻子,心想這一邊是母親,一邊是男朋友,自己夾在中間好難做人。好在別個老師這時都還有午休,沒有來,沒有人會看到她的狼狽樣兒。那天下午,放在屜子包里的電話響了好幾遍,她知道是男友朱大明打來的,是要催她拿錢的。他的一個電話就惹得自己白白地挨了母親的一頓罵,正惱他呢,所以就任它在屜子里響,響得火急火燎也懶得理他。
一直到了放學,她要看時間,才從屜子里掏出電話,一看果然是四五個未接來電,可沒想到再一按鍵,那電話上顯示的號碼卻讓她很覺意外,那不是男朋友朱大明的熟悉的號碼,是一串陌生的數字,一個從沒有接過的陌生電話。
是誰?還打了四五遍?莫不是打錯了吧。
正在疑惑,那個號碼又打來了。
喂,請問您找誰?葉心怡禮貌地問。
你好!是葉心怡吧?
對方完全是熟人的語氣。這是一個非常——磁性的男中音!葉心怡身心一震,可仍是不相信似地遲疑道:
請問您是?
哈,怎么,大教授聽不出我的聲音來了?
你說什么?我們小學是沒有教授的。毫無生活情趣的葉心怡老老實實地糾正道,請問你是?
對方嘆了一口氣,葉心怡感覺到人家是在說,你怎么還是老樣子啊,接著就聽到了一個讓她心跳的名字:
我是田小寶。
怎么會是你?!你怎么會有我的電話?!
怎么不能是我?怎么不能有你的電話?哈哈,你不想我,也不允許我想想你嗎?
調侃著的田小寶在電話里開起了玩笑。
你現在在哪里啊?還在水月寺中學嗎?葉心怡覺得自己太敏感了,有些不好意思地掩飾說。他們那一個年級的同學,不少是委培生,大多分回了山區的鄉鎮,除了她這種本身是城市戶口的人。
哈,就知道你一點兒也不關心我——早不在那個學校了!
田小寶告訴她,他已跳槽到一家企業工作——那是一家非常有名的企業,各國各地都設有分公司,現在他已是一個部門的經理,來聊城參加那個企業的中層干部培訓班的。
晚上有時間嗎,聚一聚?
電話那頭,田小寶熱情萬丈地邀請道。
還有誰?葉心怡的意思是說,還請了哪些同學?畢業后,也有幾個本市戶口的同學留在了聊城,可是葉心怡向來獨身自好,很少跟同學們來往。
沒有,就我們兩個!田小寶毫不遮掩地說。
如果只是一般的同學,吃吃飯見見面也未嘗不可。可是,田小寶,她曾經的戀人,應該說是被自己拋棄的人,再見面能說什么?再說只有他們兩個人,搞得像約會似的,如果讓朱大明知道她還在和初戀的情人見面,朱大明會怎么想?一時間很多的念頭蜜蜂似的在她腦子中轉著,電話那頭的人也明顯地感覺出她的猶疑來。
怎么啊,這么多年了,還是見也不想見我啊?
不不不——葉心怡急忙說。畢竟這田小寶是她的初戀情人,她人生的許多第一次都和這人相關相連,再說,她也不是那種能下得起面皮的人。
對不起呀,我差點兒忘記了,今天晚上我還有事,不能來。
是要到江心花園,看你們正在裝修的新房吧?
你怎么知道?!葉心怡一愣。
電話那頭大度地笑了起來,說,也好,你先忙吧,等你有空兒再說,我也要在這里呆一段時間的。
那好,有時間我請你。葉心怡突然溜出一句,說過后又覺得很后悔,仿佛一下背上了什么責任似的。
算了,還是我請你吧,只要你肯賞光!
回到家里,一進門,葉心怡的老媽就心痛地說:
你看你!快三十歲了,還像個小孩兒,說你兩句就使氣!快,這碗銀耳湯,快喝了——餓了吧,還有一個菜炒了就吃飯。
老媽總是像個醫生似的,說要給她補這補那的,不是這種菜好就是那種湯好,總之都很有道理。對于母親這無微不至的關懷,葉心怡曾經也很幸福,很自豪,總是跟伙伴兒同學們說,我媽怎么怎么的,惹得人家一臉的羨慕,可時間一長,特別是她已年近三十,對母親的這種關懷越來越不適應起來。她沒有任何主權,不能在家發表任何言論,她話一出口,母親總是說,你這個兒,怎么這樣說——意思是說她很幼稚也很無知,特別是在婚姻的問題上,母親基本上是大包大攬,她的那場自由戀愛,和田小寶在學校的戀情被母親無情地掐斷之后,她對戀愛對婚姻沒有了任何興趣,如果不是考慮到這世上人人在成個家,母親天天在家的嘮叨,她也不會去跟現在的男朋友朱大明去相見相識,而且這個朱大明,還是母親先替她選中的。嫁任何人都是一嫁,母親說了,這朱大明是本地城市戶口,是公務員,單位好,家里也沒有負擔。總之,母親說好就好吧。葉心怡端著早喝膩了的銀耳湯,就坐在客廳里,湯匙碰得碗沿砰砰響,那是告訴母親她在認真地喝,然后好抽個機會倒進廁所——這是她唯一反抗母親的方式。正當她要站起身,裝做倒殘渣進衛生間的時候,電話響了,是男朋友朱大明打來的,他中彩了似的告訴她,他借到錢了。
你知道,我找誰借的嗎?朱大明十分興奮。
不知道。葉心怡毫無興趣。心想,你找誰借與我什么相干?
你的同學!
我的同學?葉心怡好奇了。
哇塞,你那同學真有錢!手提包里一沓沓的。你們在學校關系不錯吧,一聽說你是我女朋友,人家就眼也不乏地掏出了三萬塊錢,問我還要不要——
竟有這事兒?!葉心怡忙問:
我那同學是誰?
叫什么——很土氣的名字,哦,記起來了,叫田小寶!
葉心怡差點兒倒噎一口氣,是他!接著非常惱火地說,找我同學借錢,你怎么不先問問我?
對不起對不起,是該請教老婆大人的!朱大明在電話里油腔滑調起來。
誰是你老婆!葉心怡火了。
原來,為裝潢材料款的事,朱大明跟人家老板吵了起來,田小寶剛好有事到了那個建材店,便上去勸說,沒想到朱大明就找到了一個借錢的。葉心怡知道朱大明有那個本事,他是一個見面熟,就是一個樹樁也可以說上半天的話。沒想到,他竟然找田小寶借到了錢,不知道他是怎么在田小寶面前說的自己!
聽見女兒在客廳里打電話打得很氣憤,圍著圍裙炒菜的母親拿著一把鍋鏟出了廚房,站在客廳那頭,警覺地問:
是不是朱大明打來的,還在說錢的事?
他說找到錢了。
這還差不多!母親警覺的臉放松了,笑著說,房子本就該他搞嘛。
他是找我大學同學借的!打完了電話的葉心怡還氣憤憤的。
管他找誰借!他借就該他還。
他是找田小寶借的!
田小寶?哪個田小寶?這名字怎么聽起來這么熟?
你當然熟悉,當初是你把人家趕出去的!葉心怡突然有了一種埋怨。是因為田小寶事業有成,竟然象個大款了嗎?她不愿意去想。
是他,那個要跟你談朋友,一年四季穿著雙破球鞋的?
葉心怡今天象是氣沒有地方撒,有意要氣氣自己的老媽,便說:人家現在發財了,是大老板了——哦,他?母親那蒼老的目光一時變得十分深遠。
這個田小寶的突然出現,一下打亂了的葉心怡的生活,也擾亂了她寧靜的心。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她克制著不去接田小寶的電話,可是接下來的幾天里,一連好幾個未接來電之后,就想,就算是出于禮節,也該主動打一個問候電話。
男朋友朱大明找他借錢的事情,葉心怡第二天就打電話道謝了,可是田小寶卻顯得很不屑一提,如果再說道謝借錢,就顯得自己俗氣了。總之,那錢自己會找機會還他的。還是說點兒別的吧。
電話一撥就通,電話那頭也顯得十分熱情。
——不是說在培訓嗎,怎么不好好地聽課,又跑出教室了?簡單的問候之后,葉心怡說。
聽不進去!
不是都請的名教授嗎,人家講得不好?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不是人家講得不好,是我坐在那里心不在“馬”。
他說了一句玩笑話。這曾經熟悉的玩笑象針一樣刺了一下葉心怡的心。這是他們戀愛時經常用的口頭禪,也是性情刻板的葉心怡唯一接受和偶爾也用一下的開心笑語。
為什么?她幽幽地問。
想你啊!
哈哈哈,不會吧。話雖這樣說,葉心怡心里還是像吃了顆糖一樣,甜得渾身舒泰,交流的興趣也高漲了。
說真的。我現在坐在這賓館花園里的一條長凳上,就跟我們原來的學校里的那條長木凳一模一樣,也是綠色的——
葉心怡的某根神經突然被扯了一下。她仿佛看見一對學生,一對情侶,兩人都拿著書本,在含情相視,兩只手沿著那綠色的木凳,寒顫似地爬到了一起——陷入了某中往事里的女教師突然醒來似地,忙對電話中說,對不起,我要上課去了。
接下來的幾天,一天要打好幾個電話的田小寶,突然像消失了,一個短信也沒了。到了上課的時候,葉心怡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拉開抽屜,拿出電話,看有沒有什么漏掉的末接電話和短信,下課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打開電話來看。可除了男朋友朱大明匯報裝房的電話外,再也沒了那個人的任何消息。
自己畢竟是當地人,要盡地主之誼不是?何況人家還主動借給了自己的錢,不能感謝的意思也不表示一下吧。葉心怡與其說是安慰著自己,不如說是在為躁動的心找一個借口。于是在放學后,辦公室里一片空蕩寂靜的時候,落寞的女教師拿起了電話。
過了半個小時,江邊小學的葉老師走出了校門,她沒像往常一樣,到停車棚去騎她的那輛粉紅色的女式自行車,而是朝校門走去。剛才,她在辦公室里看看窗外沒人,還悄悄掏出化妝盒來,對著那面小鏡補了個淡妝。她一出校門就朝馬路上張望,習慣性地望那些紅色的出租車。正在她遼望的時候,一輛銀白色的小轎車,從她背后滑到了她的面前。她嚇得一讓,正惱火地想,誰開車不長眼,要壓到了自己的腳呢,車窗門卻緩緩搖了下來,露出一張多年不見的嘻笑著的臉:
葉教授——哦,葉老師好!
雖然她事前已經知道,他現在已一個大企業的部門經理了,但仍然一時不能把眼前這個看上去事業有成,一身的名牌,開著自己的轎車來接她的人和原來的那個寒酸的形象結合起來。啊,眼前的變化太大了,變戲法似的。學生時代的那個田小寶,一件衣服可以穿幾年,一雙球鞋可以從春天穿到冬天,接她吃個冷飲,多數是一毛錢一根的冰棒,還說那是純天然的,不含色素什么的,很少買貴一點兒的雪糕;頭發也是胡亂的搭在頭上,為了圖便宜,總是讓學校門前的那個老頭兒給他剪,剪得長一根短一根,難看死了,可現在一根根的整整齊齊地豎列在頭上,有條不紊,不僅是精心修理過,還保持得很好,讓人一看,就是個成功人士,是個有錢有勢的,對生活絲毫不馬虎的。變了,完全變了。
看什么,不認識了?請上車啊。
田小寶見這個昔日的戀人盯著自己,便也把自已從前胸望到了后腳,見沒有什么不妥當的,便微笑著拉開了車門,一手很自然地輕搭在葉心怡的肩頭,推她上車。
車里正放著鋼琴曲,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那首《秋日的思念》。葉心怡一坐進車去,熟悉的旋律一下漫上身來,她像潛進了溫曖的浴水一樣,全身沉浸到往日的歲月里。
你怎么還喜歡這首曲子?幾年后出現在眼前的昔日戀人的形象,遠出于葉心怡所料,雖然之前朱大明說過他怎么有錢,怎么氣派,見了面,她仍然感到很意外,很驚奇,心中涌起種種不能言狀的感覺,為了怕田小寶識破自己的內心,總要無話找話說。
田小寶一面盯著倒車鏡,熟練地倒著車,一面有意無意地說,我和別人不一樣,喜歡上的就永遠丟不了。
這話說的葉心怡臉上像被什么鉗了一下,感覺臉是紅了。她像個傻子似的又說,你什么時候還學會了開車?這真的是你自己的車嗎?
田小寶打著方向盤說,難道我不配有車嗎?
不不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真見鬼了,自己怎么老說錯話?葉心怡見了這份兒高貴和華麗,感覺自己一下矮了許多,說話也像不靈便了。真象夢一樣,這世界完全倒了個個兒,昔日那個寒酸的男生哪兒去了?想到這個家伙昔日的那個窮酸樣,葉心怡仿佛找到了一份自信,說,想吃什么,我帶你去?
算了吧,田小寶說,還是我請吧——我不習慣女人請男人的。
這家伙還是這個脾氣。就是在他最貧寒的時候,遇到付錢的事情也總是搶在前面。這一點兒和她現在的男朋友朱大明不同,就是倆人出去吃一頓飯,朱大明吃完了也是坐在那里,悠閑地拿著牙簽剔牙,好象不記得還要埋單的,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兒。結果都是她坐得實在不好意思了,起身噔噔噔地去付悵,朱大明回家的路上就會顯得十分高興,酒足飯飽,像撿了什么便宜似的,話也會比平時多多了。嘿,怎么了,怎么老是把朱大明和他比?葉心怡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不應該,便立刻打消了心底的那些讓人遺憾的想法,裝做輕松的樣子說:
行啊,你發達了,就該吃你的!
葉心怡現在也記不起了,多年前,準確地說是六年前,倆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可能和倆人都當學校廣播室的播音員有關吧。每次播音完,田小寶就要按上那個《秋日的私語》的磁帶,校園里就到處蕩漾著那鋼琴曲的柔波。那是在大學畢業的前一年,播完了音,葉心怡一如既往地收拾桌上的那些播完的稿子,準備回家去吃飯了,那廣播結束的鋼琴曲剛響起來,說著話的田小寶突然按住了她那收拾著稿紙的手。
我們——談朋友吧。
那個時候,同學中談朋友的已不是一對兩對了,兩個人在廣播室里,還常常談論這個同學和那個同學的事情,可葉心怡從沒想到自己也會走到這一步。就在田小寶拉著她的手的時候,門外有個叫張小玲的女同學喊著她的名字,約她一起回家。感覺到來人的腳步聲了,葉心怡便在慌亂中急得點了一下頭,扯出了自己的手,然后紅著臉跑出了廣播室。
葉心怡你怎么了,臉這么紅?哇,你們一定是在談朋友!那個叫張小玲的女同學無不羨慕地說,還踮起腳望了廣播室一眼,是跟田小寶吧——你真幸福!
不久他們便像很多到了大三的同學們一樣,并不遮人耳目的談起了朋友。學校公園,樹蔭下的那條綠色長凳上,成了他們相約相會的主要場所,有時是倆人坐在那里看書,一頭坐著一個,互不相擾,突然有一個聲也不作地離開了,過了一會兒,手里拿著兩棍冰棍或者一根雪糕,笑瞇瞇地來了;有時談論修改著要播出的播音稿,倆人你一言我一語預播得繪聲繪色,有一個突然意識到對方的脈脈含情,便害羞地低下頭去。在一個月色如水,柔風輕拂的晚上,坐在那條樹影長凳上,規劃著未來,傾心長談的兩個年輕人,緊緊地擁抱到了一起。
可是甜蜜的愛情并沒有維持多久。獨生子女寶貝女兒談朋友的事兒,很快母親知道了。從她那放學回來過晚,情緒亢奮中,都是從這條道上走過來的母親首先嗅到了蛛絲馬跡,經過跟蹤和觀察,再一審問,毫無經驗的女兒什么都招了。
不行!母親武斷地說。
為什么?!女兒眼中含滿淚水。
他是委培生,從山區來的,畢業后要回到鄉下下,你愿意跟他到鄉下去過一輩子?原來老媽像個克格勃一樣,什么都調查清楚了。
不是你教育我說,談朋友是會選的選人才,不會選的選家財嗎?
我看那個田小寶也并不是個什么會成器的才!會寫個廣播稿,能播個音,就算是人才?!母親教訓起女兒的目光短淺,孤陋寡聞。
你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兒女反駁道。
看著這小妮子真是鬼迷心竅了,當媽的怕鬧出什么事來,就答應抽個時間叫那個姓田的小伙子來家一趟,認真調查調查。
沒有想到,母親的所謂調查是在徹底打消對方的希望,不,根本是在做賤人家。葉心怡注意到,幾天以后,當衣著寒酸,舉止局促,沒了在學校時的自信和瀟灑的田小寶一跨進自己的家門,向來喜歡以貌取人和挑剔的母親就皺起了眉頭,嘴角掛起了鄙夷的不屑。
你爸媽在哪兒上班?
我爹媽是農民。
你覺得自己有可能留在我們聊城嗎?
不可能,我們委陪生,合同上說,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你就安心,我們心怡跟你到山區受苦?
我——田小寶額上流出汗來。
考察變成了審察,詢問變成了審問。在尚末確定的未來的岳母嚴厲的追問和犀利的目光下,算得上是能言善辯的田小寶變得張口結舌,面紅耳赤。
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希望你們就此而止——你們不會有什么結果的;不是我們嫌你家貧,是我們心怡不可能跟你回到你那個山區,只有山里嫁到城里,哪有城里人睜著眼睛嫁到山區去的。心怡是我的獨生女兒,我老了還要指望她;如果她不聽,我們就斷絕母女關系!
聽完這最后的通牒,田小寶像望著救命稻草似的望葉心怡,可是坐在她母親身邊的葉心怡始終低著頭,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并不敢抬頭來望他一眼。年輕小伙兒眼中燃著的急切希求的目光漸漸暗淡了。他站了起來,朝葉心怡的母親鞠了一個躬:
伯母,打擾了!
這個時候,電光一閃,接著窗外下起了小雨。
田小寶告辭出門,一直低著頭的葉心怡,聽見了窗外的雨點兒聲,本能地抓起雨傘要去送他,可是被母親一把扯住了,只聽她厲聲喝道:
送什么送?你給我站住!你不要再和他有什么瓜葛!
已走出門外的田小寶,聽見門內的聲音,只是站了一瞬,然后一低頭,走進了冰冷的雨水中。
怎么樣,伯母身體還好吧。葉心怡見了田小寶,與他學生時代的形象判若兩人,正在感慨萬端,回憶往事,駕車的田小寶突然問道。
嗯,早退休了——葉心怡一面應答著他的話,一面想,如果現在西裝革履寶馬香車的田小寶出現在自己的母親面前,她又會怎么想呢,會后悔嗎。她葉心怡就感到后悔,感到一種從心底泛出來的淡淡的酸味兒,一屢屢與這鋼琴曲一樣泛動著的怨愁。怎么就那么聽媽的話呢,叫不跟他談朋友了,就不談朋友了,叫不跟田小寶來往了,就不跟他來往了,為了避免與他的單獨相處,學校廣播室的播音也推辭不干了,跟輔導員說自己患了咽炎;一天要去坐好幾回的那個公園的長條凳,從此也讓它空寂在樹影下,有時見田小寶一個苦苦等候的影子在那里呆坐著,不久,那里便成了另一對戀人聚會的天下;在校園里走著走著,突然遠遠地望見田小寶站在過道上,明顯地是在等待著,期待著,她便繞一個道,繞一個大大的彎也不去見他,或者夾在一幫同學中,說說笑笑地一路走過,裝做沒有看見他那一臉的失望。田小寶給她寫的條子,寫的信,有時是看一眼就丟到一邊,有時是連看也不看就原樣退了回去。望著田小寶那段日子的失魂落魄和一臉憔悴,有時也很難過,可又一想,怎不能丟下媽去跟他處朋友啊,父親去世得早,媽也沒再嫁人,就是為了怕她受什么委屈,總不能為了自己的幸福,丟下母親吧。再說,也不能真的就跟他到山區生活不是,自己這樣好象很無情,其實也是在為他好,好讓他早死了這份心。
可沒有想到的是,事過多年,他那一份執戀自己的心仍在燃燒,在田小寶那時而喃喃和時而自我調侃的敘述中,葉心怡知道昔日的戀人一顆灼熱的愛她的心并沒有變,也知道了自己當年對他造成了如何難于彌補的傷害。這既讓葉心怡害怕,更讓她感動,讓她一份虛榮的心也感到了滿足,這個被朱大明奉若神明,大家都看上去是如此成功的男人,仍然是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依然是自己至死不渝的追隨者;她覺得,自己日后在朱大明的面前會更高大。或者那西餐廳搖曳的燭光,讓人心醉的音樂,適合追憶往事,談情說愛,或者自己當年那近乎殘忍的絕決,對人傷害后的覺醒和對眼前這個癡情人的憐憫,或者本身就是喜歡這個男人,只是由于母親的強擾才禁錮著自己的熱情,當幾杯紅酒下肚,臉上泛起了紅光,在一種追憶式的語調停下來的間歇,兩目相對,女主人公害羞地低下頭去的時候,男主人公適時地伸出了手,握住了女主公的纖纖玉腕。一種幸福的電流貫穿葉心怡的全身,她感到自己的心也在幸福又充滿期待地顫抖著,她仿佛回到多年前,那個月華如水的初戀夜晚。
好夢——男人捏著她依舊白嫩的手,深情呼喚著,喘息聲變得急促,他欲站起身來,將有所作為。
不!
葉心怡幾乎是驚叫了一聲,聲音大的附近的客人都回過頭來。這一聲驚叫也阻止了田小寶的動作,他頹然回到坐位,不安地地問:
怎么了?
葉心怡意識到自己反映的過分和唐突,甚至缺乏修養。可是,自己是有男朋友的啊。她幾乎是痛苦地搖了搖頭,然后下了決心似地說:
對不起——不早了,你送我回家吧。
當田小寶開車送她到家的時候,葉心怡象是要急于擺脫他似的,推開車門就跳了下去,說了一聲再見,就穿著高跟鞋噔噔噔地跑向自己的家門,也沒有起碼的禮節似的揮揮手,站在那里目送人家的遠去,或者禮節性地詢問要不要進屋去坐坐,她只顧逃離這輛車,逃離這個男人。在車窗里的田小寶不解的目光中,“啪”的一聲,進屋去的葉心怡關上了鐵門。
不是說晚點兒回來的嗎,怎么這么早?坐在沙發上戴著老花眼鏡,看著電視打著毛衣的母親,見了問。
葉心怡不理母親的,徑直進了自己的房,呯的關上了房門,給老太婆的感覺是不要來打擾,她是要備課,要工作了。她坐到了電腦前,有些慌亂地掏出了電話。她要打給男友朱大明,要朱大明來陪陪她,陪她說說話,或者陪她到江邊去走走,總之今天晚上必須要和朱大明在一起;她仿佛已感到了什么危險,朱大明就是她安全的屏障。
可是,連打了幾個電話,都沒有接,過了好一會兒,電話打回來了。
老婆,我在打牌,有什么指示?油腔滑調的朱大明,雖然倆人還沒結婚,但他已經覺得是板上釘釘,十拿九穩了。
聽了葉心怡的話,朱大明不解地說,這都什么時候了,還要到江邊去散步?!我說老婆,你今天就不去了吧,過一天我陪你行不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今天手氣特好,已經贏了一臺電瓷爐了。
“啪”的一聲,那頭還在說,葉心怡已經關上了電話。庸俗,真庸俗!怎么攤上了這么一個庸俗的男人!葉心怡憤憤地想。接著她又想,自己難道不庸俗嗎?不庸俗,會有今天的后悔?
她突然感到一種難受。她的臉仍在發燙,她的心仍在亂跳。她雙肘搭在電腦前的那一片桌上,撐著自己發燒的臉,望著臺燈燈光外,那一片讓人舒適又暗淡的空間,心想自己該怎么辦?
接下來的幾天里,男友朱大明單位組織出去旅游去了,臨走,打電話問葉心怡要不要帶什么紀念品,平時熱情萬丈的葉心怡,這次卻冷冷地說,隨便!前戀人田小寶也打來電話,說留在本市的幾個老同學相聚,請她也參加。葉心怡接到田小寶的電話,竟然沒做任何推辭,就爽快地答應了,原來自己是在那么期待這個人的電話。那一次的聚會,男男女女喝得天翻地覆,熟悉他倆談過戀愛的人更是拿他們開玩笑,每一句玩笑葉心怡既覺得甜蜜,又覺得像針在刺著她;當田小寶送她回家上車的時候,她竟軟軟地靠在了他的身上。
以后便是經常的約請。
有一天跟在外吃完飯回家,她母親見了問:
又跟田小寶出去的吧?
葉心怡懶怠回答。喝了點兒酒,身子很泛,便軟軟攤坐在沙發上;母親見狀,便馬上去給她沖了一杯糖醋水,說是解酒。
人啊人,只怪當初我沒長后眼——真比一百個朱大明強!
母親顯得無比后悔。見女兒沒做聲,母親又問:
田小寶結婚了嗎?
她早問過他了,他說談了朋友,還不知道什么時候結。
她媽聽了,神秘地說,我看田小寶還在像以前樣喜歡你。
媽!你說什么?!我們只是同學!葉心怡沒好氣地說,不要想多了!
可是,葉心怡叫母親不要想多了,可她自己呢,一回家,嘴里念道的卻都是田小寶這,田小寶那的;一提起田小寶,母女倆兒就有說不完的話題,一說起他,葉心怡的心就在笑,一直笑到了臉上。那個朱大明呢,仿佛在這個家庭里消失了,母親天天追問的裝修房子的事情,仿佛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很少提及了。
在葉心怡過生日的時候,記性真好的田小寶請花店的給她送去一束鮮花,送到了學校。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她男友朱大明送的——他,那個小氣鬼?嗤——手捧鮮花的葉老師毫不掩飾一臉的蔑視;那一天,田小寶還拖她到名牌店買了一套昂貴的衣服,葉心怡推辭不要,田小寶說,他們戀愛時,他一直想送她一個什么紀念品,可是窮啊,除了送送冰棍,什么也送不起,現在是將功補過;田小寶又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又說,你也穿得太——節約了。她知道,斟詞酌句的田小寶是在照顧她的自尊。的確,在同學們的聚合中,她穿的雖然說不上最低檔,但也絕對不是上檔次的,很多以前并不起眼的女同學,也跟田小寶一樣,一出場就明星樣的惹人注目。如果她是田小寶的妻子或者女女朋友呢,她還會是那樣讓人可以忽視嗎?她不敢想。
在一個周六的晚上,倆人吃了晚餐之后,突發奇想,竟然開車穿了幾條街道,找到了昔日的師院,悄悄溜進了母校的操場。在操場的那一片樹林,那個公園,那昔日放置長條凳的地方,他們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時光。他們又像昔日那樣,說說笑笑,回憶著往事,每一件現在都覺得幼稚可笑的細微的事情;不過不同的是,昔日人約黃昏,月上柳梢的那輪明月,是月華如水,了無輕塵,可現今,那柳梢上的明月已是殘缺,也沒有了昔日的冰清玉澈。
在當晚回家的路上,倆人都像余興未盡,興致勃然,都沉溺在往事的興奮中。葉心怡已是身心如水,她那一顆冷凍了多年的心,如今又被田小寶融化了。她已然悄悄決定,既然田小寶還如此愛她,她就要嫁給他,后悔還來得及。
葉心怡把手搭在開車的田小寶的腿上,仿佛是要做什么強調:
小寶。
什么?
有一句話,我一直想對你說——好幾年了。
什么話呀,說你愛我?開著車的田小寶偏過頭來,仍是一臉的戲謔。
不是。我想對我的母親,對幾年前對你的不公平,表示道歉。
田小寶聽了,漸漸收起了嘻笑的神情,什么也沒說,仿佛在專注地開著他的車。
我媽叫我跟你說,想接你到家去玩。
有了時間,我會去看伯母的。
田小寶說。夜色中,這輛銀色的轎車穿過一團團迷離的霓虹燈光,穿行在城市這夜的長街。
田小寶的培訓學習結束了,一下又忙了起來,今天打電話,說是在廣州,明天打電話,又到了北京,說是請他到家吃頓飯的,母親像一件什么大事似的,在家準備了很久,可臨時他又說來不成了;葉心怡知道,他在聊城,在江心花園的銀坐,買了一套豪華的住房,說是要帶她去參觀的,也因為他的忙,沒能成行。時間真快,一晃半年過去了;朱大明的房子已經裝修完了,說是裝好了房就結婚的,可一說到結婚的事,葉心怡和她的母親就吱吱唔唔的。媽的,現在是四條腿的螞蚱不好找,兩條腿兒的女人哪里沒有?并不笨的朱大明看出什么端倪,一發恨,轉眼就找了一個醫院的護士,閃電般地結婚了。
聽到朱大明結婚的消息,葉心怡沒有任何表情,她的媽卻像放下了心:聽我的話沒錯吧,萬幸那時你沒借給他錢——哎,他借的田小寶的錢怎么辦?
說起田小寶,自從朱大明結婚以后,葉心怡基本是一天要給他打一個電話,倆人的關系像是倒了一個個兒。遠在千里之外的田小寶,電話里雖是那么熱情,卻顯得極其繁忙:實在對不起啊,我現在的確是有事,等我回來了我們再聚!
媽問了好幾回了,問她倆人的關系確定了沒有,可她,做為女方怎么好老下臉皮說呢,求婚,歷來都應該是男人的事兒。不過葉心怡確信,以她在田小寶心目中的份量,還有她的多次暗示,田小寶應該明白她的心。但是,這事兒不挑穿,也會讓人心頭發慌是不是,葉心怡就決定,等下次田小寶出差回到聊城,她就主動把這事兒提出來,也還管什么女方不女方,自尊不自尊了。也許,是那第一次戀愛,自己和母親傷害了人家,讓他不敢再提了。
他不提我來提!
女老師像終于做出了什么重大的決定,頭一回要對自己的生活做主似的,抱著課本的臉上喜滋滋的一臉燦然,惹得學生們私下猜測不已。
到了秋天,街頭的樹葉兒變成一樹金黃色的時候,田小寶終于回來了。
今天晚上有空嗎,請了一些老同學,到某某賓館聚聚,六點——
有有有——,葉心怡顯得迫不及待,也激動得語無倫次,她已經想好了詞兒,問這個家伙打算要拖到什么時候,才肯說出那些讓人高傲又欣然的求婚的詞。
在一間豪華的賓館餐廳,葉心怡很奇怪見到了那么多老同學,有的是市內的,有的是市外的,更讓她奇怪的,是打著領帶,西裝革履的田小寶面前,站著一個同樣打扮高貴的好象見過的女人,而田小寶介紹的話更讓葉心怡驚呆了:
這是我們的老同學葉心怡;這是我未來的夫人張小玲。
原來,田小寶是在舉行定婚宴;那個本應是由葉心怡站的位置,卻站著葉心怡從來沒有正眼瞧過的過去的同學,張小玲。
在以后的很長時間,葉心怡一直跟她的母親生活在一起,她成了這座城市里乘女隊伍中的一員;這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母女倆,坐在電視機前,常常半天不說一句話,結婚論嫁更像成了回避的話題;在花開花落的日子里,人們透過窗口望見的,也是一對沉默的身影。
譚巖,湖北省作協簽約作家。發表作品多篇。小說入選《小說選刊》、獲新世紀第三屆北京文學獎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