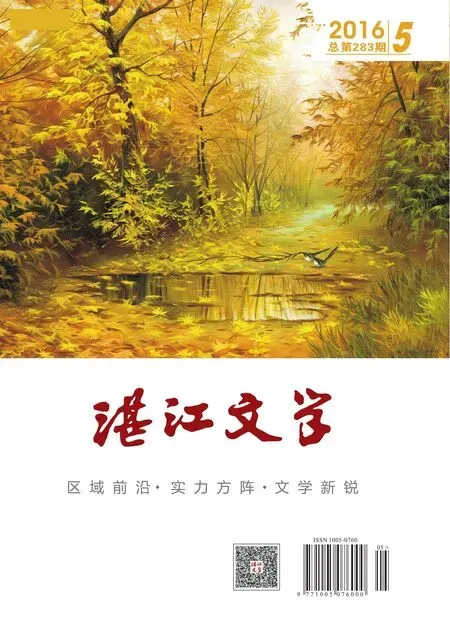老屋瑣憶
※ 采 薇
老屋瑣憶
※ 采 薇
老屋,五十余年前爺爺奶奶建造的泥草房。三間主屋,左右兩邊是臥室,中間的謂之“堂屋”,相當于今天的客廳和餐廳,多待客和用餐用。主屋兩邊有廂房,共四間。一邊的兩間是廚房和雜物儲存處,一邊的廂房是客間和儲糧室。老屋以麥秸為頂,一層層繕上去,雨天水順著麥秸稈兒不停流下,少有滲漏;屋頂大概每年都要修繕,畢竟經不得過多的風吹雨打。老屋的墻體是泥土摻和零星細碎麥秸而成,天長日久,墻的外層歷經雨點和狂風的打磨,有無數的坑坑點點,偶遇蛇洞穿墻而過,洞口若雞蛋大小。夏天一人在家,抬眼望去,一根粗布花腰帶似的蛇不住的“簌簌”往墻里鉆,還以為是自己花了眼睛看錯了那廝。
老屋周庭有墻垣,大半人高,墻內有棗樹一棵,榆樹兩棵,一棵槐樹和一棵杏樹。庭院東緊鄰我家,我父母結婚時從老屋分家出來成了老屋的鄰居。我和弟弟妹妹時常從矮矮的墻頭爬上去騎在墻頭上跟奶奶嘮嗑,或者奶奶家來了貴客,主人傾囊,炸些美味,殺只小雞,香味從矮墻飄到我家,閨女小子聞著香味翻墻而過,魚貫而入,自然做了陪客,自然口腹皆飽……那時叔叔還年輕,惡我們貪食,常持雙筷子敲我們這些小孩子腦殼,敲到哭了,遭到奶奶呵斥:人家都是逗孩子笑,就你逗孩子哭!叔叔訕訕地自然無趣,我們則心滿意足,饕餮而回。
到了春天,二月始,榆錢槐樹開始競相綻放。綠色的榆錢,白色的槐花,在老屋前面妖嬈起來。各有各的狐媚法子,槐花拼了命的開放,香氣溢滿庭院;榆錢則拼了命的長個兒,長成大大圓圓的榆錢,卻也嫩到絲絲的香甜沁人心脾。奶奶往往長竹竿頭綁了鐮刀,揚著頭,瞇細著老花眼,照準花兒多的枝條勾上一鐮刀,使勁往下一拽,榆錢和槐花頓時亂顫到一地……孩子們猴子似的早爬上樹梢,擼了榆錢,摘了槐花,一串串扔下來,直到奶奶恐懼的望著我們大呼小叫著要我們下來,才嬉鬧著滑下樹來。槐花榆錢蒸了菜,或把槐花焯了水,涼拌,那香味近乎美到我的不惑之年。如今只聞花香,不見奶奶。每念及此,心中凄然。
農歷三四月份,杏花華麗麗的來到人間。我總是覺得杏花的魅力無可比擬。盛開時的杏花,胭脂萬點,占盡春風。我癡纏于它的艷態嬌姿、繁花錦簇,大概也是加入了對杏子的萬分熱愛的印象。那杏子剛離了花托,毛汪汪的滴著嫩氣,小孩子就開始了貪吃之旅。伸手能夠到的,就摘了來,放在嘴里,澀澀的,酸酸的,即使酸倒了牙也在所不惜;伸手夠不到的,就拿了竹竿細細的連葉一起敲下來。等到偷偷吃完可以吃到的,還剩在高處不勝寒的那些,慢慢的黃了皮,慢慢透出來原本屬于杏子的清香,再也忍不住,等到爺爺奶奶不在家時,拿小磚頭碴子一個一個投下來,來不及洗就吞下去了……等到麥焦杏黃時候,爺爺奶奶突然想起來院子里還有棵叫杏子的樹,左瞅右瞅,只見杏葉不見杏果……
農歷五六月,庭院里棗花開放,不幾天,落蕊伴著花香覆蓋了院落。那棵棗樹很大,樹身很粗,樹冠遮住了小半個院子,亂虬斜刺,藝術氣息濃厚。花蕊細碎,黃色,風一吹,院落里撒得到處都是。若是有月亮的晚上,月光透過枝枝葉葉投射到院子里,頓時滿院藝術的剪影。棗樹下有一個壓水井,棗子快熟的時候,站在壓水井的高臺上可以輕而易舉的摘到棗子。棗子不熟不能吃,吃了會上火。有孩子不聽話,偷吃了沒有成熟的棗子,很快就會在他身上顯示出威力來——長出滿腦袋的黏糊子瘡。據說不成熟的棗子火氣很大,即使是活潑異常的孩子也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火氣攻擊,于是化作“賴瘡”長在頭上,為治那瘡,需把頭發剃掉,剃成狗啃似的一塊青一塊白。成熟的棗子火氣也很大,吃多了會流鼻血,小孩子一般對棗子興趣不大,因此棗子能夠得善終。印象中每年奶奶都要收上一大簸籮,曬呀曬的好多天,過年蒸大饃和饃花,里面用的棗子還是自家的收成。
那棵棗樹雖然比老屋的存在還要早,卻沒有老屋壽終正寢的福氣。我大概十歲左右的模樣,那些年的計生工作做得如火如荼。我嬸嬸懷上第二個孩子,快要生產了卻被引產;棗樹被貼著地皮鋸掉;東廂房被扒掉;糧囤的口糧被拉走,顆粒不剩……那幾年,村里像遭了土匪,老屋也雞飛狗跳了很長時間。三年后嬸嬸去世,那時她又孕而生的二兒子大概一歲左右,正牙牙學語,指頭放在嘴里吮吸著,流著口水站在嬸嬸靈床前,喊著:媽,媽,媽……棗花飄香的季節,我偶爾會想起那個25歲上生命戛然而止的嬸嬸——生命如夏花,美麗卻短暫。
……
老屋泥土坯壘砌而成,墻厚實異常,雖歷經半個多世紀而巋然屹立。墻面有雨水淋漓而成的雨道兒,蜿蜒如蚯蚓。小時候手上不小心劃了個小傷口,刮下來雨道土摁在傷口處,可以很快的愈合,而且減少發炎的可能性。大自然就是這樣神奇,無償提供所需,而人類又自然而然用其可用。
堂屋的地面凹凸不平,但歷久使用,錚光發亮,沒有一粒揚塵。陽光透過門楣映照到堂屋,奶奶倚門而坐縫著永遠也縫不完的孫子的衣服,爺爺則戴上老花鏡看他的各種名著。貪玩的我就著光滑的地面抓一種叫“子”的玩具。這種玩具多泥瓦制成,撿了壞掉的瓦片,砸成五分硬幣大小的圓,磨去四周的粗糲,即成。多女孩子玩,可以自己玩,也可以結伴玩。我安靜的蹲著,安靜的玩著手中的“子”上下翻飛而不落;弟弟妹妹們則在院子里攆狗打雞,追逐玩鬧,奶奶時不時的呵斥上兩句,爺爺則在到書中的人生里安穩如山。那時歲月靜好,生命安然。
堂屋正中供奉著我的祖輩,我常常凝視著他們,牌位上的名與字似乎在給我講述他們的故事。祖輩中有一貢生,輩分久遠了些,爺爺的爺爺是一秀才,墳冢就在我家南地。爺爺讀書時還有一個經常的動作:眼光從眼鏡框上沿投向我,告我一定要好好讀書,爭當秀才貢生……我當時懵懂而應,也不知現在算否實現了爺爺的愿望。爺爺是一個極正直的人,熱情、真誠、公正,讀書人的溫潤雖然少了點,但小農缺點很少有。我父親大概七八歲時,爺爺的親哥告發他口不擇言,爺爺被發配青海十幾年。在那里爺爺大口喝酒大塊吃肉,毫無心機與人交往,享受了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雖然如此,奶奶在家一人拉扯三個孩子,受盡了欺侮和磨難,我唯一的一個姑姑在十二歲上因為高燒不治而亡。
……
零零年我大學畢業,為脫貧嘗試多種營生,后終于不再給社會主義抹黑,安穩了一個可以讓諸弟有事干的生意,并在鄭州安了家。那時奶奶已經隨著叔叔生活在西南一個小城,爺爺一人在家守候著老屋。我請他來鄭居住,死乞白咧,終于成行。但不久就要歸家,他說家里還有幾間老房,住著安穩。
老屋年久失修,庭院中杏樹榆樹槐樹日益老去,失去往日精神,毛杏再也沒有偷嘴的孩子摘取,孩子們都已經長大成人,青杏也不再具有吸引力……爺爺依然坐在堂屋在陽光下讀他永遠讀不完的名著,時不時透過眼鏡下方瞄一下腳邊的“石榴”,“石榴”13歲,在狗的世界里已是老年。
樹非樹,花非花,牛羊無蹤,雞鳴皆無,滿院一片蕭瑟。
2007年爺爺去世,兩年后奶奶去世,老屋有點歪斜的屹立在歲月的風雨中,陪著它的是一樣蒼老的榆槐,還有一個結著毛杏的春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