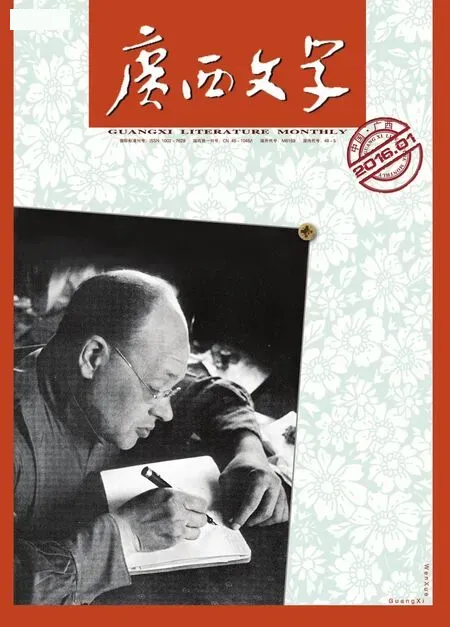羅鳳紈小小說二題
羅鳳紈/著
獻 血
這兩天阿興樂呵呵的。
他的小食雜批發店開張六個月了,他既當老板又當工仔,既是采購員理貨員售貨員又是送貨員,忙得兩腳不著地。貼在店面的“招人”廣告都快褪色了,總算給他招來了一個打工妹小王。小王二十四歲,剛剛新婚兩個月,從鄉下來投奔在南寧做保安的老公。這兩天試工,小王手腳麻利,嘴巴甜蜜,店里的主打商品“達香奇雪米餅”銷量翻了一番。阿興能不樂嗎?
阿興想好了,等小王熟悉業務后就由她打理店面,他專門跑業務,拓展銷路。
阿興只樂了幾天,麻煩來了。小王得了急性胰腺炎,被醫院誤診為急性闌尾炎,做了闌尾炎手術,錯過治療胰腺炎的時機,進了重癥室搶救,天天都在輸血。阿興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兩次為小王獻了血。但是,相對小王的輸血量,他那些血微不足道。醫院提醒他們可以開展互助獻血。
阿興關了店門,四處為小王的互助獻血奔忙。剛開始,老婆擔憂小店關門人家會以為倒閉了,客源流失。阿興虎起臉甕聲甕氣地說如果得病的人是你,我就一走了之看看你怎么辦。老婆不吱聲了,并加入了互助獻血的奔忙中。小兩口發微信發短信打電話傳Q Q群,請求好友們援助。有好友愿意獻血的,阿興就開車送到血站,檢查,采血,一天在血站的路上來來回回奔波,比經營小店還忙。
阿興的兩個姐姐也加入了發動互助獻血的隊伍。
大姐在政府機關工作,信心滿滿的。她有三四個微信群、三四個Q Q群、大學同學的,本科進修班同學的、中青班同學的、政府同事工作群、家長群、作家群、攝影群……一個群少的二三十號人,多的上百號人。群里每天人聲鼎沸,多數時候是曬旅游照片,大談特談美食時裝,相約下一站到哪里旅游、采風,晚上在哪家酒店聚餐云云,表現出生活的富足美滿。
二姐開了家只有一張美容床的小美容店,一人身兼店主和按摩美容師,也有兩三個微信群、Q Q群,美容按摩客戶群,美容學員群、友仔友女群。友仔友女們有的自己開小店,冷飲店、燒鴨店、服裝店、美發店,有的做保安、美容按摩、洗碗工、賣菜賣肉……群友們沒什么時間聊天,群里經常靜悄悄的,工余才互相發一些賣萌賣騷的自拍照片取樂,偶爾轉發一些團購打折的消息。
大姐和二姐都把互助獻血的求援信息發到了自己的群里。二姐問大姐你怎么寫的啊?大姐說寫小王是我干妹妹,讓他們聯系阿興。二姐說好,那小王也是我干妹妹了。
大姐還別出心裁親筆寫了一封求助信連夜拍發到個人微信上。
第二天,大姐問阿興小王的情況怎么樣了。阿興說還是危險狀態,血液問題沒解決,他的朋友來了二十幾個,只有四個符合獻血條件,血脂高的占大多數,近日大量喝酒的也不少。大姐說你自己以后也要注意少喝酒少吃肉了,你的朋友個個都啤酒肚,血脂不高才怪。阿興說我年年獻血幾次,不會有事了。
大姐的那些群尚未有人回復說要去獻血,微信點擊率居然比往時少得多。雖然大姐不停刷新,依然沒有跳出她期待的回復。往時,她隨便發一朵花,哪怕是發幾張自己種的豆芽圖片,都會在幾秒鐘內有好幾個人點贊回應,每個帖子都有幾十個點擊數。所發的獻血求助信竟然靜悄悄的,像一個被遺忘的孤島,發出去很久才有一兩個外地的好友回應送來遙遠的祈禱。
一整天大姐都開著微信開著Q Q,時不時看看,唯恐錯過任何信息。奇怪的是,平日里微信群、Q Q群里的人聲鼎沸這會都銷聲匿跡了,每個群都可怕地沉默著。她又把獻血求助信息重發了一遍,發完她盯著手機屏幕,各個群用更加可怕的沉默回應她。
二姐也打電話問阿興,她的人有去獻血的嗎?阿興說來了好幾撥了,三五成群地來,都不要他接送。血站在遠郊,交通不是那么便利,他們自己打車或者拼車或者坐三輪車來去得小半天。但是符合獻血條件的也是那么幾個,有些是體質問題,太瘦、貧血,有些是長期服藥,高血壓什么的。難怪血站血庫庫存會告急。
第三天,互助獻血量和小王的輸血需求量還是相差甚遠。五月份的南寧市已是熱浪滾滾,滾滾熱浪裹著滾滾車流在城市里橫行,讓人愈加煩躁不安。
阿興舉著手機站在血站側門張望來路,高大壯實的身軀把側門占了將近一半。汗水蒙了眼,擦了又擦,才過了十點,上衣早濕透了。嘭嘭嘭嘭開來一輛五菱車。二姐的閨蜜張姐第一個跳下車,隨后鉆出六七個女人。阿興驚喜地說不是說只你一個人嗎?張姐說她們是我那個菜市的,今早出攤聽說了也都要來,我等她們收好攤,所以來晚了,不礙事吧?阿興說不礙事不礙事,正好正好。七個人,只有一個人符合獻血條件,三個人長期服減肥藥,兩個人高血壓,一個人重感冒。
二姐來電話說不要著急,我這邊還有人來的,我友女小娟說她和她一塊在工地做飯的那些阿姨,還有民工馬上過來,可能有十幾個人,他們長期勞動很壯實會符合要求的。
第四天、第五天,二姐的熟人,阿興的朋友們攜家帶口,呼朋引伴,又來了一百多號人,卻也只有十幾個符合獻血條件。
大姐的朋友依然沒一個前往獻血,她忍不住給一些比較交好的朋友發短信求助。一半沒有回復,回復的那些,有的說正出差外地,有的說在加班,有的說在開會,有的說忙著實在走不開。
第六天,大姐收到阿興發來的信息,說小王妹搶救無效,人沒了,不用找人去獻血了。大姐沒有把這個消息發到群里,微信圖片也不再更新。沒幾天,她的那些群里又開始人聲鼎沸了,話題都和獻血無關。
老舅游公園
大年初二,老媽突然收到老舅來電,說初四到南寧來探她,我的表哥、表妹們攜家帶口一塊來。老媽高興得像個孩子那樣傻笑了半天,有些不知所措。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親戚們便疏于走動了。老媽從老家搬到南寧幾年了,她娘家的親戚還沒來過。
當晚,我們議論怎么招待老舅,議論買什么酒,議論菜譜,議論游玩線路,家里頓時有了在老家過年的熱烈氣氛。
初四上午,老舅一行十幾個人,浩浩蕩蕩從鄉下到了南寧。按照行程安排,午飯后我帶他們去人民公園玩,老爸老媽陪同。
一路上我們說說笑笑,雖然已多年沒見,但是,一點不影響我們親近。說到小時候,說到外婆在世那會,說到舅舅們對我們的寵愛,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老舅這是第一次到大城市游公園,六十多歲了依然充滿新鮮好奇感。看到奇特的建筑物就跑過去要照相,企鵝造型的垃圾桶也是他合影的對象。他拉著老媽的手在垃圾桶旁邊擺出各種拍照姿勢,逗得小輩們哈哈大笑。他孫子說,爺爺,那是垃圾桶耶。老舅說這城市就是好,連垃圾桶都這么好看,遂伸手摸了摸企鵝的頭。我不停按下快門,留下每一個快樂瞬間。
老舅自己也掏出手機拍照,手機是早已被淘汰的款式,屏幕小,像素極低,用他孫子的話說老舊得掉牙的古董,拍回去也看不見。老舅卻非常地認真,往前,退后,左擺右擺,一絲不茍地取景,很有成就感地摁下按鍵,那神態讓人忍俊不禁。
走到半路,我去給孩子們買零食飲料,聽到老舅洪鐘般的聲音:“阿執!阿執!快過來!快過來給我拍這個。”
我一看,不遠處,老舅爬上了公園的一座雕塑“鯉魚跳龍門”的鯉魚頭上。我連奔帶跑過去,叫他,舅舅,你快下來,太危險了!他笑哈哈地抄起手說你先給我拍照。不少游客駐足觀看,我很尷尬,說這個不可以爬的,舅舅。他說你拍了我就下來。我只好給他拍,拍了一張他又轉到鯉魚尾巴那里讓再拍一張,才肯下來。我想上前扶著他,他卻噗一聲跳躍下來了。
我說,舅舅,這公園里的景觀建筑不能攀爬,要罰款的。
他啊了一聲說你不早說,現在要罰款了沒有?
我說,你下來了不用罰款了。他摸摸后腦勺說,我只懂得種地,這種規矩不懂,你多教我一點。兀自呵呵樂了一會,紅褐色的臉膛上深深的皺紋一圈圈蕩漾開去。
走到炮臺景點,我忙著給表哥一家三口拍合影的當兒,又聽見老舅洪鐘般的聲音傳來,“阿執!阿執!快過來給我拍。”我循聲跑過去,左看右看卻不見老舅。
老媽掩嘴笑,用手指指頭頂的樹冠。我的媽呀,老舅正躺在大榕樹十幾米高的樹丫上,得意地蹺著二郎腿。
我急切地說,舅舅這么高,你怎么爬上去的,快點下來。
他說你先拍照。
我知道拗不過他,只好給他拍。他仍不肯下來,從這枝樹丫蕩到另外一枝樹丫去,還沖我做鬼臉。我嚇得直跺腳。
老媽說,你不用跟他急,他就這個德性,在家哪天不爬到門前的大楊梅樹上去涼快的。
老舅說,你媽說對了,爬樹是你老舅的絕活,二十幾米的八角樹我都能爬到頂去摘八角。說著忽地又蕩到了另一枝更小的樹丫,圍觀的游客有人尖叫起來,擔心樹丫折斷人摔下來。
我按了好幾次快門,說舅舅,拍了很多張了,下來吧,這樹也是不能爬的,一會管理員來要罰款了。他說人造的東西不能爬,這樹是天養的就是給人爬的。我說公園有規定,樹也不能爬,也要罰款。老舅聽了,一蕩就滑溜了下來,那敏捷的動作和猴子差不多,看得圍觀的游客目瞪口呆。
老舅嘟噥道,這城里怎么這樣要罰款,那樣也要罰款的。
老媽說,你以為在你那山里頭啊。老舅說,你別說,我在山里住了一輩子,還真沒見過這么大的樹,三棵樹怎么就長成了一棵。我說,從小人工培植的,小樹苗的時候用鐵絲給纏繞在一起,長大就長在一起了。老舅說,城里人這么殘忍!
到了兒童游樂場,孩子們有的要去劃船,有的要去坐過山車、碰碰車,就兵分兩路,老爸帶一路,我繼續帶著老舅、老媽和表嫂們。老舅和老媽走到哪里都手拉著手,看著讓人心里暖暖的。
在湖邊的大花圃,表嫂們爭相拉老媽在花叢中合影,我快樂地咔嚓咔嚓給她們拍。拍完一組花照,大家才發現老舅不見影子了。
湖邊有三條小道,誰也沒注意老舅往哪條道上去了。表嫂給他打電話,電話關機,許是老舅剛才使勁用來拍照把電池拍沒了。
最緊張的是老媽,急得團團轉,一個勁說這可怎么辦,他不認識路回去的。
我說,我們先到大門等,剛才不是說好了一會兒大家在大門集中回去嗎?等下他找不見我們會到大門去的。
在大門等了半個多小時還不見老舅來,我急忙返回湖邊找。
走到后湖涼亭,我聽到老舅洪鐘般的聲音,怒氣沖沖的,我就是鄉巴佬,怎么樣,你是城里人,你金貴,你還到處扔垃圾。
一圈人圍著涼亭指指點點。
老舅見到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拉過我說阿執,你來評評理,她吃葵瓜子,一路吐瓜子殼,我跟在她后面撿了一大把,我讓她丟垃圾桶去,她不聽,還罵我鄉巴佬,你們城里這么干凈不是我們鄉巴佬掃的嗎?你看看人家在那邊掃著,多辛苦。這種人應該罰款,阿執,叫管理員來罰她款。
吃葵瓜子的女人三十多歲的模樣,穿著玫瑰紅的羽絨服,艷麗耀眼,在眾人的指點下低頭鉆出人群。老舅追上去,說你不能走,你把這把瓜子殼丟垃圾桶再走,不然就罰你款。女人扭頭說神經病!
我拉住老舅,說我媽找不見你都急死了,別管了,舅舅,你管不了那么多的,要回去吃晚飯了。
老舅氣哼哼的,說,管得一個算一個。
他一直拿著那把瓜子殼,直到看見垃圾桶丟進去后才松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