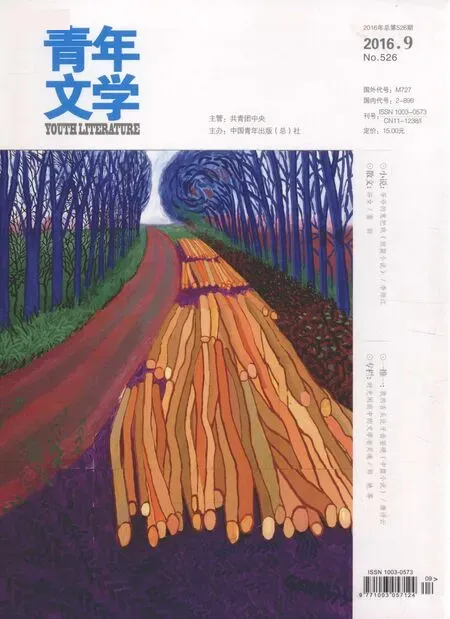借 刀
⊙ 文/陳美者
借 刀
⊙文/陳美者
陳美者:一九八三年出生,福建莆田人。作品散見(jiàn)于《文藝報(bào)》《中國(guó)藝術(shù)報(bào)》《福建文學(xué)》等。著有《中國(guó)西學(xué)第一人——嚴(yán)復(fù)》。現(xiàn)居福州。
晚上十點(diǎn)鐘,兒子睡著了。她在衣柜前整理衣服。
先生走進(jìn)來(lái)的時(shí)候,她心里咯噔了一下,手上繼續(xù)把十條圍巾按照顏色深淺排列掛好。她寧可他不要在這個(gè)時(shí)候走進(jìn)來(lái),整理衣柜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是一種重要儀式,被打擾之余,還有一種擔(dān)心。
現(xiàn)在,他走到她的面前了。她咬著嘴唇,把幾件不穿的高領(lǐng)毛衣放進(jìn)最上面的柜子。她仰著臉,踮著腳尖的時(shí)候,先生伸出手捏了一下她的臉。她不由得回頭看了一下他的臉,已經(jīng)很久沒(méi)有盯著他的臉看,正如他也很久沒(méi)有盯著她的臉看。很久以前,先生經(jīng)常一邊捏她肉嘟嘟的小臉,一邊喊她“茉莉”。現(xiàn)在,她臉上的肉也少了,蘋(píng)果肌下垂,拍照時(shí)很難擠出甜美的笑意,而他也很少碰觸她的臉。但是,此刻,她看見(jiàn)他的臉上居然帶著難得的笑意。她也笑了,不僅是臉,全身的細(xì)胞都松開(kāi)了,看樣子今晚不必再承受那樣的指責(zé)——“你看看你買(mǎi)這么多衣服”!她有個(gè)隱秘的習(xí)慣,只要一買(mǎi)新衣服,就會(huì)有換了一個(gè)身體的感覺(jué),似乎要展開(kāi)新的人生,于是就整理衣柜,把舊衣高高收起,或是干脆扔進(jìn)黑色塑料袋,在某個(gè)上班的早晨,躲閃著拎出門(mén)去,假裝那里面裝的是垃圾。關(guān)上房門(mén)的一剎那,她常常越過(guò)火線(xiàn)一般,穿著高跟鞋健步如飛,生怕先生背后追上來(lái),問(wèn)她手里拎的是什么。好在一次又一次,他都沒(méi)有追上來(lái)。
今晚她的運(yùn)氣似乎更好。先生好像沒(méi)有看見(jiàn)那十條圍巾似的,捏完她的臉,又過(guò)來(lái)握她的手。她的手常年冰冰涼涼的,先生的手很大很暖。這雙大手現(xiàn)在握著她的小小的冰涼的手。她感受著一個(gè)男人的體溫,這是很久沒(méi)有的事了。
“晚上我到這邊來(lái)睡吧!”先生含著笑說(shuō)。她低下了頭,與其說(shuō)感覺(jué)甜蜜,不如說(shuō)是驚訝。
窗玻璃被關(guān)緊了。窗簾被拉上了。她從衣服堆里揪出一件很短的旗袍,換上,只能用這個(gè)湊合。上一次整理衣服的時(shí)候,她看見(jiàn)那些長(zhǎng)長(zhǎng)短短碎片式的情趣內(nèi)衣,不知道為何就生氣,一把卷起來(lái)全塞進(jìn)垃圾袋里扔了。
先生修長(zhǎng)的手指碰到她胸口的時(shí)候,她的心緊了一下。生孩子之前,她愛(ài)穿V領(lǐng)衣服,那時(shí)只知人人都這么穿,不覺(jué)著有什么。可是現(xiàn)在,她再也穿不了V領(lǐng)衣服了。孩子出生后,大家都覺(jué)得一個(gè)床太擠,先生變成了多余的家具,于是,先生就到隔壁房間睡。夜里孩子哭鬧了、生病了、尿布濕了,她只大聲喊著:“孩子爸!孩子爸!”
沒(méi)生孩子前,聽(tīng)人家喊老公叫“孩子他爸”,覺(jué)得不可思議,愛(ài)人之間可以有多少昵稱(chēng)啊,可現(xiàn)在才明白,原來(lái)老公過(guò)著過(guò)著就成了“孩子他爸”了。聽(tīng)到叫喊,孩子爸就過(guò)來(lái)了,帶著睡眠中的迷糊,有時(shí)也帶著怨氣,這股怨氣從他開(kāi)門(mén)的一剎那就像風(fēng)一樣,撲進(jìn)來(lái),彌漫在臥室中。她當(dāng)然什么也不會(huì)說(shuō),一天天更加沉默,但她是那么需要他,有時(shí)先生晚上會(huì)跑出去和朋友喝一杯(她甚至嫉妒他居然在恢復(fù)單身漢的時(shí)光),她感覺(jué)到隔壁房間是空的,心里也會(huì)空出一塊。她一遍遍呼喚他,渴望他的出現(xiàn),心中卻可以不帶任何愛(ài)意。
此刻,兩個(gè)人身體之間的碰觸,讓她覺(jué)得熟悉又陌生。先生習(xí)慣不變,每一個(gè)步驟都井井有條,不需要大腦,她的身體就能準(zhǔn)確地預(yù)測(cè)到他的手。結(jié)婚多年,這種感覺(jué)好像在復(fù)習(xí)功課。但前面沒(méi)有一場(chǎng)考試在等著。反正孩子已經(jīng)有了。前面還有什么呢?她不知道,只覺(jué)得孤單,每一寸肌膚每一截骨頭都在孤單,但每一天都要扮演知性母親之角色,國(guó)內(nèi)外各種繪本講得抑揚(yáng)頓挫,能模仿十二種動(dòng)物的叫聲,簡(jiǎn)筆畫(huà)剪紙黏土樣樣拿得出手。每天累到全身疼,這樣才好,自己是多么重要的被需要的角色,日復(fù)一日地旋轉(zhuǎn),至少讓家看起來(lái)像家。人生是需要表演的。不明真相者,方能久遠(yuǎn)。正如此刻,她閉著眼,一邊偷偷放縱自己走神,一邊盡量不讓先生察覺(jué)到什么。
先生真的沒(méi)有察覺(jué)。他似乎從來(lái)都是個(gè)感覺(jué)不敏銳之人。在無(wú)數(shù)個(gè)節(jié)日里,圣誕節(jié)、情人節(jié)、生日、結(jié)婚紀(jì)念日,她總期待他能察覺(jué)到一些什么,但是他連提都沒(méi)有提,仿佛是另外一個(gè)星球上在發(fā)生的事。她后來(lái)干脆也學(xué)習(xí)他,不關(guān)心任何節(jié)日,只是那些鋪天蓋地的廣告和微信朋友圈喪心病狂的秀恩愛(ài),總能把她的情緒撩起來(lái)。漸漸地,她覺(jué)得羞愧,這種從來(lái)得不到呼應(yīng)的期待讓她整個(gè)人透出一股可憐的味道,她為自己的這種可憐而羞愧。好在,他們的銀行卡也和他們的心一樣分得很開(kāi),于是,那一件一件的新衣服新圍巾就這樣陸陸續(xù)續(xù)走進(jìn)她的衣柜,挨著她,靠著她,陪她說(shuō)話(huà),讓她不再覺(jué)得寒冷。
先生喘著均勻的呼吸,睡著了,仍將她摟得緊緊的,她背對(duì)著蜷縮在他的懷里。她享受這種安靜,就這樣,安安靜靜地抱在一起,真好,雖然他睡著了,但仍有體溫的交換,讓彼此融合。先生變得像那件價(jià)格高昂的羊呢大衣一樣,讓她忍不住想擁有。她摸著這個(gè)男人壓在自己腰上的手掌,內(nèi)心有了一種久違的安寧。這樣的擁抱才是一個(gè)女人應(yīng)得的幸福啊。沒(méi)有良心的撕扯,不必附帶一點(diǎn)點(diǎn)的負(fù)罪感。在這樣的安心與舒適中,她也漸漸地睡過(guò)去了。
忽然,她覺(jué)得腰上的手掌動(dòng)了,將她的肩膀扳了過(guò)來(lái),這樣他們就面對(duì)面。她看著他的臉,這么近啊,多么熟悉的臉啊,再看他的眼,睫毛依舊那么長(zhǎng)。仍是她喜愛(ài)的男性的標(biāo)準(zhǔn),比如長(zhǎng)長(zhǎng)的睫毛和纖長(zhǎng)的手指,是那種大男孩的美貌。先生也在看她的臉,她卻不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她自知自己五官并不精致,一有人細(xì)細(xì)端詳她,她便心虛,抽起煙或是蹺起腿,她畢竟有一雙長(zhǎng)腿,好在人家細(xì)細(xì)端詳她五官的時(shí)間并不長(zhǎng)。大家關(guān)心的并不是這個(gè)。一切只要過(guò)得去就好,沒(méi)有人想要記住什么。現(xiàn)在,先生端詳著她,什么話(huà)也沒(méi)說(shuō),她亦無(wú)法從他的眼眸中看見(jiàn)自己,床頭燈被調(diào)得非常灰暗。既怕影響到睡眠中的孩子,也是他們的習(xí)慣,從戀愛(ài)開(kāi)始就喜歡在昏暗中相擁,沒(méi)有完完全全地互相裸露過(guò)身體,這是不是一開(kāi)始就出現(xiàn)了的不詳預(yù)示呢?
先生的想法果然很難捉摸。他柔聲說(shuō)道:“你想吃醬牛肉嗎?”
她心里訝異,醬牛肉?這個(gè)時(shí)候?反對(duì)的話(huà)?cǎi)R上要脫口而出,舌尖卻滲出了一股甜意。她做他妻子多年,只有在兩件事上做得像樣,一個(gè)當(dāng)然是生了兒子,還有一個(gè)就是做醬牛肉。和他父母同住,三餐都是他父母料理,她不必忍受廚房的油煙,但也少了端菜上桌時(shí)那份驕傲,讓她獲得家庭主婦的尊嚴(yán),唯一參演作品就是做醬牛肉。她從自己母親那里學(xué)來(lái)的,先生吃了一口就喊:“天哪,怎么這么好吃?”先生的母親撇撇嘴:“不就是醬牛肉嘛!”搶著也做了一次,可是先生不顧憤憤不平的母親,居然直接說(shuō)出口:“不如她做得好吃!”她沉默著多做了一點(diǎn),好大的一塊牛肉,醬好后放在冰箱里,先生喜歡在晚餐時(shí)切一些,配點(diǎn)小酒,便是極好的美味了。
臥室里燈光昏暗,她看不清手表上的指針。她一直喜歡戴手表,手表和大包包一樣,給她安全感。但現(xiàn)在,她少有地看不清時(shí)間了。也許,應(yīng)該去買(mǎi)個(gè)帶夜光功能的手表了。她想開(kāi)口問(wèn)他“你知道幾點(diǎn)了嗎”,但又擔(dān)心掃了他的興致,雖然她只是想知道一下時(shí)間而已。
被窩里涌進(jìn)來(lái)一股冷風(fēng),體溫交換結(jié)束了,她的身邊變空了。先生起身,套上了那件黑色羽絨服。這是幾年前她陪他去買(mǎi)的,春節(jié)商場(chǎng)打三折,純黑色,沒(méi)有一點(diǎn)線(xiàn)條或設(shè)計(jì),每年冬天先生都穿它,倒像是他身上的皮膚一樣了。她不知道,他們之間今天的局面是否和他的穿著有關(guān)。她明白自己無(wú)力說(shuō)服他,正如他也無(wú)法改變她。但此刻,他們至少有一個(gè)共同點(diǎn):想吃醬牛肉。晚餐她根本沒(méi)有吃飽,他的母親做的飯菜一直都只能保證她不被餓死而已,數(shù)年了仍舊不適應(yīng)。剛才的溫存又消耗了體力,何況她感到快樂(lè),快樂(lè)得想要大吃一頓。
先生開(kāi)門(mén),去廚房,開(kāi)冰箱的聲音,然后就沒(méi)有聲音。她疑惑著,先生又回來(lái)了:“奇怪,家里的菜刀去哪里了?”她也納悶,穿好衣服,親自到廚房去找,原本應(yīng)該放菜刀的地方,真的空空的。擔(dān)心吵醒他的父母,她盡量輕手輕腳,打開(kāi)廚房里上上下下的柜子,沒(méi)有,沒(méi)有,還是沒(méi)有……她回頭朝先生搖了搖頭,先生手上正端著一大塊醬牛肉,一臉失望,過(guò)了一會(huì)兒,他忽然高興道:“沒(méi)事,我知道哪里有,我去借來(lái)!”她比找不到菜刀還更疑惑,大晚上的去誰(shuí)家里借菜刀啊?
先生似乎顧不上解釋?zhuān)d致盎然地說(shuō):“你在家等著,我馬上回來(lái)!”他邊說(shuō)邊往房間走,出來(lái)時(shí)已經(jīng)套上了外褲,到門(mén)口穿鞋,是那雙夾趾拖鞋。
“砰”的一聲關(guān)上了門(mén)。
她從貓眼往外看,先生往樓梯上走。她見(jiàn)他拐彎不見(jiàn)了,立刻也跟了出來(lái)。先生的拖鞋聲一直往上走。她悄悄地跟著,絲毫沒(méi)有意識(shí)到這是一個(gè)多么危險(xiǎn)的夜晚。
九樓。先生敲了門(mén),然后進(jìn)去了。
她也走過(guò)去,開(kāi)門(mén)的人正要把門(mén)關(guān)上,被她一手按住了,等看清對(duì)方的臉,她已經(jīng)驚呆了。對(duì)方似乎也驚住了。一時(shí)空氣凝固。
“你不是去北京了嗎?”她扶著自己的胸口問(wèn)。開(kāi)門(mén)的女人不是別人,正是高中同學(xué)、閨密黃蕓。
“我回來(lái)了嘛。”黃蕓斜著身子靠在門(mén)框上,她已留成了長(zhǎng)發(fā),染著栗色,燙著小小的卷,那是她們倆在一起時(shí)曾經(jīng)討論過(guò)的最漂亮的發(fā)型,多么女人和風(fēng)情。可是她們倆總是等不到留及披肩就剪了。想不到黃蕓一年多不見(jiàn),居然做成了這個(gè)完美發(fā)型。這讓她有一種被拋棄和背叛的感覺(jué)。更可氣的是,她那懶洋洋的姿勢(shì)和口氣,說(shuō)話(huà)的時(shí)候嘴唇微微上揚(yáng),似笑非笑,半裹的睡衣里,隱約露出潔白修長(zhǎng)的雙腿,一副受盡寵溺的得意樣子。兩人過(guò)往相處中的種種深藏的嫉妒,此刻全部浮出,這個(gè)小妖精,她恨不得撲過(guò)去一口咬死。
什么時(shí)候回來(lái)的?回來(lái)干什么?為什么只和我先生聯(lián)絡(luò)?……她的心里冒出無(wú)數(shù)疑問(wèn),它們翻滾著爭(zhēng)先要冒出來(lái),但她決定控制住自己,慢慢來(lái),慢慢來(lái),她已經(jīng)嗅到了秘密這個(gè)罐子的獨(dú)特味道。她要掀開(kāi),看看里面到底裝了什么。所以,研究黃蕓是接下來(lái)的事情,當(dāng)務(wù)之急,她必須找到自己的先生。她已經(jīng)看不見(jiàn)自己先生的身影了,正不知他去了哪里,不知從何處找起,里面卻傳來(lái)聲音:“我就是好她這一口,懷疑是不是加了鴉片了,下次帶點(diǎn)給你嘗嘗哈!”然后,就看見(jiàn)先生提著刀走出來(lái)了,加入門(mén)框后的畫(huà)面中。
她望著這個(gè)畫(huà)面中的兩張臉,熟悉、陌生、可怕。特別是先生那種放松的閑適的表情,她已經(jīng)很久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的。他們?cè)谝黄鸬娜兆樱坪蹩偸蔷o張而無(wú)趣。
先生似乎也愣了一下,然后立刻又恢復(fù)到放松狀態(tài),還難得的一副好興致的樣子:“借到刀了,我們走吧。”好像這個(gè)片段是可以和剛剛在家的那些畫(huà)面直接剪輯粘貼在一起的。
她的怒氣正是在這時(shí)候升騰起來(lái)的,她才知道自己有多憤怒,憤怒到不知如何是好,是要歇斯底里上天入地詛咒發(fā)作一通,還是咬緊雙唇一言不發(fā)嘴角一抹冷笑就轉(zhuǎn)身離去?這樣的劇情她在小說(shuō)中、電視中見(jiàn)得太多,也曾嗑著瓜子對(duì)著屏幕大肆評(píng)論,各種尖銳的言辭隨著瓜子殼一同飛舞。但真的換成女主角是自己時(shí),她傻了。嘴里也不知該說(shuō)什么,手腳也不懂該怎么動(dòng)。她苦笑了一下,畢竟這是第一次面對(duì)這樣的情況。畢竟這是學(xué)校里也沒(méi)有教過(guò)的。也許她應(yīng)該多補(bǔ)充些應(yīng)急救生課。在她三十多年的人生中,一直沒(méi)有松弛過(guò)神經(jīng),前二十年作為優(yōu)秀學(xué)生和優(yōu)秀班干部活著,后十多年成了同事眼中的一位埋頭認(rèn)真做事、從不敢說(shuō)不的最底層職員。她一直告訴自己,如果不努力的話(huà),你也不會(huì)一直都是又丑又窮,而是變成又老又丑又窮。于是,她努力表現(xiàn)完美,內(nèi)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不安,害怕自己所在的單位轉(zhuǎn)企,害怕開(kāi)車(chē)的時(shí)候出車(chē)禍,害怕某個(gè)男人幫她掖被角的時(shí)候突然有人砸門(mén)進(jìn)來(lái),更害怕網(wǎng)購(gòu)的記事本有一絲一毫的不符合心意(她有“記事本病”,隨身帶著的本子,尺寸、款式、顏色都必須是她最想要的,一旦開(kāi)始用了,不可以寫(xiě)錯(cuò)一個(gè)字),但是她從未害怕過(guò)她的先生會(huì)給她這方面的傷害。她的先生,怎么可能?她已經(jīng)想不起他有什么優(yōu)點(diǎn),但如果讓她盡情列舉出他的不好,她大概可以坐在那邊講一天,不喝水,或者也可以只要一句話(huà)就夠了不用再說(shuō)了:他是那么老實(shí)、呆滯、平庸的一個(gè)人,還小氣。
而現(xiàn)在,最不可能的事情發(fā)生了。所以,人活著根本不必顧慮重重,因?yàn)槿松蟹N“倒霉定律”,你能想到的基本不會(huì)發(fā)生,發(fā)生的基本都是你想不到的。她不得不再次打量起天上砸下來(lái)的這個(gè)災(zāi)難。作為曾經(jīng)的閨密,災(zāi)難的化身,黃蕓活得顯然比她更好。文著時(shí)下最流行的霧眉,雙眼竟是晶瑩的,賤人,一定是戴了美瞳,大晚上還在家戴美瞳。最叫她納悶的是,她的小腿瘦成了細(xì)細(xì)長(zhǎng)長(zhǎng)的樣子,而她印象中,黃蕓最羨慕她的大長(zhǎng)腿,總嬉笑自己是小短腿,冬天一穿靴子,整個(gè)小腿都找不著了。她一向要強(qiáng),覺(jué)得自己出色,不想人人竟各自有辦法。她打量著黃蕓,盡量不動(dòng)聲色,努力撐起自己的氣場(chǎng)。兩個(gè)女人之間的友情,多多少少都帶著互相的嫉妒和攀比,以往她與黃蕓之間,總是她藏起自己的光芒,現(xiàn)在她多么希望自己變得光芒四射,來(lái)對(duì)這個(gè)災(zāi)難羞辱一番。
先生完全不懂她在想什么,他好像剛吃完陽(yáng)光的向日葵,明媚著臉:“不走是吧,那就都進(jìn)來(lái)坐會(huì)兒吧。”
她不知他是佯裝鎮(zhèn)定,還是真的鎮(zhèn)定,如果是后者,就太可怕了。
就真的都進(jìn)了門(mén)。黃蕓邊關(guān)門(mén)邊說(shuō):“你們倆都給我換一下拖鞋吧。”好像他們是平常來(lái)串門(mén)的一樣。她居然聽(tīng)話(huà)地?fù)Q了鞋。先生已經(jīng)坐在沙發(fā)上了,抖了抖腳,笑嘻嘻道:“已經(jīng)是拖鞋了!”
詭異的氣氛就是這樣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加重了。先生不是應(yīng)該要驚慌、掩飾和解釋嗎?為何還有如此從容與“調(diào)皮”,她與他結(jié)婚多年,竟是從未見(jiàn)過(guò)他有這樣一面的性情。
她打量房子,小小的單身公寓,物品皆簡(jiǎn)潔而時(shí)尚,都是純色的,沒(méi)有圖案,角落里三五處都點(diǎn)綴著花,那花也是細(xì)細(xì)瘦瘦的,一兩枝丫,插在拙樸的瓶里,有一種說(shuō)不出的精致。
黃蕓叫她坐,她不坐,黃蕓也不管她了,自己拐到沙發(fā)上坐下。
這樣,畫(huà)面就很滑稽。先生和黃蕓在沙發(fā)上坐著,她站著,雖然他們倆之間隔了一段距離,但她就是知道,他們之間一定什么都發(fā)生過(guò)了。
“這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訴我,這一切他媽的是什么意思?”她站在那里,沒(méi)有歇斯底里的詛咒,也沒(méi)有咬緊雙唇的冷笑,而是很平靜地說(shuō)著臟話(huà)。
“什么什么意思?既然你都看到了,我也沒(méi)什么好解釋的。”先生動(dòng)了動(dòng)身子,好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他說(shuō)話(huà)的時(shí)候甚至還攤了攤手,這種明顯掌控著局勢(shì)的、瀟灑的姿勢(shì)也是她從未見(jiàn)過(guò)的。
她扭曲著臉,眼神掃向了他放在茶幾上的那把菜刀。茶幾是白色的,邊上是一把刀。很平常的那種菜刀。但又實(shí)在不平常。因?yàn)椴说队幸环N令人恐怖的熟悉感,不僅款式一樣,甚至連刀柄處那個(gè)凹痕也很像。她在家是不做飯的,也就是說(shuō)沒(méi)有什么機(jī)會(huì)碰到菜刀,但有一次先生的母親嘴巴一張一合地沒(méi)完沒(méi)了地說(shuō)她的不是,她靜靜地走到廚房抽出菜刀就遞給她,既然這么不滿(mǎn),不如殺了我吧。先生的母親爆發(fā)出一種被冒犯的憤怒,場(chǎng)面更加不可收拾,而她則靜靜地欣賞著菜刀上的那個(gè)凹痕。這樣的凹痕應(yīng)該是世上獨(dú)一無(wú)二的呀。除非這是同一把刀。她被這個(gè)想法嚇了一跳,身上的毛孔在張大。她又看向先生。先生的五官其實(shí)仍是英俊的。她是視覺(jué)動(dòng)物,當(dāng)年就是看上了他的英俊。只不過(guò)多年共同生活,再多英俊也蒙上油煙味。而此刻,先生的臉充滿(mǎn)了陌生感,仿佛有一只手,拂去了那些油煙味,讓她又重新能看見(jiàn)他的英俊。
先生很悠然地說(shuō):“你的錢(qián)都買(mǎi)衣服了,我再不存錢(qián),我們家就完蛋了。事情也沒(méi)什么,我就是湊上我爸媽的錢(qián),買(mǎi)了這個(gè)房子。還有房租收著。”說(shuō)“房租”這個(gè)詞的時(shí)候,先生和黃蕓相視一笑。她感覺(jué)到茶幾上的那把刀似乎也在笑,它在問(wèn)先生和黃蕓,什么時(shí)候動(dòng)手呢?
黃蕓不知什么時(shí)候也換了姿勢(shì)坐,枕著手臂側(cè)向了先生,笑瞇瞇地聽(tīng)他講。
這是一個(gè)女人很喜歡用的角度。這種角度,能夠顯出腰間的那道S曲線(xiàn)。黃蕓在故意展示她的性感。那一瞬間,她覺(jué)得所有的精致都是偽裝出來(lái)的,真正優(yōu)雅的女人應(yīng)該是美而不自知的,至少是不炫耀的,而黃蕓其實(shí)就是個(gè)廉價(jià)陪酒小妹。一定是的。先生不過(guò)是被蒙騙了。男人看女人,向來(lái)和女人看女人都不一樣的。那些女人用來(lái)迷惑男人的伎倆,也只有身為女人才能體會(huì)和看透。
“然后呢?”她在等先生講。盡量保持平靜,告訴自己不要失態(tài)。失態(tài)的話(huà),首先氣場(chǎng)上就輸了。再說(shuō),漸漸彌漫起來(lái)的悲傷,也沖調(diào)了她原本的憤怒。
“沒(méi)有然后啊。”先生攤了攤手。
她走上前一步,瞥向菜刀。感覺(jué)到心中的怒氣像一個(gè)移動(dòng)的火球,被摁下去后又升起來(lái),升起來(lái)后又被摁下去。眼前的局勢(shì)顯然很不利,先生和黃蕓說(shuō)不定已經(jīng)瘋狂了呢?與他們廝殺多么不值,如此平庸和粗糙,況且她最?lèi)?ài)自己,L牌的護(hù)膚品,O字母打頭的衣服,代購(gòu)的名牌包還有瑜伽私教,她愛(ài)這些,也只想維持這些。如果還能有個(gè)衣帽間就更完美了。那些無(wú)疾而終的短暫戀情,早就給她上過(guò)課,她在三十三歲時(shí)終于弄明白:所謂愛(ài)情不過(guò)是一分溫柔惹來(lái)十分想象,兩人相愛(ài)多半是一種對(duì)手游戲,夾雜著資質(zhì)的較量和匹配,人生想要精彩,除了用心經(jīng)營(yíng)自己之外,別無(wú)他法。既如此,嫁給誰(shuí),還不都一樣?
所以,到底要不要繼續(xù)捅穿真相?
沒(méi)有人心疼真相,沒(méi)有人在意真相,但是孩子呢?她想起自己熟睡中的兒子,離開(kāi)了這么久,他會(huì)不會(huì)已經(jīng)從睡夢(mèng)中驚醒?正在哇哇大哭?翻身掉下床磕破頭?他每晚睡覺(jué)必枕著她的手臂,摸摸她臉上和后脖子上的兩顆痣,快睡著時(shí)必定會(huì)用力摳一下她的痣,她去擋臉上的,他必定會(huì)去摳她脖子上的,她去護(hù)自己的脖子,他必定會(huì)去摳她臉上的。最后,他安靜一會(huì)兒,她以為他睡著了,結(jié)果他把胖嘟嘟的腳丫子伸到她鼻子前:“媽媽?zhuān)窍挛业某裟_丫!”她吻。他又把胖嘟嘟的小手伸到她鼻子前:“媽媽?zhuān)且幌挛业某羰质郑 彼傥恰K┲┲ㄐχ瑓s已經(jīng)睡著。每晚,必得如此這般玩一陣,算是母子之間的睡前游戲。而現(xiàn)在,仿佛離開(kāi)了半個(gè)世紀(jì),她已經(jīng)開(kāi)始想念他小小的柔軟的身子,抱著他的感覺(jué),那才是她的全世界。她想明白了,為了這個(gè)美好的柔軟的小世界,她愿意吞咽下一切屈辱。
這時(shí),黃蕓起身了。走到她面前,未語(yǔ)先笑:“你說(shuō)巧不巧,我剛回福州,才在中介登記沒(méi)幾天,就剛好租到了你老公的房子。那時(shí)我還在想,怎么跟你這么有緣,你老公說(shuō)你還不知道有這套房子,叫我先保密。我想也是,讓你知道了,你肯定是不要我的房租的。”黃蕓說(shuō)得清脆清脆的,滴水不漏啊。她心里感慨。她看向先生,先生的表情仍是放松閑適的,那一刻,她似乎有些相信,世界仍是完好無(wú)損的,坦坦蕩蕩的,太陽(yáng)底下根本沒(méi)有秘密。也許真的是她多慮了。
黃蕓又來(lái)拉她的手:“別發(fā)神經(jīng)了。快過(guò)來(lái)坐下。”她就被黃蕓拉著,走到沙發(fā)邊,被摁下。
現(xiàn)在的畫(huà)面是,她坐在先生和黃蕓之間。既可以理解成友情愛(ài)情雙豐收,也可以理解成被某種秘密綁架著。那把刀,仍舊在茶幾上,在燈下反射出熱烈的光。她不明白,一把菜刀而已,切菜切肉就好,黃蕓為何將它磨得如此鋒利,特別是還留出了尖角?她打了個(gè)寒戰(zhàn),驚覺(jué)這根本就不是廚房用的菜刀,這是一把尖刀。
先生將臉逼近她的鼻子前,用低沉的嗓音說(shuō):“親愛(ài)的,你說(shuō),你這十年都存了多少錢(qián)?拿出來(lái)給我們看看吧。”
是的。先生叫她親愛(ài)的。先生從來(lái)沒(méi)有叫她親愛(ài)的,被她迷得神魂顛倒時(shí)也不過(guò)喊她“茉莉”。那是本地方言,意思是小貓咪。她當(dāng)然沒(méi)有錢(qián),她是來(lái)找他的,而先生是來(lái)找菜刀的,他們本來(lái)是要吃醬牛肉的。她沒(méi)有錢(qián),錢(qián)包里也沒(méi)有多少錢(qián),賬戶(hù)上也沒(méi)有多少錢(qián),所有的錢(qián)她都花掉了,來(lái)為她那座內(nèi)里空虛、腐蝕的生活之屋貼上一些華麗的瓦片。而這,他是知道的。她搖了搖頭。淚水彌漫了雙眼。
“沒(méi)有錢(qián)?你一向清高,覺(jué)得比人聰明,看不起這個(gè),看不起那個(gè)。我倒是很好奇,你的心到底有多了不起。”先生忽然收起笑意,嚴(yán)肅著說(shuō),他修長(zhǎng)的手指輕輕地摩挲著那把尖刀,忽然,那把刀就直抵她的胸口。
她能感到刀的尖銳和冰冷。先生的臉在刀光映襯下,格外英俊。他一點(diǎn)都不平庸,一點(diǎn)都不孱弱。此刻,她方悟出來(lái):孱弱的,一直是她自己。她只知拿自己的靈與肉與這個(gè)世界碰撞、磨損,從來(lái)不知為自己造一個(gè)堅(jiān)固的殼。而先生也好,黃蕓也好,他們都是有殼的。他們躲在殼后面,此刻才伸出觸角來(lái)。
她想喊,可是恐懼已經(jīng)把喉嚨堵塞住了,發(fā)不出任何聲音。
“躺下來(lái),親愛(ài)的。”先生說(shuō)。
她聽(tīng)話(huà)地躺下,淚水已經(jīng)流下來(lái)了。她一直以為為了維持生活表面的完整,懷著恨意的一方是自己,從未想過(guò),先生居然也如此恨她,而她卻從未發(fā)覺(jué)。她想到她的兒子,可憐的孩子。
先生居然伸手將她眼角的淚擦去:“不哭,不哭,親愛(ài)的。”有那么一瞬,她似乎好像笑了一下,多少年了,早已沒(méi)有人能為她拭淚。開(kāi)始她哭的時(shí)候,先生會(huì)看著她哭,偶爾抽張紙巾給她,這便已經(jīng)是極好的了,后來(lái)她哭,先生就煩,關(guān)上門(mén)離去。再后來(lái),先生再也看不見(jiàn)她哭了。她寧可自己痛苦到躲在衛(wèi)生間里用刀片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手腕,也不要讓他看見(jiàn)她哭的樣子。好在,多年來(lái)的訓(xùn)練,她已經(jīng)能夠?qū)I(yè)而熟練地掌握著刀片運(yùn)轉(zhuǎn)的力度,有那么一點(diǎn)點(diǎn)痛,流一點(diǎn)點(diǎn)血,但又不至于致命。她的手腕上終年繞著一圈又一圈的手串,硨磲、綠松石、黃水晶、南紅、青金,還綴著幾顆黃金的小吊飾,多美。她和那些男人約會(huì)的時(shí)候,也從不脫下手串。沒(méi)有人要看傷口。人人都要美好啊。
要不是那把刀的冰冷,她以為下一刻她就可以飛奔離開(kāi)這里,跑回自己的床上。看,這就是報(bào)應(yīng)。夜里丟下自己的孩子。她多么懷念夜里抱著兒子睡覺(jué)的那種安全感。盡管在這以前,孩子夜里哭鬧,她渴望睡眠、疲憊至極、耐性喪失的時(shí)候,會(huì)忍不住打耳光發(fā)泄,一下,一下,一下,啪啪啪,響亮而清脆,當(dāng)然是打在自己臉上,她不至于發(fā)瘋到打兒子。但是有次從臺(tái)燈昏暗的燈光中,她還是瞥見(jiàn)了兒子眼中的驚恐。兒子看見(jiàn)她在抽自己的耳光,立刻就安靜下來(lái),不敢哭了。她被那個(gè)小小的驚恐眼神驚住了。聽(tīng)說(shuō)人在三歲之前所見(jiàn)的一切,會(huì)成為他此后一生的痕跡。她害怕了,再也不愿將傷害移植到純潔無(wú)辜的嬰孩身上,從此便不再打自己耳光。孩子也一天一天漸漸長(zhǎng)大,鬧睡的時(shí)間也越來(lái)越短。有次她刮腿毛不小心劃了一道口子,孩子心疼得哭了起來(lái),第二天一早醒來(lái)就摟住她:“媽媽?zhuān)悻F(xiàn)在還疼嗎?”媽媽現(xiàn)在不疼了,但是她卻被困在一把刀前。
她想挽回一點(diǎn)自尊,結(jié)果還是淚流滿(mǎn)面:“我想回家,我覺(jué)得兒子在哭。”多少有點(diǎn)拿孩子來(lái)當(dāng)籌碼的心機(jī),但她也真的想孩子。兒子一直想要一個(gè)變形金剛大黃蜂,她還沒(méi)給他買(mǎi)呢。
先生拿著刀的手靜止了。
黃蕓卻仍是笑,笑意像水一樣,蕩漾在她妝容精致的臉龐。
此刻,那把刀就在她的胸口,她平躺著,一動(dòng)都不敢動(dòng)。先生和黃蕓一左一右地圍著她。她成為核心。一直以來(lái)她都希望成為核心。她痛恨平庸。但總也成不了核心。在單位里,她總是會(huì)脫口而出一些蠢話(huà),或是信手做了一些蠢事,盡管每次過(guò)后她都會(huì)恨不得將自己的舌頭剪下,或是干脆將自己關(guān)進(jìn)小黑屋,但這并不妨礙她下次繼續(xù)說(shuō)蠢話(huà),或是做蠢事。所以,一直以來(lái)她都成不了核心,至少不能手握重權(quán)。這點(diǎn)多少讓她在痛恨先生的平庸的時(shí)候,順便進(jìn)行一些自省。滑稽的是,現(xiàn)在,她是核心了。
先生把刀扔在桌面上,轉(zhuǎn)身。
她看著刀在桌面上抖了幾下,終于完全停下來(lái),居然忘了爬起來(lái)就跑。這一遲疑十分要命。黃蕓拿起刀,走到她的面前,俯下身來(lái),專(zhuān)注地看著她。
她的眼神里沒(méi)有嫉恨、沒(méi)有竊喜、沒(méi)有歡喜。似乎她做過(guò)無(wú)數(shù)次這樣的事,不過(guò)是在等待時(shí)間的移動(dòng)而已。黃蕓輕啟朱唇,說(shuō)道:“不疼。就算疼,你也忍一下吧。我們很快就能看到真相了。”
先生立刻回過(guò)身來(lái):“你在干什么?不是說(shuō)好,就是給她個(gè)教訓(xùn)嗎?”
黃蕓笑。這個(gè)女人的笑,已經(jīng)有一些神經(jīng)質(zhì)的味道。她怕先生來(lái)奪刀,手上竟然用了力,刀尖開(kāi)始微微地頂進(jìn)她的胸口。
她睜大了雙眼,眼里是巨大的恐懼。死亡?她從沒(méi)想過(guò)死亡。她甚至連衰老都沒(méi)有想過(guò)。她愛(ài)自己,服飾得體,保持有腹肌,抱怨這抱怨那,一直在期待更完美的生活。
先生企圖走過(guò)來(lái),黃蕓手上又加了些力氣。她感覺(jué)到疼了。也就是在那一刻,她才明白,原來(lái)今晚的一切都是按照劇本在演的。先生是導(dǎo)演,黃蕓是導(dǎo)演,他們合起來(lái)導(dǎo)演了這場(chǎng)戲,那么自己算什么呢?女一號(hào),反派,還是馬上就要退場(chǎng)的路人?然而,她求助的眼神只能望向先生。她能確定,先生并不想取她性命,他需要一個(gè)精神出口,他只是想給這操蛋窒息的生活,這乏味發(fā)霉的婚姻一個(gè)教訓(xùn),抑或就是給她一個(gè)教訓(xùn)。到了這樣的關(guān)鍵時(shí)刻,諸如生死邊緣,她十分清楚,能夠指望的也許就只有他了。孩子爸,竟是最可靠最親密的關(guān)系。
先生在急切地說(shuō)著什么。他和黃蕓爭(zhēng)吵起來(lái)。她卻什么也聽(tīng)不見(jiàn)。如果可以,她想好好和先生說(shuō)說(shuō)話(huà)。她想起,自己已經(jīng)很久沒(méi)有和先生說(shuō)話(huà)或是吵架了。她想告訴先生,先生的父親,在一次酒后失控下,打過(guò)她三個(gè)耳光,一下,一下,一下,啪,啪,啪,響亮而清脆。重要的是,她的兒子還在一旁看著。而這,就是為什么她恨著他們的這個(gè)家。但現(xiàn)在,快要死了,她就不恨了,和生死相比、和毫無(wú)干系的外人相比,再支離破碎、貌合神離的家也終究是家,而這也正是為何“家家有本難念的經(jīng)”,然而家家都會(huì)念得下去。有了家,有了孩子,人人下了班或出了酒吧都往家里回,第二天吃完難以下咽的早餐再去上班。天哪,她不要死,她舍不得死,更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黃蕓卻不顧她的這些領(lǐng)悟。與黃蕓手中的刀比,她的領(lǐng)悟來(lái)得太遲了。黃蕓和先生吵完,又往她身上俯下來(lái),表情冰冷,一言不發(fā)。這一次,黃蕓她不笑了。
氣氛就更加可怖了。她下意識(shí)地閉上了眼睛,知道最壞的事情正要發(fā)生了。每次練習(xí)瑜伽的時(shí)候,她也會(huì)下意識(shí)地閉上眼睛,在每一個(gè)延伸的動(dòng)作中,在深長(zhǎng)的呼吸中,她感受到自己身體的自由。而此刻,她竟然也有這樣的自由。
刀在游走。疼。很疼。一點(diǎn)一點(diǎn)加劇的疼。血。越來(lái)越多的血。黏稠的、溫潤(rùn)的血,沿著胸口流下、沿著高聳的肋骨滑下。她懷孕時(shí)肚子好大,兩排肋骨也被高高撐起,孩子生下后,依然高聳著,沒(méi)能縮回去,這大概是她產(chǎn)后恢復(fù)最不成功的地方。
現(xiàn)在只剩下一個(gè)問(wèn)題了。那就是她最想知道的答案:自己的心到底是長(zhǎng)什么樣的?畢竟這么多年來(lái),她活得如此自欺欺人,也沒(méi)有好好面對(duì)過(guò)自己的內(nèi)心。黑色的心應(yīng)該不會(huì),她從未謀害算計(jì)過(guò)人(正是因?yàn)檫@樣,才不能成為核心吧),紅色的心也不會(huì),她深知自己并非無(wú)罪之人。單就她拎出一袋又一袋完好的衣服塞到樓下垃圾箱里扔掉,就是一個(gè)罪孽。
先生終于撲過(guò)來(lái)。他努力想按住黃蕓,大聲吵嚷著,聲音里有了哭腔。這真是觸目驚心。這個(gè)男人,居然還愛(ài)著她。
她忍著疼,欠起身來(lái),去看。她看向自己的胸口,那里,是一把尖刀。刀尖向著這個(gè)世界。
地板上還有一把刀,沾滿(mǎn)了血跡。桌腳邊,先生和黃蕓扭打在一起。他居然連打敗一個(gè)女人都要這么費(fèi)時(shí)費(fèi)勁。這么長(zhǎng)時(shí)間了,才把她手中的刀踢開(kāi)。她這么想著,胸口的尖刀又往外長(zhǎng)出了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