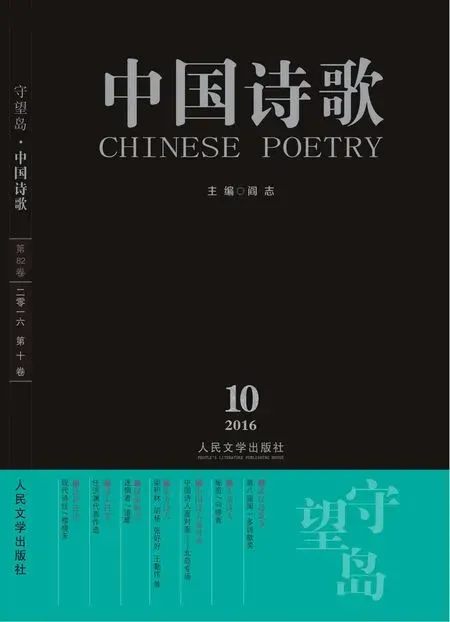齒輪〔組詩〕
星芽
齒輪〔組詩〕
星芽
齒輪
這些年 我聽命于身體里小小的齒輪
它們往西轉動 我的步子就不會邁向東邊
它們睡著了 我在書頁里低頭
食用青草 學會了鉆木取火 海底撈針
修理失眠的右眼
給身體里的犀牛 野豹子
補一補牙 為它們制作
防水的面具和膠鞋
醒來的齒輪 是一連串
鏗鏘的冒號 它們往西轉動 發出的
可能是父親的聲音
弟兄姐妹的聲音
教授的聲音
上司的聲音
睡在黃土里爺爺舅公的聲音
活著的人牽著我走進羊群
喂給我黃金和螺母 死去的人
依舊在夢中 對我滔滔訴說
而我肚子里的青草仍在徒勞地竄長
多么親密的齒輪 日以繼夜消磨著
奔跑的野豹和犀牛
刺猬的生日
我出生的時間正好有刺猬經過
它們是潮濕的 但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接下來的幾年 她將要借我年幼的軀體遮蔽鋒端
動物學家 那些嘗試用一本教科書
就將我們分離的
事實 外面的陽光爬上了屋脊
圓圓的刺猬不適合作為我聲音的一部分
不止一次 我模仿它們滾過中央公園的草坪
在機車橫穿的馬路上發出致命的尖叫
我回憶起與它們出生的同一天里
那日陰雨綿綿
刺猬細軟的爪子朝著泥塊翻動
像幾片濕云
冬天的饋贈
抹了蜜糖的收音機 以一只馬蜂的方式告別雙耳
更多的親人跑到冰花上去喝冷凍啤酒
那是在一個別樣的冬天 藝術家試圖在甲魚的身上大做文章
微苦植物的小刺果們 趕走屋舍周圍的野獸
我們一會兒去河的上游垂釣
一會兒擰開筆頭聽宇宙的聲音如何在詩歌中死去
雪簌簌地落在瓦檐
一個時辰的酒宴后 繼續勞作的人
將要搬開木桶 把星辰一點點地裝回鹽袋
盡管父親曾經教給我們唱誦圣歌
除了勞作 就要感恩天空土地
除了勞作 我們剩下的就只有眼前的這座小木屋了
每天 父親把肥沃的雪塊鏟走 拿苞谷喂食麻雀
像這個冬天對待我們一樣地
以在寒氣中打旋的荒唐形式 幾片雪花
給予我們幻想的牛奶與爐火
降落傘
降落傘墜下來
小a 小b都收到了我的信號
泥土因為扭結而蜷曲得更深
我們必將在共同體的記憶中
懷揣往事
像水池里被頻頻震碎的草木
降落傘一夜之間
成為我們飄忽不定的魚鉤
野地里
她養的金絲鳥跛了一條腿
她運送蔬菜的木車輪胎剛剛被換掉
她否認自己栽的田禾是綠色的 搖曳在草坡上
蟋蟀的眼皮垂下來
像個化開的大葫蘆
孔雀之美
孔雀 請你們轉過前世的身子
無需用開屏之美劫掠男人女人的關注
你們肩膀上的纖細面粉
終于被指甲摳出一株荷藕
在馬車橋公園里 它們被一個精神病人焚燒
留下烏黑的根須 從此 不會有孔雀再去相信
事物一成不變的美之倫理
我所遇見的孔雀 有的已經參破紅塵 被裝進道長的皂靴
有的則成為審判官五顆腳趾中的其中一顆
孔雀在小學生的政治課本上正面臨枯竭的危機
誰在日以繼夜窺視著我們 要求惡人解放孔雀
為它們美麗的代價摘下哲學面紗
像這個新生時代解放女子的縛足禮
孔雀可以平等地坐在我們對面 端起一只茶杯
災難關頭
有時也會像一位紳士那樣風度翩翩
話馬
拴在馬腿上的國家只是借馬的嘶鳴聲
來威懾四方 其實共和國的旗幟遠沒有馬的脖子長
騎士的臂力也比不過馬車夫
鞭子揚起的沙土卻讓我們望塵莫及
你們有砍掉的馬頭
用來替換懸在國王脖子上的鈴鐺
因此屠夫才是連通耶穌的大使
他們碩大的耳垂成了天堂與人間的活性塞子
我們匍匐在馬的腰段下
給這些四條腿的動物穿上人類的皮鞋
為它們發表演說的喉舌準備一只高音話筒
等到夜深人靜 月亮忘記了殺人
國王就會把多出來的一對馬腿
埋進他后花園的水晶棺
來自海域的信
我的第一封信來自水底
目睹鯨魚的鰓幫被海盜研成墨汁
印象中有關海洋的無非是沉船里的青銅寶藏
在岸邊 我的鞋子與信件同時被撲上來的浪花打濕
一個人可以騎著螃蟹出海
也可以把魚鉤別在衣領前向來往的船只敬禮
昨夜死去的詩歌已經被我裝進了信封
在今晚的月亮將小鎮淹沒之前
希望你們可以收到它
白蘿卜
我的口琴 買于屯溪三馬路的一家文具店
十一年了 店鋪對面的小學建起了徽州牌坊
遠遠望過去 里面背雙肩包踏著牧童牌旅游鞋的孩子們
我仿佛在哪兒見過
一定是小a 小b 小c的身體都縮小了
像一只只努力鉆回土地的白蘿卜
只留出頭頂的一點點葉子
游子吟
脾氣遇火會變薄 但從不發出開裂的爆鳴
表情上麻木的魚類因此一捅即破
多年來 替自己打好一副棺材 只用檀木 雞冠花
在泥土周圍灑一圈白酒
就像我不談及死亡 牙齒也會被沙棘鼠埋進冰雪
喉嚨遲早給心懷不軌的啞巴偷走
仍在生長的頭發也無法掘地三尺
好在 還有機會食用家鄉漫過我下巴的凄凄荒草
以及一次次掀翻牛羊的浪子春風
返鄉
我們繳獲的鎳幣
被投入水潭清渾的兩面
朋友喜歡蹲在岸邊 指著那些裂腹魚的鱗甲
“它們背負一身紅藕 披麻戴孝 卻不哀之過及”
多像我們零落成泥的故鄉
又在魚兒的身骨里陷落
凌晨 太陽翻出山坳
我們折斷晨露深處的細柳
竹木屐綁翻詩中的黃鸝
許多年以后 水潭里的鎳幣全銹成了呼嘯的魚紋
我們攙扶著雙雙病倒在返鄉的古道上
二十只喜鵲
春天 他們把喜鵲的聲音拿來做酒
二十只活喜鵲的嗓子
醫好了村子里的啞巴
一部分的胸脯發綠如喪鐘
全是中年的喜鵲
在教堂里背《圣經》 啃木頭
喜鵲通體明亮 卻不食人間煙火
夢游的時候單腳著地
心懷不軌的人會在它們的脖子上
系起吊繩 另一些苦命赤貧者
將雙手放在喜鵲的腮幫下
拼命乞求這些幸運的鳥兒 磕破了頭顱
他們相信喜鵲的身體里
藏著一輪滿月 像掏出高粱里的鐵器
村莊里所有的聾子和啞巴
口皆不能發聲 耳朵丟在了荒野
只有這二十只喜鵲的意義
被偶爾刮過的春風
鞭打得越來越新鮮明亮
我們在談論動物的腿
四條腿的動物可以是叢林走獸
兩條腿的一般是飛禽 游魚是無腿的
我和表姐談到動物的時候
會預先算計好腿的數量
至于毛色 性格 它們脖子里的糧食
全不是我們關心的話題
我們只偏愛議論它們的腿
比如我一提到八條腿
姐姐會立馬說出蜜蜂 蟋蟀 金龜子
等一系列詞 仿佛這些昆蟲
是從她嘴邊突然蹦出來的
我提到兩條腿 姐姐卻從來不會想到人
相比于家里夜夜酗酒的哥哥
從兩條腿走成三條腿的祖父
隔壁用一條腿走路的跛子叔叔
她更愛說出停在圍墻外面的鳥兒
比如山雀 烏鴉
紅嘴巴的鸚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