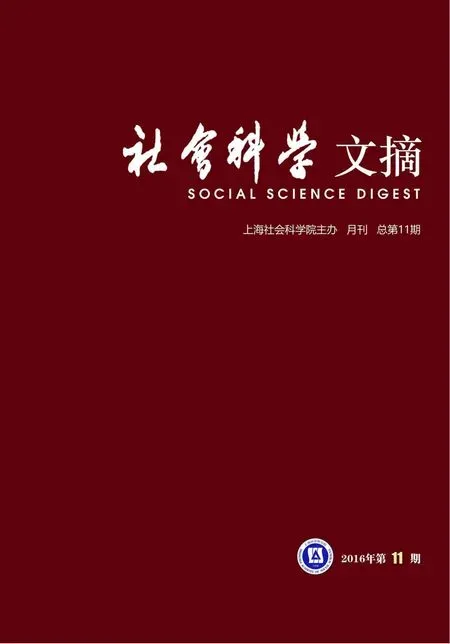死亡的尊嚴:儒家和西方觀點的比較
文/李亞明 李建會
死亡的尊嚴:儒家和西方觀點的比較
文/李亞明 李建會
在當代醫療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如何保護患有嚴重疾病的老年人和瀕臨死亡的人,以及他們是否可以安樂死,成為了緊迫而重要的問題。然而在當代西方倫理學的探討中,人的尊嚴概念本身尚未得到清晰的闡釋,死亡的尊嚴概念更是存在著混亂。應當如何利用尊嚴概念來為老年人提供保護以及尊嚴原則能夠提供什么樣的保護并不是十分明確,存在各種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觀點。讓人的尊嚴概念在臨終情境的倫理抉擇過程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就需要對人的尊嚴概念進行明確的說明,區分這個概念所包含的多重含義,澄清一個人的尊嚴對于其自身以及他人的具體要求。
儒家倫理是對當代文化有著深刻影響的思想體系。儒家雖然沒有人類尊嚴和死亡的尊嚴這個概念,但在其經典中有許多與人的尊嚴有關的論述。將儒家的死亡的尊嚴觀念與西方觀念進行比較,對我們理解臨終醫療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尊嚴概念與死亡的尊嚴
在當代關于死亡的生命倫理討論中,人的尊嚴概念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理論資源。比如,在人是否可以對死亡的時間和方式做出自主選擇的問題上,觀點對立的學者都通過援引人的尊嚴概念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一些學者認為,人們有權利決定自己何時死亡,并選擇自己希望的死亡方式,只有這樣才稱得上有尊嚴的死。然而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人的尊嚴包含著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生命的要求。因為人的尊嚴具有至高性,所以維持生命的要求也就高于人自身的意愿。可見,爭論的雙方都把人的尊嚴概念作為其觀點的基礎。
尊嚴這個概念本身的含糊不清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最主要原因,因而澄清尊嚴概念的含義是我們回答死亡的尊嚴問題的關鍵。通過文獻分析,我們發現,人的尊嚴概念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含義:即普遍尊嚴(Universal Dignity)和人格尊嚴( Personal Dignity )。這兩種含義在中西方的倫理學理論中都可以找到。所謂普遍尊嚴,是指人類所有成員都擁有的內在價值。比如康德認為,尊嚴是絕對的和無條件的內在價值,所有人類成員都因具有自主行為的能力而擁有尊嚴。所謂人格尊嚴則是指人們擁有的一種受尊重的品質。比如美德倫理傳統認為,尊嚴不是內在的,是我們通過特殊的努力和教養獲得的。普遍尊嚴是每個人天生就具有的,而人格尊嚴則是通過個人的行為獲取的;普遍尊嚴與個體自身道德行為無關,而人格尊嚴要建立在道德行為的基礎上;普遍尊嚴是不會喪失的,而人格尊嚴卻是可以喪失的。人格尊嚴能夠為普遍尊嚴提供很好的保護,比如,如果一個人不能尊重他人的普遍尊嚴,那么這個人自身的人格尊嚴就會受到傷害。
每個人的普遍尊嚴的道德要求都指向他人,要求他人給予我們基本的尊重。在照顧臨終患者問題上,普遍尊嚴意味著家庭、國家和社會對于患者都負有責任。每個人的人格尊嚴的道德要求則指向其自身,要求每個人完成自己的義務。尊嚴在死亡問題上的應用指的是有關如何度過一生最后階段的觀念和理想。一個人在死亡過程中所做的抉擇符合道德與否也是決定其人格尊嚴的重要內容。
反對安樂死和支持安樂死的學者雖然都援引尊嚴概念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但他們所意指的尊嚴的含義不同。反對安樂死的一方關注的是人的普遍尊嚴,而支持安樂死的一方關注的是人的人格尊嚴。由此可見,區分尊嚴的不同含義是我們理解各種理論爭論,解決實踐上的難題的重要方法。雖然尊嚴的兩種含義在古代和當代的西方倫理思想中均有體現,但只有儒家思想能在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中對尊嚴的兩種含義做出融貫的表述。
儒家倫理對尊嚴的兩種含義有著詳細的論述。儒家倫理認為普遍尊嚴是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的。天賦予的人道的特性使人區別于動物,成為世間最珍貴的存在。相比于西方倫理中的理性、自由和自主,儒家認為道德潛能才是最為根本的人類特征。對儒家來說,這種潛能是人的普遍尊嚴的真正基礎。但并不是所有道德潛能都能發展為充分的美德。有的人可能沒有發展自己的道德天賦,有的人可能發展出對立于自然道德天賦的性質。在儒家思想中這就意味著人格尊嚴的喪失。只有努力把道德潛能發展為美德,才能獲得人格尊嚴。普遍尊嚴和人格尊嚴都對于尊嚴的擁有者或他人構成道德上的要求。普遍尊嚴要求我們對每一個人類個體給予基本的尊重,人格尊嚴鼓勵我們實踐自身的道德追求。
更進一步理解尊嚴的兩種含義及其對于死亡的意義,我們還需要結合特定情境,在具體問題中探討死亡的尊嚴。
死亡的尊嚴與人的生物學生命
把生命的神圣性看作人的尊嚴原則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西方歷史上一種很強的傳統,特別是在基督教的理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探討自殺和安樂死等問題的時候,這一傳統認為,人的尊嚴的原則對我們提出一種不惜一切代價來拯救生命的義務。因而,自殺和安樂死因與人的尊嚴相矛盾而受到絕對的反對。康德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這一傳統觀念,他提出把人視為其自身的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的原則,并由此提出了人在明顯沒有質量的生活中也有義務保存自身。
然而就生物學生命與人的尊嚴的關聯,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觀念。比如當代的“死亡的義務”的鼓吹者約翰·哈德韋希(John Hardwig)認為,如果一個人繼續生存下去只會給別人帶來困難,他繼續活下去的利益可能不會比受到他繼續存在的負面影響的人的利益更重,那么這個人有死亡的義務。美國哲學教授、生命倫理學家希爾德·林德曼·內爾森(Hilde Lindemann Nelson)也曾經提出,如果一個人堅持活下去只能給他人帶來困境,這種狀況下繼續維持生命就是把他人當作了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即使從康德的尊嚴概念來說,這種做法都是在道德上不允許的。
強調人的尊嚴概念包含生命神圣性的觀點,都是從個體自身內在價值的角度來講的,而提出人的尊嚴概念支持結束生命的觀點則大多基于個體的生活同他人之間的關系。儒家尊嚴概念既推崇人的生命的內在價值,又關注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儒家尊嚴概念所包含的這兩個不同內容體現在普遍尊嚴與人格尊嚴的劃分之中。
儒家倫理認為個體的道德修為比生命更加重要,因而人格尊嚴相比普遍尊嚴更加重要。儒家倫理并不把生物學生命的保存作為人的尊嚴原則的最高要求。甚至在有的時候,為了維護人的尊嚴,儒家倫理明確表示支持個體結束生命的行為。比如某些情境下,只有結束生命才能維護自己的尊嚴,此時死亡反而是美好的、正義的和值得追求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表達的都是這種觀念。當代西方部分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比如大衛·威爾曼(David Velleman)認為,如果一個人不再能夠以尊嚴的方式生活下去,那么他的死就是可以接受的。
在儒家倫理中,道德的完滿應是一個人終生的追求,也是人生命最高的意義和價值,人的生命本身在很多時候只是實現道德圓滿的手段。生命的最大意義就是可以讓我們不斷追求道。可以繼續求道的生命則不應該放棄自身的道德責任,哪怕承受著身體上或精神上的各種痛苦,也不能放棄生命。相反無法繼續追求道,或與道背道而馳的生命則是不值得留戀的。因為這樣就為了較低級的價值而放棄了高一級的價值。
儒家的人格尊嚴高于普遍尊嚴的觀點與康德的倫理學是不同的。康德的倫理學認為,尊嚴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理性行動能力是人類尊嚴的基礎。說結束生命在道德上是錯誤的,是因為錯在沒有尊重這種價值。但康德的這種觀點存在著自相矛盾,因為,根據康德,所有的人類成員因為有自主行動的能力而擁有尊嚴,但有時為了執行這種自主的道德判斷,人恰恰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生命也就并不一定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價值。康德倫理學因為把人的內在價值絕對化而難以為尊嚴死辯護;而儒家倫理學因為堅持主張人格尊嚴高于普遍尊嚴而可以為某些情況下放棄生命的行為做出辯護。
死亡的尊嚴與痛苦感受
如果生物學的生命與仁和義的道德價值并不發生直接的沖突,但個體生物學生命的自然延續要伴隨著巨大的生理的或心理的痛苦,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或安樂死是否可以得到儒家倫理的支持呢?
儒家倫理與很多西方倫理學理論一樣,都區分了有尊嚴的生活質量和沒有尊嚴的生活質量,認為當生命的質量低到一個不可接受的程度,就應選擇死亡。西方對生命質量的定義主要圍繞生命的痛苦來進行。比如安樂死的定義中就包含患者正遭受不可忍受的痛苦的折磨,并且沒有康復的可能。但是儒家生命質量的概念則主要地等同于道德生命的質量。生理性生命本身的低質量并不能成為儒家倫理支持結束生命的理由。在儒家倫理學中,道德與身體相比具有優先性,甚至身體只是求道的工具。即使承受再大的痛苦,只要能夠實現道德上的價值,放棄生命就是錯誤的。
比如司馬遷被定誣罔之罪后,如果要活下來就要承受巨大的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仍選擇活下來,以腐刑贖身死,為的是創作史記,完成自己的使命。司馬遷的選擇在歷史上一直受到推崇。可見如果巨大的痛苦尚不能阻止個體承擔自己的責任,那么儒家倫理并不支持為消除痛苦而死,反而會鼓勵生命的延續。特別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儒家倫理中就更不能夠成為死亡的理由,精神上的痛苦恰恰是儒家提倡去克服、去戰勝的。因為精神上的痛苦而選擇死亡則會使人喪失尊嚴。
在這一點上,儒家的觀念與西方當代的某些觀念有所不同。很多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當生命的質量低到一個不可接受的水平,生命就不值得過下去。如果“低質量的生命”這個概念把承受不能接受的巨大的心理痛苦也包括在它的內涵之中,那么人就有理由為了結束巨大的心理痛苦而進行安樂死。比如1991年發生在荷蘭的一個安樂死的案例,就反映了這種觀念。荷蘭的鮑舍爾(Hilly Bosscher)女士身體健康,但因為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擊而要求安樂死。最終查波特(Boudewijn Chabot)醫生為她實施了安樂死。查波特醫生的支持者認為,精神上的痛苦與肉體痛苦一樣,同樣都可能成為不可忍受的痛苦。但是在儒家倫理中,鮑舍爾女士的行為則會被視為懦夫的行徑。儒家反對精神生活的醫學化。精神上的修煉本來就是道德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儒家倫理僅在一種情況下支持因為不可忍受的痛苦而選擇死亡。這里的痛苦一定是生理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并且這種痛苦已經阻礙了個體實現道德上的價值。痛苦的程度已經讓人無法繼續履行自己的義務,或者痛苦的程度讓個體全然無法顧及道德準則。在這種情況下活下去就很有可能造成人格尊嚴的貶損。
這種邏輯同當代康德倫理研究者提出的觀點有相似之處。當代的康德哲學的研究者通常都認可“劇烈的,不可補救的疼痛和痛苦”對于人生的質量有著毀滅性的影響,因為這種痛苦威脅了一個人的理性行動能力。威爾曼提出,“當一個人的生活中出現了這樣難以忍受的痛苦,這個人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了這種痛苦上,他就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在這種情況下,對其原來的尊嚴的尊重可能會允許或甚至要求一個人來幫助她結束他的生命。”在儒家倫理中,如果主體所承受的痛苦已經讓主體無法繼續承擔責任,死亡是得到許可的。
死亡的尊嚴與人的自主性
很多當代西方理論認為,人的尊嚴就等同于自主性。在死亡情境中,這一類觀點要求我們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接受治療與否以及接受何種治療的決定是不是個體自己的意愿。這也就是生前預囑在西方國家普遍開展的主要原因。
雖然自主選擇的實踐在不斷地普遍化,但理論上,完全以自主為基礎的尊嚴理論大多包含矛盾,對于相關實踐問題的解釋也并不充分。比如德沃金(Dworkin)的理論推崇自主性的同時,認為應當限制主體不尊重自身價值的自主行為。德沃金提出,“除非一個人堅持主導自己的生活,否則就不可能通過自己的行為體現生活具有的內在的和客觀的重要性。”但同時德沃金提出,以尊嚴的方式對待某人有時意味著通過強制性的干預保護其內在價值。德沃金把尊嚴的概念定義為考慮并執行我們自己關于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最根本問題的答案,而他卻又要求我們尊重他人最根本的利益,哪怕會妨礙他人執行其對于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根本問題的答案的權利。
西方尊嚴概念對自主性的強調顯示這樣一種觀念,即我們的個人生活的最本質和核心的部分是與他人無關的。可是事實上所有的人關于自己生活的決定都與他人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這類理論很難回答一個人的尊嚴對他人的要求是什么,也容易混淆個人感覺到的尊嚴的生活和普遍的、最低的尊嚴的要求。區分普遍尊嚴和人格尊嚴有助于澄清這些問題。
儒家倫理認為,一個主體擁有普遍尊嚴就要求其他人意識到并且尊重他的普遍尊嚴,出于對普遍的人類的內在價值的尊重,他人甚至可以通過強制的方式保護某一個人的這種尊嚴。在儒家生命倫理學中,行善原則相對于自主性原則具有優先性就體現出對普遍尊嚴的保護具有一定強制性。同時儒家并非不重視自主性,這種自主性體現在人格尊嚴的獲得和維護上。要獲得人格尊嚴,就要自主地做出正確的道德抉擇。通常只有自主的決定才會與個體的人格尊嚴有關,因為自主的道德選擇具有更加明確的道德意義。康德人的尊嚴的核心是執行一種自愿接受的道德律的能力,也突出了道德抉擇中自主決定的重要意義。
德沃金的理論中準許我們強制性地維護他人的尊嚴,認為這樣是在保護一個人最根本的利益。對照儒家尊嚴理論,這里的尊嚴顯然是普遍尊嚴。而德沃金主張通過自主為個體生命賦予的價值則可以用人格尊嚴來進行說明。這就解釋了尊嚴準許他人干涉涉及一個人最根本利益的問題,同時卻在其他問題上鼓勵個體行使自主性,以形成體現每個人特殊價值的人格尊嚴。
很多傳統的和當代的倫理學理論都強調尊嚴是不可喪失的,與美德、行為或成就無關,并且尊嚴是絕對平等的。但現實中我們又常常感到某些境遇下的人失去了尊嚴,或感到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程度的尊嚴。因此理論和常識之間似乎存在著矛盾。儒家雙重結構的人的尊嚴概念通過普遍尊嚴和人格尊嚴區別和聯系,解釋了理論上不可喪失的、平等的尊嚴和現實中的可能喪失、不絕對平等的尊嚴之間的關系。兩種尊嚴含義的區分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理論與常識之間的矛盾,而且有益于解決當代關于死亡的尊嚴的理論爭論中概念的混亂。
(李亞明系首都醫科大學醫學人文系副教授,李建會系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摘自《世界哲學》2016年第5期)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