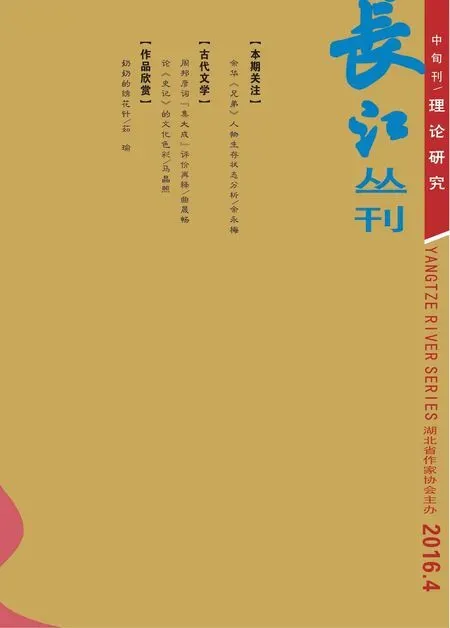河北地區佛教傳承與民族文化認同
包得義 王樹平
?
河北地區佛教傳承與民族文化認同
包得義 王樹平
【摘 要】河北地區佛教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影響深遠,在促進民族融合、維護國家統一、保障社會穩定方面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在當代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發掘河北地區佛教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對于實現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友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
【關鍵詞】河北佛教 文化傳承 民族認同
一、前言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在大力培育自身本土文化的同時,以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開放姿態,不斷接納、吸收外來思想,形成了融合儒、釋、道等思想的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外來的思想和文化,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長足發展,至隋唐時期達到鼎盛,最終實現佛教中國化,從而形成儒、釋、道三教鼎立的格局,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之相伴的是,佛教也逐漸影響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社會習俗,進而影響到了人民的心理結構和文化認同。而河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佛教文化傳播的重要區域,歷代出現了無數知名的僧人,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佛教文化,在民族融合、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方面發揮過重大的作用。探究河北地區佛教文化傳承與民族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河北地區佛教歷史文化傳承
佛教具體什么時候傳入河北地區,史無明文,但從考古發現來看,至遲在東漢中后期河北地區就已受佛教影響。[1]9在其后的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河北地區漢傳佛教先后經歷了六朝時期不斷發展壯大、至唐宋時期禪宗盛極一時、至元明清時期又日漸衰微、現當代社會又重新煥發活力和生機的總體動態過程。同時,我們可看到河北地區佛教文化底蘊深厚,呈現出歷史悠久、高僧輩出、成績顯著、影響深遠等特點,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晉代著名的西域僧人竺佛圖澄,依靠自己的神異贏得了后趙統治者石勒、石虎兄弟的信任,進而在燕趙大地推廣佛教,吸引了眾多僧人前來學法,也影響了一大批民眾奉佛造寺,堪稱燕趙地區佛教的奠基人[1]309;東晉著名高僧道安早年時曾在鄴城師事佛圖澄十有四年,精研佛教大小乘典籍,深通佛法義理,旁及老莊玄學,為其后來在襄陽和長安領袖佛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北齊著名的禪師僧稠以禪法名世,深得北齊文宣帝高洋和廢帝高殷的崇信,大弘禪學,影響很大;唐代紀國寺上座釋慧凈精通三藏,曾奉詔翻譯《大莊嚴論》,詞旨深妙,并制有多種經疏,遠近傳誦,被時人譽為“東方菩薩”;唐代的從諗禪師,應趙州當地僧眾之情,以80高齡駐錫于趙州觀音院(今柏林禪寺),此后弘法四十余載,道化大行,弟子遍布天下,形成天下聞名的自然活潑的“趙州禪風”;而義玄禪師開法于鎮州(今正定縣)臨濟院,創造了以棒喝著稱、禪風峻烈的“臨濟宗”,成為禪宗“五家七宗”之一,徒侶遍天下,盛極一時。此外,唐代禪宗的實際開創者慧能大師、唐代偉大的天文學家一行禪師、偉大的翻譯家義凈律師、宋代知名的精通工程建筑的懷丙法師等,他們的籍貫都在今天的河北地區,他們也為河北地區的佛教文化的繁榮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到元明清時期,隨著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尊崇,尤其是清代康熙、乾隆為鞏固邊防、加強民族團結,自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間先后于承德避暑山莊東北外圍陸續建成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寧寺、普佑寺、安遠廟、普樂寺、普陀宗乘之廟、羅漢堂、殊像寺、廣安寺、須彌福壽之廟和廣緣寺等12皇家寺廟建筑群,用以供養藏傳佛教的領袖,從而使藏傳佛教的傳承在河北地區迎來一個興盛期。當時,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直屬理藩院的廟宇,京城三十二座,承德八座,又因承德地處長城古北口以外,故俗稱“口外八廟”,簡稱為外八廟。外八廟中最先建造的是溥仁寺和溥善寺(已毀),這兩座寺院均建于康熙五十二年,是蒙古諸部王公為慶祝康熙六十壽辰上書請建。這也是康熙在承德僅建的兩座寺廟,其余的10座寺廟,均建于乾隆御宇時期。其中普寧寺建于乾隆二十(1755)年,是為紀念平定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達瓦齊叛亂勝利而建造。二十五年,為紀念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亂,增建普佑寺。二十九(1764)年為新疆達什達瓦部二千余眾遷居熱河后提供參拜之所而建安遠廟,建筑模仿新疆固爾扎廟。三十一年為滿足土爾扈特、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等民族前來承德朝覲瞻仰而建普樂寺。三十二年三月至三十六年八月建成普陀宗乘之廟,作為慶祝乾隆六十壽辰時蒙古、青海、厄魯特等少數民族上層首領進貢朝賀之所,因模仿布達拉宮而建,俗稱“小布達拉宮”,之后達賴喇嘛到熱河覲見時多居此處。三十七年建廣安寺(已毀),既為皇太后祝壽,又為蒙古王公瞻禮。三十九年建殊像寺,從名稱到寺的布局,全仿五臺山殊像寺。同年又仿浙江海寧安國寺的形制建羅漢堂(已毀)。最后為接待西藏六世班禪到承德祝賀乾隆七十壽辰,四十五年建須彌福壽之廟,作為班禪行宮以示優渥。外八廟以及北京城中藏傳佛教寺院的修建,極大地推動了藏傳佛教在河北地區的傳播。
還有,河北邯鄲、保定、涿州等地有佛教石刻、摩崖造像等眾多佛教遺跡保留至今,鄴城等地不斷發現新的佛教造像,都表明了河北地區佛教之盛況。總之,考查河北地區佛教傳承歷史,具有如下重要特點:第一,佛教傳承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名僧輩出,在中國佛教史上影響很大;第二,河北地區佛教兼具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兩大系統,顯密二宗皆有,佛教文化形態和佛教發展更加全面;第三,古代佛教僧侶創造了無數輝煌燦爛的文明,在創宗立派、推動佛教文化事業,促進民族團結和發展對外友好關系等方面都作出過重要貢獻。
三、河北地區佛教文化與民族文化認同
(一)在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方面發揮過巨大的作用
雖然常言僧人為出世之人,但并不表示僧人就完全能夠脫離現實生活。歷史上有不少僧人,在出世的同時,又利用自身的佛教影響力,積極地引導者社會風氣。如五胡十六國時期,后趙君主石勒、石虎先后拜佛圖澄為國師,全面參與軍國大事。在佛圖澄的教導下,二石減少了對異族人民的屠殺,緩和了當時突出的民族矛盾,還解除了禁止漢人出家的規定,從此胡漢之人可以同寺梵修,為民族之間增進交流、融合創造了良好環境。[2]李四龍研究佛教與民族融合時曾言:“佛教為外來文化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范例,客觀上增進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或外來民族的親和力與包容性。佛教的這種親和力與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這在我國歷史上的各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3]
清初,康熙皇帝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綏撫蒙古,鞏固邊防,對蒙、藏少數民族采取了“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俗習為治”的民族宗教政策,摒棄了修建長城、分兵駐守的軍事防御政策,代之以懷柔政策,加強與蒙古族的聯系,同時十分重視利用佛教的力量,此后推崇和利用喇嘛教是清王朝一貫推行的政策。[1]139乾隆在《安遠廟瞻禮書事》中明確道出推崇喇嘛教的原因:“然予之所以為此者,非惟闡揚黃教之謂,蓋以緩靖荒服,柔懷遠人,俾之長享樂利,永永無極云。”乾隆在《出山莊北門瞻禮梵廟之作》中總說修建外八廟的原因:“山莊城外北山一帶,崇建寺廟。如普寧寺,系乾隆二十年,平定西陲,四衛拉特來覲,仿西藏三摩耶廟式,建此以紀武成。安遠廟,則二十四年,因降人達什達瓦部落還居于此,仿伊犁固爾扎廟式為之。普樂寺,則三十一年所建,以備諸藩瞻覲。至布達拉廟,成于三十五年,仿西藏大昭式,敬建以祝慈厘。扎什倫布廟,乃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來熱河,為予祝七旬萬壽時,仿后藏班禪所居創建者。其他如殊像寺、廣安寺、羅漢堂,諸所營建,實以舊藩新附,接踵輸忱,其俗皆崇信黃教,用構茲梵宇,以遂瞻禮而寓綏懷,非徒侈巨麗之觀也。”此外,普寧寺中《普寧寺碑文》、《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平定準噶爾后勒銘伊犁之碑》三塊石碑,記載了清王朝為平定西北邊陲,鞏固國家統一而做的努力,是進行民族團結教育的生動教材。須彌福壽之廟是西藏與中原政府聯合的結果,清王朝鞏固國家統一、民族和睦團結的豐碑。以外八廟為代表的懷柔政策的成功,既是清朝統治者民族政策的成功,又是佛教文化促進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的積極價值。
(二)佛教文化影響下的民俗信仰,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價值理念
佛教傳入中國后,其精致高深的哲理思辨吸引了知識精英的關注,其淺顯粗俗的信仰心態則收獲了普通民眾的信奉,進而對中國的民間風俗產生不少的影響,導致我國眾多民族就增添了很多新的習俗,如:燒香拜佛、轉經祈福、水陸法會、薦亡度靈等活動。其中,既有愚昧落后的東西,也有一些豐富民眾生活、調節個人心理的有益習俗。
佛教影響下出現的風俗習慣,諸如浴佛會、盂蘭盆會、修七七齋功德等,已經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的風俗。
佛誕節是大乘佛教紀念和慶祝佛教創始人佛祖釋迦牟尼誕生的日子,又稱“浴佛節”、“灌佛會”、“華嚴會”等。歷史上,由于各地歷法的轉換,依據不同佛經以及流傳到不同地域形成的傳統,佛誕日的確定在公歷日期上差距甚大。一般而言,中國佛教界認為農歷四月初八是佛誕日。東漢末期就有這種風俗了,在這一天,各寺廟都要舉行“浴佛法會”,在大殿內用“香湯”為“太子像”洗浴。
盂蘭盆是梵文的音譯,意譯為“解倒懸。”盂蘭盆會原是佛教徒為了追薦亡靈而設的一種宗教儀式,傳說在七月十五供養佛法僧三寶,可以仗三寶之功德,解救倒懸之苦。而中國古代的傳說中認為盂蘭盆與目連救母的故事有關,就又跟傳統的孝道文化發生了聯系。
在佛教因果報應、輪回轉世思想的影響下,國人一般對死者后事的處理比較慎重而復雜。一般人死后,家人常請僧人念經,以超度亡靈。有的甚至舉辦水陸法會,為一切水陸生物供養齋食,誦念經文,以懺悔所造成的罪孽。又受佛教“中陰”思想的影響,國人往往在人死后四十九日間,親屬每七日為其營齋作法。這原本是個體家庭的做法,現在也逐漸成為社會、政府遵守的方式。比如每當國內出現嚴重地震、重大安全事故時,政府往往會在事件發生的第七天進行大規模公開悼念活動。這種做法,對于追寄哀思、祝福逝者和安慰生者具有重大的意義,也能夠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強化民族文化認同。
正如學者所言,“民族共同體中的約定俗成的風俗傳統,體現著民族文化的價值理念,是民族共同體生活與行為的模式和標準,為個體成員提供行為的預期和價值的定向,對他們自然認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導和規約作用。依附于規定的習俗和傳統民族文化的自然養成甚至可以保留幾個世紀。”這些佛教文化影響下的習俗的存在,維系了普通民眾的生活和心理訴求,體現著民族文化的價值理念。
(三)佛教文化中蘊含的積極因素,具有普世價值,在現代社會仍有意義
佛教所提倡的眾生平等、戒惡勸善、萬物和諧的思想以及吉祥美好的寓意,具有普世價值,在當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具有積極的價值。
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后,打破了印度婆羅門教宣揚的種姓制度,提倡眾生平等的主張,且言人人皆有成佛的機會。這是一個非常進步的思想,也是吸引普羅大眾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更是促進民族團結和和解的重要理論。直到現在,國際社會提倡不同國籍、不同民族、不同人種之間互相平等,中國國內提倡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之間互相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說法。
在藏傳佛教寺廟和藏族人民家中,我們時常能看到這樣一幅圖畫:在一個美麗的地方,有一棵尼拘盧樹,枝葉茂盛、果實豐碩,樹旁邊站著一頭馱有猴子的大象,猴子手捧一枚果子,肩負一只兔子,兔子頭上蹲有一只鷓鴣鳥,四只動物相親相愛,團結和睦的過著幸福和諧的生活。這就是藏族著名的吉祥圖案“和睦四瑞圖”。此圖中所蘊含的團結友愛、和諧相處和尊老愛幼的思想,不只是藏族同胞的理念,更是完美契合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總之,如《和睦四瑞圖》表達的團結和睦以及佛經中宣揚的戒惡勸善的思想,是教導人心、引人向善的有利資源,也是加強民族融合、民族認同的心靈橋梁。而這也是和睦四瑞吉祥圖案成為藏族最尊崇、最喜愛的吉祥圖案,而頻
頻出現在民間各個角落的真正原因。
四、結論
歷史上的河北佛教,在創宗立派、推動佛教文化事業,促進民族團結和發展對外友好關系等方面都作出過重要貢獻。以外八廟為代表的寺廟,加強了滿、蒙、藏族人民之間的聯系,也維系了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關系,增強了國家認同感。時至今日,西藏、青海、內蒙的佛教徒還經常來承德寺廟膜拜,外八廟仍然起著促進民族團結的作用。
構造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礎和文化象征符號的重建,增加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疊內容。首先要構建涵蓋少數民族文化內容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概念和符號系統。而“文化符號系統涉及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感的培養,這包括文化符號、典禮儀式、傳統節日等。”佛教文化影響的各種節日、風俗以及佛教宣揚的眾生平等、萬物和諧、慈悲為懷的思想以及佛教壁畫、造像中所蘊含的吉祥美好的寓意,在當代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發掘河北地區佛教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對于實現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友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馮金忠.燕趙佛教[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袁志明.北朝佛教信仰與民族文化認同[J].青海民族研究,2001(3).
[3]李四龍.中國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N].中國民族報,2009-4-28(6).
作者單位:(河北民族師范學院)
基金項目:2014年度國家民委項目“河北地區佛教傳承與民族文化認同研究”(項目編號:14HSZ004)成果。
作者簡介:包得義(1984-),男,甘肅永登人,河北民族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古典文獻、民俗研究;王樹平(1983-),女,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古代文學、古典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