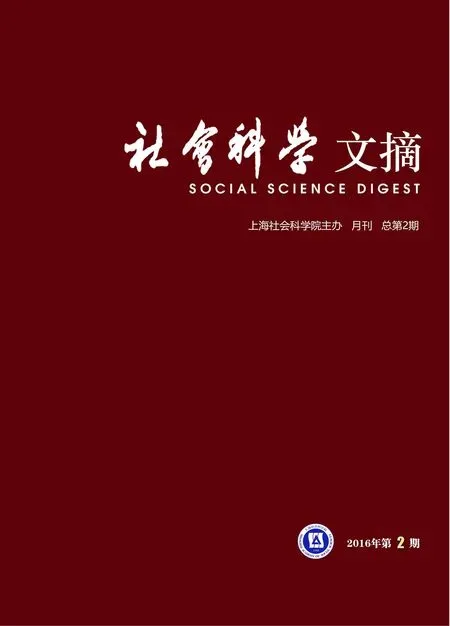家庭結構和代際交換對養老意愿的影響
文/楊帆 楊成鋼
家庭結構和代際交換對養老意愿的影響
文/楊帆 楊成鋼
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功能的完善,家庭的養老職能也隨之變動,政府承擔了越來越多的養老職能,家庭養老不再是單一的養老方式。就目前我國實際來看,家庭養老職能向家庭外部轉移是必然的趨勢。同時,家庭中老人是否居家生活會對家庭關系和家庭結構等產生直接影響,老人的養老行為逐漸成為與生育行為和遷移行為同等重要的可能對家庭產生一系列深遠變化的因素之一。基于此,研究個體主觀養老意愿及其影響因素至少有兩點好處:第一,有利于探查被供養者自身在家庭養老職能外移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對于他們是主動推進這一進程還是僅僅被動接受有所把握,進而對家庭職能變化有更理性和深刻的認識;第二,有利于對家庭變遷有更全面的理解和預期。
相關研究有以下特征:一方面,認同家庭結構和代際交換可能影響家庭養老,但這里的家庭養老主要局限于行為人選擇家庭養老的客觀條件,如養老支持來源、子女的態度等,就家庭結構和代際交換如何影響行為人主觀意愿仍需要進一步討論;另一方面,明確了家庭因素對行為人主觀養老意愿影響,但仍需深化對家庭結構作用以及家庭因素發揮作用途徑和機制的探討。本文以個體養老意愿為目標變量,分析家庭結構和家庭代際交換的影響。
研究設計
本文將有親屬關系且共同組成一個生活單位即共同居住在一起生活的成員所組成的家庭稱為“共居家庭”或“小家庭”;將有緊密聯系的親屬關系但不局限在一個生活單位(即不局限于共同居住)的成員所組成的家庭稱為“不局限共居家庭”或“大家庭”。本文在分析家庭結構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影響時,主要從“共居家庭”出發;而在分析家庭代際交換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影響時,從“不局限共居家庭”出發。
1.目標變量。養老意愿一般指行為人對養老方式所持有的主觀態度。關于養老方式的定義已有非常豐富的討論,養老涉及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關懷這三個方面基本可達成共識,盡管這三方面有時并不容易進行絕對區分。事實上,以“養老支持力”來源分析,生活照料和精神關懷更緊密地附著在老人的居住選擇之上,且居家生活和到社會養老機構生活兩者互斥,而經濟支持則可能同時從老人自己、家庭、社會保障、福利組織等多個途徑得到。因此本文認為,老人居家生活還是到社會養老機構生活是區分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最直接的標準。
2.方法和數據。本研究基于ordered logit模型,數據來源于2011年一項關于四川家庭發展問題的調查,調查在四川省8個區(縣)內分城鄉進行,以家庭住戶為基本單位,共發放問卷800份,其中城鎮和農村各400份。調查由家庭某位成員響應,調查內容既包括回答人本人的基本信息,也包括其他家庭成員(包括共同居住和未共同居住)的基本信息和有關的家庭整體情況。
3.影響變量。本文從作為控制變顯的個體基本特征、按“共居家庭”成員不同屬性分類所表示的家庭結構以及“不局限共居家庭”的代際交換三方面選擇可能的影響變量。個體基本特征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個體主要經濟來源、個體健康狀況。家庭范圍內的代際交換指父母一代與子女一代在經濟、家務和日常照料等方面非正式的相互幫助。家庭代際交換已經超越“撫養”和“贍養”,在我國家庭代際關系中,父母不但對自己的子女承擔撫育義務,幫助其成家立業,而且往往還要盡撫養他們子女(第三代)的義務,子女相應地對父母承擔有贍養的責任。本文分別從反映家庭代際交換基礎的老人與子女親疏程度以及家中老人在代際交換中的“付出”和“回報”角度,選擇可能影響行為人養老意愿的因素。
結果分析
采用maximum likelihood方法構建兩模型,模型一假設個體養老意愿僅受行為人基本特征影響;模型二假設個體養老意愿除受個體特征影響外,還受家庭結構和家庭代際交換的影響。兩模型分別借助逐步回歸方法和Likelihoodratio檢驗逐步選擇相關變量納入,最終得到擬合結果。家庭城鄉類型由于與其他變量相關性很強未進入模型。
1.個體特征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影響
若只考慮個體基本特征,行為人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以及主要經濟來源成為影響個體養老意愿的顯著因素。具體來說,年輕者較年長者更傾向于認同社會養老,男性比女性更認同社會養老,相對而言受教育年限長的個體更認同社會養老;作為整體,行為人主要經濟來源對個體養老意愿有明顯影響,其中家庭成員供養和勞動收入對個體養老意愿的影響顯著,且通過比較發現,主要靠家庭成員供養者(54.6%)相比勞動收入者(30.7%)更傾向于認同家庭養老。
由于年齡和性別所反映出的行為人自我生活照料能力和生活獨立性對行為人養老意愿影響明顯,具有相對更高自我生活照料能力和生活獨立性的個體更易于適應到社會養老機構居住生活,因而更傾向于認同社會養老。受教育年限反映行為人的人力資本,它在對養老意愿產生影響時,主要通過幫助行為人比較兩種養老方式,使行為人對社會養老這一與傳統家庭養老有顯著差異的相對新穎的養老方式有更清晰和全面的認識和理解。主要經濟來源出自其他家庭成員則反映了行為人對家庭的依賴情況,即使這種依賴未必一定是經濟上的,對家庭依賴越重的人認同社會養老的可能性越小。
2.個體特征、家庭結構、代際交換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影響
當將家庭結構和家庭代際交換納入模型,行為人性別和主要經濟來源、“共居家庭”中60歲及以上成員比重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成員比重、“不局限共居家庭”中老人和子女見面的頻率以及老人幫忙隔代照料的頻率成為影響個體養老意愿的顯著因素。加入家庭因素后總體上個體特征影響減弱,部分反映個體特征的變量未進入模型。
個人特征方面,男性比女性更認同社會養老,行為人主要經濟來源整體上對養老意愿有顯著影響,各類收入者都傾向于認同家庭養老。
家庭結構方面,家庭中老人占比越高,行為人越傾向于家庭養老;家庭中較高文化程度成員比重越高,行為人越傾向于認同社會養老。與個人受教育年限的作用類似,家中較高文化程度成員比重影響個體養老意愿,主要為行為人提供了更全面和深刻理解社會養老的環境,有助于提高行為人對這種養老方式的認同程度。家中老人比重與個體對家庭養老的認同呈正向關系,因此從家庭人均供養資源分配的角度分析行為人養老意愿與家庭中老人比重之間的關系就無法得到支持。可能的解釋是,由于本文所指養老意愿未考慮養老的經濟支持而只從居住方式的選擇入手,因此更多反映經濟屬性的供養資源解釋未發揮主要作用;相反,無論出于生活習慣還是情感需要,家中老人比重大這一既成事實會強化行為人對老人在家居住的認同程度,進而反向作用于對社會養老的認同。
代際交換方面,家庭中老人和子女之間關系越疏遠,行為人越傾向于認同社會養老;代際交換中老人的“付出”越少,行為人越傾向于社會養老。可見,無論是老人與子女之間關系緊密(老人和子女見面頻率高)還是代際交換中老人的“付出”多(老人幫忙隔代照料頻繁),即使這僅發生在行為人“不局限共居家庭”中而不是自己身上,它都可能直接影響或通過“示范”的方式使行為人產生相應預期進而間接影響行為人的主觀養老意愿。行為人能夠從家庭代際交換中感受到家庭對老年人的需要(如幫忙隔代照顧孫子女),或因這種存在的與子女之間的緊密關系以及與孫子女之間的感情,而從情感上產生對在家庭生活的向往,最終更傾向于家庭居住的老年生活安排。
3.家庭結構和代際交換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作用
無論是否考慮家庭因素的影響,在同等條件下男性都較女性更傾向于認同社會養老。將個體因素、“共居家庭”結構以及“不局限共居家庭”代際交換因素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影響進行比較發現:其一,家庭結構和代際交換也對個體養老意愿有明顯的影響,且相比“小家庭”的結構,“大家庭”中代際交換的影響更明顯。就單位變化而言,家庭代際交換對行為人傾向于社會養老odds變化比例的影響明顯高于個人因素和家庭結構因素。盡管因素單位存在差異,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比具有客觀性質的個人特征和家庭結構因素,具有主觀性質的家庭代際交換的改變對行為人養老意愿變化的作用可能更為明顯。其二,用以反映家庭代際交換的變量中,老人與子女關系的親疏程度以及老人的“付出”都表現出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顯著影響,而無論是精神關懷(未選入模型)還是生活照料(不顯著),老人所得“回報”的影響都未得到體現。
基于上述分析,關于家庭結構和代際交換對行為人養老意愿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可嘗試作如下推斷:家庭代際交換是一種互惠行為,雖然作為社會支持的一個層面,互惠影響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顧關系,但相比“回報”而言,“付出”可能對行為人養老意愿具有更大的作用。而且,無論是孫子女被隔代照料的客觀需要還是從與子女及孫輩的關系考慮,家中老人這種滿足家庭需要的責任感和因情感需要而對家庭生活的向往,在影響行為人養老居住方式的選擇時,比其他諸如個體性別、主要收入來源、家庭結構以及老人可能受到的生活照料和精神關懷等客觀因素發揮的作用更加直接和重要。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摘自《人口學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