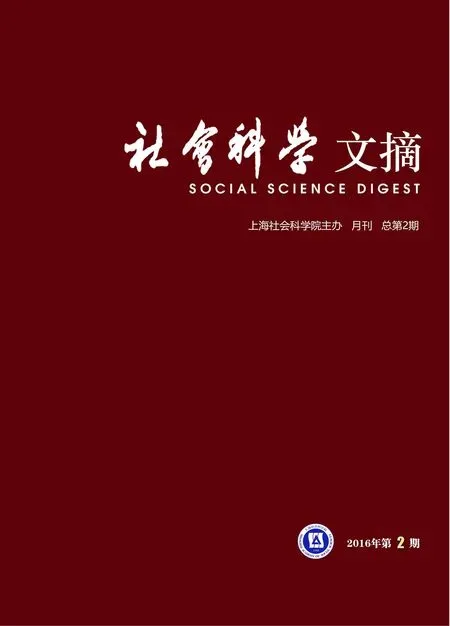中國憲法教義學的時代回應:方法綜合與交叉學科的可能性
文/李忠夏
中國憲法教義學的時代回應:方法綜合與交叉學科的可能性
文/李忠夏
傳統憲法教義學主要定位于三方面的工作:法律概念的邏輯建構,法律體系的形成,以及將案件事實涵攝至法律概念之下的法律適用和司法裁判工作。阿列克西因此將法教義學的工作總結為經驗(現行實證法和相關司法裁判的描述)、分析(概念加工和法律體系的形成)與規范(法律適用)這三重維度。在傳統法教義學所建構的工作流程中,并不存在偶因性,然而在社會系統功能分化的背景下,法教義學的工作也相應發生調整,具體到憲法教義學,則是通過憲法變遷來界定憲法文本“意義理解之可能性的各種條件”,在多種可能性之間選擇最為適當的憲法決定。這一轉變也促成了憲法學方法論的轉型,并有助于解決目前在法學方法論討論中所存在的幾點爭議和困惑:是否存在獨特的、專屬的法教義學方法?事實與規范的方法論二元主義是否仍然適用?“價值判斷”難題如何解決?
中國憲法教義學陷入封閉與開放的糾結當中
迄今為止,中國的憲法教義學存在兩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是憲法教義學能否通過概念和文本解釋來適應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急劇轉型,如果脫離社會的大環境和政治背景,能否真正理解中國的憲法;二是憲法教義學能否解決終極的價值判斷難題。正是這兩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導致了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爭論。
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沖突是中國的本土性遭遇現代性之后所衍生的問題。中國自晚清和辛亥革命以來,就開始接受現代性的移植,從帝制向民主制的轉型,這意味著社會習俗、文化觀念、政治方式、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的變革,而變革就意味著產生陣痛,改革開放以來產生的民間習慣與制定法之間的沖突仍然是這種變革的延續。對于此種轉型,社科法學者認為應該拋棄文本的束縛,在規范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中,應強調“實效性”,側重效率分析、實證調研、政治決定等元素。
對于中國的社會轉型,法教義學者看到的畫面卻是截然相反的。在法教義學眼中,轉型社會最大的問題恰恰是制定法權威的流失。因社會變遷快,法律的制定無法跟上社會轉型的步伐,或者無法適應社會變遷的節奏而失效,其結果便是改革中存在大量規避法律甚至直接違法和違憲的情況,從而形成改革與法治之間的內在張力,這一情況直到今天仍繼續存在。在法教義學看來,固守實證法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這是近代法治的應有之義,并不需過多爭論,需要爭論的只是法律應如何解釋和適用的問題。因此,法教義學對現實中比比皆是的違法現象和社科法學者通過學術將現實包裝為規范的做法感到擔憂。在這種情況下,法教義學為了維護制定法的權威,不遺余力地通過概念提煉、法條解釋、體系建構等方式確保法的規范效力,強調實證法作為規范體系的重要性,并不遺余力地強調憲法解釋方法的重要性。
上述因素導致在中國目前關于法學方法的討論中,存在兩種各執一端的觀點。一種觀點堅持認為法學有其自身賴以安身立命的方法。林來梵將法學固有的思考方法定位于“規范法學的方法”。張翔認為任何一個學科均應有其自身的“紀律”和“方法”,否則該學科便失去獨立存在的意義,教義學便是法學的“紀律”“根本”,并要求法學恪守新康德主義的方法論二元主義(事實與規范的嚴格界分),避免“方法論上的雜糅主義”,形成一種“形式法治觀”。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法學屬于社會科學,故應將“社科法學”的方法植入法學當中,由此超越法學的“法條主義”邏輯。
在上述不同的方法取向之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憲法教義學者的糾結和困惑:既想使法教義學保持一種開放性,使憲法學能夠“圍繞規范”得以建構,但是又不想犧牲法學之根本,從而仍然恪守“方法論的二元主義”以及“形式法治”的立場;既想使法教義學容納價值判斷,但是又無法通過純粹的法學方法獲得終極理性的價值判斷。為了避免使法教義學這一法律人自身陣營的淪陷,有學者甚至以一種清教徒般的方式對法教義學進行了畫地為牢的嚴格界定。這也使得今天的中國憲法教義學者對憲法學自身規范屬性、法度、紀律和方法的強調有一種執念,反而未能深刻反思法教義學因時代變遷而出現的轉向,憲法在現代多元主義和功能分化社會中的功能及其與一般法律的區別,從而無法深刻反思憲法教義學所具有的特殊性,陷入封閉與開放的糾結當中,無法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兩全其美的路徑。
憲法學須回應30余年來的急劇社會轉型
法教義學的概念和體系建構工作對于維系法的安定性而言固然重要,但如果對于傳統法教義學的路徑過于執著,則可能會使憲法學無法更好回應中國這30余年以來的急劇社會轉型。于是,在這兩種觀點之間可以看到法律人進行折衷的樸素嘗試,也可以看到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趨近。
現實情況是,當凱爾森所言的法政治(法律解釋和價值判斷)成為法學最為核心的工作時,法學中的“方法論二元主義”就已經被打破了,由此就需要跳出新康德主義、尤其凱爾森從認識論角度對“規范性”的純粹性理解。法學在確定“合法又非法”的過程中,并沒有拘泥于一種“唯一正確”的方法。所謂“規范性”或“規范分析的方法”,只是在強調法律的規范屬性,比如盧曼就將規范性僅界定為“對失望情形的抵抗”,而剝離了自自然法以來規范性所包含的理性、正確性和科學性。新康德主義西南德意志學派將法規范視為與價值關涉的現實,雖然仍然堅持“方法論二元主義”的立場,但法規范并非是純粹的、超驗的價值規范,也不是純粹的價值無涉的事實,而是與價值關聯的現實,實際已經開始承認法規范所具有的價值與事實相結合的特點。羅文斯坦與德國學者穆勒也一致認為,如果跳出新康德主義對規范性的理解,則可以將規范性視為與現實經驗相契合的規范內容,前者從超驗形式角度理解規范性,后者從規范內容角度理解規范性。
但規范與事實的融合并不意味著規范是簡單從事實中推導出來的,“方法論二元主義”的打破并不意味著法學在方法論的路途中可以走得這么遠。有許多案例都可表明,看似是從事實推導出來的規范,實際上都包含了主觀的“價值判斷”,只是該價值判斷最終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事實或后果。在一些后果定向的規范解釋中,同樣涉及對后果的價值評估,比如因為“核電站”產生的風險而禁止核電站,本身就是對“核電站”風險到底會對人的健康產生何種損害這一事實進行調查并對其嚴重性進行評估的結果。后果本身是一種“是/非”的事實判斷,要轉換成“好/壞”的價值判斷就仍然需要一個價值設定。一個完整的表述是:價值判斷的作出有時要依賴事實的調查,但事實又需要評估,這又需要回到一個特定情勢下的價值預設,從而形成了事實與價值(規范)之間的循環。
中國法學方法論中存在的爭論表明,“將教義與現實簡單對立起來的做法自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沒有任何解釋是完全沒有現實性的,同樣,沒有任何現實是完全沒有經過解釋加工的。方法上的分離撐開了多樣化的理解視域,并劃分了學科,也就是整個思維世界,同時要求研究者進行單一的歸類決定:他必須申明其所運用的方法,并固守在特定基本概念的關聯系統上,否則,他就既不能獲得明晰性也不能被理解”。這一現象自然需要糾正。在建構中國憲法教義學時,就須在社會系統功能分化的新范式下,在保證“適度的社會復雜性”和回應環境變化的功能下,實現教義與現實、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甚至政治憲法學與規范憲法學之間的溝通與對話,在教義學中實現方法的多元與綜合。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為憲法教義學尋找新的定位點和理論基礎,并找到憲法教義學保持其開放性、圍繞規范以及實現方法綜合的具體道路。
綜合而言,上文所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并非“水火不容”,但需要為其找到一個恰當的結合點,這就需要對現代社會的特征和法教義學的轉向有清醒的認識,并在方法論層面為之找到社會理論的基礎和恰當的溝通合作渠道,否則就會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在中國面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憲法如果要真正發揮其在現代功能分化社會中的作用,就需要介于“技”與“藝”之間的、scientia和prudentia并存的憲法教義學:一方面,憲法教義學是一種知識體系,需要借助于學術上而不僅僅實證法上的概念體系,將繁雜的實證法規范、相關的憲法決定結合成為一個邏輯融貫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憲法教義學同樣也包含了價值判斷,需要通過“抽象化”的概念形成,將多重選擇的可能性涵括在內,而且從“可能性邊界”的范圍中作出選擇,考量相關決定的后果等事實性因素,作出“最優的決定”,比如討論國企改制等問題時就不能不考慮改制之后的“效率”問題。此時,就不能僅僅主張單純的規范分析方法,而是需要“圍繞規范”,在不同的問題領域,綜合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說,在將環境的信息轉換進法律系統時,就涉及“方法論上的綜合主義”。在今天社會功能分化的語境下,憲法學方法論一方面應堅持形式化的體系建構;另一方面需要突破傳統方法束縛,在關注憲法文本的前提下,容納多元的方法。正如拉倫茨所主張的,“教義學”一詞在今天意味著:認識程序受到此框架內不可再質疑的法律規定的約束,只有當對法律的研究獨立于實證法而存在時,才不適用于“教義學”一詞。
(作者系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摘自《法學研究》2015年第6期;原題為《憲法教義學反思:一個社會系統理論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