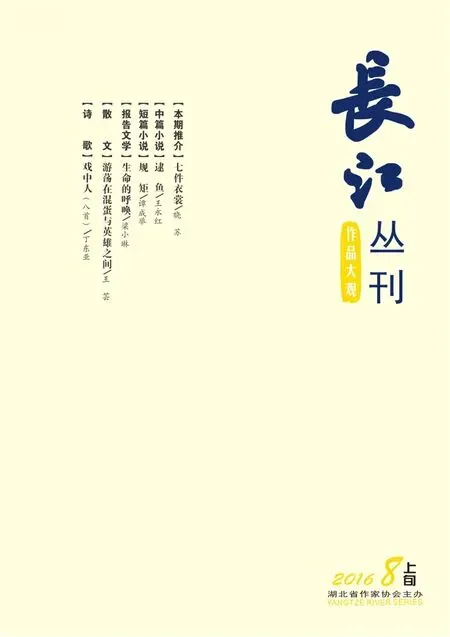母 親(外一篇)
黃 海
母親(外一篇)
黃海
近幾天老是夢到母親,醒來時想起清明節又快到了,我將偕老婆孩兒,回老家金口街南岸村的義山給母親掃墓。屈指一算,母親已經離開我們35周年了,她的音容笑貌還時常浮現在我眼前,她的品德永遠銘刻在我心里。
一
母親1932年農歷9月11亥時出生,屬猴,名叫周菊香。1979年農歷十一月初三,她47歲生日的第二天,因長期患病不治身亡。她生命短暫,如流星一閃,但她所經歷的苦難、辛勞和病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我外公兄弟八人,外公排行老幺,人稱周滿爹。
母親只有兄妹兩人,兄長叫周大健,大母親二三歲。外公是大革命時期的地下黨員,在母親2歲多時,被人暗殺于銅官一小商鋪的樓上,鮮血流到樓下才被人發現。白色恐怖時期,革命處于低潮,兇手難找,家仇難報,只好由朋友們湊了點錢,將外公安葬在銅官旁的袁家山。
外公犧牲后,外婆投靠在漢口謀生的親姐姐,到京漢路一帶給人做保姆。接觸到在武漢做石匠的老鄉,也是望城哈山灣的張一爹,兩人組成家庭相依為命。但外婆因患痢疾回到望城哈山灣,很快病逝。病逝前,舅舅周大健去探視,結果受到傳染,不久也離開人世,去世時不到10歲,母親住在南竹山四伯家,故而留下了一條命,留下了外公這位革命先烈的唯一后人。
我的祖籍地望城丁字灣是全國最好的花崗巖石產地,我們鄉里人叫做“出麻石的地方”。鄉里人靠山吃山,所以學石匠的人很多,我的祖父黃漢清就是其中之一,他參加過漢口江漢關和南京中山陵的建設,同老鄰居張一爹共事。我母親有時由外婆帶到武漢玩,母親長得很可愛,也很活潑,祖父經常逗她開心,叫她唱歌就唱歌,叫她跳舞就跳舞,所以很喜歡她。過去農村有“指腹為婚”和收“童養媳”的風俗,于是兩個大人商量,將母親許配給我父親。
祖父壽命也不高,只有四十歲左右就去世了,死在一個叫小柏州的地方的一個廟里。大伯祖父和幺祖父駕船在洞庭湖上走了一個月左右才將他的遺體運回望城丁字灣。當父親到碼頭去接時,木棺底部滲出烏黑的血水。祖父去世一個多月,而遺體在回家見到兒子時卻能流出血水,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父親一直覺得血緣親情是個難解的迷。
祖父去世時,祖母只有35歲,父親10歲,母親7歲。祖母叫母親過來叩個頭,算是對去世的祖父定下的這門親事的一個確認,這是父母的第一次見面,爾后兩年,父母之間來來往往,母親就被祖母當作“童養媳”收養過來。
二
當時,祖母帶著年幼的父親、姑姑過日子,生活已很艱難,多了母親一張嘴更是困難,完全靠討飯度日。雖然祖父有兄弟八人,但除老四、老五、老六外,其余兄弟均已成家單過,而五叔爹信佛吃齋,六叔爹打鐵喝酒是個酒麻木,只有四叔爹在湖北種田。他們都成了泥菩薩過江,哪里還能照顧到祖母這孤兒寡母的一家。
正在山窮水盡之際,在湖北金口開荒種田的四叔爹捎信回去,說兄弟們可以下湖北來,開荒種田填飽肚子。大伯爹召集幾兄弟商量,確定由我祖母帶父親、母親、姑姑下來,也可能看四叔爹尚未娶親,更沒有后人,有由四叔爹將這個門戶頂起來的意思。
1942年,祖母帶著兒子、媳婦、女兒,帶著熟人寫的路條開始了下湖北的行程。當時交通不便,也沒有錢搭車,還有日本人的橫行霸道,因此他們只好邊討飯邊往湖北走,一路上經歷的苦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白天行走,不僅肚子餓,而且口也干,看到牛腳眼里有點黃水,又不敢喝,晚上經常躲在人家的屋檐下過夜。有次看到一隊日本人從遠處過來,趕忙躲到蘆葦蕩里,讓水淹沒到頸部,日本人看到了,可憐他們,做手勢叫他們出來,他們哪里敢出來,只有看日本人走遠后,他們才舒了口氣,趕忙從齊頸的水里爬上岸來。祖母看靠討飯很難養活這一家人,就將母親送給一富戶人家,換了一點盤纏。母親大聲哭喊,祖母走了很遠還聽到她的哭聲,就停下腳來,她想:這孩子已當媳婦接過來了,家里這樣窮,要是將她給了人,那自己的兒子將來找不到媳婦又怎么辦?于是她又轉去,將錢退給那戶人家,要回了母親。
這樣一家四口,經過二個多月的風雨兼程,終于來到了金口地區的蓮湖墩,也就是四叔爹種田的地方。誰料屋漏又遭連夜雨,四叔爹在不久前因突發急病已離開人世。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他們僅有的一線希望也破滅了。年幼的父親和母親挑起了這個家庭的重擔,他們在四叔爹結拜的盟兄弟的幫助下,在蓮湖墩搭了個草棚子落腳,父親給地主家打長工,舂米放牛樣樣干。母親和姑姑黃淑貞幫人栽田割谷打短工,挖藕砍柴補貼家用。祖母則將四叔爹借給別人的糧食能收的收些回來,湊合著過日子,這樣直到解放。
三
1951年,土改工作隊進村,號召貧雇農起來翻身鬧革命。父母親都是貧苦農民出身,于是積極參加運動,成為骨干分子。他們于當年就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并當選為南岸鄉農協委員,父親于1952年11月30日由武昌縣第十區(即法泗區)區委領導董定楨、馬云嵐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母親則同周云清等一起發動婦女參加土改運動,1953年父親擔任南岸鄉團支部書記,主要負責土改復查、統購統銷等工作。期間,母親曾到武昌參加共青團湖北省代表大會。1954年,母親帶頭辦起了一個長年互助組,父親任組長。當年長江居字號堤段潰堤,受災后搬到土地堂任子弟那個地方避災。1955年回到家鄉南岸鄉從事生產自救重建家園工作。1956年冬季開始,參加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工作,直到1962年。
這期間,母親已生養四個小孩,但第一個和第二個由于疾病夭折,1956年出生的大姐黃漢枝和1958年出生的二姐黃漢球相對來說身體較好,祖母看已有了兩個孫女,便想要一個孫兒,于是給小姐姐取了“求伢子”這樣一個男兒的名字,希望求來一個男伢子。果然就求來了。1962年我來到了這個世界上,全家人高興不已,本家的一位算命先生說,這伢命大,有縣官級別,你家魚大塘小,要小心哺養。父親支付了2元錢的算命錢,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開支。1966年父母又生育了小妹黃紅。
由于兒時的苦難和養育兒女的辛勞,母親的身體從懷我開始就虛弱起來,我出生后,母親就一直生病,從未間斷,先是支氣管炎,肺結核,后來發展到心膜炎、肺氣腫、腎炎。直到1978年,她在病床上煎熬了十多年之后,終于油干燈熄。
母親的這些病在當今都不是不治之癥,但當時醫療條件有限,從小我稚嫩的肩膀就同父親一起用自制的土轎子抬著母親到咸寧,到金口等地看病,但都沒什么效果。加上家大口闊,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生活十分艱難,經常是吃了上頓愁下頓,有時連柴米油鹽都要找人家借。三間茅草屋一間祖母單住,一間是堂屋客廳,剩下一間隔成兩間廂房,一間做廚房,一間做臥室,而且隔墻只隔了一半,每次廚房燒火,炊煙就彌漫到臥房里,不僅將蚊帳等熏成“牛肉筋”,而且將躺在床上的母親熏得咳痰不止,病情加重。
雖然生活艱苦,疾病纏身,但母親仍保持樂觀豁達的胸懷,她把苦痛埋在心底,臉上總是洋溢著微微的笑容。母親總是克己待人,不論是工作組的同志到我家吃飯,還是鄉鄰到我家,找在村里當干部的父親反映和解決問題,母親都熱情接待,生怕怠慢了人家,只要有一點好吃的東西,都要拿出來與人共享,因此,人們親切地稱她為“菊姐”。
那些年想吃點肉非常困難,只有逢年過節隊里才殺豬給每戶分點肉。我是農歷5 月26日出生的,母親每年五月端午節,就將隊里分的幾斤肉留下一大塊,抹點酒擦點鹽,裝進抹得干凈的壇子里,蓋上蓋,在壇銜里灌上水密封起來,到我生日這天,將充滿著酒香的肉塊拿出來切好,再將在菜園里采摘來的新鮮青椒炒上一盤,作為我的生日大餐。母親憐憫我個頭小,身體差,干農活不行,總希望我多讀點書離開農村。1978年我高考落榜后,她去大城中學找校長想要我復讀再考,校長說你兒子嚴重跛腿,數理化不行,復讀也難考上。她悻悻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淚,1979年夏季征兵,我報名應征,身體檢查合格,但由于想當兵的人多,我這個沒有關系和后臺的人就自然落選了。母親非常氣憤,但也非常無奈,只好勸我說:“兒啊,你是媽的獨子,就算組織同意你去當兵,媽也舍不得你去。”
母親臨終的那天晚上,我們姊妹圍坐在她的床前,她反復地鼓勵我們,你們不要怕,你們長大了,日子就會好起來的……就在“不要怕,不要怕”的囑托聲中,母親閉上了眼睛。
故鄉的柳樹
我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的一個村莊。童年和少年時代,故鄉的堤埂上、大路邊、農戶的庭院里,集體的空地上,到處都種著柳樹。
柳樹樹形高大,樹干粗壯。每年立春過后,它們就在料峭的寒風中吐出淡黃色的細長嫩芽,一條條嫩黃的細枝微微的彎曲著,毛茸茸的金黃色就像一縷縷的金絲。經過幾場春雨,柔軟枝條上的嫩芽便伸展成細長的葉子,生長在纖細的枝條上,悠長地下垂著,好像一條條柔長的絲絳,在春風細雨中婆娑飄蕩,舞動著煙雨朦朧的水鄉江南。到了暮春時節,那滿樹的綠葉里飛出白色絲狀的柳絮,飄到地上鋪成薄薄的一層,猶如天上下了一場春雪,非常壯觀。
柳樹來源簡單,在老樹上砍下新枝,隨意栽插都可以成活長大,它耐漬耐旱,生命力強,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處處成蔭,所以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我故鄉前后左右四面環水,只有一條小路跟外面相連。房前屋后兩大片曠場及四周小渠旁種的全是柳樹。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經濟困難和物質匱乏的時期,這四處栽種的柳樹就成了我們全家的經濟支撐和精神寄托。家里的每一件器物都是柳樹做的,家里的每一個人都與柳樹有不解的情緣。父親是家里的頂梁柱,他用自己栽種的成材的柳樹干作為梁柱,用樹枝隔出墻壁,再把塘泥糊上去,搭建出冬暖夏涼的住房;他還用剽學來的木匠手藝,做出床鋪和桌椅板凳以及犁、耙等農具,所以家里的生活和生產用具從來沒有花錢去市場買過。有一次,家里兩天揭不開鍋了,大家都絕望地看著父親。父親圍著房屋一轉,急中生智,想起了柳樹。他帶領我們將樹上粗壯的枝杈砍下來,足足有幾大梱,裝在手推車上,他和我一個在前面拉繩,一個在后邊推車,拖到離家十來里地的長江邊上的一個廠子里去賣。父親沾著口水,數著那能夠幫全家度過難關的幾元錢,捶打著酸疼的腰背,然后抹一把額頭的汗水,長滿皺紋的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我的眼窩里也盈滿了淚水。母親是個心細手巧的女人,家里沒柴燒,她將父親砍下的柳樹的枝葉曬干,將父親挖出來的樹蔸和樹根曬干,用來燒火做飯。她用柳樹那柔軟的枝條編成各式各樣的精美的用品。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到夕陽下母親坐在院子里將柳條去皮編織柳籃柳筐等用品時,那雙靈巧的手上下翻飛,每每出神。母親還將柳樹的嫩芽采摘下來,曬干后當作茶葉泡水喝,每次她用開水沖泡時,那股柳芽的清香氣味,真是迷人。姐姐要出嫁了,沒有錢買嫁妝,父親想起了姐姐出生時為她栽下的那棵柳樹,現在已是有22個年輪的大樹了。他請來木匠,砍倒大樹,曬干后做成了箱子、柜子和梳妝臺等家俱,然后刷上鮮紅的油漆。出嫁那天,姐姐紅撲撲的臉映襯著紅彤彤的嫁妝,是我見到的姐姐最美的時刻,也引來了村塆里那些頭戴柳枝編成花環的姑娘姐妹們羨慕的眼光。而我是個酷愛音樂的小男孩,家里沒有錢到街上去買二胡和笛子這些最初級的樂器,就抽空那圓潤的枝條,在那層鮮嫩的樹皮上釘一排小孔做成柳笛,鼓著腮幫興奮地吹奏出美妙的樂曲……
現在,我已人到中年,在喧鬧的城市里工作。周末休閑遠足,總少不了到江邊湖畔走走。看到湖上煙波浩渺,遠近的大小建筑上綠瓦紅墻在陽光的照射下閃爍著五顏六色的光芒,在江邊湖岸上,一排排的垂柳婆娑地垂下萬條絲絳,一對對情人在垂柳下悠閑地談情說愛,一陣陣清風吹來,使人心曠神怡。這里折射著時代的光和影,反映了社會的發展和變遷!
然而,母親早已作古,姐姐也為人妻人母。但我始終放心不下的是年邁的父親。父親不習慣跟我們到城里生活,仍在故鄉那個空曠的院子里住著,只是房子已改建成三層小樓,房前屋后及四周的空場上也種上了多種花卉以及樟樹桂花樹,仿佛一個小花園,當年的柳樹早已不見蹤跡。我每次回家,陪父親聊天時,總會講些宅子里的花卉是如何的鮮艷,苗木是如何的蔥蘢,講起外面世界的變化。然而父親總是深思半晌才說,外面再好不如家里好。院子里的花卉苗木再多,還是比不得當年院子里的柳樹。
哦,柳樹!幫我們度過艱難歲月的柳樹,故鄉的生命樹,恩人樹,柳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