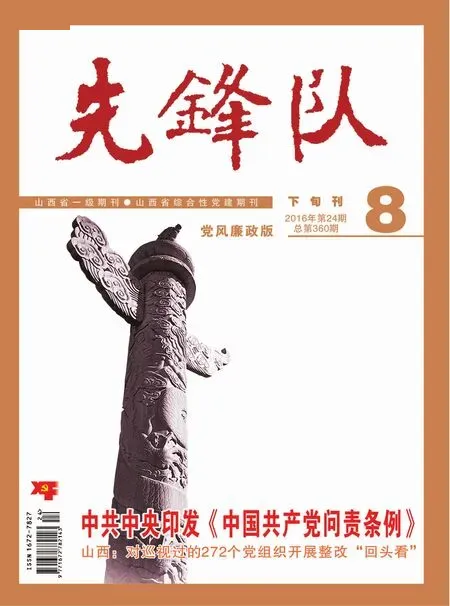問責條例的三大看點
■ 曾亞波
問責條例的三大看點
■ 曾亞波
正當全黨開展“兩學一做”活動之際,一部全新的黨內法規《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世了。問責條例來得很及時,而且亮點很多,對黨員干部來說,深入領會條例精神不僅非常必要,而且很迫切。
——從時間節點上看,緊鑼密鼓,不耽誤片刻
沒有選在重大節日,甚至也沒有選在建黨95周年這樣的日子,問責條例的施行,讓人倍感中央從嚴治黨的緊迫性。
問責條例的出臺本身就是因時而生,是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提出的要求,更是從嚴治黨的必然。2015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在中央政治局獲得通過后,根據黨中央部署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中央紀委當即著手研究起草《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2016年1月,黨的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提出,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5月18日,經中央批準,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征求各地區各部門共180余家單位對條例的意見建議。
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別審議通過條例送審稿,并正式向全黨全社會公布。正當人們翹首以盼條例的真實面目時,7月17日晚上,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和新華社受權全文發布了問責條例。值得注意的是,問責條例并沒有像之前的廉潔自律準則和紀律處分條例一樣,規定在幾個月之后的新年伊始才正式施行,而是在向社會公布的前十天即2016年7月8日就正式施行了。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具有標志性、關鍵性、引領性的法規制度陸續出臺,問責條例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必將在從嚴治黨的征途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從條例內容來看,務實可行,不貪多求大
問責條例只有13條,切口很小,僅限于發生問題后的問責,彌補了此前種種黨內法規的不足。問責條例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從指導思想和問責工作原則,到對問責“負面清單”的列舉、問責方式的確定,都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巡視工作和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所踐行的成果。
與紀律處分條例一致,問責條例也是堅持問題導向,但它把握的目標更小:主要是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它并不貪大求全,也不羅列無法定性或落實的條文,更加突出重點,注重實效。問責所要實現的目標很明確,行文簡潔而凝練,措施務實且管用,并且會根據新發生、新出現的問題適時作出新的解釋和補充,因而是一部與時俱進的新黨規。
——從法規間關系看,銜接補充,不交叉重復
有的同志認為,黨的紀律處分條例已經是最好的問責方式了,既有對黨組織的處理,也有大量條文規定了對黨員違犯黨紀的處理,為何還要出臺問責條例呢?是不是重復規定呢?
從法規關系看,廉潔自律準則是正面倡導,重在立德,是給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豎起一個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黨的紀律處分條例是圍繞黨紀戒尺要求,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劃出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但“負面清單”是不可能全面列出的,黨的紀律處分條例側重對違犯紀律的處理,黨的問責條例則側重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責任擔當的衡量。責任擔當并不能在紀律處理中都得到體現,尤其是不作為、亂作為以及應當承擔黨內責任而未盡到責任的組織和個人,以黨的紀律處分條例尚無法追究責任。非直接違紀,也可能被問責,這是比紀律“底線”更嚴格的“紅線”,將使黨員干部更加珍重自己的黨員身份,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在黨內政治生活和具體工作中更加積極主動作為,而不是坐等問題發生或對問題坐視不管。與紀律處分條例相比,問責條例十分精簡,因為它強調的是責任的分清和落實,并且紀律處分本身也是問責的方式之一,涉及如何給予紀律處分的內容并不重復。
從法規條文的關聯看,兩個條例的關聯度更高,但側重點不同。譬如,黨的紀律處分條例第八條規定了對嚴重違犯黨紀的黨組織的紀律處理措施:改組和解散。而問責條例第七條也同樣規定了“改組”這樣一種問責方式,定義也是一樣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但是,紀律處分條例在第十四條增加了對“受到改組處理的黨組織領導機構成員”個人處理的規定,即“除應當受到撤銷黨內職務以上(含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的外,均自然免職。”是交代了改組之后組織成員的自然歸屬,并未直接對組織成員作出處理。而問責條例則在“改組”之前,規定了“檢查”和“通報”兩項問責措施,側重的是對黨組織的問責處理。對黨組織改組后,黨的領導干部的處理,則是一個單獨的部分,方式有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和紀律處分。問責條例特別規定:“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就是說,不是說黨組織改組了,其領導成員就沒事了,根據情況會“單獨”處理或并行處理。
紀律是可見的,而責任是無形的。從遵紀到盡責,這是一個新的提升。問責條例在很多方面也具有獨創性和獨立性,在落實管黨治黨、治國理政重任方面,在維護黨紀執行等多個方面,凡是落實不力的,都只能適用黨的問責條例,而無法適用其他黨紀黨規。
(責編:許樹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