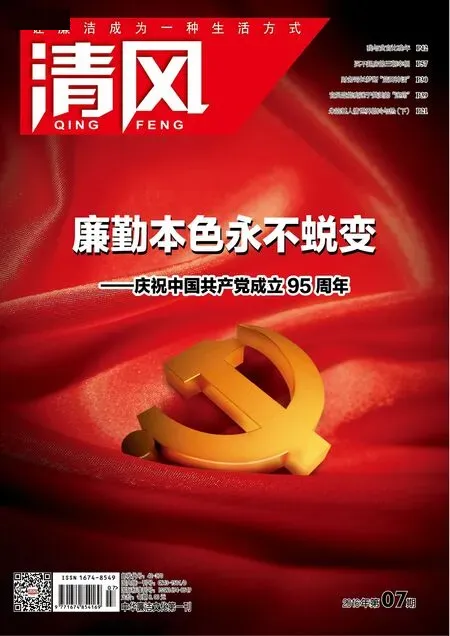一人貪腐,禍害全家
文_沈淦(發自江蘇南通)
一人貪腐,禍害全家
文_沈淦(發自江蘇南通)
元載是鳳翔岐山(今陜西岐山)人,出身可不大“高貴”。《新唐書》里說其父姓景名昇,一個姓元的王妃有田在岐山,景昇因替其管理租稅等頗有功勞,便請求王妃“冒為元氏”。《舊唐書》里更說“載母攜載適景昇”,如此看來,元載真正的父親究竟是誰,簡直已無從查考了。而景昇又“不理產業”,終于導致“家貧”。
元載之妻王蘊秀可就不同了,新、舊《唐書》與《資治通鑒》中都說她是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節度使的名將王忠嗣的女兒。元載年輕的時候多次應過鄉試,不過都沒能考上。但奇怪的是,這個困窘潦倒的窮書生竟被王蘊秀的父親看中了,并將女兒嫁給了他。
這對夫婦的故事,前期可謂勵志,然而得志之后,他們卻日益驕縱,忘記了原則底線,終于落得慘淡收場,其中的教訓,今人不可不察。
書生逆襲
元載大概是招贅進了王家,時間一長,漸漸地受到冷落。王家的人起先對他還只是偶爾冷嘲熱諷,到后來竟惡聲相向、視同奴仆了,尤其是王家那些姊妹們,更是“以載夫婦皆乞兒,厭薄之甚”。在這種情況下,蘊秀勸丈夫道:“何不繼續學習呢?奴家積蓄了一些妝奩首飾,可以全部拿出來,讓你作為購買紙墨的費用。”
于是,夫婦倆攜手來到京城。其時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年間,玄宗皇帝崇奉道教,下詔求取精通《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四家學說的學者。老、莊是道家的代表,恰巧元載對道家典籍尤為精通,于是,他應詔撰寫的策論文章便被列入“高科”,由此而授職為邠州新平縣尉,從此步入了仕途。
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避入西蜀,其子唐肅宗李亨即位后,元載由于“智性敏悟,善奏對”,深受肅宗器重,被提拔為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管理國家財政;又由于元載結交了權傾朝野的大宦官李輔國,不久即入閣拜相——升任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后十多年,他的官位雖然也有些變動,如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等,宰相的職位卻一直沒有變。
唐肅宗死后,其子代宗李豫即位,不久便派人刺殺了驕橫專權的李輔國,元載也參與其中出了一些力。后來,另一個掌握軍權的宦官魚朝恩,不但與元載的關系不好,還“驕橫震天下”(《新唐書?元載傳》),嚴重地威脅了皇權。元載請求代宗除掉魚朝恩,代宗“畏有變”,遲遲不敢動手。元載便結交了魚朝恩的愛將作內助,終于成功地殺掉了魚朝恩。從那以后,他更加受到代宗的信任,“貴盛無比”。
于是,元載廣建樓臺亭閣,交游權貴,躊躇滿志,漸漸地學會了傲慢,一般的賓客往往被阻擋在相府門外,想見其一面而不可得。由于元載位高權重,王家的親屬們紛紛前來謁見并祝賀,蘊秀將他們都安置于閑院之中。忽然碰上一個大晴天,蘊秀于西院掛曬青紫絳帶,共四十條,每條長三十丈,下面又整整齊齊地排列著二十只金銀香爐,爐內焚著名貴異香,以薰絳帶。蘊秀則故意帶著諸多親戚到西院散步。有親戚不識絳帶為何物,詢問婢女,婢女們答道:“今天是我家相公與夫人在曝曬衣服啊。”蘊秀則對王家姊妹們說:“沒想到乞丐夫婦竟然還置辦了一點家私。不過,這都是些粗劣貨,你們可千萬別見笑啊。”諸姊妹們都很羞愧,沒幾天便都辭別而去。
蘊秀經常將衣服、器皿、首飾等分給外人,唯獨一絲一毫也不給骨肉姊妹。有長輩勸她幾句,她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實在是當年所受的羞辱太深太重,令人刻骨銘心、終生難忘啊!”
恃權驕縱
元載當上宰相后,隨著權勢的膨脹,貪欲也與日俱增。首先,由于皇帝的長期信任,他便飄飄然,目空一切地認為“文武才略莫己若”,滿朝文武大臣的“才略”,沒有一個能與自己相比!他恰恰忘了,自己之所以受到皇帝的長久信任,除了確實有才、有功,還有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在李輔國死后,又結交了——更準確點說,是用大量金錢收買了一個重要的宦官董秀,讓董秀專門刺探皇帝的真實想法并悄悄地告訴自己,因此元載在皇帝面前奏對議論“無不諧契”。
由于單憑主觀想象,率意而為,這位元丞相在文武百官奏章上的批示多有“謬舛”,簡直可以說是錯誤百出了,有關部門自然要給予駁斥,加以阻撓。元載便施展神通,從皇帝那兒請了一道圣旨:但凡六品以下官員的奏章等,宰相批示后,有關部門不必再復核了,直接照批示辦理吧。這樣一來,他才真正地權重一時了。
有了權,又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約,不以權謀私、不濫用職權才怪。元載將許多具體事務委托自己親信的兩個主管文書卓英倩與李代榮辦理,又縱容幾個兒子借自己的權勢收取賄賂。結果,無論京師要職還是地方大員,忠良正直之士都受到排擠與傾軋,貪鄙諂佞之徒則得到提拔與重用,以致凡是想在仕途上有所“長進”或者想辦成什么事情的,不去結交元家子弟,就要請托元之“秘書”。
且看元載的腐敗業績:首先看住房。元載在長安城中開有南北二甲第,室宇之宏偉壯麗,室內陳設之豪華奢糜,冠絕當時;近郊建有樓亭臺榭,而城南之“膏腴別墅,連疆接軫,凡數十所”,元載卻還不滿足,甚至欲借替朝廷營建中都之機擴建私宅。再看穿著及其余消費。元家的婢仆,身著綾羅綢緞的就有一百余人;域外進貢的奇珍異寶,大多匯集于元宰相的門下,名姝異樂,連皇宮中沒有的,元宰相家也一應俱全;其余資財貨物,不可勝計。據《資治通鑒》第二百二十五卷所載,元家被抄時,僅胡椒一項,就多達八百石。抄家前有人實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地上書揭發其罪行。元載得到消息后,玩弄權術,將這些人全都杖殺于衙署之中。從那以后,道路以目,再也沒人敢隨便議論“載之短”了。
慘淡收場
由于元載“權傾四海”而又日益驕縱,連唐代宗也看不下去了。新、舊《唐書》記載,由于元載是兩朝重臣,身居相位多年,又有除掉魚朝恩的大功,唐代宗開始時還想保全君臣之間的名分,曾借元載單獨晉見之際予以訓誡,然而元載卻不以為然。
賓客中也有人以詞賦諷勸,并告誡他長此以往將很危險,元載一度頗受觸動,甚至流下了眼淚。然而,要久嘗腐敗甜頭的人放棄既得利益,談何容易!元載始終“不能悟”,直到最后“眾怒上聞”,代宗才終于下了決心,下詔將他處死;那與元載聯系密切的宦官董秀及元載的兩個“秘書”卓英倩與李代榮,也一并被殺掉了;因與元載過從甚密而受到貶謫或治罪的官員“凡數十百人”。元載臨死的時候,還希望少受些痛苦,請求行刑官員道:“愿得快死!”行刑官員卻道:“相公必須稍微受些污辱,萬勿見怪!”說完,脫下骯臟的襪子,塞進其口中,然后“殺之”。
王蘊秀呢,新、舊《唐書》都說她“悍驕戾沓”“狠戾自專”“素以兇戾聞”;《舊唐書》還說她“縱其子伯和等為虐”,而這個元伯和又“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征求音樂為事”。結果,王蘊秀及元載的三個兒子元伯和、元仲武、元秀能都被處死了。除了這三個兒子,元載還有一個女兒,從小就到資敬寺出家為尼,法名真一。元載死后,她也被“沒入掖庭”。
而晚唐范攄所撰的《云溪友議》中,對王蘊秀的結局卻有著與正史不一樣的描寫:當元載受到處置時,她請一高姓丞相替她到皇帝面前委婉致辭謝罪。唐代宗知道她是一個才女,同意免其一死,令她進宮廷擔任一名女史官,記載宮中一些事務。當高丞相將這一消息轉告給她時,蘊秀嘆道:“我做了二十年節度使的女兒,當了十六年當朝宰相的妻子,誰能到宮廷之中去書寫那些長信昭陽之事呢?兩者相衡,還是一死為幸啊!”堅決不肯從命,在《云溪友議》中,含含糊糊地給了她兩種結局:“或曰上宥連罪,或云京兆笞而斃矣。”
不管是哪種記載,王蘊秀的最后結局都可謂不幸,然而,縱然再憐香惜玉,誰又能挽救她呢?她長期處于巨貪大蠹的腐敗窩中,猶如身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其本身也是個既得利益者,并且曾在腐敗窩中推波助瀾。何況,像王蘊秀這樣長期養尊處優而又個性鮮明的才女,一則不能入皇宮忍受他人吆來喝去,二則不屑卷入殘酷的宮廷斗爭,三則丈夫與三個兒子都被處死,一個女兒以“罪犯家屬”的身份而被沒入宮廷,家又被抄了,與娘家的關系又很僵。她孤零零地活在世上還有什么意思呢?
平心而論,元載夫婦固然可惡、可恨,有可死之罪。然而,元載不過是一介書生,如果有人可以“執箠以鞭笞之”,讓他悔過自新,他也不會養成大惡。反觀今天許多落馬的高官,不也是因為沒有了監督,肆意妄為,最后迷失了自我,滑向腐敗犯罪深淵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