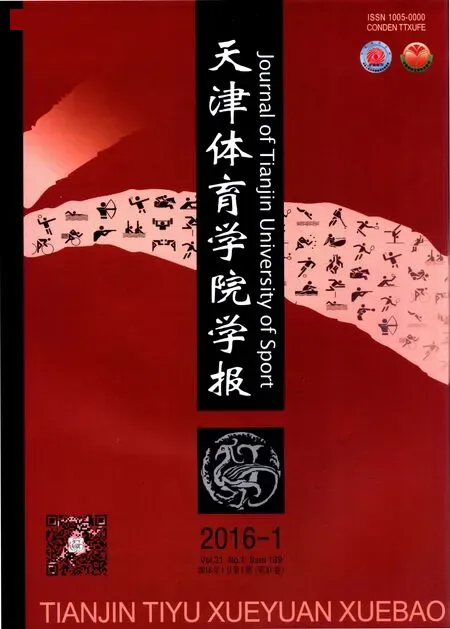由“武舞”至“拳種”:論歷史進程中傳統武術套路所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及其動因分析
武 超,呂韶鈞
?
由“武舞”至“拳種”:論歷史進程中傳統武術套路所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及其動因分析
武超1,呂韶鈞2
摘要武術套路是中國武術區別于世界其他武技的重要特征,是了解中國武術乃至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然而,長期以來,在已有史料史據基礎上,“形上學”的思維方式將我們的視野禁錮在起源學的領域加以推論,以至于我們今日仍無法合理解釋武術套路這一現象發生的根本機制。運用文獻史料、專家訪談以及邏輯演繹等研究方法,從發生學的理論視角闡析傳統武術套路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所呈現出的特征變化及其相關成因。結果認為:(1)傳統武術套路在歷史進程中,依次呈現出武舞→(打)套子→拳種3個階段性特征;在習練目的上,相應依次呈現為“練為戰”→“練為看”→“練為修”的目的變化;在技術特點上,相應依次表現出身體技術→身體藝術→身體文化的發展特點;在進階歸旨上相應依次歸類為武技階段→武藝階段→武學階段的發展趨勢。(2)在形成動因上,武舞的形成是由集體意志、個人動機以及意象思維等因素促成;(打)套子的形成是由社會、個人的雙向需要因素促成;拳種的形成是由武術套路自身發展的需要、地理環境的使然以及傳統思想文化的內化自覺等因素而促成。
關鍵詞傳統武術;套路;武舞;打套子;拳種;武藝;身體文化
From“Martial Arts”to“Boxing”:The Analysis of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Shown by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inthe Courseof History
WU Chao1,LV Shaojun2
(1.School of Graduate,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School of WUSHU,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Wushu routin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to distinguish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others in the world,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its thoughts and culture.However,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the thinking way of Metaphysics imprisons our horizon in the area of Origin to deduct for a long time,so that we still can’t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of Wushu routine reasonably until now.By using historical documents,expert interviews,logical deduct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ain the changes of characteristic and related causes which is show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genetics,we can find:1)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 shows three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urn,they are“Fighting Dance”→(play)cap→boxing;On the purpose of exercise,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are presented as“practice for fight?ing”→“practice for showing”→“practice for performing”;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kill,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ment are:body skill→body art→body culture;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ession are classified as martial skills→types of feats→martial arts.2)In the formation of motivation,Fighting Dance is facilitated by collective will,personal motivation,imagery of thinking and other factors.The formation of(play)cap is facilitated by the bidi?rectional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Wushu techniques is formed by the needs of Wushu routine’s development,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the internal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culture.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r occurrence of traditional Wushu rou?tine,reveal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Wushu routine and provide directional guidance and reflection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Wushu routine.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routine;Martial Arts Dance;(play)cap;boxing;martial arts;physical culture
武術套路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瑰麗珍寶,蘊含著我國先民的思想智慧,是中華武術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中國武術區別于世界其他武技的最顯著特征。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人指出:“國術在形式上的特點就是注重套路。[1]”但是,一直以來,由于史料的匱乏,已有的對傳統武術套路歷史形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編纂的《中國武術史》里的觀點為依據展開論述,而富有標新的研究成果卻不多見。基于傳統武術套路在整個中國武術中的重要地位,迫切需要我們對它的發展歷程及其動因加以研究。
現有的武術套路起源學說最常見的有“勞動說”“模仿說”“禮儀說”“巫術宗教說”“軍事戰爭說”“禮樂文化說”等,這些論說在某種視角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又未能完全說明問題,經不起推敲。如“勞動說”,難倒外國就沒有勞動嗎?為什么在國外沒有形成武術套路?又如“模仿說”,其他民族就沒有模仿行為嗎?其他國家古代就沒有軍事戰爭嗎?以此類推發現,這些學說似乎統統都站不住腳。從武術的本質屬性“技擊性”上看,武術的起源應與人類起源是一致的,它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是伴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的。自人類出現之日起,求生的技擊本能便已存在,武術套路業已孕育。可見,探討武術套路的起源問題,同探討人類起源無異,研究意義并不大。因此,對于武術套路研究的關鍵不在于此,而是應從武術套路在歷史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一系列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顯著的個性特征入手加以研究,深入剖析其個性特征成因,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查閱相關武術史料,從發生學的理論視角發現,傳統武術套路在記載中有3個顯著“節點”,即先秦時期的武舞、宋代的(打)套子和明清之際的拳種。根據因果關系的哲學理論,先秦武舞是傳統武術套路發展史上的第一個“果”,同時亦是宋代(打)套子的“因”;而宋代的(打)套子既是先秦武舞的“果”,同時亦是明清拳種的“因”;明清的拳種涌現既是宋代(打)套子的“果”,同時又是現代競技武術套路的“因”。武舞、(打)套子和拳種三個因素緊密相連,不可分割,構成我國傳統武術套路發展的基本規律。因此,本文從傳統武術套路在歷史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所依次呈現出的“武舞”“(打)套子”和“拳種”三個“節點”入手加以研究,深入剖析其成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期為傳統武術套路的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以及為當前競技武術套路的發展提供具有方向性意義的思考與指導。
1 先秦時期“練為戰”的武舞:一種簡單而野蠻的“身體技術”
傳統武術套路的第一個“節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時期的武舞。武舞在成立之初主要以“練為戰”為主旨,“以武為舞”的藝術表現形式決定了其藝術審美的觀賞性和威懾殺敵的實用性,成為原始巫術活動中重要的身體表達方式、宗教祭祀中不可或缺的慶典內容以及軍事操練的重要手段。另外,從個人視角出發,內心情感的抒發、防身自衛的需要、記憶傳承的愿望以及意象的思維方式亦是武舞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原動力。
1.1集體意志:圖騰崇拜與武力威懾
武舞,顧名思義是指武術與舞蹈的融合,“是一種以人的身體為載體,以武術動作為素材串編而成的表現一定思想內涵的生命運動形式。[2]”一直以來,主流武術學者將原始人類在采集狩獵活動中所出現的一些簡單的與攻防技擊有關的方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搏斗視為武術的萌芽,而將原始巫術活動和宗教祭祀以及軍事操練中出現的武舞視為武術套路的源頭[3]。武舞從形成上由無到有、從規模上由小到大成為原始社會的“社會符號”和“集體儀式”,得到族群部落的一致認同與廣泛參與,并非依靠一兩個統治者所能企及的,它是得到集體共識和推動的結果,是原始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而能夠在原始人類社會中產生集體“共鳴”力量的便是原始人類的圖騰崇拜,它不僅具有自我身份認同、團結族群部落的功能,更是巫術與宗教以及武舞產生的動力之源。
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對“現實世界的反映”,是被顛倒的社會意識形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說道:“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4]”武舞在“巫術”中用以“巫祝”,是女巫師“以舞降神”的把戲,是希冀借此獲取“超自然”的力量以戰勝鬼神的意淫。盡管如此,不可否認宗教和巫術對原始武舞的形成與發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因此,原始武舞無論是從“外顯的”物器技術層,還是至“內隱的”心理價值層無不處處彰顯出對“現實世界的反映”和“超人間的力量形式”。時至今日,無論是傳統武術套路還是競技武術套路仍可處處窺到此“遺風”。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先秦時期的武舞記載多見于祭祀和軍事戰爭中,其作用概括起來主要有二:一是用以慶典,即作為原始宗教巫術的祭祀活動和宣揚統治者政治功績的重要內容。如《說文》中載:“巫,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指出原始巫術武舞的作用是以舞降神,巫女幻想著通過“跳”一些帶有技擊性動作的“舞蹈”,產生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以控制神靈,使其聽從自己的號令,實現自己的愿望。而周代著名的“大武舞”則以表現武王克商的過程與功績,是帶有一定劇情和政治意圖的慶典活動[5]。二是用以戰爭,即用以軍事操練和威懾敵人。《韓非子·五蠹》里記有用以軍事操練及武力炫耀的“干戚舞”。故事描寫的是三苗族反叛,舜帝三次打敗他們,仍不降服。后來禹帶領軍隊表演手執巨斧與盾牌的“干戚舞”給三苗看,這個武舞所表現出威武雄壯的氣魄與高超的武功,使三苗既感動又害怕而終于降服[5]。在《華陽國志·巴志》里載,周武王伐紂時,聯合巴蜀軍隊。巴蜀軍隊跳著威猛的武舞,唱著雄勁的戰歌“以凌殷人”,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想象出原始武舞所具有的威武雄壯的氣勢[5]。
經反思后不難發現,關于原始武舞的記載,多以軍事祭祀的“集體武舞”為主,而類似“巫術”所跳的個人武舞的記載較為鮮見。但是今日的武術套路多以個人演練為主。因此,本文認為個人演練的武舞才應是今日武術套路之始祖。經查閱,刑天與帝爭神的干戚舞,可以說是關于武舞的最早史料記載,但從其描述論斷,刑天的干戚舞是頭被黃帝砍掉后無意識的“亂舞”,嚴格意義上講不能視為“武舞”。至周代,出現個人武舞的記載。《禮記·內則》記:“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廈”。其中的象舞指的便是個人武舞。它雖是個人演練的武舞,但卻是“象用兵時刺伐之舞”,目的還是為軍事戰爭服務的。由此推論,在原始社會,個人武舞與軍事武舞之間似乎并沒有明顯的界限,象舞練習不僅是為了個人的防身自衛,更多地還是為軍事戰爭的需要做準備。
另外,從原始武舞技術描述上分析,由于原始社會生存環境的惡劣和戰爭搏斗的頻繁,無論是軍事武舞還是個人武舞,訓練的主要目的都是“練為戰”,用以戰爭搏斗的,因此,原始武舞又被稱為“戰舞”。如同今日軍隊里面的擒敵術和搏擊比賽中的技擊術一樣,其動作應該是簡單、野蠻且實用的。《禮記·樂記》:“一擊一刺為一伐”“文王時有擊刺之法……”等記載表明原始武舞多是持械而舞,方法多以擊、刺、伐等動作為主,是直接從軍事戰爭的搏殺經驗中提煉出來的,未經太多的藝術化加工,可以直接用于軍事戰爭搏斗。到了春秋戰國,各種武術論著相繼問世(如《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越女論劍》、《莊子·雜篇·說劍》、《劍道三十八篇》等),才表明軍事武舞與個人武藝的分野,標志著個人武藝技理的基本成熟,并開始與傳統文化相融合,為宋代程式化、藝術化“(打)套子”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1.2個人情懷:防身自衛與記憶傳承
原始時代,人類生存環境異常惡劣,各群族部落內部和群族部落之間或為了爭奪食物、或為了占領領地、或為了爭奪異性經常會發生爭斗,我們的祖先正是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大小爭斗中積累了豐富的技擊經驗,武術套路開始孕育。這是人類共有之現象,似乎并無其他獨特之處。
然而,人類是弱小的,同時又是最強大的。弱小在于人的身體條件并不是自然界生物中最強大的,強大在于人是這世界上最聰明最有思想的生物。帕斯卡爾曾明確地表達了這種見解: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他知道自己的生,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而人由于思想卻囊括了宇宙[6]。我們先民正是依靠著自己的思想,有意識地將在平時爭斗中所使用的一些非常實用的技擊方法提煉出來專門加以練習,借此提高自身的搏斗能力。諸如我們今天與某人發生了肢體沖突,當沖突過后平靜下來時,我們一般都會去習慣性地思考這次沖突所帶來的教訓,思考在這次沖突中,我是贏了還是虧了?贏是怎么贏的?虧又虧在了哪里?下次遇到用樣的問題該怎么辦?等。另外,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處于不同的情緒狀態下,人類的表現亦不同。無論贏虧,沖突過后人的情緒不免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波動,當這種情緒難以抑制時,除了訴諸于神情上的喜怒哀樂外,還經常會訴諸于行為上,以“手舞足蹈”的方式幫助宣泄和疏通,這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生理本能,是正常人體生理機能的自我保護調節,以維護我們的身心健康,這也是武舞產生的重要方面。
我們的祖先正是通過這種人與人之間爭斗后的不斷思考以及借以“手舞足蹈”情感宣泄方式激發了創造武舞的意識沖動,不斷地在親身爭斗的實踐中提取自以為實用的技擊“因子”加以專門練習或情感抒發。久而久之,隨著我們祖先技擊經驗的大量積累,為了方便記憶,便于練習,也為了將它們更好地傳承下去,我們的祖先便會有意識地將這些實用的技擊經驗以一種固定的形式組合起來,從而形成武舞。
1.3意象思維:由意至象的符號提煉
熊曉正于2004年在臺灣的《從搏擊技藝到武學文化》的演講稿中指出:中華武術傳統拳法暗含著一個重要的創編原則,即“象形而取意”和“遺形而取神”的原則。這正是我國傳統審美取向“得意忘象”的濫觴。這一原則要求對技擊格斗技藝的整合“源于實踐,而高于實踐”,取其意而遺其形[7]。因此,本文認為,武術套路的產生與我們先民的“意象”思維方式也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
“意象”一詞是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古人以為意是內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體的物象;意源于內心并借助于象來表達,象其實是意的寄托物[8]。“意”和“象”在武舞的形成過程中互為依存,缺一不可。若是缺少內在的善于從戰爭搏斗的實踐中創造“象”的“意”,抑或是缺少外在的能夠充分表達“意”的“象”,武舞都不會形成。在武舞形成上,“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即便是具備了產生“象”的客觀條件,也未必就會產生主觀意義上的具有創造力的“意”。正如本文開頭部分所述那樣,采集狩獵、生產勞動、軍事戰爭、宗教巫術等這些客觀條件不只是我們國家存在,其他國家民族也同樣存在,然而最終亦只有我們國家民族形成了風格各異、流派眾多的武術套路。這就是“意”對武舞的形成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二者關系中,“意”在先,“象”在后,“象”是“意”對客觀條件(戰爭搏斗里的技擊動作)的提煉、加工和抽象,而現實的客觀條件又決定了“意”對“象”的具體反映和反映程度。武舞便是沿著客觀條件(戰爭搏斗)→意(“意化”加工)→象(武舞形式)這一發展模式而形成。
正因如此,原始武舞所具有的意象特征蘊含著豐富的“符號信息”。正如吳松[9]等人在《武術意象:一種典型的藝術化物象——對中國武術藝術理論的初探》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中國武術就如同“一種意象符號”,每一個技術動作就好似一個審美意象,足以令觀賞者進入到武術的想象空間,并感受到武術的藝術韻味。”“意象”的思維方式培養了我們祖先由“意”至“象”、由“形象”至“抽象”的思維能力,成為后來武術套路產生的一個重要意識形態。因此,從符號學意義上講,無論是原始宗教祭祀的武舞還是武術套路里的每一招一式都隱含著不同的“符號意義”,具有耐人尋味的文化價值。如同我們的漢字一樣,如果說每一個象形文字的符號意義在于描繪一個生動活潑的畫面故事,那么武舞或傳統武術套路里的每一招一式又何嘗不是呢?兩者在傳承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傳遞先人思想智慧上可謂有著遙相呼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原始武舞同我國古代的象形文字一樣,也擁有著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符號意義。
正如符號美學的代表蘇珊·朗格認為:“現實生活中,姿勢是表達我們各種愿望、意圖、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號和征兆……是我們生活行為中的一部分。”這種帶有個人情懷和“符號意義”的武舞和今日各門各派的拳種套路不僅是一種利于傳承的象形技擊術,同時也蘊含著一個個“符號”背后的“生動故事”,將這些故事整合起來又何嘗不是一部歷史呢?我們通過這種帶有個人情懷和“符號意蘊”的肢體練習,便可以與先人進行隔空對話,從中領悟并傳承他們的思想智慧。
2 兩宋時期“練為看”的套子:一種象形而程式化的“身體藝術”
兩宋時期出現了與現今武術套路極為相識的“(打)套子”,是中國傳統武術套路發展史上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時代,奠定了中國武術套路未來發展的基本格局。套子的出現是當時社會和個人之間在精神文娛追求上雙向呼應的結果。
2.1社會需求:輕技擊重娛樂
“套子”形成于宋代一說得到了武術主流學界的認可,常引的例證是《武林舊事》里江湖藝人在表演摔跤前,“先以‘女飐’數對打套子,令人觀睹,然后以臂力爭交。”另據宋代周密的《武林舊事·瓦子勾欄》載,兩宋時期還出現了以跑江湖賣藝為生的“路歧人”,他們不入勾欄,而是在“耍鬧寬闊之處作場,謂之‘打野呵’”。從史料對“打野呵”的描述上分析,它和“(打)套子”應該是同類事物的不同說辭,只因表演場域的不同而別名區分,它們的表演目的是一致的,都以吸引觀眾,供人欣賞娛樂為主。另外,還有賣藥的人,為吸引路人,也要扯圈子舞刀弄棒。如《太平廣紀》卷八十五載:“見室內有一個弄刀、槍賣藥,遂喚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槍’”。由此可知,當時的套子表演十分盛行,不僅是瓦舍、勾欄里博人眼球的表演項目,而且也是從事其他街頭行當的招攬顧客的必備技能。套子發展至宋太祖三十六勢長拳的出現,被大多學者視為我國武術套路正式形成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0],表明此時已經形成較為穩定而程式化的武術套路。
“套子”的出現不是歷史的偶然,相反,它是歷史的必然,是社會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象征和順應時代的精神文化產物,是武舞發展與時俱進的體現,充分反映了當時社會大眾對精神文娛的需求。歷史學家們普遍認為:宋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10]。瓦舍的涌現便是很好的例證。“瓦舍”又稱“瓦子”,是宋代城市中出現的群眾性游藝場所。瓦舍之中,有花紋圖案裝飾的欄木或繩網,攔成一個個的圈子叫“勾欄”或“游棚”,是專門表演各種技藝的場所。據《夢梁錄》、《西湖老人繁勝錄》、《武林舊事》等書記載,京城內外的瓦舍有二十多處,如清冷橋的南瓦、三元樓的中瓦子、三橋巷的大瓦子、眾安橋的下瓦子、鹽橋下蒲橋東的東瓦子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瓦子。其中,北瓦子最大,有勾欄十三座之多。在瓦舍演出的各種技藝名目也非常的繁多[5]。
此外,在宋代朝廷的“默許”下,社會上出現眾多的輻射面極廣的結社組織,不僅城市里有,農村也有,很多結社組織的人員數量龐大。如南宋時期都城臨安府(今杭州)就有爭交的“角抵社”“相撲社”;射弩有“錦標社”、使棒的有“英略社”等,每社規模都“不下百人”。民間自發組成的結社組織有北方農村以習武御敵為目的而組成的“弓箭社”“忠義巡社”等。另外,在農村中還有以“社”“堡”“山寨”等形式出現的武藝結社組織,如“棍子社”等,但規模較小,多勞武結合,行俠仗義于民間。城市和民間的武藝結社組織盡管同是武藝結社組織,但二者性質不同,城市結社多以娛樂休閑為目的,而鄉村結社則趨于保家御敵,求得安定之用,這對于當時抵御外強和安定團結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5]。
宋代,因軍隊武藝表演活動多在城鎮舉行,極大地促進了軍事武藝與民間武藝的交流,為各自武藝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崇觀以來,在京瓦肆呈伎藝中,亦有‘相撲’、‘掉刀、蠻牌’、‘牌棒’的表演者,有“善角觝,都人號為小關索”的李寶。這與軍中表演的“掉刀、蠻牌”“禁軍中角觝戲”都有著一定關系,反映了當時民間武藝與軍隊武藝之間的交流與影響。南宋時,城鎮民間武藝活動進一步發展,內容增多,表演形式多樣,如“角觝”“使拳”“舞斫刀”“舞蠻牌”“舞劍”“射弓(弩)”“使棒”等[12]。
“套子”正是在勾欄瓦舍涌現的社會背景下,在城市娛樂休閑結社組織的影響下,在軍事武藝表演與民間武藝活動的交融中以滿足社會大眾的精神文娛需求應運而生,加速了先前簡單野蠻的“武舞”形態向著復雜程式化的“套子”模式發展。套子的出現徹底擺脫了“以武為舞”的“舞”性束縛和從屬于軍事武藝的范疇,決定了未來傳統武術套路的價值功用,規定了未來中國武術套路的表現形式,指明了未來傳統武術套路的發展模式,奠定了未來傳統武術套路發展的基本格局,并在廣大群眾中間得到了廣泛傳播和迅速地發展。
2.2個人需求:入仕途求謀生
北宋時期,軍中出現武術表演的專業隊伍,“花法武藝”成為招兵納賢的重要條件。“皇室集天下精兵于京師,組成數量龐大的禁軍。東京左右兩廂禁軍從各地軍隊和民間征召了一些精于武藝、擅長雜技百戲的藝人。他們名列軍籍,每月領取糧餉,專習技藝以供表演。”表明當時的軍隊招募非常重視武藝的表演功能。從《東京夢華錄》的記載中可得知,當時軍中的武藝表演不僅有劍舞、相撲等,還有雙人、多人的武藝對練和集體武術表演等[5]。軍中武藝表演的盛行,使身有“花法武藝”的江湖藝人有了進入軍旅的機會,借以走向戎馬仕途的生涯。同時,軍中“花法武藝”的聚集、交流與切磋又進一步促進花法技藝的精進。
在軍旅之外,由于瓦舍勾欄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和全國城鄉各種結社組織的盛行,“花法武藝”成為吸引大眾眼球的一大看點和市民所喜愛的重要文娛活動之一,這種活動方式逐漸固定下來,并成為武藝人謀生的行道[13]。因此,社會上出現了眾多專門從事“花法武藝”的鄉井市民,其水平也在不斷地提高。
宋代出現的“套子”較前秦時期的武舞有著很大不同,概括起來主要有五:(1)二者名稱不同。武舞“以武為舞”,將攻防技擊動作組合起來,以舞蹈形式進行的編排。從先秦至宋代之前,凡是個人演練的“武”均會在其后加上“舞”字,如“干戚舞”“劍器舞”“劍舞”等。而“套子”一詞的使用徹底擺脫了“舞”性,將武與舞之間劃清界限,并在名稱上指出套子的特點不是“舞”而是具有一定程式的“套”。(2)二者功用不同。武舞主要用以宗教祭祀與軍事操練,即便是個人的武舞練習,也是“練為戰”,為軍事戰爭做準備。而“套子”則是“令人觀睹”,供給大家欣賞娛樂;(3)二者演練形式不同。武舞分為集體演練和個人演練兩類,但是以集體演練為主,而“套子”主要是個人演練的形式。(4)二者欣賞對象不同。武舞的表演多是為了祭祀,或宣揚統治者的政績以滿足他們的娛樂欣賞,或借以威懾敵人“不戰而屈人之兵”,只有少數人在特定場合才能欣賞到,而“套子”是瓦舍、勾欄里的一項專門的武藝表演,深受社會普通大眾的喜愛;(5)二者習練群體不同。武舞的參與人員多是軍隊的人員或巫師,而“打套子”大多是以此為生的“鄉井市民”。
從以上分析看出,宋代“套子”的習練目的不同于先秦時期武舞的“練為戰”,注重的是“套化”的“練為看”。因而,較先秦時期的武舞,“套子”更加接近于今日的武術套路。
3 明清時期“練為修”的拳種:一種復雜而文明的“身體文化”
明清時期是傳統武術發展的集大成時期。這一時期,武術套路與傳統文化哲理相融,形成了風格迥異蔚為大觀的武術拳種流派,武學體系建立。這不僅是由我國廣袤復雜的自然地理風貌所決定的,也是由傳統武術自身延續的需要和傳統思想文化的內化自覺所決定的。
3.1生存所迫:由軍事失寵至武學修為的升格
鴉片戰爭以來,火器在軍事戰爭中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優越性,普及化程度愈來愈高,冷兵器逐漸退出了軍事戰爭的舞臺,武藝開始在民間肆意蔓延。此時,人們已經深刻意識到傳統武藝在防身自衛和保家衛國上如同敝屣,意識到其今后發展所面臨的尷尬境地。然而,所幸的是明清之際無論是傳統文化還是武術技藝歷經數千年的發展都已趨于成熟,在農耕文明下孕育出的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生產生活方式為傳統文化與傳統武藝的相融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以此為契機,傳統武術在講求“練為戰”的基礎上繼而上升為對傳統文化哲理精髓中“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的道的層次追求。在這一追求過程中,武術套路中所蘊含的技擊屬性始終是不可撼動的根本和核心。而武術拳諺中常講的“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一日練一日功,一日不練十日空”等艱苦體悟的習練過程成為砥礪人們意志修道得道的箴言。中華武術之所以被稱為“功夫”,大抵既源于此。
進入清晚期,以太極哲理學說立論的太極拳、以八卦哲理學說立論的八卦掌和以五行哲理學說立論的形意拳相繼出現,開啟了不是先前以傳統文化哲理為技理指導而是純粹以之為創拳立論的歷史先河。另外,少林功夫亦“參融禪理,兼修氣功”,使少林功夫向著“禪武合一、內外兼修”的方向演進。傳統武藝最終得以在“地緣”上找到棲身于民間的富饒遼闊之地,在“親緣”上找到了依附于傳統文化的立身安命之本,從而使得在軍中失寵一度被戲謔為“江湖末技”的傳統武藝在民間經過一段時間的“整裝待發”醞釀之后逐步步入“雅正文化”的“武學”殿堂,武術一躍上升為“武學”的范疇。這一華麗地轉身正是迫于化解自身的生存危機以提升自身獲得更大發展空間的需要。
3.2地理使然:在農耕文明氤氳下的小農產物
自然地理環境決定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生產生活方式決定社會的經濟結構,社會經濟結構決定其文化類型以及人們的文化意識形態,而這一切又將會具體反映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對此,列寧曾這樣論述:“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決定著經濟關系的以及隨在經濟關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會關系的發展”。武術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映射,由“技”到“藝”再至“道”的升格,歸根結底,和我們祖先所生存的地理環境亦分不開。在長江黃河哺育下的華夏大地,在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模式下,我們的祖先曾創造出世界上最先進最燦爛的農耕文化。武術歷史發展的“源遠流長”與武術內容體系的“博大精深”若是缺少了這一長期而穩定的以農耕文明作為支撐的社會結構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王崗在《武術與農耕文明》一文中所言:“農耕文明及其影響下的超穩定的社會結構為武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使武術能夠成就今天的蔚為大觀。與此同時,農耕文明也在武術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無論是武術的理論指導,抑或是武術的傳承方式都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數千年來,我國在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模式下形成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這一“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為拳種的多樣性和技理的精進化提供了保障,民間武術師傅們才得以在“衣食無憂”的條件下過著“忙來時種田,閑來時造拳”的田園生活。
農耕文明,是指由農民在長期農業生產中形成的一種適應農業生產、生活需要的國家制度、禮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14]。農耕文明突出的特點是家族的傳承性和對土地的依賴性,由此也產生了人們在思想上的保守性、性格上的溫和性以及交際上的封閉性,造就了中華民族狹隘的小農思想,人們相互之間過著“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這在農耕文明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當時對傳統武術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傳統武術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生活方式下,形成了拳種套路的多樣性、流派門派的龐雜性以及傳承方式的宗法性。從歷時性上看,“武術套路的形成與發展,有著一如流水的歷史綿延,大致經歷了古代武術套路的氤氳、萌芽、形成、成熟以及近代武術套路的演進等階段,從中展現出武術套路在不同時期的足跡屐痕。[15]”而在這些足跡屐痕中又無不深深地烙有農耕文明的印記。從共時性上看,傳統武術從習武者的思想觀念上、傳統武術的技術理論上和它的傳承方式上又無不映射出農耕文明所孕育出的小農思想色彩。
因此,盡管鴉片戰爭以降,冷兵器在軍事領域中完全失去自身存在的價值意義,但是在農耕文明下孕育出的小農思想,仍對曾數千年來捍衛自己家國安全的傳統武術敝帚自珍,懷有難以割舍的情懷。正是這種難舍難分的情懷下促成人們對傳統武術在習練目的上由“練為戰”至“練為修”、在發展認識上由“武藝”至“武學”的思想升華,完成了傳統武術“由術及道”的追求與改造。
3.3內化自覺:由身體體練至精神道悟的自覺
武術套路發展至清代,習練目的在保持“技擊性”本質的基礎上進一步升華,不再一味地追求“技擊”,而是在“技以載道”的認識下自覺內化為畢生的“悟道修為”。這是我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一切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如同中國的茶文化一樣,茶葉最初的產生并不是作為飲品,而是作為一種治病療傷的藥物出現的,春秋時期人們開始用其做飯菜,直至大唐時期才將其作為解渴飲品飲之,發展至今形成“茶道”,出現了“茶文化”。茶的功能價值隨著人們認知的深化和時代的不同需求而得到了廣闊的延伸和升華。盡管如此,茶最初的藥用、食用以及解渴等價值功能至今仍然存在,仍在不同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功用,只是人們不再強調它,而是搖身一變升級為一種高雅時尚的休閑消遣飲品。傳統武術由最初的武舞(練為戰)至宋代的武藝(練為看),再至清代的武學(練為修)的發展歷程與茶文化的發展又是何等相似!盡管在這一發展歷程中,出現了武術所蘊含的眾多價值功能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需求下“此消彼長”的現象,但武術的“技擊本質”始終是一貫的、毋容置疑的。在我國傳統思想文化中這既是一切事物發展的一種內化自覺,也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必然歸宿。
當傳統武術上升為“武學”,追求“道”的旨趣后,“技擊性”雖然仍是其鮮明特征,但更多地只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多招數在實際搏殺中未必見得多么實用。也就是說,明清之際的武術習練旨趣本身便脫離了原始野蠻的殺人搏斗術的訓練,不再是單純地追求“技擊”,而是將原本野蠻粗暴的“技擊術”賦予以“文明性”,通過對這種帶有“文明性”的且具有“技以載道”內涵的艱苦卓絕的形意“修行”達到對“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的頓悟。武術套路亦正是在這一發展旨趣下,技術體系日益向著復雜多樣化發展,構成了武術套路審美的“形似、不似、不似之似”的3個技術境界[16-18]。并且,武術套路里的“大開大合”“走立圓、平圓、八字圓”等動作技術特點和“以柔克剛”“以小博大”等技擊理念在真實實戰中也很難派上用場。這已在原來中央五套播放的《武林大會》節目和筆者20余年的習武經驗中得到充分證實。
另外,中國傳統的君子文化素來提倡“以德服人”,講求“動口不動手”。動口主要是指的說理,講道理,即以理服人。當“逼不得已而為之”時,往往也是“點到為止”“手下留情”,而這時候的“點到為止”“手下留情”,并不是眾人所想象的在搏斗時對力道的把控,而是按照雙方約定俗成的彼此同流同派的“套路”框架內“出牌”。如太極拳的推手,雙方手一搭,在彼此推讓之間去感知對方的功力深淺,幾個回合下來便能感受到對方功夫的高低,負者主動示弱,對勝者行禮致歉,以示誠服,而盡力避免人身的直接攻擊。而在不同拳種流派之間,雙方更多地是在“功夫”上的較量比試。這時候的雙方甚至可不必搭手,不必有肢體的接觸,僅僅通過功力的展示便可以達到威懾對方的目的,這恰好也符合“和為貴”“中庸之道”等的傳統文化思想,也是兵家所講“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的深刻體現。這或許亦是傳統武術被稱為“功夫”的緣故罷!故退出軍事戰爭舞臺的傳統武術被火藥巨大的殺人威力折服后,繼而走向對“功夫”和“悟道”境界的追求,在這一追求過程中通過體驗常人難以忍受的對身體和意志上磨礪而達到對精神文明的修為,即達到毛澤東所說的“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的終極關懷。
4 結語
綜上所述,傳統武術套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依次呈現出武舞→(打)套子→拳種3個階段特征;在習練目的上,相應依次呈現為“練為戰”→“練為看”→“練為修”的目的變化;在技術特點上,相應依次表現出身體技術→身體藝術→身體文化的發展特點;在進階旨趣上相應依次歸類為武技階段→武藝階段→武學階段的發展趨勢。在形成動因方面,武舞的形成是由集體意志、個人動機以及意象思維等因素促成;(打)套子的形成是由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雙向呼應因素促成;拳種的形成是由武術套路自身發展的需要、地理環境的使然以及傳統思想文化的內化自覺等因素而促成。我國的傳統武術套路數千年來正是沿著由“武舞”至“拳種”的發展軌跡而形成今日蔚為壯觀的景象,并在世界上獨樹一幟。
參考文獻:
[1]戴仁聲.對于國術的觀感[J].中國青年體育季刊,1945,1(1):1-5.
[2]劉濤.對武舞的歷史解讀—兼論武術套路對古典舞蹈的影響[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07,26(2):124.
[3]陳沛菊,喬鳳杰.武術與舞蹈[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5,21(66):12.
[4]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4.
[5]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中國武術史[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6.
[6]帕斯卡爾.思想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157- 158.
[7]熊曉正.嚙崖集[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11:352.
[8]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xx-v6LCw64wBs-5BXXczDkFPMXGk3T44VB9QSsWeXHOX3oQSplB4Za-vJ8A_DQ3e7BsufECMID4y48YRsi7VGZUNw5h6yo2JbBJmiIFjGGu
[9]吳松,王崗,張君賢.武術意象:一種典型的藝術化物象——對中國武術藝術理論的初探[J].體育科學,2012,32(5):88.
[10]蔡寶忠.中國武術史專論[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3:97.
[11]余水清.中國武術史概要[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90.
[12]林伯源.試論宋代武術的發展變化[J].北京體育學院學報,1989,(1):52-53.
[13]馬文友.套子武術最早出現在宋代的社會學闡析[J].浙江體育科學,2008,30(5):93.
[14]胡曦嘉.淺析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異[J].科技創新導報,2010,34:224.
[15]周偉良.論武術套路的歷史形成與發展[J].中華武術研究,2013,2 (4):6.
[16]張勇,馬文友,李守培.從技擊走向審美:中國武術套路特征分析[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3,28(1):31.
[17]李暉,于善安.武術動作名稱翻譯的美學考量[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15(5):93-98.
[18]李福剛.中華武術美學研究的歷史演進及其未來展望[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5(3):75-83.
●研究報道Short Comunications
作者簡介:武超(1985-),男,山東鄒城人,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族傳統體育學;通信作者:呂韶鈞(1963-),男,山東煙臺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民族傳統體育理論與方法。
收稿日期:2015-09-30;修回日期:2015-12-01;錄用日期:2015-12-02
DOI: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16.01.012
中圖分類號:G 8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0000(2016)01-063-06
作者單位:1.北京體育大學研究生院,北京100084;2.北京體育大學武術學院,北京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