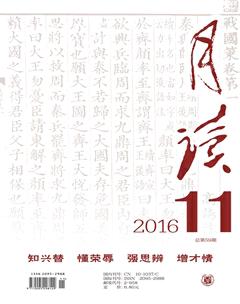稷下學宮的思想交融
李山
春秋戰國各主要思想巨流的出現,各有其地域文化的酵母。同時,思想的流傳和交融,其作用也不可小看。這樣的交融以齊國的稷下學官突出。
稷下為齊都臨淄西門之稱,有系水經過,齊君在此立學宮,稱“稷下學宮”,學宮產生的學術稱“稷下之學”。稷下之學起于齊桓公田午,經齊威王至宣王達到鼎盛,延續至湣王,后因戰亂而冷落;齊襄王時曾再度恢復,直到齊王建時期而止,持續約一百五十年之久。極盛時期,游于稷下的學士達“數百千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今可考見的有淳于髡、彭蒙、宋钘子、尹文、兒說、告子、孟軻、季真、接予、田駢、慎到、環淵、王斗、荀況、田巴、徐劫、魯仲連、鄒衍、鄒奭共十九人。其中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等七十六人,“為上大夫”之職,“不治而議論”(同上),“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先秦禮賢之風從未有齊國這樣的隆盛。“數百千人”的學士中,不都是“上大夫”,齊國的學宮里,還有追隨在這些大德名師左右的學子,如荀子,年十五即來齊游學,成為一個思想大師后,又曾在這里“最為老師”(同上);《管子》中又有《弟子職》一篇,即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這是一個“天下賢士”的風云際會之地,這些學術大師們來自各地,來自各個學派,強大的齊國,霸主的雄心,將他們召集在一起,共同議論,互相交流,劉向《別錄》說是“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史記》裴駰《集解》引),泱泱大國,方有此泱泱學術,在當時這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學園。
戰國時期的幾個大思想家,差不多都與稷下有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在這里可以看到各學派的人物,看到他們的思想交鋒。例如孟子和淳于髡就曾就“男女授受不親”問題進行辯論。淳于髡譏諷孟子“天下溺”而不能“援之以道”,孟子則高揚“禮”的“常”與“權”,是儒家“經權”思想的一次重要表述。孟子與告子爭論人性善惡的話題,更加重要。告子主張“生之謂性”,即一切生理本能是“性”,而孟子則堅決主張人性善。孟子高談性善時,曾借牛山為喻。有學者據此考證孟子性善論的主張正是發自稷下。“予豈好辯,予不得已!”孟子此話,想來是參與稷下學術活動的每一派學人的感受。思想在爭辯中出新,稷下造學之功,亦大矣!
稷下,不僅有學術的爭辯,還有學術的相互吸收,從而造就出思想的大師。宋钘子是一個集道術、墨家之學為一身的人物。此外,還有慎到,趙國人,他是法家人物,也是道家人物,或許他還與墨家有關聯;而且像“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慎子·威德》)這樣嘹亮的句子,也絕不是三晉或秦那樣文化氛圍下能說出的
言語。
根據文獻,孟子、荀子從稷下交流中吸收滋養最多、最明顯。
兩者都是堅定的儒家,孟子的師承來自子思,荀子最敬服仲尼和子弓;兩者在稷下的爭辯中都嚴守儒家立場。但在《荀子》中,稷下交融的痕跡到處可見。荀子的社會觀點強調“群”,強調“分”,強調“群”而有“分”;所謂“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荀子·富國》)。檢討與稷下先生們相關的文獻,早于荀子談論“分”的,是彭蒙和慎到。《意林》卷二引彭蒙之說:“雉兔在野,眾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大致相同的說法亦見于《慎子》。又《管子》一書中,涉及到“分”的篇章則有《宙合》《小問》《君臣下》《幼官》和《乘馬》諸篇。《管子》又很可能是稷下先生們遺著的匯集。荀子關于“分”的論述自有其不同于稷下學者之處,有取于稷下之學則是可以肯定的。與“分”的觀點相連,在治國之道上,可以發現荀子還是一個政治“無為”主義者。只是他不那樣講,而是說“垂衣裳而天下定”(《荀子·王霸》),要做到這樣的不治而治,君主要以“禮”來“修身”,君主要守“法”;而守法的內容,又不外“符契”“衡石”之類,與黃老家“法”的意思大體相同。同時,荀子還強調君主要杜絕一己之私心私意,如“誕詐”“好曲私”和“貪利”等,幾乎與黃老家主張一致。上述幾點列舉,不難看出這位儒家的大師,其政治哲學與孔子的“仁”與“禮”的對峙,與孟子的“制民之產”頗為不同,其儒家政治哲學的建構,明顯受到稷下黃老之學的影響。
儒家強調“正名”,而儒家“名學”的建構,荀子功勞特大,這也得拜稷下之賜。正是兒說、田巴的大唱“白馬”“堅白”“同異”之說,才使得荀子作《正名》,對名家之學作出儒家的反駁,從而建立本學派的名學。儒家學術傳統中,荀子最強調認識論,他是一個主智的儒家。在這方面的造詣,給他最大幫助的不是他的先師。從孔子起,重德性就壓過對外界的求知,德性之知亦即“反身而誠”的知識論,是儒家的大流。給荀子認識論以巨大啟發的是稷下黃老之學,具體說即《管子·心術》上、下兩篇。《心術》篇的主旨是講明君主如想有效地督責臣下,必須去掉一己之心意(即私心、私意),所謂“潔其宮,開其門”,這就是“無為”,所謂“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管子·心術上》)。這影響了荀子。他強調“心”與各感官之分,又特別強調心的“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于室而見四海,處于今而論久遠……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荀子·解蔽》)黃老督責臣下的技巧,在荀子則發展為“恢恢廣廣”認識論,他由此而成為“制割大理”的理性贊
美者!
稷下對孟子的啟發,也是多方面的,如“心之官則思”(《孟子·告子上》)的說法。還有一點最重要,就是“浩然之氣”的修煉,明顯地是從稷下黃老之說那里汲取的資源。關于“浩然之氣”,見于《孟子·公孫丑上》,也見于《管子·內業》篇。學術界對孟子“浩然之氣”是否受黃老影響有不同的意見。解決這一問題,不能靠文獻考據,現有的文獻條件解決不了這一問題,而是要從學術統緒中尋找答案。有一點必須清楚,“浩然之氣”在孟子,不是一個純粹的道德性概念,它表述的“行氣”的內在體驗,所以孟子說它“難言也”,又形容“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這與《內業》篇“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之說是一致的。再檢核《論語》和《中庸》及新出土的一些儒家相關文獻,孔子和孟子以前的儒家,很少談“氣”,“氣”根本就不是他們的重要問題,所談之“氣”也只是“血氣”“食氣”之類的概念,與孟子所“難言”之“氣”,不是一個范疇中的事。也就是說,孟子所說的“氣”不屬儒家固有之術,它是一個新東西。這就必須從孟子在齊國的生活經歷,與齊國當時盛行的黃老之術聯系起來看了。他的說法與《內業》篇如此相像,絕不是偶然的。孟子學問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士人主體人格的造就。他所以要修煉黃老家的“浩然之氣”,與他建構“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氣格有密切的關系。
(選自《先秦文化史講義》,有刪節,中華書局。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