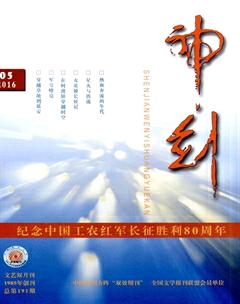《瘋狂的榛子》:抗戰題材小說的重大突破
鄭潤良
抗日戰爭勝利是百年來飽受屈辱的中華民族第一次在完全意義上打敗外國侵略者,是民族走向獨立的偉大轉折點,并為此付出了無法盡數的代價。但是把中國抗戰題材小說放在整個世界二戰文學的視野上,與美國、蘇聯等國家的同一題材的作家作品相比,我們的抗戰題材小說無論在對戰爭復雜圖景的全景式描繪還是在人性反思的倫理深度方面,都有許多明顯不足,所取得的成績無法與我們作為東方反抗法西斯的主戰場這一歷史地位相稱。
總而言之,我們的抗戰題材小說沒有大的突破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戰爭倫理觀的問題,二是缺乏對復雜歷史圖景的總體把握。從戰爭倫理觀而言,現代以來的中國抗戰小說由于意識形態宣傳與教化的需要,大多洋溢著一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主要反映我抗日軍民的光輝形象。這些作品在戰爭時期確實能激勵普通國人的斗志,在戰后的和平歲月也能讓后人銘記先輩為今日幸福生活所付出的巨大犧牲而生景仰之心。但現當代以來的大部分中國抗戰小說則由于巨大的民族義憤與創傷記憶,依然遵循簡單的二元對立邏輯,導致作品的總體思想境界沒有得到提升。中國抗日戰爭是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領導下進行的,涉及多方力量的合作、對峙、抗衡等復雜因素,其復雜性遠遠超過其他反法西斯國家的斗爭。由于意識形態等諸種因素的影響,我們的作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全景展示還有許多需要拓展,比如對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的敘述多年來一直是比較薄弱的。
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表明抗戰題材領域的創作還有巨大的可開掘空間。近年來,已經有許多有見識、有歷史擔當的作家投入了這一領域的深入發掘。著名華裔作家袁勁梅的長篇小說《瘋狂的榛子》令人眼前一亮。這部首次反映之美空軍混合聯隊“飛虎隊”抗戰史實的長篇小說,事實上已經超越了戰爭題材小說的范疇,通過時空的穿插、地域的切換、哲理的沉思,這部小說不僅解決了筆者上面所提到的中國抗戰題材小說的通病,而且通過戰爭和歷史對文化與人性癥候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討。
小說主要寫了兩代人,第一代的男女主角分別是范笳河和舒曖。他們的經歷主要是通過別人的追·}己和范笳河的“戰事信札”得以鋪陳。舒曖出身于桂林的一個名門望族,范笳河則來自一個偏僻的村落范水。范笳河爺爺死后,被舒曖的姐夫國民黨將領叢司令送到舒曖家寄養,并與舒曖成了一對情侶,之后,范笳河被送去學航空并成為“飛虎隊”的一員。解放戰爭時期,范笳河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到了臺灣后又駕機返回大陸,成為人人稱頌的英雄。這期間范笳河與舒曖在飛行基地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舒曖生下了一個男孩但只能送給別人,范笳河返回大陸時,舒曖也追尋愛情從澳門回到了大陸。范笳河被組織告知不能和國民黨將領的小姨子結合,最后只好和組織認可的甘依英結婚。舒曖尋死未成,和愿意娶她的大學教授頤希光結了婚。反右時期,范笳河和舒曖在一個小村落意外重逢,又有了一個愛情的結晶。第二代的男女主角則是他們的子女。多年之后,他們的子女因為追尋父母的足跡而團圓。舒曖和頤希光的女兒喇叭隨丈夫畫家寧照到了美國,在一家保險公司上班。浪榛子在一家美國大學教法學,她的男友沙頓上校因為心理問題認識了范笳河和甘依英的女兒——心理醫生范白萍。他們相約到衡陽老空軍基地和戚道寬、宋輩新一起會合去燒范笳河給舒曖的祭文,結果戚道寬卻因為違規將醫藥開發基地變成房地產項目被浪榛子的朋友善全春博士起訴而無法成行。
小說以范笳河的戰事信札穿插和結構全篇,在信札中盡量詳盡地敘述了飛虎隊的戰斗經歷、塑造了飛虎隊隊員性情各異、立體感人的形象。
在飛虎隊所在的第14航空軍中,還有黑人、印第安人、馬來人、菲律賓人,他們在遠離家鄉的戰場,為了正義和和平,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正如舒曖的姐夫叢將軍曾代表中國陸軍感謝美國航空戰士為抗日貢獻了他們年輕的生命時所說的,從1942年以來,美國航空戰士在空中和日軍打了近五千次仗,轟炸敵人地面基地和兵力一千八百多次,打下并炸毀三千兩百多架日軍軍機。但作者并沒有讓范笳河在戰事信札中將大量篇幅放在敘述抗日將士和飛虎隊隊員的英勇善戰上,而是將焦點放在隊員們在戰爭中的糾結心理,他們英勇參戰并不是因為熱愛戰爭,而是因為渴望盡快結束戰爭、渴望和平的到來、渴望和自己的女友過上正常的日子。“戰爭拿生命做籌碼賭輸贏,我們只能把生命押在正義上,死得才有意義。”對于范笳河們來說,有兩個“我”存在。一個“我”只做著我們任務里說的事兒。生活再苦,空戰再激烈,這個“我”是個航空戰士。他都承受,都得去做,最大可能地完成任務、摧毀對手。還有一個“我”卻不在戰場。在家鄉,他是個好人、正常人,誰也別想碰他。范笳河的那個“我”,在桂林,在舒曖身邊。馬希爾上尉的“我”,在美國賓州水碼頭的紅楓林里,他的女友身邊。這個“我”是高高地待在天上,或藏在他們心里的一個角落,絕不讓戰爭碰的。這兩個我是分裂的、矛盾的。一個充當戰爭的一個零件,雖然是正義的,但畢竟是血淋淋的,另一個則是有血有肉知冷知熱的正常人。所以,馬希爾上尉和他的副機長看見日本人的金牙感到惡心。因為日本人雖然是敵人,但也是人。那個“金牙”離他們太近,這么近的距離,那一口的飯臭氣,吹到了馬希爾和他的副機長臉上,碰了那個他們絕不想讓別人碰的、另一個與戰事無關的“我”,所以惡心。但是,盡管如此,他們別無選擇。這個戰士的“我”得先活著,那個遠在天上、在女友身邊的正常“我”才能生存,用瑞德中校的話說,“戰爭是壞事,但我們到了不打,是更壞的事的時刻。”
《瘋狂的榛子》是一部學者小說,它不僅有著細膩豐富的人物形象、心理的塑造,更有著宏大的對歷史、對文化問題的深度思考,也因此,它對歷史場景的描寫顧及到了它的豐富性和多面性,顧及到它的來龍與去脈。因此,作品不僅寫了大部分飛虎隊戰士和叢司令等人的正面形象,也寫到了個別美國士兵參與黑市交易發國難財以及部分正面戰場官兵的負面形象。報道過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美國記者泰德·懷特很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上層官員們你恨我、我恨你,大家打的不都是同一場“抗日戰爭”嗎?對這個問題,范笳河從他在老家范水的經驗出發,認為很好理解。范水在小說中顯然是一個有著濃厚象征色彩的符號。范水是一個封閉而又自給自足的地域,自成系統。在范水,有一種等級秩序,像個大家庭一樣,上人壓下人,萬事得“爸爸”仲裁決斷。在范水,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位置,個人不重要,位置才重要。“爸爸”占據金字塔的頂端,兒子為了“盡孝”甚至必須將自己老婆的初夜送給父親。這種荒唐的事情在范水被視為正常,不做這種荒唐事的人會被視為異端遭排斥。宗法秩序第一,個人感受無足輕重。所以,兄弟之間你爭我奪、搶權分利,是為了在秩序中占據一個更好的位置。范水的秩序遵從的總是一種范式:從治到腐,再從腐到亂,等著亂中打出新皇帝。亂世,那天生制造“恨”的宗法劣根性能全表現出來。所以,泰德·懷特看到中國上層官員們大敵當前,還是你恨我,我恨你。對于范笳河來說,他的最大愿望是等打完仗,一定要改掉這個舊秩序。但這個舊秩序卻不是那么容易撼動的,不會隨著戰爭的消失而消失,它會以新的形式出現,在作者看來,“文革”就是這種宗法制仇恨的再一次爆發。因此,小說的中間部分,通過主人公的追憶,我們又來到了那段特殊的荒唐歲月。
得了老年癡呆癥的頤希光還會因為偶爾提及當年的砸墓碑事件而行為失控。十年內亂相當于又打了一次內戰。內戰結束了,但文化根基中的等級制因素、宗法制暴力并沒有結束,比如善博士看到的網絡語言暴力,好像“文革”病沒好似的。如作者所強調的,“人如果不自己站著,走不動現代文明。”如果不從宗法制暴力的陰影中走出來,現代文明依然只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從戰爭中爭得和平,是一條艱難的路。然而,從擺脫戰爭思維到學會過和平的日子,從用暴力說話到用法律說話,也是一條艱難的路。可人們別無選擇,在走過暴力流血的道路之后,非得走后一條路不可。因為,只有后一條路走好了,父輩親人在前一條路上付出的代價才有意義。”《瘋狂的榛子》往往借由人物之口對歷史與現實生發一些沉痛的議論與感慨。過多議論本來是小說創作的大忌。但這些議論的確從鮮活的人物故事中衍生出來,并且借助信札等形式得以自然表述,所以不但沒有降低文本的審美感染力,反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內涵。
按照作者的原意,“我寫戰爭、寫航空戰士,我本想寫一部單純的戰亂與愛情故事。可是,愛情故事一到中國,就單純不了。”寫戰爭不能僅僅局限于戰爭或者已有的敘述模式,必須將歷史、文化、人性涵納進來。所以,作者的筆觸超越戰爭,觸及歷史、文化與人性的深層癥候。學者的素養成全了她這種深入探究的野心,使得《瘋狂的榛子》成為抗日題材小說的突破之作。
責任編輯/劉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