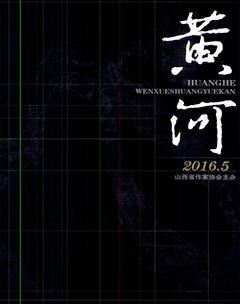從個體生存體驗折射萬物生命本質
指尖
傳統散文所呈現出的拘泥和局限,已無法承載當下時代蕪雜而充滿變數的特質。在多元化和信息化充斥人類生活的今天,許多自覺且警醒的散文作家開始有意識地打破傳統的敘事、結構程式和題材選擇,在文體創新的同時,加入大量其他領域的信息,試圖通過諸信息的交叉、對比、運用和實踐,扭轉和挽救散文的被同化、被踐踏,且日趨式微的現狀。新世紀以來,新散文、原生態散文、非虛構散文、在場散文等理論的提出和踐行,無疑給散文界帶來了新鮮明亮的氣息,散文作家將極大的個體熱情投入到一個全新而陌生的領域,他們犀利而有力地插入當下生活僵硬的土壤中,嘗試挖掘被長期掩蓋的事件真相及幽微部分,并由此引發一系列來自內在和外部環境的顛簸和振動。這種帶有勇士性質和革命意識的探索精神,使當下散文寫作更有力度,更有擔當,且更具拓展和延續性。
歷時六年,六易其稿,長達28萬字。《蟲洞》的艱難出生,無疑為這樣品質的散文式樣提供了例證。它的異質性、陌生化、包容性、探索性和反叛精神,在當下散文中散發著獨樹一幟的氣質。它的出現既表明這是一次成功的實踐,同時,也顛覆了傳統的散文觀念。
一、《蟲洞》呈現出來的陌生化
陌生化理論由俄國文學評論家和小說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在西方詩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陌生化的出現給詩界帶來集體性的驚醒,也成為詩人們推崇的主要理論之一。陌生化所倡導的,是詩人在內容和形式上違反常情常理,在藝術上超越常規。也即表面看似互不相關,內里卻千絲萬縷,內外互相交叉、對立,引起沖突,這種類同于物質之間所產生的化學反應,具有另一種形態和情境,會使讀者受到感官刺激,或者情感震動。近年來,陌生化不斷被散文界提及,但更多的只是被外在語言所利用,有些散文作者以身試之,但效果平平。囿于生活的相似性、生存的同類性,散文作家更多地擁擠在同一條路上人云亦云,相互模仿、復制,這種蓬頭垢面的現狀,使散文作品一直趨于一種平淡且下跌的狀態,有成千上萬的散文作家在成千上萬的雜志上發表散文,卻鮮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有位散文家這樣說:漢語散文寫作在經歷“新散文”大規模拒絕體制寫作的努力后,大量“美化鄉村”、“美化庸常”的“偽抒情”和“泛文化泡沫”的存在,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現在仍然沒有步出“公共寫作時代”。此語可謂一針見血。
《蟲洞》采用小說的結構、詩歌的語言和散文的敘事方式,將科學觀察、哲學思考、藝術表現和文學視角融為一體,用現代物理學解讀哲學,用哲學解讀生命,用生命體驗解讀死亡文化,內容龐雜,語言華麗,情感一氣呵成,字里行間充滿機鋒和思辨。蟲洞本是一個天體物理學概念,指介于黑洞與白洞之間的橋梁,也即愛因斯坦最早提出的時空隧道。但在《蟲洞》一書中,趙樹義先生卻以白洞隱喻生命之誕生,以黑洞隱喻生命之死亡,以蟲洞隱喻生命之旅程,賦予這一神秘天體生命旅行的意味。《蟲洞》三條主線交叉推進,這在散文作品中是不多見的。一是以科學、哲學和藝術為線索,內容涉及東方哲學、霍金的《時間筒史》、熵、耗散結構理論、薛定諤的貓、惠勒的云、托馬斯·品欽的小說《熵》《萬有引力之虹》以及電影《通天塔》《入殮師》、音樂《殤》《憂郁的星期天》等,從科學、哲學、藝術等視霹對生命死亡展開考察、論證和探求。二是以死亡體驗為線索,如意外、犯罪、戰爭、災難、城市和文化的消亡等多種瀕死或非正常死亡形態,解讀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三是以迎澤公園為線索,通過一座公園兩年多的四季輪替,景色變換,感悟生活磨難,思考時間、空間、自然和生命。《蟲洞》大量采用了隱喻、互文等后現代藝術手法,書中穿插了作者23首不同時期的原創詩歌,是一部詩意的長篇散文巨制,這種宏大的敘述本身就是一種標識,一種獨屬于《蟲洞》的呈現方式。篇幅的陌生化本身或許并不具有特別的優勢,《蟲洞》也未止步于此。《蟲洞》架構的龐雜和宏大內生自作品自身的需求,全文6章36節,章與章之簡、節與節之間是牽連式的,具有連續性和交叉性的,仿佛一部大型復調音樂劇,如果說回旋不斷的生命意識是它的音符,那么,生命哲學則是它的基調。在《蟲洞》中,僅作者親歷的時間跨度就長達30年,在事件與事件之間,隱我與顯我之間,乃至年份與年份之間,總有一些表面看似無關、內里卻千頭萬緒的聯接,這種潛意識的陌生化,或許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種“不確定性”的敘事風格。
《蟲洞》語言的陌生化表現在詩話語言的運用上,這或許得益于作者是一位詩人的緣故。通篇讀下來,有違常規的語言格式和氣息無處不在,它隨時都會給讀者帶來全方位的刺痛:
但在這一刻,我感受到的傷感卻是突然的,它遠比肌體撕裂還刻骨。它還是冷漠的,冰刀一樣刺入我的心底,卻拔不出來,斬不斷,甚至看不到一絲血腥。仔細品味,它倒是有點低輻射的特質,被侵害的細胞慢慢損傷,癌變,最終以磨牙的速度緩緩接近死亡;它還有點像漫延的黃昏,我可以把這樣的傷感命名為流水,直到黑夜來臨;它就涌在我的四周,我的五臟六腑俱已被它濕透,我卻無法抓住它的外形,更無法觸摸它的內心。
《蟲洞》不斷以熟悉事物之間的陌生關聯來制造粗糲的陌生感,同時,又將讀者拉到一個作者所預設的某個全新的角度。這個角度當然也是陌生的,讀者因為角度的不同,認識和審視的角度也會不同。因為角度的變化,環境隨之也出現了變化,一種恍然悟道的相似感既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又獲取到一種共鳴感。
《蟲洞》的構思方式打破了常規,是有悖常理的。整體上講,《蟲洞》是一部個人里程的記錄史,但跟齊邦媛的非虛構作品《巨流河》不同,它并未通過家族史來詮釋和刻畫時代的悲歡離合,似乎并不具備大事記的性質;同時,也跟阿來的《瞻對》有本質上的區別。《蟲洞》似乎并不追求宏大敘事,甚至在刻意消解宏大敘事,在不斷消解的背后,卻又建構起文化和哲學的宏大。或許在作者看來,宏大事物與卑微事物是平等的,萬物相通,生命本質并無二致。《蟲洞》僅在通過個體生存和生命體驗,來呈現作者30年親歷或目睹的、發生在身邊的事件,并將這些事件與歷史勾連起來,看似更小眾,更幽密,更具個體氣息,同時,又在時空穿越中實現了“在場”。《蟲洞》通篇彌散著生命迷惘和思想覺醒的情緒,充斥著煩惱、無奈和悲憫,恰恰是這種獨特的,不跟風、不復制的體驗和書寫,使它具備了散文陌生化的特質。
二、《蟲洞》蘊涵的現實性
散文家祝勇認為:散文可以觸及一切題材,它是自由的文體,在觸及歷史、思想、政評時,進入的角度是不同的。一般來說,人們已習慣了文化大散文的存在,似乎只有文化散文是跟長和深有最直接關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散文的大體裁、大感覺、大情意、大篇幅,使它在關注歷史和思想性的同時,較易忽略個體體驗和心靈觸及,它越來越遠地偏離了我們的生活和需求,尤其一些口號性、標志性、矯飾性的語言,導致其正在淡出散文界的主干道。而《蟲洞》恰恰跟文化散文相反,它仿佛一個碩大的容器,不只包納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藝術,甚至還涉獵物理學、心理學等領域,它在不斷呈現事物表象的同時,又在不斷剔除事物表象,直抵事物本質,可謂萬花入眼,五彩繽紛,曲徑通幽,絲絲入扣。更可貴的是,它在關注個體生存體驗、內心世界的同時,不乏一些生活細節的描述和感悟,使自身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在場性:
黃昏如期降臨,仿佛鳥兒垂下巨大的翅翼,靜謐中等待小鳥們歸巢。偏向西南的道路開始轉向正西,太陽轉移到車窗正前方,窗外的視野更加開闊。天空漸漸發白,好像一片沒有邊際的海水,太陽仿佛一只浮在水平面上的球,一團鍺紅的顏色或隱或現,偶爾偏向車南,偶爾偏向車北。我盯著這只懸浮在空中的球,看它在擋風玻璃上方游動,這只鍺紅的球或遠或近,不離不棄,直到引領我們駛出華北平原。很快就要踏入山西地界,眼前的景致越來越具體,山巒結隊而至,黃昏由淺而深落下來,轉眼之間,我們便從空曠的平原走進連綿的山脈,就像鳥兒從天空隱沒在樹林。光線越來越暗,娘子關那邊出現很大的霧,太陽突然隱沒在一片霧里,無聲無息。太陽隱沒的瞬間,夜色欲來未來,層疊的山巒僅剩粗獷的輪廓,路邊的樹上看不到烏鴉,也看不到烏鴉歌唱的村莊。
但同時,《蟲洞》又與當下的風花雪月、小橋流水、童年回憶、故鄉缺失等散文有大不同,它雖也是通過親身經歷和體悟來展開的現實化寫作,但它又不是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照搬記錄,更不是枯燥乏味的流水賬簿。《蟲洞》呈現的并非局部的、偶然的表層生活,而是通過個人際遇、感受,通過現實、歷史,準確地將社會和時代的變革呈現出來。一次車禍是通篇的關節點,拉開了30年漫長卻短暫的歲月之簾,我們隨同作者經歷了“嚴打”、踩踏、地震、海嘯、恐怖襲擊等帶有某種或必然、或偶然的突發事件之后,又被帶到霍金面前讀他的《時間簡史》。此時,莊周正在濮水河邊釣魚,薛定諤的貓正在箱子里衰變“方生方死”,惠勒的云讓歷史變得虛無和迷離,而在更遠的地方,我們看見晉陽古城和雁門關外的烽火狼煙,看見天龍山石窟和走西口人的命運沉浮,看見來自春秋和未來的愛情穿越,看見南沙河風沙彌漫卻遮不住春天的花開……《蟲洞》建構的時空足夠闊大,而在這闊大中,“我”與歷史同在,與此刻同在,與明天也同在。個體的就是集體的,而集體的便是大眾的。
有學者提出,散文的主觀性要求作品表現作家的個性,袒露作家的心靈,展現作家的人格,因此,主觀性要求情感必須具有真實性。《蟲洞》整體散發著一種紀實性,近距離觸及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性。人與社會同時擁有某種接納和排斥,二者之間所生發出來的另類物質,便是那叫作苦難的東西。苦難應是人生最本質的、無法剔除的質地,但同樣,當人處于社會當中,處于時代當中,苦難同時也是社會和時代的質地。在散文寫作日漸抽象化、粗鄙化、技術化的當下,《蟲洞》具有孤傲、剛毅、沉潛的氣質,且散發著內心觀照的通達,生命體驗的清澈,乃至具備了去蔽、存真、探求更大真相的野心,這也是這部長篇散文難能可貴的品質。
三、《蟲洞》隱藏的反叛精神
羅馬作家特倫斯和西塞羅將“風格”一詞演化為書體、文體之意,表示以文學表達思想的某種特定方式。在漢語中,風格是指人的風度品格。在《文心雕龍》中,風格一詞是指文章的風范格局。《蟲洞》具有強烈的古典自由主義色彩和家國情懷,它不流俗,不獻媚,擺脫了傳統散文模式化的束縛,內在氣質深邃、堅硬、廣博、開闊,無論文字表達、文章架構,還是內容呈現和邏輯思辨,都個性十足,具有特立獨行的反叛精神。
《蟲洞》的風格化首先是語言的,極具個性的語言表達為讀者帶來最直接的愉悅感受。作者的語速是緩慢的,帶有某種悠閑意味,甚而某時會頓下來,這種略帶慵懶的語言無疑最適合一部長篇散文的鋪陳和展開。正是這種不急不緩、從容淡定而又可觸可感的水流一般的敘述,使得作品中無處不在的生存困惑、生活苦難以及個體憂傷得到了緩解,讀來更流暢,更觸動人心:
莫名地,在這一樹接一樹的白里,我看到的都是無法言說的痛,都是無法言說的磨難。這痛和磨難就像躲不過、放不下的日子,每個日子都是一塊卵石,我們仔細打磨,便會看到隱隱的帶著血絲的紋路。是的,所謂的日子便是一塊塊磨難的卵石,我們把它捂出熱度,把它打磨出光澤,我們把它寶貝一樣傳遞給后八,我們的使命便算完結。這時候,我們看到的就該是滿眼的白了,這白一瓣一瓣地,一團一團地,一樹一樹地,一坡一坡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這白溫暖得那樣無辜,那樣傷感,那樣斷腸,這個時候,我們還需要紅的、黃的、紫的、粉的點綴嗎?
而在這種緩慢之中,又穿插著詩性:
我看見冬天的背影略顯疲憊。一年又一年,冬天的日子總是略顯單薄,略顯蹣跚,雪花飄落的方式比果實輕了許多,冰凌懸掛的方式比果實透明了許多,秋天的秧、藤或樹,拔除的拔除,枯死的枯死,干凈的干凈,寂寥的冬天依舊苦苦舉著一柏樹的綠。果實收藏了,種子在;冰河凍結了,流水在;花兒凋謝了,綠葉在;寒夜來了,爐火在。我抬頭望著灰蒙蒙的天,看見一只麻雀飛過。麻雀說曾去看過春天,春天的青草太苦澀,浸泡著太多的心事;麻雀說曾去看過夏天,夏天的花朵太爛漫,刺傷過太多的眼神;麻雀說曾去看過秋天,秋天的果實太沉重,人們的心一直往下沉——雪說來便來了,說走便走了,麻雀其實什么也沒有說,也不會說。
這樣時而冷峻、時而溫情的敘述,是否能吸引更多讀者的眼球呢?《蟲洞》的出現,對讀者的閱讀習慣無疑是一種挑戰。
從本質上講,散文是個體生命的民間史,是最接近本真的歷史。《蟲洞》在選材上力避30年大事記這樣一種平面記錄,作者有選擇、有預謀、有規劃地使一些人物和事件以點狀或塊狀的形式,支撐起整部作品的骨架,無論作品開始的車禍記憶,還是文中關乎生命、死亡、來世的描述,皆有一種打破常規、另辟蹊徑的反叛精神,這種精神恰是一種帶有作者獨特思想印戳的行文,懷有散文藝術的豐富性和活躍性特征。在散文提倡個性化、獨特性的今天,《蟲洞》所帶來的體驗和思考充盈而完整,凸顯出堅定的先鋒性和實驗性姿態。
歌德說過,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內心生活的準確標志。作家的反叛精神,即個性和風格,遠非朝夕之間便可形成,它與作家的創作實踐、人生經驗和哲學領悟密切相關。在自覺融入社會生活、時代變革、生存困惑、順應俗世圭臬的前提下,作家情感覺醒的曲折變化,對社會和人生執拗、尖銳、深刻的體驗和強烈感觸,造就了作家生命高蹈、精神潔癖、理性光芒的個性情懷,這便是《蟲洞》整體的姿態和氣質,它很好地容納了作者的興趣愛好、秉性天賦、氣質性格、藝術修養。趙樹義先生是理科生出身,他的思辨手術刀一般冷靜,甚至近乎冷酷,觀照世界的方式卻是飄忽的、不確定的。在他的“量子力學”視野里,世界只是各種事件不確定性交織之后的結果,這一結果并非事件的全部,而是當時正好發生了且被我們看到了。趙樹義先生把現代物理學、哲學和藝術融為一體,企圖在《蟲洞》中提供一種全新的觀照世界的方式,以此顛覆我們看世界的傳統習慣,從行為上,這無疑是一種反叛,但在精神上,卻在追求另一種更高層面的融合。
四、《蟲洞》獨特的散文性
與其他文體比起來,散文是最接近真實生活、最靠近心靈的一種文學式樣。在散文歷史中,曾有過多次大的變革,理性、感性、個性化,乃至當今的“大散文”、“復調散文”、“文化散文”、“生命散文”、“新散文”等等散文形式的興起和衰敗,其實都很難脫離散文所堅持和倡導的真實、介入、擔當的天性。在相互爭奪話語權的同時,雖有不少散文家在散文的外在表現形式、語言新奇及選材新穎上進行了變革,散文的抒情本質其實一直未曾改變。比起有勇氣打破傳統的先鋒詩人和小說家,散文家無疑是猶疑且彷徨的,在追求理性、智性的散文大道上,蹀躞不已。《蟲洞》是一部具有探索意義的散文作品,它在審智的深入和冷峻的智性方面做了極好的嘗試,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散文性。
1945年,法國最重要的哲學家薩特提出了“介入文學”的美學觀點:“作家選擇揭露世界,特別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這些人面對被如此赤裸裸呈現出來的客體負起他們全部的責任”。《蟲洞》所踐行的無疑就是這種介入性,在這部長篇巨制中,生命個體、生活經驗、生存事件無一不在介入和填充。我國“在場主義”倡導散文創作的精神性、介入性、當下性、自由性、發現性,其中,介入性是最難把握的一種姿態,作家要用語言、思想乃至肉體,整個介入到作品的“場”甚至縫隙當中,讓作者的生命氣息無邊地擴散、融入、消解、中和,使作品更獨特,更個性,從而具有超意義的、標簽式的、印戳般的功用。《蟲洞》在這方面做得很到位,它無論姿態,還是立場,都有某種執拗的、凌厲的、若刀鋒般的介入性:
記憶中的陰影無疑是時光的折痕,它是彎曲的,或者說,時光是有皺紋的,陰影便低垂在這皺紋里,好似一道峽谷。而峽谷不止是一道皺紋,峽谷之中還可能藏著更多更深更密的皺紋。這些皺紋上生長著草、花朵、樹木,還有泥土和石頭,而皺紋之下呢?人的一生有多種時光皺紋,我便睡在這皺紋當中。想象一個正午,樹枝間有蟬鳴,草叢間有蛇,腳下還有流水,再往高處是飛鳥,再往深處是野獸。可這又能如何?我不會因為花香就不醒來,也不會因為蟲獸就不入眠。生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死如此之長,又如此之短;磨難如此之深,又如此之淺。生死不過鹽或磷的晶體,不過晶體侵蝕的皺紋,如果說晶體是生命中的風景,那么,我們為什么不把皺紋也當作風景呢?
由于個體及大眾經驗的有限性、狹隘性,散文文體同類化的特點一度使其淪為一種私己的、低頻的、乃至底層需求和傾訴的文體,而同時,散文的平民化、大眾化、社會化走勢,又決定了它的受眾面有無限擴大的可能。散文的這一特質,決定了其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應具有某種道義上的擔當。《蟲洞》的變革和探索精神本身就是一種擔當,它像一個實驗室,將一粒沙和一滴水,全部投入到作品的大漠大湖中,通過精神上的溝通和審美,呈現出一種對現實、對社會、對時代的道義情懷。更難得的,《蟲洞》的現實性、社會性、時代性并不局限于當下,它還是歷史的。《蟲洞》仿佛一桿旗,有著干預和指引的意義,這種干預和指引適用于每個時代,這一點尤為可貴。當然,《蟲洞》也有瑕疵,作者將他人生的軌跡劃出《蟲洞》30年的弧線,但這個弧度未免太滿了點,滿便會溢出來,某些枝節稍感突兀,令人遺憾。但瑕不掩瑜,《蟲洞》本身存在的意義顯然要大于作者傾注于它的心血,它更像一枚徽記和指紋,在詮釋人與時代、民族和文化關系的同時,又在當代散文領域顯現出一種罕見的典籍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