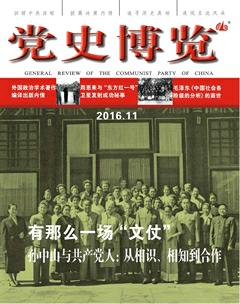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著作編譯出版內(nèi)情
史義軍
“灰皮書”“黃皮書”的由來
20世紀(jì)60年代初至1980年,在中宣部直接領(lǐng)導(dǎo)和計劃下,由人民出版社(用三聯(lián)書店名義)、商務(wù)印書館、世界知識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社出版了兩套叢書,一套習(xí)稱“灰皮書”(時稱老修正主義的著作),一套習(xí)稱“黃皮書”(時稱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著作)。
“灰皮書”的名字是怎么來的呢?漓江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鄭異凡主編的《灰皮書回憶與研究》中說這個發(fā)明權(quán)是康生的。當(dāng)時在中宣部負(fù)責(zé)《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書籍編譯工作簡報》編輯工作的馮修蕙回憶說:“在我的印象中,反修批判工作是在康生的直接關(guān)懷下進(jìn)行的。1963年(或1964年)我曾參加康生在舊中宣部教育樓主持的一次反修批判文章分工和資料工作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許多研究單位和大學(xué)。……‘灰皮書的稱號和發(fā)行據(jù)說都是康生提出來的,康生說這些壞書用一種顏色紙做包裝封,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壞書了……”“黃皮書”基本是以文藝類圖書為主,“文革”后期出版較多。
這些書的范圍很廣,如托洛茨基的著作現(xiàn)已查出八種(《托洛茨基言論》《斯大林評傳》等),《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一至第五輯;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階段》《同斯大林的談話》《卡斯特羅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納吉與匈牙利革命)》;還有《蘇聯(lián)大使館內(nèi)幕》《共產(chǎn)主義掘墓人》《日本結(jié)構(gòu)改革論》,以及吉田茂的《十年回憶》等。這些書的出版,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對于幫助中央及學(xué)術(shù)界了解當(dāng)時外部世界的情況起了不小的作用。
筆者手頭有全套的《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書籍編譯工作簡報》。通過這套《簡報》可以看出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書籍編譯工作流程和當(dāng)年中央有關(guān)部門結(jié)合反修對外國政治出版物的關(guān)注程度。《簡報》是1962年2月5日創(chuàng)刊,至1966年4月13日第65期結(jié)束。
當(dāng)年,負(fù)責(zé)這項工作的具體部門的名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處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書籍編譯工作辦公室”。
這兩套叢書“文革”期間曾一度中斷出版,從1972年起又陸續(xù)出版。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到1984年“灰皮書”已出版190多種,據(jù)說“黃皮書”還要多許多。
中央領(lǐng)導(dǎo)對編譯工作的重視
鄭異凡在《從“灰皮書”到“人民文庫”——“灰皮書”的來龍去脈》一文中回憶說:“1962年秋冬,中宣部曾給毛澤東打報告,匯報解放前和解放后‘老修正主義者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的出版情況(這是編譯局國際室編寫的),同時附上《蘇聯(lián)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的言論選集》(中國人民大學(xué)編譯出版)兩本。同年底,許立群又在編譯局主持寫了一個《關(guān)于一年來(1962年)工作情況和今后工作安排的請示報告》,提出把14個‘老修正主義、機(jī)會主義者的言論編成一部50萬字的《機(jī)會主義、修正主義思想發(fā)展史料選編》。康生看過這個報告后指示,就照這個報告做。”毛澤東對于翻譯出版“老修正主義、機(jī)會主義者”的著作有過多次指示,這些指示多由康生通過主管宣傳工作的部門層層下達(dá),然后由編譯局根據(jù)指示的精神加以落實。康生說:“主席要我們編修正主義文章匯編,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統(tǒng)地出一些書。”還說,毛澤東看了《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論選》很有興趣。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批“灰皮書”。康生對姚溱和包之靜說:“你們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講了幾年了,現(xiàn)在總算出了,你們要把這些書收集齊。”
1962年2月8日,第2期《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書籍編譯工作簡報》刊登了南斯拉夫哲學(xué)家普弗蘭尼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史》上冊已經(jīng)出版、下冊當(dāng)月中旬出版的消息,此消息引起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興趣。隨后,中央理論小組要求中央編譯局譯出該書目錄并寫出簡介報送中央。1962年六七月間,目錄和簡介先由編譯局報送康生、陸定一、陳伯達(dá)、周揚、許立群、姚溱、胡繩等,并由康生辦公室轉(zhuǎn)送中央。在接到鄧小平批示后,中宣部立即開會討論組織翻譯力量,并指令盡快譯出。編譯局南斯拉夫組共組織了20多人進(jìn)行翻譯,跨部門運作,不到半年譯竣,并于次年2月由三聯(lián)書店作為“灰皮書”出版。據(jù)《灰皮書回憶與研究》記載,康生對《馬克思主義史》同樣饒有興趣,當(dāng)他把書拿到手時,非常高興地對寫作班子說:“好書來了,好書來了!你們都應(yīng)該看看!”
1967年,中宣部出版處原處長包之靜回憶說:“六二年秋冬之際,周揚對我說,主席的意見要出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的書,周還說不僅要研究修正主義,還要研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后來康生說要抓緊。沒幾天周揚要姚溱抓。”
1963年11月30日,《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書籍編譯工作簡報》第29期刊登了《修正主義書籍翻譯出版情況和明年的初步設(shè)想》,1964年計劃出版的現(xiàn)代修正主義書籍82種,計劃出版的西方資產(chǎn)階級(包括共產(chǎn)黨的叛徒)評介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書12種,計劃出版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等人的書37種,“托派”第四國際書籍4種。鄭異凡在《灰皮書回憶與研究》中披露了康生的批示:“同意,送主席、常委和書記處。”鄭異凡說:“‘灰皮書的出版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中央辦公廳的逄先知曾電話通知,‘灰皮書的購書證要送給江青;后來通知說‘灰皮書每次要送主席秘書林克同志若干本(兩本或三本)。”
“文革”后重啟“灰皮書”出版工程
從鄭異凡主編的《灰皮書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可知,“文革”前這套叢書的具體領(lǐng)導(dǎo)單位是中宣部。中央編譯局、人民出版社、商務(wù)印書館等單位負(fù)責(zé)組稿、翻譯和出版,許立群、王惠德、包之靜、張惠卿、范用、馮修蕙、沈昌文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后重啟這項工程基本還是這些人,1980年剛剛平反后擔(dān)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曾彥修也加入并具體負(fù)責(zé)了這項工作。
“文革”前出版“灰皮書”是為“反修”斗爭服務(wù),是為了批判這些書。據(jù)曾彥修1984年回憶:“事實上,對那些書一本也沒真批過。可能有過要批判某些書的想法,但因為僅僅知道人家一點東西,又沒有人專門研究過,也就沒有可能去批了。像一論再論陶里亞蒂和‘九評這類當(dāng)時的‘反修文章,并不需要也不是參考了這些書才寫出來的。出版這些書,無論在當(dāng)時及現(xiàn)在最主要的都只是起了了解外部世界,了解敵友我的政治、經(jīng)濟(jì)、思想動態(tài)的作用。”
“文革”結(jié)束后,各方面痛感閉關(guān)鎖國10多年,對外部世界是更加無知,而對外交、國際聯(lián)絡(luò)、理論宣傳、學(xué)術(shù)研究、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教學(xué)研究各方面來說,都有加強(qiáng)了解外部世界的必要。因此,各方面均有繼續(xù)出版這類內(nèi)部參考書的強(qiáng)烈需求。1980年3月,當(dāng)時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負(fù)責(zé)人在與中聯(lián)部七局、蘇聯(lián)東歐研究所的有關(guān)業(yè)務(wù)骨干及負(fù)責(zé)人多次交換意見后,寫出了一份詳細(xì)的《關(guān)于編譯出版有關(guān)當(dāng)代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書籍的意見》,提出:“過去,我們只著重在共運的歷史方面……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何把它轉(zhuǎn)移到當(dāng)代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方面。我們應(yīng)當(dāng)在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chǔ)上,有計劃地翻譯出版這方面的書。”人民出版社一位副總編批示同意,并提出擬在近期內(nèi)找?guī)讉€單位座談一下,再定計劃。此件送到總編輯曾彥修處,曾彥修表示同意。
1980年3月25日,曾彥修寫信給于光遠(yuǎn)(社科院),王惠德(中央編譯局),陳翰伯、王子野、許力以(以上三人屬國家出版事業(yè)管理局。國家出版事業(yè)管理局以下簡稱國家出版局)等五同志,建議由他們出面邀請有關(guān)單位開一次籌備座談會,成立書目選譯小組,然后再開一次有外地三五家出版社參加的具體分工會議。3月31日,陳翰伯在原信上批:“送曾彥修同志。惠德、光遠(yuǎn)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來未能開展此項工作。建議把此件送陳原同志一閱。我希望在七月間開會(指具體分配出版任務(wù)的全國部分出版社會議)。”
4月16日,由王惠德、于光遠(yuǎn)、陳翰伯三人聯(lián)名代表編譯局、社科院馬列所、國家出版局發(fā)出邀請信。4月16日當(dāng)天,全國部分出版社第一次座談會在國家出版局召開。陳翰伯、王惠德、于光遠(yuǎn)以及國家出版局的幾位負(fù)責(zé)人都出席了。會議由陳翰伯主持,與會人員都不約而同地覺得這是把過去荒廢了15年的工作重新拾起來做的一項有意義的工作。會議原則確定先成立一個選題小組,由20世紀(jì)60年代初始終參與此事的馮修蕙任臨時小組召集人,選目小組由中聯(lián)部七局、中聯(lián)部蘇聯(lián)東歐研究所、外交部蘇歐司、馬恩編譯局、北京圖書館、中國圖書進(jìn)口公司、商務(wù)印書館、人民出版社等單位代表組成。并原則決定一旦書目初步弄好后,即由國家出版局召集全國部分出版社會議,分工承擔(dān)任務(wù)。
胡耀邦的重要批示
書目選題小組經(jīng)過多次研究后,擬出了一個初步書目,有100種。因為此項工作時斷時停多年,一下子恢復(fù)這件工作,選目做得有些粗糙。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將這份初步目錄自行打印,并于1980年7月18日以該室名義將書目草稿分發(fā)一些單位和個人征求意見,又單獨分送胡耀邦、胡喬木各一信,并各附打印書目草稿一份,請他們指示意見。據(jù)曾彥修回憶,國際政治編輯室給胡耀邦、胡喬木送材料是自行決定辦理的,事先未征求過任何社級領(lǐng)導(dǎo)人的意見。三天后,即1980年7月21日,胡耀邦在注有“胡(80)1003”編號、注明退還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的原信上批示如下:
我贊成翻譯一些現(xiàn)代社會主義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資產(chǎn)階級關(guān)于社會學(xué)的一些名著。現(xiàn)在我們這方面知識貧乏得驚人。我不知道全國是否有十來個人認(rèn)真讀了十來本這樣的著作。沒有這一條,談什么探索新理論?但這類著作浩如煙海,紙張翻譯都有限,因此要認(rèn)真選譯。你們這一百本,至少有兩千萬字吧。這恐怕不行。應(yīng)該指定一二十人有水平的專家再精選一下。
此件由中央秘書局編號后正式發(fā)回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批示中的“你們”即是對該室而言,不是無對象的批示。胡耀邦并在極少數(shù)書名、作者名或簡介下畫了紅鉛筆線或符號,這就是《斯大林政治傳記》、曼德爾的《關(guān)于過渡社會的理論》等幾本。
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得到胡耀邦復(fù)件后,十分驚喜感動,立即告訴了曾彥修。曾彥修后來回憶說:“因為要大致看完這份目錄并畫上符號,恐非二小時不可。我當(dāng)即批評了有關(guān)同志幾句,大意是:一件這么粗糙的東西為什么可以直送總書記,而且社領(lǐng)導(dǎo)全不知道;其次,籌備會上談過,這東西將來弄好后報書記處,是中宣部的事,不應(yīng)由我們報。之后我深覺此事直寄總書記有點孟浪,當(dāng)即寫了一信與耀邦同志辦公室表示道歉,說明此件是不該送的,但‘文革后的無政府狀態(tài)還未能完全克服,雖承耀邦同志批示鼓勵,但在我們領(lǐng)導(dǎo)的工作上是混亂的,失于控制的,并說明此事將來當(dāng)另由發(fā)起單位向中宣部請示。”
人民出版社得到胡耀邦批示后,選目小組又反復(fù)研究領(lǐng)會這個批示,并修改選題,初步定下了95本選譯書目。
人民出版社牽頭全國多家出版社承擔(dān)任務(wù)
根據(jù)胡耀邦批示精神,1981年1月經(jīng)中宣部同意,國家出版局在京西賓館召開了由全國幾十家出版社和有關(guān)單位參加的座談會。會上確定了這套外國學(xué)術(shù)著作的名稱為“現(xiàn)代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著作選譯”,并確定以人民出版社牽頭全國26家出版社共同承擔(dān)95本中的絕大部分的編譯出版工作。
會議由國家出版局局長陳翰伯主持,副局長許力以在會上說明出版這些書的必要性。王惠德、于光遠(yuǎn)、邊春光(中宣部出版局局長)講話,曾彥修也作為實際的發(fā)起人之一和出版社之一的代表發(fā)了言。
會議規(guī)定,這些書作為內(nèi)部發(fā)行與限國內(nèi)發(fā)行(也不上書架),個別性質(zhì)嚴(yán)重的交有關(guān)機(jī)關(guān)分發(fā)(控制發(fā)行),共三種方式。會上,曾彥修還反復(fù)建議這套書一律不發(fā)到縣,國家出版局同意并做出了決定。
出版座談會后不久,新華出版社已經(jīng)譯好并且已經(jīng)發(fā)排了《權(quán)力學(xué)》《斯大林死亡之謎——貝利亞的陰謀》等書,他們要求將這些書列入這套書內(nèi)。選目小組同意了。原來選目小組并沒有選這些書,這純粹是接受了既成事實。
1981年7月,選目小組準(zhǔn)備了第二批選譯目錄草稿。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張惠卿于7月29日對之提了意見,認(rèn)為第二批書目太雜,很不平衡,要求再精選,然后又將此書目送曾彥修再提意見。曾彥修鑒于當(dāng)年1月分配選譯書目時已有爭搶驚人書名的傾向,即寫出了一份較有系統(tǒng)的意見,并請求國家出版局登在《出版工作》上,作為向有關(guān)兄弟出版社的一點建議。曾彥修認(rèn)為選書的目的應(yīng)該十分明確,重點是:一、馬列主義理論的最新探索;二、歷史上重要的(指馬、恩、列以外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代表性的錯誤著作;三、探索社會主義各國發(fā)展規(guī)律的實事求是的著作(包括對蘇聯(lián)、東歐、古巴、朝鮮、中國等的研究、批評在內(nèi));四、探索在不同國家無產(chǎn)階級如何取得政權(quán)和保持政權(quán),取得政權(quán)后各國共產(chǎn)黨將采取何等措施等問題的著作;五、第三世界中落后地區(qū)的社會主義問題(包括真相、成績、彎路,以至完全失敗等)。同時又提出對下列情況要特別注意,不要選:“一、大量的大部頭的為蘇聯(lián)現(xiàn)政權(quán)吹噓的著作;二、一點馬克思主義不懂,而又批評反對了一輩子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的著作;三、單純以獵奇、爆內(nèi)幕為號召,或沒有重大意義的自傳、回憶錄等一類著作。”并提出“我們要始終強(qiáng)調(diào)嚴(yán)肅性、科學(xué)性和有重要資料價值的資料性著作”。選目小組于1981年8月28日、9月5日兩次討論修訂第二批書目時,曾把曾彥修的意見人手一份作為參考,大家認(rèn)為可以接受。
第二批書目初稿弄出后,選目小組將書目寄給了中宣部的王惠德。王惠德復(fù)信同意,并說比第一批書目好。
胡耀邦批評《權(quán)力學(xué)》等書
1982年,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了蘇聯(lián)阿夫托爾哈諾夫的《權(quán)力學(xué)》。這本書從政治上全面否定斯大林,并對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jìn)行了批判。
5月,胡耀邦批評了《權(quán)力學(xué)》《斯大林死亡之謎——貝利亞的陰謀》等書,人民出版社黨委及總編辦公會議為此專門討論,并于同年6月1日對上級做了詳細(xì)的書面報告,其中說:“今后應(yīng)進(jìn)一步明確選書標(biāo)準(zhǔn),要是名副其實的‘現(xiàn)代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著作選譯,即關(guān)于蘇聯(lián)的歷史經(jīng)驗和現(xiàn)狀,東歐各國的理論與實踐,歐洲共產(chǎn)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lǐng)和學(xué)說,關(guān)于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新探討,‘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性的著作,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政治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歷史理論、未來探索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凡專門以‘爆內(nèi)幕、揭‘罪行而風(fēng)格低、煽動力強(qiáng)的著作、回憶錄,今后一概不得列入本叢書的目錄中。”曾彥修后來回憶說:“這次討論及寫上述報告時,我本人不在京,但我以為這個報告的精神內(nèi)容都是對的,我過去也多次講過這些話。至于耀邦同志指出的那類偏向,則這個報告已明確規(guī)定‘今后一概不得列入本叢書。因此這類問題早在1982年5月就已明確解決。”
8月20日,中宣部根據(jù)胡耀邦指示的精神,以中宣部文件形式發(fā)出《關(guān)于改進(jìn)現(xiàn)代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著作翻譯出版工作的通知》,對出版這類書做了很嚴(yán)格的規(guī)定,并規(guī)定今后甲類書(即問題嚴(yán)重的)只能由人民出版社及其他中央級出版社出版。10月,中宣部又召開了第二次關(guān)于改進(jìn)承擔(dān)出版這套書的全國出版社會議,會議負(fù)責(zé)人、中宣部出版局局長許力以再次詳細(xì)說明了出版這套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強(qiáng)調(diào)了越是反動的書越只能由人民出版社負(fù)責(zé)出版的道理。
到1984年初,列入選目的書出版了近100種,后有人認(rèn)為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書有問題,并提出了嚴(yán)厲的批評。這套承繼20世紀(jì)60年代“灰皮書”的“現(xiàn)代外國政治學(xué)術(shù)著作選譯”叢書的出版工作也就宣告結(jié)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