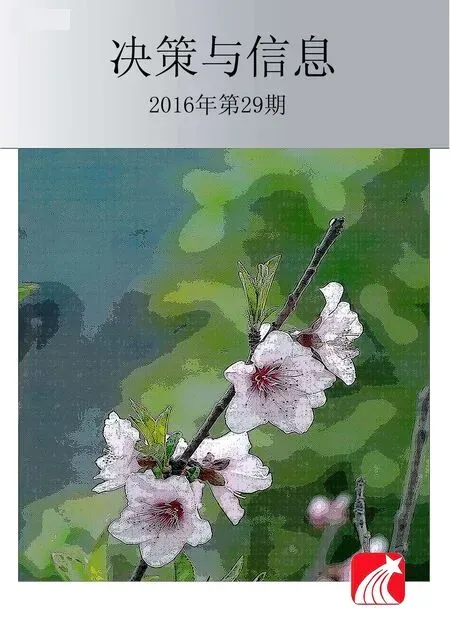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權力觀”
孫婉璐
北京市大興區榆垡鎮人民政府 北京 102603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權力觀”
孫婉璐
北京市大興區榆垡鎮人民政府 北京 102603
“權力和愛情一樣,比較容易被感受到,但是很難被界定和衡量”。權力是國際關系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對這一概念的解釋見仁見智。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是幾次主流大論戰中更高一階段的論戰,本文試圖從權力的來源、國家安全與權力目標、權力如何發生作用以及兩種理論在信息時代的糾葛這幾方面,對比兩者的不同。
權力;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
相同的原因有時會導致不同的效果,反之,當原因發生變化時,國際結果卻依然如此,這是新現實主義的立題之本,華爾茲就是圍繞這個“相等決定性”的問題,拋開個人和國家的層面的問題,圍繞系統結構和互動單元兩個變量來解釋國際政治現實的。國家間存在著現實的或潛在的沖突,在自助系統中它們是理性的行為體,國家把權力作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不遵循自助準則的會被“優勝劣汰”出局。弱小國家會傾向加入聯盟中較弱的一方,因為他們不希望強大一方威脅到其安全,國家的命運取決于對其他國家行為的反應,致使競爭者趨于一致,均勢狀態反復出現,這是新現實主義建構的理論模型。新自由主義是在對新現實主義的批判中發展起來的,基歐漢和奈專注于相互依賴這個概念,以相互依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作為分析變量,把世界的依賴關系分為四種權力模式,試圖對現實世界做出更詳盡、貼切的解釋。后者認為,隨著跨國公司、國際組織作用的凸顯,社會聯系渠道多元化使國內問題和國外問題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化,各種問題沒有明確的等級之分,軍事力量不是解決問題最行之有效的手段,“權力不僅來自于槍桿子”,也來源于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即使在多方面都強大的國家也可能在另一方面存在嚴重的脆弱性。
新現實主義基于剛性的結構,長于在結構框架內對復雜的國際關系精簡化分析;由于對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控制,新自由主義長于從雙邊的角度解釋相互依賴關系。二者都是以一組關鍵的假設為基礎,或推翻別人的假設,建立自己的假設,對不同的核心命題賦予了不同的重要性。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可能沒有哪一概念“權力”更重要了,隨著國際政治現實的多元化發展,“權力”的概念也隨之發展,它的表現形式和作用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權力的來源
已出現的近代合法國家,為什么它們的職能相同,但能力卻不同,有的在國際社會上處于從屬地位,有的處于主導地位,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差別?霍夫曼在70年代時就講過:“與過去相比,權力的衡量標準變得棘手,甚或具有欺騙性”。摩根索把權力界定為“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動的控制力”,華爾茲從誰更能影響誰的角度出發定義權力,由于一國控制他國的能力通常與該國所掌握的資源是分不開的,現實主義往往強調權力的剛性結構,即對資源的擁有和控制。這些資源的擁有者往往是國家行為體,尤其是大國權力的變化往往能影響結構的變化,因此,新現實主義往往具有一些“國家主義”傾向,“極”是一個重要的分析單元。
但日本和韓國等這樣資源稀缺國家,仍然憑其后發之勢,取得了驚人的發展,提升了國家實力。于是,新自由主義辯駁說,權力的大小不能僅僅以國家擁有資源的多少來判斷,他們往往把權力劃分為軟權力和硬權力,并強調軟權力的重要性在不斷上升。非對稱性相互依賴是權力的來源,依賴性較小的行為體擁有較強的權力,該行為體有能力引起變化或以變化相威脅,一旦變化發生,該行為體付出的代價小于他者。如石油輸出國同時對美國和日本減少35%的石油供給,對資源稀缺的日本來說可能是一場嚴重的能源危機,于美國,他可以開發國內一種新的能源代替石油不同,美國在能源方面更有獨立性,權力的差異便顯現出來了。一個在世界多地都有駐軍的美國對于一小撮恐怖分子存在嚴重脆弱性,在信息開放的時代,恐怖分子獲取信息相對容易,而美國對外關注主要是擁有常規軍備的國家行為體。恐怖襲擊者通過控制美國民航飛機的9·11事件,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了致命打擊,那些能夠對結果施加影響的機構、組織甚至個人,都是潛在的權力主體。
二、國家安全與權力目標
現實主義看來,無政府狀態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國家彼此之間存在著安全性競爭,任何國家都不能保證彼此存在矛盾和危機升級時,對手不會動用武力。權力是維護國家基本安全的最好的生存手段。
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生態等各個領域越來越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各國都認識到使用武力解決沖突代價之高,軍事解決變得不那么行之有效。基歐漢和奈以海洋和貨幣領域為例指出,軍事安全目標并不總是優先于其他目標。隨著國家間關系日趨復雜,國家的目標也更加廣泛,非傳統安全重要性日益凸顯。國際體系變得復雜和沒有邊界,問題和行為體增多了,弱國敢于維護自己權力了,大國的相對影響力下降了,世界民主化和平的趨勢必將有所發展,美國的削弱給了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衰落”以有力的現實佐證。
三、權力發生作用的方式
新現實主義對均勢狀態的分析意味著,在一個和平的年代里,強大軍事力量并不意味著戰爭發生或蓄意挑起戰爭,但沒有這種實力,即便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也并不意味著免遭戰爭的危險,從這一點來看,它只是行為體自身安全的一個保護傘,只要擁有相當的權力,即使不發動戰爭,權力的作用可以自動發生,自主行為體間的競爭為世界政治提供了基本驅動力。一旦擁有了權力,權力自然會對潛在的敵人產生威懾力。面對失衡的權力,各國除了試圖增加自身的防衛能力,也會與其他國家結盟以恢復實力均衡,各國對于西班牙的查理一世、法國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侖·波拿巴以及德國的阿道夫·希特勒追求霸權的反應就是如此。
新自由主義認為,“以資源類型為衡量標準的權力與以對結果的影響力為衡量標準的權力之間很少出現一一對應”,衡量權力有兩種途徑,一是資源和潛力,二是對結果的影響力。實力大國往往沒有得到看似與其地位相當的預想結果,如美國在越南、蘇聯在阿富汗戰爭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二戰后,蘇聯也曾在歐洲有相當可觀的軟權力,卻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在國際社會上顏面掃地。這就涉及到一個權力轉化的問題,如何把手中的資源轉化為你想要的結果,對結果更好的把握,具備一定的資源是對結果擁有控制力的基礎。當然,也會有反面的例子,一個善于玩轉權力的國家往往能把自己的實際影響力作為與他國交換或談判的籌碼,就好比一個紙牌高手往往能夠以弱勝強。
為此,國際機制和討價還價式的談判在權力轉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大國認為政治領域的國際機制是合理的,各國的政策選擇受制于機制,政治發生在機制所設定的基本規則內。
華爾茲卻認為,國際社會無法產生一個有效的權力管理者,即使是美國這樣的一枝獨秀。但不論大國還是小國,規則的制定者還是被動遵守者,都尋求自身利益的調整和規則的例外。例如,關貿總協定規則的合法性并未受到參與者的挑戰,但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免受制約,成員試圖曲解或延緩執行規則。這解釋了國際組織本身不可避免的困境,一個規則制定下來或條約的簽訂,在現實中卻看不到效果,并不是規則本身出了問題,而是規則參與者的問題。有人解釋為,規則的具體概念不明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概念的解釋就不同了,但我們也不能排除規則參與者“有意為之”的可能。規則的制定者總是尋求例外,例如,英國是航海自由的保護著,這種地位并未阻止它在戰時干涉航運中立,威爾遜是自由主義理想藍圖的“設計師”,美國自己卻沒有加入國聯,這也是國聯失敗的原因之一,中小國家難免不指責美國“雙重標準”。如此,機制和規范就失去了很大的說服力。成員曲解或延緩規則的執行,正是利用敏感性方面相互依賴的不對稱。
四、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信息時代的糾葛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同樣給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出了一道難題。信息作為一種資源越在經濟、軍事領域的重要性不必贅述。電影《盧旺達飯店》中,胡圖族政客控制的廣播電臺在盧旺達大范圍渲染了圖西族的罪行,強化了兩族之間的矛盾,導致了政治屠殺,這只是90年代信息傳播的作用。21世紀的計算機、通訊設備無論在傳播速度還是影響范圍上都更勝一籌。
現實主義永遠給這個緊密的世界敲響警鐘,最緊密的相互依賴意味著交往的密切,提高了至少是偶爾沖突的可能性,“最激烈的內戰和最血腥的國際戰爭往往發生于高度相似且事務變得密切交織的民族聚居地帶”。新自由主義反駁道,有效的信息傳遞和溝通可以部分地解決安全困境的難題,至少威脅不會那么難以預測,國與國對對方的安全威脅認知會下降,或者說它的認知更接近于現實,以致彼此都能做出有效的危機管理。信息革命使世界的多渠道聯系加深,交往的成本大大降低,世界更接近于相互依賴模式。國家更容易被外界滲透,而不一個暗箱,維持一致的精英政治和等級秩序越來越難。
然而,我們不能否認,信息革命給我們帶來了真實性和虛擬性混淆的難題。信息的制造者和信息及時獲得者掌握了權力資源,因為他們看上去更有說服力,更容易根據這些信息作出先發制人的反應;另一方面,信息量越來越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如何在大量信息中辨別真實且有價值的信息也變得極為重要。即便信息交流存在,但是信息制造者不能得到信息接收者的信任,這樣信息資源的轉化便成了問題所在。與其他資源不同,尤其在當今,信息是從其他領域分化出來的一個問題領域,不信任使信息資源找不到替代品。軍事領域的相互依賴明顯地少于經濟和環境領域的相互依賴,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結構現實主義權力的著眼點在于維持均勢,新自由主義權力的著眼點在于解釋國際機制的變遷。結構現實主義把權力看成一個集成的概念,試圖簡化對行為體的解釋,以期能更好地解釋和預測總體趨勢,然而,過于簡潔也是它的反面批判它的著眼點。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則提出了多種解釋模式,經濟進程、總體權力結構、各問題領域內的權力結構、受國際組織影響的權力模式,或者把兩種以上模式復合使用解釋相互依賴。但也不難找出例外,與民主國家相比,集權國家更像一個黑箱,二者的相互依賴一定不是對等的,但是集權國家并沒有發起戰爭,更精確地說,戰爭并不總是集權國家發起的。
縱觀兩個理論,從分析對象和分析層次上看,與現實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在解釋現實世界上確實更近了一步。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反映出了現實更難被當權者所把握的困境。因為一旦國內外因素變得模糊,利益集團增多,決策者做出決定的難度加大,這便使決策者或國家是“理性人”的假設受到質疑。再者,也可以看到基歐漢和奈在解釋相互依賴關系時的一個缺陷。他們的分析更注重經濟領域,而把政治和軍事領域的解釋看作是新現實主義的專注,進而著墨不多。誠然,石油顯而易見地是經濟領域的資源,這個極易被政治化的議題(把它作為購買武器和軍火的經濟籌碼)被技術化地推到了現實主義的懷下。從區域來看,亞洲的政治很好地證明了新現實主義的理論,中東的政治情況更是如此。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模型更適合當今的歐洲,拉美地區的政治。與其說兩學派的側重點不同,不如說他們是拾對自己論證有利的證據把問題集中到幾個點,正像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批判雖然激烈而尖銳,但卻主要集中在“資本剩余”這個經濟領域。兩個學派的矛盾雖是難以調和的,但是在它們后來的論述和互相抨擊中,卻越來越能發現對方的影子。
[1][美]肯尼迪·華爾茲著,信強譯,蘇長和校:《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2][美]肯尼迪·華爾茲著,張睿壯 劉豐譯,張睿壯校:《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3][美]小約瑟夫·奈著,張小明譯:《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世紀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4][美]羅伯特·基歐漢 約瑟夫·奈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5][美]卡倫·明斯特著,潘忠岐譯:《國際關系精要》,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6][美]羅伯特·吉爾平著,宋新寧 杜建平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孫婉璐(1987.12-),女,籍貫:黑龍江齊齊哈爾,學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關系理論與聯合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