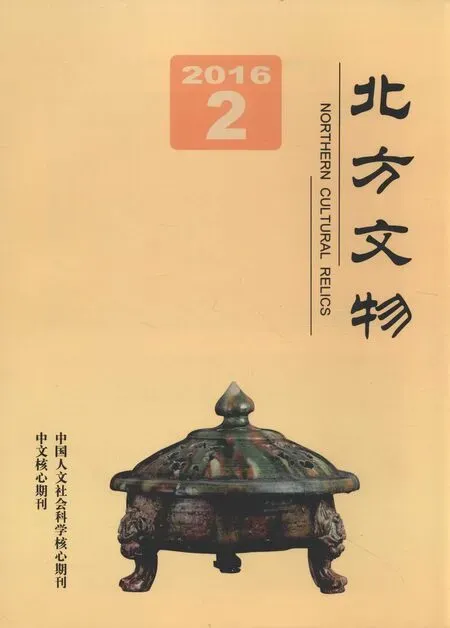元大德五年《涿州新建廟學記碑》的問題
蔡春娟
?
元大德五年《涿州新建廟學記碑》的問題
蔡春娟
元代 涿州 廟學
諸多方志記載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過廟學,且有李元禮撰文之碑,但梳理資料可知,大德五年涿州未修建過廟學,也沒有李元禮撰文之碑,《涿州新建廟學記碑》的撰文人是李謙。清代諸方志沿襲了《日下舊聞》的錯誤記載,一直訛誤至今。
元代涿州屬大都路統轄范疇,下領范陽、房山二縣,范陽為其倚郭縣。州距大都城百余里,當南北要道之沖。據地方志記載,涿州儒學始建于唐代,金、元因之,又有所修葺、重建。關于涿州儒學在元朝時期的修建狀況,相關史料記載較為混亂,本文從《涿州新建廟學記碑》和《涿州重修孔子廟碑》入手,輔以其他資料,解決如下兩個問題:一、大德五年涿州是否修建過廟學;二、大德五年立《涿州新建廟學記碑》撰文人是誰,并在此基礎上,修正清代方志及金石記載的相關錯誤。
一、大德五年修建廟學的問題
相關記載顯示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過廟學,如:
《〔乾隆〕涿州志》卷4《建置志下·碑記》部分載有三塊與元代涿州儒學相關的石碑,分別是“重建孔子廟碑,大德五年,李元禮撰”、“重修孔子廟碑,至正二年,蔡欽撰”、“儒學藏書記碑,至正十年,何伯琦撰”①。
《〔光緒〕畿輔通志》之《金石志三》載元代涿州有三方“重修孔子廟碑”:一為“至元二十二年,李公謙撰”;第二方碑立于大德五年,撰文者有李元禮、李元兩種記載;第三方碑為“至正壬午,蔡欽撰”②。這三方碑主要參考了朱彝尊《日下舊聞》的記載。
清代官修北京地區史志《日下舊聞考》關于元時期涿州儒學的修建,記載:“元大德五年重修,有李元禮撰記;至正二年重修,有蔡欽撰記。”③
《〔光緒〕順天府志》記載最為詳細:“元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病其荒陋,因城東舊址重建,翰林侍讀學士李謙己作記,未見;至正二年,判官張珪重修,蔡欽作記;大德五年重建,李元禮撰碑,未見;泰定四年,學正曹□置禮器,揭傒斯作記;學正龔仁實筑屋藏書,何伯琦作記。”④
就《〔光緒〕順天府志》記載來看,涿州廟學在元代共修建三次,分別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至正二年(1342年)、大德五年(1301年)。很明顯,三次修建并未按時間先后順序記載,可見修志并不細致,可能是將各處資料匯總堆積到了一起。
然而,據至正二年蔡欽撰《涿州重修孔子廟碑》,涿州在大德五年并未有修建廟學之舉。碑文相關記載如下:“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按部至州,憫其荒陋,割月俸,倡率郡僚因故基創造殿宇。翰林侍讀學士李公⑤已嘗文諸石,樹于廟庭。迨今幾六十年,綿歷歲久而塈涂剝落,梁棟腐敗,弗蔽風雨……至元庚辰(后至元六年,1340年),東安張珪庭玉以蔭補官,由大寧簿來判是州……拜謁宣圣廟庭,顧其傾圮,慨然興嘆……于是謀于監郡忽林赤、同知州事禿魯沙、幕賓呂忠、王元孝以及范陽屬官……是役也,經始于至正辛巳(至正元年,1341年)之秋,畢工于壬午(至正二年,1342年)之夏。”⑥文章清楚表明自至元二十一年修建后,直到至正元年才重新修建,這期間將近60年(1284—1341年)沒有重修或重建過。《〔乾隆〕涿州志》卷3《建置志上·學校》總括涿州歷代學校修建情況曰,“按金石文字記……元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按部至州,率郡僚因故基重建;至正二年,東安張珪來判是州,同監郡忽林赤等重修,蔡欽為碑記。明正統元年”⑦,亦未提及大德五年重修之事。
大德五年涿州是否修建過廟學?我們從《涿州新建廟學記》入手來分析。這篇記文存于明代《〔嘉靖〕涿州志》,作者為李謙。清代《〔康熙〕涿州志》、《〔乾隆〕涿州志》、同治續修《涿州志》都未收此文,《〔光緒〕順天府志》曰該碑記“未見”;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涿縣志》⑧亦未收此文。今人編《全元文》第九冊據《〔嘉靖〕涿州志》收錄了此文,但個別字的辨認以及斷句與筆者理解不同,且脫漏一行⑨。現將與重建廟學有關的記載摘錄如下:
襖至元二十一年,監察御史趙天爵按行至郡,謁拜先圣于廟之故墟,愀然改容曰:“郡邑皆廟事□□,涿近居王畿,四方之所觀赴,而神未有宇,何以□化。憲司所職,在宣化厲(勵)學,予何敢不虔。”乃捐俸幣□□□□,州判官馮德仁從而和之,鄉之士民迭相□□□□幣千緡。度財置用,屬役于范陽尉李甫進,首創大成殿,未幾落成。二十三年,甫進由尉升尹,會東平□復來為州學正,郡之子弟秀民皆從之學,尋構講□之堂,齋廬庖舍以次就緒。二十七年,范陽孫鈞嗣為學正,甫進出私帑楮幣千緡,鄉耆元鼎諸人又益之千五百緡,為繪塑之資。乃訪求闕里所藏司寇像,模仿塑飭,睟容惟肖,彰施足征,亞圣十哲列坐環視。越二十八年春二月,諸生行釋菜禮,郡人來觀者瞻拜肅敬,以謂前所未睹,□□盛哉。二學正來京師合辭請記。⑩
由上可知此次涿州儒學修建的大概過程:監察御史趙天爵巡按至涿州,見廟學破敗,首倡重建,捐資者有州判官馮德仁以及州中士民,工程的監督實施者是倚郭縣范陽縣尉(后升為尹)李甫進。廟學的修建不是在至元二十一年一蹴而成的,而是自至元二十一年到二十八年(1291年)間相繼進行了大成殿、講堂、齋舍、廚房的構建及先圣十哲像的繪塑。至元二十八年,涿州學正到京師請李謙為廟學作記,所以這篇記文,應作于至元二十八年或之后。新學建成,除請人撰寫記文外,往往還要刻石紀念以勵后人。這篇碑文的立石時間從現存拓片可以得知。

既然李謙所撰寫的趙天爵倡導重建廟學碑立于大德五年,那么《〔乾隆〕涿州志》“碑記”部分所載元代三塊石碑之一,即大德五年的“重建孔子廟碑”應該就是此碑。它記載的是涿州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修建廟學之事,并非大德五年重修過廟學。由于此次廟學修建,從倡導啟動到立石經歷了近20年(1284—1301年),清代方志或將之誤作為兩次修建,或將大德五年的立石時間作為一次廟學修建,因而出現錯誤記載。
二、關于大德五年立《涿州新建廟學記碑》的撰文者
從上述諸方志及現存拓片可知,大德五年立《涿州新建廟學記碑》的撰文者出現了三種不同記載,即李謙、李元禮、李元。到底誰是真的撰文人?


三、小 結
由上分析可知,大德五年涿州未有重建廟學之舉,更沒有李元禮撰文之碑。大德五年所立廟學碑是李謙撰文,李元禮書丹,記載涿州自至元二十一年監察御史趙天爵首倡,至至元二十八年范陽縣尹李甫進相繼修建廟學之事。由于自清初始,歷次修《涿州志》缺載此文,碑刻文字又已磨損不清,導致清代諸《涿州志》據《日下舊聞》或碑刻文字誤將立石時間作為重建廟學時間,將書丹人誤為撰文人抄錄,一直訛誤至今。《〔光緒〕順天府志》的《金石志》部分雖然采用了正確的記載,然卷帙浩繁,統修者未能將《經政志》和《金石志》部分充分結合考證,致使同一記事在同一書的不同卷次記載相左。
據此,相關方志及金石著作的記載應修正如下:

《〔光緒〕畿輔通志》卷140《金石三》三方“重修孔子廟碑”中,第一方是不存在的,第二方碑中相關“李元禮”、“李元”皆應修正為“李謙”。
《日下舊聞考》卷127《京畿·涿州一》應為:“元至元二十一年重修,有李謙撰記;至正二年重修,有蔡欽撰記。”
《〔光緒〕順天府志》卷61《經政志八·學校上》應為:“元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病其荒陋,因城東舊址重建,翰林侍讀學士李謙己作記;至正二年,判官張珪重修,蔡欽作記;泰定四年,學正曹□置禮器,揭傒斯作記;學正龔仁實筑屋藏書,吳當作記。”
《金石匯目分編》卷1應補充為“元涿州新建廟學記,李謙撰,李元禮正書,劉賡篆額,大德五年六月既望”。
《平安館藏碑目》應為:“涿州新建廟學記,大德五年六月,李謙撰,李元禮書,劉賡題額。”
《京畿金石考》應為:“元孔子廟碑,李謙撰,大德五年立。”
注 釋:
① 吳山鳳:《〔乾隆〕涿州志》卷4《建置志下·碑記》,乾隆三十年刻本,下同,第18頁。
② 李鴻章、黃彭年:《〔光緒〕畿輔通志》卷140《金石三》,光緒十年刻本,第51、52、55頁。
③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127《京畿·涿州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下同,第2053頁。
④ 周家楣、繆荃孫:《〔光緒〕順天府志》卷61《經政志八·學校上》, 為敘述簡略,將原文所引蔡欽《記》、揭傒斯《記》、何伯琦《記》省略。《中國地方志集成·北京府縣志輯》2,上海書店出版社等2002年,下同,第147、148頁。
⑤ 該碑文明、清及民國方志大都載錄,清代及民國方志所錄,在“李公”后有一“謙”字,然查拓片及明代《〔嘉靖〕涿州志》所錄,沒有“謙”字。拓片見《涿州貞石錄》,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40頁。
⑥ 據《涿州貞石錄》所輯《涿州重修孔子廟碑銘》拓片文字,第40頁。
⑦ 吳山鳳:《〔乾隆〕涿州志》卷3《建置志上·學校》,第12頁。
⑧ 宋大章、周存培:《〔民國〕涿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135號,成文出版社1968年。
⑨ 《全元文》該文倒數第三行“喪亂以來,達無足怪者”,中間脫漏一行,應為“喪亂以來,逮□六七十年,黨遂寂然,不聞弦誦之音,子衿挑達,無足怪者。”倒數第二行“乃今郡學異,復遙朔南混一之后”也不通,應為“乃今郡學興復,□朔南混一之后”。《全元文》第九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頁。
⑩ 史直臣:《〔嘉靖〕涿州志》卷10《涿州新建廟學記》,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287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427頁。














〔實習編輯、校對 陰美琳〕
蔡春娟,女,1970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元代史研究,郵編100732。
K247
A
1001-0483(2016)02-0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