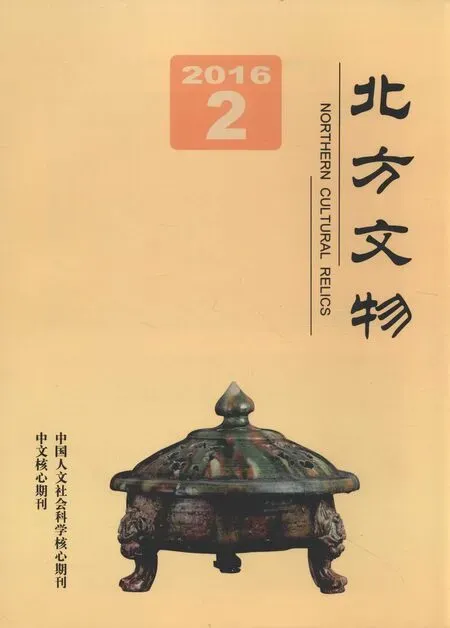博物館理事會制的本土化分析
付 瑩
?
博物館理事會制的本土化分析
付 瑩
博物館理事會制 本土化分析 人文和制度環境
目前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擬廣泛推行博物館理事會治理模式的行為應界定為“移植”。而“移植”來的理事會制需結合我國博物館賴以存在的本土資源進行再造,以及精心培育適宜理事會制存活的人文和制度環境。博物館理事會制的本土化改造主要涉及理事會的功能重塑,建構新型的博物館理事會與政府部門、與管理層的關系;培育理事會治理文化亟需涵養對關涉博物館的法律、法規之尊崇和敬畏之情;培育理事會治理的宏觀制度環境亟待提升相關規范性法律文件的位階。
由政府主管部門主導的博物館理事會制建設工作,在總結一些民辦、行業博物館理事會制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正按照區別情況、分類實施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穩步推進。然而,這項構建博物館法人治理模式的創新實踐活動也面臨諸多不解或疑慮,如目前大范圍試點和擬廣泛推行博物館理事會制的行為究竟是某種程度的“借鑒”還是“移植”,如何結合我國博物館賴以存在的本土資源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及培育可供其存活的土壤而防止“水土不服”等。著眼于構建真正“有效管用”的博物館理事會制,有必要對上述問題展開較為深入的探討。
一、“借鑒”抑或“移植”——汲取博物館理事會制精華的行為性質研判
博物館法人治理研究的相關著述在論及吸收理事會治理模式的精神時,較多使用了“借鑒”和“移植”兩個概念。但據專門從事中外法律制度比較研究的學者看來,“借鑒”是將別國的制度、原則作為一種參考、參照,并不負有一定要將其所指向的事物引入的義務。而“移植”則必須達到將別國的東西吸收進來,植入本國的制度之中,并予以施行的程度。因此,“借鑒”比“移植”程度淺得多,二者不能互換①。這種區分對判斷我國博物館之于理事會制的行為性質有著現實意義。目前擬廣泛推行理事會制的行為究竟是“借鑒”,還是屬于“移植”?若為前者,則斷無引入理事會制的義務和緊迫性可言;若為后者,則實施理事會制乃構建法人治理結構的必然舉措。從“移植”一詞本身的特征和規律及我國博物館的制度發展史考察,目前推行博物館理事會制的做法或解讀為“移植”似乎更為妥帖,理由:其一,“移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積極、主動地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先進制度形式、體系和理論“植入”到自己的制度體系之中的實踐活動。目前在博物館推行理事會制正是由政府主導的推進型行為,這可以從“明確要求”公共博物館逐步實行理事會決策的運行機制,到“推動”博物館組建理事會的政策演變②及具體部署③等方面得以印證;其二,縱觀歷史,雖然民國時期的博物館普遍沿用歐美模式,實行理事會制度④,但一來因為政治跌宕,其并沒有得以很好延續和推行,二來博物館事業“尚在萌芽”⑤,理事會制的運用不過是“西學東漸”背景下一些博物館的“仿照”之作⑥,最多可稱之為某種“借鑒”而欠缺制度“移植”的基本特性;其三,雖然理事會(或董事會)治理模式在我國一些經濟體中有著較為成功的實踐,但博物館界建構理事會治理模式時,依然將目光聚焦于其在國外博物館運行的歷史和現況。
二、博物館理事會制的本土化改造
現有管理機制中久存有礙博物館高效運行的痼疾,因此期望“舶來”的理事會制能夠祛除頑疾并激發博物館的活力。但須承認,博物館理事會制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普遍存在著差異化的實踐,這或可從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治理結構及法律政策環境等方面加以考察,或可從不同類型博物館的性質、資源配置模式等方面得到反映⑦。故而,應結合本土資源對其進行本土化建構,以減弱移植來的理事會制與現有博物館治理文化、制度的沖突,避免陷入“南橘北枳”的窘境。現有兩種不同觀點。贊同者認為,理事會制早已在國外博物館中有了成熟的運用,我國博物館理當加以吸收和利用;與此相反的觀點是,我國博物館,尤其是作為政府部門附屬和職能延伸的國有博物館,理事會制根本不適宜。其實,它們表象上的交鋒映襯出的恰巧是對理事會制的本土化改造及其適宜環境的培育問題,主要涉及從現實環境出發的博物館理事會功能重塑、在厘清“政事關系”中建構新型的博物館理事會與政府關系,以及恰當界定博物館理事會與管理層關系等內容。
(一)結合博物館角色定位,重塑理事會功能

其次,考慮到博物館處于逐步“去行政化”的過渡階段,從穩妥角度出發,主張博物館理事會可先進行一些咨詢、監督工作。然而,如果暫且在使博物館理事會發揮應有的作用方面作出某種“妥協”和“退讓”,或許會產生某些負面影響。譬如,這或許為不贊同博物館理事會制的觀點作了最好的注解,而且長期來看,將更為不利真正意義上理事會制的推行。因為,一個不能充分發揮應有功能的理事會,難以消弭博物館理事會制不過是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應景之作”之認識。
(二)厘清“政事關系”, 建構新型博物館理事會與政府關系


(三)建構權責清晰、地位獨立的博物館理事會與管理層關系

三、培育適宜博物館理事會制存活的人文和制度環境
(一)營造博物館理事會制運行的文化氛圍
博物館理事會制是博物館治理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無不刻著特定國家或地區的歷史人文、社會價值和制度運作環境的烙印。如不經過本土化的生發養成過程,硬性植入的結果只能是簡單模仿或者復制一個軀殼性質的理事會架構。我國博物館受到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級、服從等觀念和思維的影響,行政化色彩極為濃厚。雖然民國時期的博物館效仿歐美治館模式時,“法人治理”文化有過短暫的輝煌,但畢竟沒有延續。《文物保護法》《博物館條例》等專門調整博物館相關行為的法律法規所承載的現代政府依法依規行事、權力有限且邊界清晰、公共文化資源的公眾參與和享有等價值觀念、理念和精神并沒有內化為從業者的內心需要。顯然,將這種治理文化置于法人治理構架下檢視,很容易發現其與理事會制所要求的社會共同參與、各相關方均依法依規行事的治理文化格格不入。事實表明,理事會制的實施尤其需要治理文化中內含著制度和規則被尊崇和信仰的成分。具體地可從如下方面著手培育這種治理文化,即培養對《文物保護法》《博物館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敬畏之情、慣于法治思維;理事會依《博物館章程》《理事會規則》行事,管理層僅對理事會負責;形成重大事項由博物館理事會決策的機制;形成對違反上述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和懲戒機制。
(二)培育博物館理事會制運行的制度環境
目前我國博物館運行中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無論位階還是相關制度和規則的完備程度,均不能解決博物館理事會制的制度依托問題。不可否認,建立文化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的試點單位在理事會組織架構、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但多數并沒有真正實現“決策監督”職能,而僅停留在“輔助決策機構”和“議事決策機構”層面。可見,理事會制的實施有必要從治理結構、治理機制和治理規則等方面構建微觀制度環境外,還需要一個銜接和配套合理的宏觀制度環境。概而論之,理想的博物館理事會制的宏觀制度環境至少應滿足下述條件:明確規定博物館實行法人治理結構,其中決策機構法定為理事會(或董事會、管委會等形式)。一些博物館發達國家均有專門和詳盡規定理事會制的法律,如1963年《大英博物館法》規定其館的法人團體為博物館的理事會;昭和二十六年《日本博物館法》規定董事會(理事會)成員應由該博物館的當地政府教育委員會指定;1982年《韓國社會教育法》明確規定博物館和圖書館的社會教育機構地位。
如此看來,我國博物館運行的宏觀制度環境顯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無論涉及組建理事會的全國公共博物館定級與評估制度,還是“明確提出”探索理事會決策機制要求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和《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等,均為政策性質的文件而不屬法律、法規,而作為唯一專門性行政法規的《博物館條例》也僅規定“博物館應當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健全有關組織管理制度”。因此,我國博物館實施理事會制的宏觀制度環境仍有待改善,制定專門的《博物館法》、《理事會組織法》等,乃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推行博物館理事會制“于法有據”的題中應有之義。
注 釋:
① 何勤華:《關于法律移植語境中幾個概念的分析》,《法治論叢》2002年第5 期。
② 詳見2010年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關于進一步做好公共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文物博發〔2010〕8號);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③ 根據國家文物局安排,2015年上半年完成博物館理事會制度試點工作,下半年在總結經驗基礎上逐步擴大:2016年年底之前,爭取一半以上的省級博物館建立理事會制度。
④ 周婧景、嚴建強:《民國時期的博物館理事會及其啟示》,《東南文化》2014年第4期。
⑤ 中國博物館協會:《中國博物館一覽》,中國博物館協會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出版(1936年),第1頁。
⑥⑦⑧宋新潮:《關于博物館理事會制度建設的若干思考》,《東南文化》2014年第5期。
⑨ 張健 :《對發達國家博物館管理的學習與借鑒》,《博物館研究》2011 年第1 期。
⑩ 付瑩:《博物館理事制建設的幾個認識誤區》,《中國文物報》2015年6月9日第6版。





〔責任編輯、校對 王孝華〕
付瑩,男,1966年生,深圳博物館改革開放史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館員,郵編518026。
G26
A
1001-0483(2016)02-01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