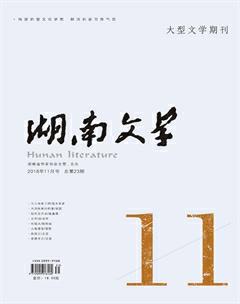我那月光下的溪流
→文紫湘
我那月光下的溪流
→文紫湘
我是在一個有月光的晚上走近了這條小溪,走進了一個伸手可以觸摸到的遙遠的時代,走進了一個人山重水復的心靈境域。這個人也是走了很遠的路才來到這里的。他一到這里就愛上了這個地方,愛上了這條暫時還沒有命名的溪流,愛上了這一方山水,愛上了這一地的月光。他說:這是我的溪流,這是我的風景,我要把那些隱藏在石頭內部的光亮喚醒。
一個壯闊的時代慢慢地浮現在崖壁上。
一個遙遠的時代因此可以伸手觸摸到。
浯溪,因此就有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地的月光,因此而流淌著潺潺的浪漫情思。
哪怕是千年之后,你來聆聽浯溪,也不要在白天來,而要選擇一個有月光的晚上來。浯溪的明月光,無疑給人以“疑是地上霜”的感覺。浯溪的月光灑在湘江上,讓人瞬間就想起杜子美“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的詩句來。
湘江從九嶷山和海洋山兩個源頭一路跌宕而來,把瀟和湘兩條大水匯合在一起,在永州城邊的蘋島那個地方“瀟水添湘闊”,浩浩蕩蕩,有了大江大河的氣象。流到浯溪時,又前行了一百多里,又有十數條小澗小溪撲進了她的懷抱。浯溪就是其中的一條。
一千年以前的浯溪是清澈見底的,是掬一捧起來就可以喝的。那些贊美她的人形容:“凝流綠可染,積翠浮堪擷”,“龍宮開玉閘,瀉出碎瓊琚”;“溪聲如共語,山鳥自呼名”,是一幅有色有聲的畫。讓人流連忘返,讓人“策杖閑吟久”!當一個宦游的詩人路過這里,為殊異的風景吸引,深深地愛上她,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這個人出生在遠離我們已有千年之久的遙遠的唐朝,姓元名結字次山。
元結不是永州人。但元結與永州這塊土地注定要有糾結不清的緣分。
這個鮮卑族拓拔氏的后人出生在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時光之一的大唐盛世。那一年是公元七一九年,唐玄宗開元七年。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加、安王篤薩波提皆上表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唐救援。康國表文稱與大食爭戰已三十五年,六年以來,以眾寡懸殊,力不能敵,獻好馬一、波斯駱駝一,乞望援助。俱密王且表請“處分大食”。養馬奴毛仲“有寵”,“玄宗或時不見,輒悄然若失”。與元結同一年出生的還有個后來名揚整個大唐甚至永垂后世的女人,宮廷音樂家、歌舞家楊玉環。這個小當朝皇帝三十四歲的女人,注定要在青春華年被老皇帝寵愛進而影響帝國的命運,并以她三十七歲的悲劇人生為王朝的變亂埋單。
當時,這個國家正在充當著國際警察的角色,能養戰馬的人被視為功臣。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可能就要命途多舛了!
元結起步時就很不順利。二十八歲,第一次赴京都長安應試,遇到宰相李林甫以“野無遺賢”的混賬邏輯為借口,使當年士子無一人中榜,其中還包括后來名垂千古的曠世詩圣杜甫亦鎩羽而歸。熬到三十四歲,因為創作成績突出,元結受到中央政府文化官員的賞識,破格舉進士,擢為進士第,撈到了一張進入體制的門票。但是,仍然沒有官做,仍然“偏寓商余”,隱居在商余山中,遠遠地翹首等待機會。
他正式步入仕途時已經四十歲了。而且,是在時局變亂的端口。
開元盛世把大唐的氣數推向了極至,推到了頂峰,推到了分水嶺的最高處。接下來便是下滑,便是衰弱。標志性的事件是被貴妃楊玉環收為干兒子的邊陲大將安祿山和其部將史思明的叛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余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白居易《長恨歌》)逃亡途中,唐玄宗在自己的謫系衛戍部隊的緊緊逼迫下,于萬般無奈之際賜死被認為是“禍水”的心愛紅顏楊玉環,并遠避蜀地。太子李亨即位,稱肅宗。
元結在官場人物的推薦下,被新皇帝召見問策,獻上三篇《時議》,受到賞識,被授為右金吾兵曹參軍,文人帶兵,參與平亂。所謂亂世出英雄,元結抓住了時機,在動亂的時局中表現出臨危不亂的英雄品格。他鎮守泌南地區,“見危不撓,臨難遺身”,將士們備受鼓舞,精神抖擻,威風凜凜,叛軍不敢貿然南侵,從而保全十五座城池,寸土不失。叛亂平息后,因為領兵有功,晉升為水部員外郎,后又授為道州刺史。
這便有了元結與浯溪、與瀟湘、與永州的邂逅。
雖然道州和永州在歷史上曾經平起平坐過,但更多的時候,它是永州轄區的一部分,地理上更是瀟湘流域不可分割的襟帶。我在這里是把道州當作永州的一部分來說的,即便是說唐代元結時期的道州。這不僅是一個習慣,而是一種尊重。對現實和歷史的尊重。
元結一家仿佛是與永州這塊土地有著上天注定的緣分。還在他年少的時候,他的父親被調任為道州延唐縣丞,即今永州寧遠縣,是個政府辦主任一類的職務。書上有說沒有到任的,也有說到任后一段時間就辭職不干了,反正是沒有權威的記載,算是存疑。但元結是扎扎實實到道州做了刺史的,他的兒子元友讓也曾來到道州做過官,這都是留有事跡、史冊有載的。地方志上也寫得明明白白。
元結來道州的時候是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二月,到達的時候是代宗二年五月,在路上足足走了六個月。當然不是元結步行了六個月,而是船走了六個月。他是坐船來的,從他帶兵鎮守的九江出發,溯長江,越洞庭湖,又沿湘江而上,走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在九江的時候,他熬到了安史之亂最終被平息。他經歷了這場變亂,他看到了天下蒼生流離失所,困苦不堪,生靈涂炭。他本人也在領軍平叛的過程中飽受了離亂之苦,他理所當然要對戰亂的平息而歡欣鼓舞。他打心眼里盼望中興的局面出現。于是拿起手中的筆,乘興寫下心中的感受——《大唐中興頌》。文章不長,總共才二百六十三個字,先用八十余字的短序說明安史之亂的來龍去脈,再用十五韻三句一韻的頌文來歌頌肅宗“盛德之興”,為“群生萬福”而歡欣鼓舞。這是一篇引起爭議的文字,批評的人當然引之為歌功頌德的馬屁文章;褒揚的人則認為,這是一篇“高簡古雅,義正辭嚴”的稀世雄文,明頌暗譏,警策后人,是“金石之音,星斗之文,云煙之字”,充分地表現了元次山的忠肝義膽。
元結是不是想憑這一篇文章取悅皇權我們不得而知,事實是元結寫了這篇頌文的第二年就向朝廷表達了辭官歸養的心愿,并被皇帝應允。只是不久,生病的皇帝在宮廷政變中驚憂而死,后繼者沒有讓元結歸養休息,反而授其道州刺史。
元結走了六個月才走到道州。
他走得很辛苦。在過陽明山大峽谷時,他用“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航船似欲升天”的詩句,描述被稱為“瀧河”的湘江上游河道的湍急。他的目的地自古以來即被稱為南蠻之地,讓人聽了心生畏懼。即使是到了相對繁榮的唐代,道州依然被視為偏遠落后的地區,為官為吏誰都不愿意選擇這樣的地方。這個地方的官員,基本上由兩類人構成,一類是年輕干部,來這艱苦之地鍛煉,以待日后提拔重用;一類是犯了錯誤的官員,到這里來接受教育或變相懲罰。元結顯然不屬于后一類。但作為前一類,他的年紀又稍微偏大了一點,有一點點不煩舟車勞頓的感覺。可是他并無怨懟,也無畏葸,而是從容赴任了。
沿途的風景美麗而壯觀。從長江到洞庭湖,再到湘江,他肯定領略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絢麗,感受了“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的美妙情境。只是,他沒有讓船工停下手中的槁櫓,哪怕是急湍猛浪,也在逆流而上。一條又一條的支流來匯湘江,他沒有流連,沒有停下腳步來。甚至風雨兼程,一路往前。
但是在浯溪,確切地講是在瀟水與湘水匯合的下游百里處,他被一條無名的小溪感動了,被她的美深深地打動。他讓船工停下了手中的槁櫓,泊舟上岸,順著暫時還沒有被命名的小溪一路深入。那溪流的清澈、甘冽讓他情不自禁地陶醉了,還有傍水而生的猗蘭的幽香也讓他沉醉不已。一個北方人眼中的南方之美,簡直就是致命的誘惑。
不走了,就是這里了。就在這里安家吧!不管仕途還要走多遠,不管宦海還要漂泊多少年,先在這里安一個家吧,把家小安放在這里,把靈魂安放在這里,把心安放在這里,身體就任由它去顛簸。這是我的溪流,是我一生一世的家園。總有一天,我要在這里長住下來,“修耕釣以自資”,不再東奔西走,不再漂泊流浪,像陶淵明一樣詩酒自適、頤養天年。
這個愿望早晚要實現。但此時此刻,他得先到道州去履職。
元結在道州做了三年最高行政長官。其間一度為人誣陷,罷去官職,被勒令前往衡陽湖南觀察使治所述職。接著又官復原職,再授道州刺史。除去旅途上的折騰,元結在道州真正施政的時間并不是很長。但是,他雷厲風行,在很短的時間里做出了一番可觀的成績。
在他來到道州前不久,當地被稱為“西原夷”的少數民族曾舉行暴動,攻入道州城,焚燒殺掠,幾盡而去。初來乍到,元結看到道州簡直就是一座荒蕪的頹城:“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絕,言速行步遲。”“耆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馀寇蟻聚,尚未歸降。”他觸景生情,潸然淚下。懷著十分復雜的心情給皇帝寫了一封不無反諷的“感謝信”,感謝朝廷把自己派到了這個南蠻之地。他還創作了一首《舂陵行》來抒發胸中的感慨。在詩前的序文里寫道:“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任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雖然對個人的前途不抱樂觀的態度,但還是一心想著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
他是一個有膽有識的人,是一個富于正義感的人,是一個真正關心國家安危和百姓疾苦的政治家,也有很強的管理能力和施政能力,而且又愿意為民辦事。履職之初,他就大膽實施救困蘇民之政,收容流亡人口。立竿見影,“聞風而歸者萬余家”。經過一番治理,使道州漸漸地恢復了元氣。就連遠在四川過著寄寓生活的詩友杜甫也聞聽到了元結的作為,為道州的變化而贊嘆:“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連暴動的少數民族“夷軍”也為之感動,不再進攻道州。
元結是敢于為民請命的人。因為連年的戰亂,軍費浩繁,朝廷征斂苛重。作為征斂政策的具體落實者,元結甘冒抗命之罪,蠲免百姓的賦稅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余萬緡,惠及百姓。為官一任,惠澤一方。道州人理所當然要為他立石頌德。
但元結骨子里是一位詩人。他用《舂陵行》《賊退示官人》來描寫時艱,抒寫憂國憂民的深情。當政事好轉,地方安寧下來以后,他就有了怡然愉悅的心情,樂山渴水,詩興勃發,寫下了不少山水詩文。
先是在道州官衙附近信步游覽,他發現了一條無名小溪,俊秀可人,揮筆寫下《右溪記》:“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以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立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文章雖短,卻是唐宋紀游文學的開山之作。可以說,直接開啟了柳宗元《永州八記》的先聲。
道州城東瀟水河中有“獨石在水中,狀如游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貯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元結把他命名為石魚湖,并鐫銘于湖上,又作詩以歌之。境內的九嶷山更是元結心儀的地方。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九嶷山舜帝陵是中華民族人文始祖舜帝魂歸之所、靈寢之地,在元結這樣一個注重倫理道德的詩人政治家眼里,那是一定要要去朝拜的圣地。他不僅親自去朝拜了,還感山懷水,情傾筆端,寫下《九疑圖記》:“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數。中峰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抒發了景仰之情。
更遠的地方他走到了江華瑤鄉,游覽了風景幽美的陽華巖——這個名字也是元結親自命定的,他真心實意地評價:“吾游處山林幾十年,所見泉石好陽華殊異而可嘉者未有也。”在《陽華巖銘有序》中,他感嘆:“海內厭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焉。誰家能此地,終身可自全。”他的內弟,書法家瞿令問,時任江華縣大夫,于永泰丙午年(公元766年)把這篇銘記刻在巖壁上,及引來唐代以后眾多游人的題詠,使之成為一方名勝。
面對荒蕪的土地,元結似乎有命名的癖好。創造性的詩人或許都是命名者。
在數次往來湘江上時,他為湘江兩岸的旖旎風光所吸引,寫下了八首船歌——《欸乃曲》,贊美湘江。在路過零陵古城時,他于城西河岸發現了一座幽邃的巖洞,深入進去探奇,并為之賦詩寫銘,命名為“朝陽巖”。他通過命名的方式,為瀟湘大地破除了文化的荒煙。他是瀟湘文化的拓荒者、先行者,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
時代應該向那些真正的創造者脫帽致敬!
接下來,元結被派往更南邊做容州刺史,兼容管經略使、容州都督,實際上就是容州的軍政一把手。
容州,它的治所就在今天廣西的容縣。當時的容州共轄十四州六縣,包括現在廣西的容縣、陸川、玉林、博白、岑溪、合浦、浦北、靈山和廣東的信宜、茂名、亷江等地,比道州的地盤大到不知哪里去了。因為受到安史之亂的影響,“頻詔征發嶺南兵”,加之橫征暴斂,老百姓的元氣大傷。這里又是壯、瑤等少數民族居住地,他們聚首聯合,奮起反抗,曾一度攻占容州城達十幾年之久。元結的前幾任官員幾乎都沒有到職視事,或寄身梧州,或暫駐藤州,遠距離主理政務,基本上無所作為。元結剛剛上任時,也是先“寄理梧州”,沒有直接到崗位去。他得先了解一下情況。
離開道州時,他沿瀟水而下,進入湘江,到了浯溪,把家眷都安頓在這里。
元結是一個有著強烈自我意識的人。他一直在尋找一個可以安身托命的地方。他早年應舉落第歸隱商余山。安祿山反,他率族人避難猗圩洞,因號猗圩子,就是在尋找一處能從現實中脫身的隱秘的去處。但是,大地之上,真正找一個能托放身家性命、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地方又談何容易。這一次他選擇了永州,選擇了瀟湘,選擇了浯溪。他把家安在這里,把家眷安頓在這里,也把心安放在這里。然后,他“單車將命”,不顧疾病纏身,前往梧州,暫時駐節。年邁的母親想到兒子此去前途未卜,不禁心頭發酸,老淚縱橫。左鄰右舍都為那悲泣聲所動,紛紛愴然涕下。但元結還是揮揮衣袖,慨然而去。
他確實是一個優秀的官員,飽讀詩書,膽識過人,不僅精通為將之道,還熟知為人之道。他突破時俗的框郁,完全摒棄了那種歧視少數民族的觀念,摒棄了那種把少數民族不當人看、一味武力鎮壓的愚蠢辦法。在梧州短暫駐節,了解容州的情況后,就赤手空拳,直接到任上去了。他懷著一個安定團結的良好愿望,懷著一腔感天動地的悲憫情懷,深入到山區瑤寨,會見瑤族首領,曉以大義,勸勉撫慰,歃血為盟,以心換心,獲得了理解與信任。也穩定了局面。“六旬而八州定”。兩個月之內,八個州就恢復了安定。確實不簡單。
飽受流離之苦的大詩人杜甫聽到這件事,大發感慨:朝廷要是能得到十個元結這樣的人才,天下安定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元結在容州這個舞臺上揮灑自如,做了不少的事情,留下了很大的政聲。
只是,在元結的心里,一刻也沒有忘記浯溪。妻兒老母都留在浯溪,他想望著有朝一日,回到浯溪與親人團聚,長相廝守。他確實很快就回來了。這一年是公元七六九年,是他經略容州的第二年,他因母喪請辭,奉詔守制。這一次他在浯溪住了三年。對元結來說,這是寂寥的三年,也是心身解脫的三年,是非比尋常的三年。這三年里,他有足夠多的時間來打量浯溪,欣賞浯溪,經營浯溪。他在江邊的石臺上造了一座亭子,以便倚欄望江看風景。
面對著滿目青山與秀水,他一定是感到了身與心的愉悅與釋放:我的!我的!我的!這是我的山!我的水!我的溪流!我的石臺!我的亭廊!我的風景!我的家園!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在社會因權力的不容忍而整體迷失自我的時代,那還能發現自我、找回自我的人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那敢于公然宣布“自我”的人是有膽量和識見的。因為,專制時代,弘揚自我即意味著人生的無限風險,甚至有可能要掉腦袋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憑一句空口之言,就可以把你發配得遠遠的,或者直接要了你的命。只有大自然的風景是無主的。大自然的風景只屬于那些能欣賞風景的人。
至少在此時此刻,沒有人會來打擾元結。他面對著一派如詩如畫的山水,不禁脫口而出:這是我的山,我的水,我的風景。我要為你寫下一篇又一篇的銘記,把這些美好的事物以配得上它們的文字存留下來,激活與傳揚這“養在深閨無人識”的好風景。我要讓朋友們都知道我找到了一處心靈的憩園。我要把臨江的巨崖磨平。來,我的朋友,偉大的書法家,請到浯溪來做客,請把你的墨寶留下——煩請你把我的《大唐中興頌》書寫一遍,借助石頭的堅硬,我要為我們這個時代過往的一段歷史留下一些文字的痕跡,我要請最好的石匠把它刻在石頭上,讓它成為一個鏡鑒。還有你們,后來的遷客騷人、文人墨客,也把你的詩文和書藝留下,鑿刻在這天然成趣的石崖上。一塊又一塊,讓它們連成歲月的長廊、歷史的長廊、藝術的長廊,連成璀璨的碑刻瑰寶。一個一個的名字聽從了召喚,一串一串的文字聽從了召喚,一方一方的碑刻留了下來,一件一件的書法瑰寶留了下來,傳了下來。
那時節,顏真卿也在走背運,剛被免除撫州刺史的職務。便接受好朋友元結的盛情邀請,來到浯溪小住散心。浯溪風光旖旎,正可以“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他們一個詩人,一個書家,徜徉在優美的自然山水之中,創作激情自不待說。顏真卿以他爐火純青的楷體大字,把元結十年前平定“安史之亂”時寫下的《大唐中興頌》書寫一了遍,元結請名匠刻之于湘江邊的崖石上,這就有了浯溪摩崖石刻的第一塊開山之作,也是核心靈魂佳構。
還有好朋友、書法家季康以及瞿令問也來到了浯溪,他們一個以熟練的玉箸篆書寫了元結的《浯溪銘》刻石,一個以拿手的懸針篆書寫了元結的《峿臺銘》刻石,為浯溪碑林的開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然后,書法家宰相袁茲也來了,他以奇特的鐘鼎篆書寫了元結的《吾庼銘》刻在石壁上,留下自己彌足珍貴的一方篆文石刻。歷史翻過一頁之后,宋代大詩人黃庭堅來了,大書法家米芾來了,書法界有“晚清第一人”之稱的何紹基也來了,他們都留下了一流的書法石刻和可圈可點的詩文題詞。
浯溪,因此而流淌一地的文化。一地的,藝術!
多少個月白風清的夜晚,元結站在浯溪的高臺上,站在孤獨聳立的涼亭里,看著面前的湘江水浩浩而去,“逝者如斯夫”,心里感慨萬千。“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巔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他確確實實是感受到了內心的落寞。
大唐盛世,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啊!歌舞升平,八方來朝。那個與我同年來到這個世上的女人是何等的甜蜜幸福。一個舞蹈家,宮廷藝術家,她把一個爾虞我詐的朝廷變成了繽紛萬千的歌臺舞榭,把一個鐵石心腸的政治家變成了溫情脈脈的戀人,把現實變成了夢幻。
但政治畢竟是政治,太多的時候它都是冷酷無情的。
政治偶爾會容忍藝術的浸染與放縱。但這種浸染與放縱是要付出代價的。青春的代價,生命的代價,血的代價。總會有那么一些心懷叵測的人,那些狼子野心的眼睛從來就是緊緊地盯著權力那根誘人的柄杖。隨時都會有可能興風作浪。慘烈啊!“漁陽鼓鼙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那“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絕代美人,在“六軍不發無奈何”的逼迫下,只能“宛轉娥眉馬前死”,最終落得個“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可憐可悲的下場。真個是“天長地久會有時,此恨綿綿無絕期”。若干年后,一個樂天不憂的詩人將為之寫下傳遍萬世的《長恨歌》,讓多少人唏噓感嘆!藝術家一旦攪和進權力的旋渦,其結局往往會出人意料地悲慘。
我還是要提醒那些當權者,千萬不要忘記,政治必須要以民生為根本,容不得半點疏懶。《大唐中興頌》,又何此是“中興”之“頌”呢!“刊此頌焉,可千萬年!”聰明的人們難道從中讀不出來一個王朝盛極而衰的沉痛教訓嗎?“胡羯自干紀,唐綱竟不維。可憐德業淺,有愧此碑詞。”我異代的知音一定會來到這塊石碑前朝拜的,我有這個信心,我等著那個叫米芾的人的到來。我把這塊鏡石放在這里,不僅僅是照人影,更重要的是要照人心、照人世。我要讓你們明白“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的淺顯道理。
“水洗浯溪鏡石臺,漁舟花草映江開。不如元結中興頌,照見千秋事去來。”解縉是個大才子,他那雙慧眼穿越歲月的蒼茫,讀懂了我的心思。還有袁枚,他煞有介事兩次面對鏡石去照肝膽,以表白自己一生的忠貞:“五十年前臨汝郎,白頭再照心悲傷。恰有一言向鏡訴,照儂肝膽還如故。”其志可嘉,其情可愛。
還有一連串的名字讓我寬慰。劉長卿、皇甫湜、李陽冰、李諒、鄭谷;張孝祥、張栻、秦觀、李清照、范成大、楊萬里、張耒、狄青;郝經、楊維楨;沈周、董其昌;王士禎、陳大受、錢灃、吳大澂……你們肯留下自己的墨寶,我深感榮幸。還有那“越南萬里朝中國,暫借吾亭一夜眠”的清代越南使者,在這里留下五方詩詞碑刻,見證中越之間的友好交往。“地毓浯溪秀,山開鏡石名。莫叫塵蘚污,留照往來情”,鄭懷德的感嘆也正是我的擔憂。
一切都將成為過去。一切都將淹沒于歲月的塵埃。我,終將離去。
離開浯溪的時候,是公元七七二年初。元結守制三年滿,扶母柩歸葬河南老家。這一次他可能是感悟到了某種宿命的無可奈何,感悟到了宦海漂浮如萍,終將葉落歸根。他是舉家北遷,回歸故里。安葬了母親,再到長安。四月份即病重不治,溘然長逝,終年五十四歲。
一個好官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一個文章家的生命卻在無限地延伸。
國家不幸詩家幸,這話并非什么稀世真理。詩家歷來只盼國家幸,只盼百姓幸,哪怕自己寫不出一首詩來也罷。元結不是一流的大詩家。《全唐詩》收錄了元結不少的詩歌,沒有婦孺皆知的名篇佳句,如李白之“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沒有。但元結是一個創造性的詩人、一個開拓性的作家。
他的詩關注當下、關注日常、關注現實,不作無病呻吟語。
他否定聲律詞采,追求質樸、直白。主張“文以載道”,反對言之無物。
元結的文學觀或許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但無疑是進步于他自己的時代的。與其說是依附于政治或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依附于時代,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你可以無視政治與意識形態,但你不可以無視于自己的時代,任何人都不可以。元結的詩不是反諷,是直接的規諷,是大膽的揭露,是鞭撻。他的文也溢蕩著一股超拔的意氣,另類于當時流行的綿軟文字。他走在了自己時代的前面。他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先驅。
特別是對于永州、對于瀟湘文化,元結是理所當然的命名者、破荒煙的人。元結之后,誰人不識浯溪,誰人不識右溪,誰人不識朝陽巖?甚至連久遠逝去的唐朝,也因為浯溪滿地的摩崖石刻,而變得伸手可以觸摸。
今天我們來聆聽浯溪,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聆聽歷史、聆聽文化、聆聽藝術,聆聽唐代那樣一個偉大的時代和它的變遷,聆聽元結那樣一種融入時代和歷史的人生命運與個性創造,聆聽唐宋以降輝煌燦爛的書法藝術長廊。
我在這里反復流連,觀摩、辨認、審視、拜讀、欣賞,甚至是諦聽、傾聽、傾訴,心底里滿溢著一種無比的敬畏與崇敬,我把白日的喧囂全部擯棄在心靈之外。我選擇這個有月光的夜晚,一個人走到浯溪澗畔,走到湘江邊上,在刻滿前人文詞的崖壁下坐下來,靜靜地聆聽。屏氣凝神。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生怕驚擾了滿山滿坡的安寧,生怕驚擾了那些樹枝上和地面上翩躚飛舞的月光的翅膀。
我只是用眼睛去探視,用耳朵去聆聽,用心靈去摩挲。那些有生命的石頭、有靈魂的石頭、那些飛揚的文字,就枕在湘江濤聲里,枕在船櫓的槁聲里,枕在滿地流淌的月光里,充滿了靈性,仿佛不動而動,隨風而起,隨風而舞。
夜,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響。只有月光在靜靜地流淌,滿山滿坡、滿江滿河。
浯溪,一睡千年,一夢千年。或者,這一千多年來,都一直是在夢中醒著。
我終于是愛上浯溪了,沉浸其中,不再自拔。
我的心,隨那月光下的溪流潺潺不息。
責任編輯:胡汀潞